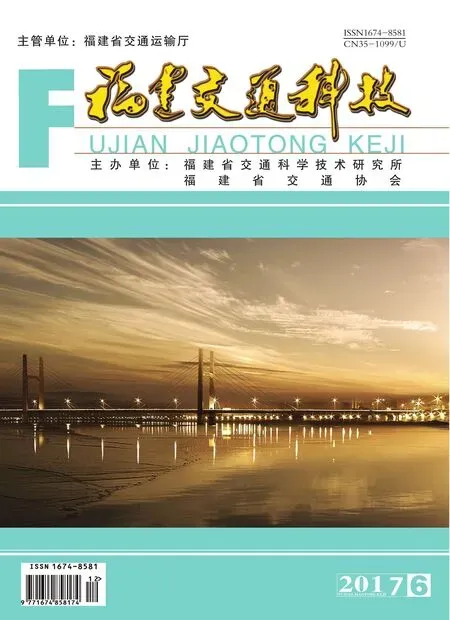高強混凝土箱梁零號塊澆筑溫度場及溫度應力的實測與仿真分析
■熊慧婷
(蘇交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210019)
高強混凝土箱梁零號塊澆筑溫度場及溫度應力的實測與仿真分析
■熊慧婷
(蘇交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210019)
對某預應力混凝土連續剛構橋箱梁零號塊的澆筑溫度場及早期應力進行實測和有限元模擬,總結了高強混凝土箱梁在水化放熱過程中存在的共性特征,討論了溫度場、溫度應力與溫度裂縫間的內在關聯。分析結果表明,箱梁零號塊各部件因澆筑體積、散熱條件的差異,在水化熱問題上呈現出一定的獨立性。其中,澆筑體積較大的部件表面具有潛在的開裂風險,是溫度控制的重點。
箱梁 水化熱 溫度場 溫度應力 有限元法 早期裂縫
1 引言
工程中混凝土的水化熱問題,以往主要出現在水工結構的大壩、大型工業設備的基礎及橋梁工程中的錨碇和承臺中。這些結構部件就地澆筑的混凝土體積巨大,內部熱量不易散失,因此必須考慮由水化放熱引起的溫度變化,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控制溫度裂縫。國內外學者對混凝土水化熱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此[1,2]。
近年來,隨著預應力技術的發展,采用懸臂現澆施工方法修建的連續剛構橋跨徑越來越大,橋墩附近箱梁的斷面尺寸也越來越大。由于多采用高強混凝土,其單位體積內水泥用量大,因此水化熱問題成為箱梁施工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正逐漸引起橋梁工程界的關注[3,4]。已有部分文獻對箱梁澆筑溫度場進行了研究[5,6],但對于由此產生的溫度應力,特別是溫度應力與早期裂縫間的相關性則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以衡昆高速重點控制工程某三跨預應力混凝土箱梁連續剛構橋為背景,對箱梁節段中體積最大的0號塊澆筑溫度場及早期應力場進行實測和有限元仿真,進而總結了高強混凝土箱梁在水化放熱過程中存在的共性特點,并著重討論了溫度場、溫度應力與早期裂縫間的內在關聯,旨在為同類橋型的施工控制和防裂抗裂提供合理的建議和參考。
2 高強混凝土箱梁零號塊溫度場測試
2.1 工程背景

圖 1 主橋橋型示意圖(單位:m)
衡昆高速重點控制工程某三跨預應力混凝土連續剛構橋跨徑為(65+110+65)m,橋型圖如圖 1所示。0號塊箱梁順橋向長19m,根部高度6.5m,底板厚70cm,箱梁高度及箱梁底板厚度按1.8次拋物線變化;箱梁腹板根部厚60cm,腹板厚度在腹板變化段按直線漸變;箱梁頂板厚度25cm;橫隔板的截面尺寸為2×6m2,與墩身相同。該橋采用逐段懸臂現澆施工,0號塊在托架上進行澆筑。0號塊施工時間為11月初,日平均氣溫在20℃左右。箱梁混凝土的設計標號雖同為C55,但1號墩0號塊和2號墩0號塊的混凝土配合比略有不同,2號墩用硅粉取代了部分水泥(見表 1)。

表1 1號墩0號塊與2號墩0號塊混凝土配合比的比較
2.2 測點布置和測試方法
筆者對兩個0號塊的澆筑溫度場均進行跟蹤測試,1號墩0號塊的測點布置如圖 2所示;2號墩的測點布置與1號墩完全相同,其編號加撇以示區分。部分測點采用普通熱敏電阻作為測溫元件。另有部分測點預埋振弦式應變計同步測試埋設點的應變和溫度,應變測量范圍為:壓縮1500με,拉伸1000με;溫度測量范圍為:–25℃~90℃,測量精度可達±0.5℃。整個測溫過程從測試混凝土的入模溫度時起,持續至箱梁溫度場最終穩定時止。前5d每隔3h測試1次,5d后視具體情況適當降低觀測頻率,測溫的同時讀取測點的應變;大氣溫度每隔2h記錄1次,持續 10d。
2.3 實測數據分析
限于篇幅,以1號墩0號塊的測試數據為例說明箱梁混凝土水化熱溫度場的共性特征:
(1)箱梁0號塊的澆筑體積并不是很大,但因使用了高強混凝土,單方水泥用量大,仍然存在水化熱問題。橫隔板中心及橫隔板與底板交接處等澆筑方量相對較大的部位隨混凝土齡期的發展,經歷了溫度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過程,具有一般大體積混凝土水化熱溫度場的典型特征,如圖3所示。

圖3 橫隔板測點溫度變化曲線

圖 2 截面測點布置示意圖(單位:cm)
(2)與錨錠、承臺等普通大體積混凝土相比,箱梁0號塊結構復雜,各部件的澆筑溫度場又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橫隔板、各部件的結合部等尺寸較大處,水化熱引起的溫升問題比較突出。橫隔板中心測點(測點19)的溫度峰值達到70.8℃,位于橫隔板、腹板、底板三者交接處的測點(測點 18)最高溫度亦超過了 60℃(見圖 3);而底板的內外溫差最大可達16℃,相對其厚度而言,這個數值還是相當之大的,如圖 4所示;頂板、腹板等部件生熱少,散熱快,水化熱問題幾乎不存在。尤其是頂板,由于厚度最薄,受大氣溫度影響較大,沒有明顯的升降溫階段,如圖 5、圖 6所示。

圖4 底板測點溫度變化曲線

圖5 腹板測點溫度變化曲線

圖6 頂板測點溫度變化曲線
對2號墩0號塊的實測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其澆筑溫度場的基本規律與1號墩0號塊一致,但各測點的溫度峰值有所下降,且達到溫度峰值的時間延遲了,如圖7、圖8所示。這是由于與水泥相比,硅粉的水化熱量小、早期放熱速度慢所致;而兩個0號塊測點溫度的下降段基本重合,正是二者散熱條件相似的體現。后續章節對實測數據的引證,如未作特別說明,均特指1號墩0號塊。

圖7 測點18與18’溫度變化曲線的對比

圖8 測點5與5’溫度變化曲線的對比
3 箱梁零號塊澆筑溫度場的有限元模擬
對箱梁零號塊澆筑溫度場進行實測的同時,我們采用ANSYS熱分析模塊對其進行有限元模擬。
3.1 計算模型

圖9 0號塊實體模型
考慮到箱梁0號塊的對稱性,只需建立1/4模型即可,結構的實體模型如圖9所示。接著選擇單元類型,Solid70是ANSYS定義的三維溫度單元,每個單元有8個節點,每個節點只有一個自由度即溫度,計算中選擇了此種單元。隨后定義材料性能參數,對于瞬態傳熱問題,需定義導熱系數、密度和比熱,這里采用了文獻[7]推薦的取值。最后在創建的幾何模型上劃分網格,如圖10所示。為了模擬混凝土的澆筑過程,在計算之初將所有單元殺死(即執行Ekill命令),并根據澆筑批次的不同,將整個結構劃分成若干區域;隨后,按澆筑順序依次激活相應區域的單元(即執行Ealive命令)。隨著澆筑面的上升,網格逐漸擴大到整個結構。

圖10 0號塊有限元模型
3.2 確定邊界條件并施加荷載
接下來,根據0號塊的實際施工狀況,模擬混凝土的放熱和對流。本文采用指數型公式描述水泥水化的放熱過程[7]:Q(τ)=Q0(1-e-mτ),其中 Q(τ)為齡期 τ時的累積水化熱,Q0為τ趨于∞時的最終水化熱,m是隨水泥品種、比表面和澆筑溫度不同而不同的常數。為準確確定Q0和m的取值,我們提取0號塊水泥試樣,委托南京工業大學土建實驗室進行了絕熱溫升實驗,參考實驗數據取Q0=346kJ/kg、m=1.09。
在箱梁邊界上存在著混凝土與空氣的熱對流,屬第三類邊界條件。ANSYS通過定義表面熱交換系數,將對流邊界條件以面荷載的形式施加于實體的外表面。表面熱交換系數與風速及混凝土表面狀況關系密切,其取值具有很大的離散性,目前尚無公認的研究成果,但多數學者認為與結構周圍的風速呈線性關系[7-10]。本文首先將實測風速代入朱伯芳[7]建議的以下經驗公式中:β=21.8+13.53v(β 為表面熱交換系數,v 為風速),對表面熱交換系數進行粗估。隨后視計算溫度場與實測溫度場的吻合程度,逐步調整其取值,直至二者吻合良好,即認為此時β的取值接近真實情況。箱梁0號塊不同部件邊界的實測風速及熱交換系數的最終取值見表 2。進行線性擬合后,得表面熱交換系數與風速的關系為:

將式(1)與目前較為常用的幾種熱交換系數表達式進行比較,如圖 11所示。由圖可知,本文擬合的公式在初值選取上與朱伯芳[7]較為接近,而隨風力的增長速率(即曲線斜率)則與 Branco[8]、Saetta[9]、魏光坪[10]等學者推薦的取值相近。

表2 不同部件邊界實測風速及熱交換系數取值

圖11 幾種常用熱交換系數表達式的比較
3.3 溫度場計算結果分析
設0.25天為一個時間步,共計40個時間步,整個時間歷程為10天,考察1號墩0號塊的計算結果。圖 12、圖 13和圖 14分別給出了三個最具代表性的溫度指征——橫隔板中心測點溫度(測點19)、橫隔板與底板交接處測點溫度(測點18)、底板內表溫差隨時間變化的曲線。

圖12 測點19溫度計算值與實測值的比較
表3對計算值與實測值作了更為全面的比較。通過該表可以看出,各測點計算值與實測值的最大誤差僅為1.71%,說明本文建立的有限元分析模型能很好的仿真實際溫度場,為溫度控制提供可靠依據。

圖13 測點18溫度計算值與實測值的比較

圖14 測點4與測點5的溫差變化曲線

表3 箱梁溫度場計算值與實測值的比較(℃)
為進一步考察箱梁0號塊澆筑溫度場的分布規律,我們給出了澆筑后1d、2.5d、5d、10d的溫度云圖,如圖15~18所示。由圖可知,第1天時,底板、腹板等部件的中心溫度達到峰值;而橫隔板內部最高溫度出現的時間相對滯后,在第2.5天達到最大值71℃;澆筑后的第5天,除橫隔板外,箱梁其余部件的溫度場已接近穩定,降溫過程基本結束;到第10天時,橫隔板內部溫度仍然高達40℃。縱觀整個升降溫過程,各部件溫度場的變化呈現出一定的獨立性:早期升溫階段,橫隔板及各部件交接處等澆筑體積較大的地方溫度上升最快;降溫階段,又是這部分的水化熱最不易散失。可見,對于幾何形狀較為復雜的箱梁結構,可按澆筑體積及散熱條件的不同將其拆分為若干部件,分別加以分析和考量,其中橫隔板等澆筑體積較大的地方是溫度控制的重點。

圖 15 澆筑后1d的溫度場(℃)

圖 16 澆筑后2.5d的溫度場(℃)

圖17 澆筑后5d的溫度場(℃)

圖18 澆筑后10d的溫度場(℃)
4 早期應力場的有限元分析
本節基于上一節的熱分析結果,對早期應力場進行分析。
4.1 彈模的處理及增量法的應用
應力分析直接利用溫度分析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只需將溫度單元Solid70轉換為對應的結構單元Solid45即可。早期混凝土的彈性模量是隨時間變化的,為考慮這一重要因素,前10d的彈性模量按指數型公式進行計算[7]:

其中,E0為C55混凝土的彈模標準值,取 3.55×1010Pa;常數m以施工單位提供的混凝土 7d、14d、21d、28d齡期的彈模實測值為依據,取0.42。10d之后即認為彈模不再變化,取其終值E0。
本文采用增量法計算混凝土的溫度應力,具體步驟如下:首先根據熱分析結果提取相鄰兩天的溫差△Ti=Ti-Ti-1,將溫差和重力場作為體載施加于有限元模型上;然后根據第i天的彈性模量值求得第i天的應力增量△σi,并與第i-1天的溫度應力疊加。共進行11次計算,前10次以1d為一個時間間隔;最后一次計算的初始時刻為第10天末,結束時刻為結構溫度場趨于穩定的時刻,此時認為箱梁0號塊處于均勻的溫度場中,與外界溫度一致。
4.2 應力場計算結果分析
本節首先給出箱梁0號塊1-1截面各代表性時刻的順橋向應力云圖,如圖 19~26所示。

圖19 澆筑后1d的應力云圖(Pa)

圖 20 澆筑后2d的應力云圖(Pa)

圖 21 澆筑后3d的應力云圖(Pa)

圖 22 澆筑后4d的應力云圖(Pa)

圖 23 澆筑后5d的應力云圖(Pa)

圖24 澆筑后7d的應力云圖(Pa)

圖25 澆筑后8d的應力云圖(Pa)

圖26 最終的應力云圖(Pa)
與此同時,我們對部分測點的順橋向應變進行了測試,直接讀取的為振弦式應變計在工作狀態下的頻率值,經下式換算后可得混凝土應變:

式(3)中,ε 為混凝土應變量(με);K 為應變計的靈敏度系數 (με/Hz2);fi和f0分別代表實測頻率和初始頻率。表4給出了底板內部測點5、18及翼緣表面測點16的實測數據。
由表4可以看出,實測應力的變化趨勢與計算結果基本一致,但計算結果偏大。這是由于計算中未考慮收縮徐變引起的應力松弛。另需注意的是,混凝土開裂與否及沿何方向開裂取決于主拉應力的大小和方向。但由于同一位置不同時刻的主應力方向不同,不能直接疊加主應力增量,而是應當先疊加應力分量,再合成得該位置的主應力。橫隔板、頂板、腹板和底板中心及表面位置的第一主應力計算結果如圖27~30所示。

圖27 橫隔板中心及側表面節點主應力

圖28 頂腹交接處及翼緣表面節點主應力

表4 1-1截面部分測點順橋向應力實測值

圖29 腹板中心及表面節點主應力

圖30 底板中心及表面節點主應力
由上圖可知,箱梁0號塊各部件的內部均為先受壓后受拉,表面則相反。拉壓轉換發生的時間、拉應力峰值出現的時間、拉應力峰值的大小與各部件混凝土的澆筑體積和散熱條件密切相關。澆筑初期,橫隔板側表面的拉應力最大,3d后達到峰值2.94MPa,見圖 27。這是由于箱梁各部件中,橫隔板最厚、內外溫差最大的緣故。圖 20、圖 21及圖 28顯示,在升溫階段,翼緣表面的拉應力同樣不容忽視,澆筑后第2天可達1.5MPa。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部壓應力逐漸變小,厚度較薄的底板和腹板率先完成內部受壓區的拉壓轉換。頂板與腹板的結合部澆筑體積較大,內部出現拉應力的時間也相對滯后,第5天內部才開始出現拉應力;到第7天時,此處取代橫隔板表面成為整個箱梁結構中拉應力最大的部位,后期殘余拉應力超過2MPa。橫隔板體積最大,內部混凝土發生拉壓轉換的時間也最遲,第10天時仍處于受壓狀態(見圖 27),但最終的殘余拉應力僅為1.68MPa。
結合上一節對溫度場的分析可知,溫度場的變化直接決定了溫度應力的分布。事實上,箱梁表面拉應力達到峰值的時刻正是內部混凝土升溫過程結束的時刻;而箱梁內部拉應力增量最大的天數則與內外溫差達到最大值的天數相吻合,因為此時內部降溫速率與外部降溫速率的差異最大,至于拉應力增量的大小則取決于溫差的大小。
需要注意的是,計算普通混凝土的溫度應力時,通常不計入升溫階段混凝土內部累積的壓應力,而將其作為混凝土抗拉的安全儲備,這是因為普通混凝土早期彈模很小,應變幾乎不會產生應力。但對于高強混凝土而言,尤其是含有早強成分的高強混凝土,早期彈模增長迅速,升溫過程在內部引起的壓應力較大,如不計入則會使計算結果過于保守。以橫隔板中心節點為例(見圖27),累加早期壓應力時算得最終殘余拉應力為1.68MPa,不會引起開裂;不累加則為3.33MPa,足以引起開裂。可見,不考慮混凝土早期累積的壓應力將有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
4.3 溫度裂縫分析
由施工單位提供的實驗數據表明,高強混凝土的抗壓強度早期發展得非常迅速。摻硅粉混凝土在密封養護的條件下,1d的抗壓強度達28d強度的30%以上,3d則達到67%;即使是不摻硅粉的高強混凝土,ld的抗壓強度也可達到28d強度的22%,3d為51%。抗壓強度隨齡期的發展規律可由下式描述[7]其中,fcu(τ)為不同齡期的抗壓強度為28d的抗壓強度;m是與水泥品種相關的系數。對于不摻硅粉的高強混凝土,當m取0.234時,與施工單位提供的實驗結果吻合較好。以混凝土的抗壓強度為基準,通過關系式可換算出對應齡期的劈裂抗拉強度[11],其中α、γ為回歸參數。本文取α=0.232、γ=0.66計算澆筑后15d的混凝土抗拉強度,并與ANSYS計算出的最大拉應力進行對比,如圖31所示。

圖31 0號塊不同齡期最大拉應力與混凝土抗拉強度的對比
由4.2節的分析可知,隨著混凝土齡期的增長及伴隨而來的溫度應力重分布,箱梁0號塊最大拉應力出現的位置并非一成不變。澆筑后的最初7d,最大拉應力出現在橫隔板的側表面;7d之后,頂板與腹板的結合部拉應力最大。這是圖31中主拉應力曲線出現起伏的原因。根據圖 31中曲線的走勢,澆筑后的1~5d,表面開裂問題較為突出。拆模后在橫隔板側面發現裂縫若干,長度5~15cm不等,寬度不足0.1mm,開裂方向與考慮溫度效應后求得的主拉應力方向基本一致,可以判定為混凝土水化熱及收縮徐變所致。隨著后期表面開始受壓,這些裂縫逐步閉合,對結構危害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結構的耐久性,故須重視早期的蓄水養護,不宜過早拆模,盡可能降低裂縫出現的幾率。5d后,混凝土承受的拉應力始終低于對應時刻的抗拉強度,且有一定的安全裕度,可以確定不會出現危及結構強度的深層裂縫。綜上所述,即使高強混凝土的早期強度很高,但由于其在硬化期間放熱速度很快,仍然有出現溫度裂縫的可能。
5 結論
(1)與錨錠、承臺等普通大體積混凝土相比,箱梁0號塊構造復雜,各部件因澆筑體積、散熱條件的差異,在水化熱問題上表現各不相同。將箱梁0號塊拆分為不同的部件分別加以考量,有助于認清其澆筑溫度場及應力場的分布規律。
(2)大型通用有限元程序ANSYS能夠準確求解混凝土的澆筑溫度場和溫度應力,但考慮澆筑過程的溫控仿真與一般的結構靜動力分析相比,具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因此仿真參數的選取至關重要。筆者以統計資料和經驗公式為依據,結合實際工程的測量數據確定溫控參數,取得了良好的仿真效果。
(3)高強混凝土早期強度較高,但由于其在硬化期間放熱速度很快,仍然有出現溫度裂縫的可能。尤其是澆筑后的1~5d,澆筑方量較大的部件(如橫隔板)其表面具有潛在的開裂風險,故須重視早期的蓄水養護,不宜過早拆模。而內部混凝土由于在升溫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壓應力,可以抵消降溫過程中產生的部分拉應力,故一般不會出現危及結構強度的深層裂縫。
[1]Kawaguchi T,Nakane S.Investigations on determining thermal stress in massive concrete structures[J].ACI Materials Journal,1996,93(1):96-101.
[2]王鐵夢.工程結構裂縫控制的綜合方法[J].施工技術,2000,(05):5-9.
[3]汪建群,方志,劉杰,等.大跨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橋施工期防裂研究[J].鐵道工程學報,2016,(11):81-86.
[4]袁助.節段箱梁預制過程溫度場監測與分析[J].公路交通科技,2017,(04):215-217.
[5]陳志堅,顧斌.大型混凝土箱梁水化熱溫度場的數值模擬[J].公路交通科技,2012,(03):64-69.
[6]張國云,郭義全,張益多.大型預制混凝土箱梁水化熱溫度場數值分析[J].混凝土,2015,(09):146-150.
[7]朱伯芳.大體積混凝土溫度應力與溫度控制[M].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1999.
[8]Branco F A,Mendes P A.Thermal actions for concrete bridge design[J].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New York,N.Y.,1993,119(8):2231-2313.
[9]Saetta A,Scotta R,Vitaliani R.Stress analysis of concrete structures subjected to variable thermal loads[J].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New York,N.Y.,1995,121(3):446-457.
[10]魏光坪.單室預應力混凝土箱梁溫度場及溫度應力研究[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1989,(04):90-97.
[11]GB 50010-2010,混凝土結構設計規范[S].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