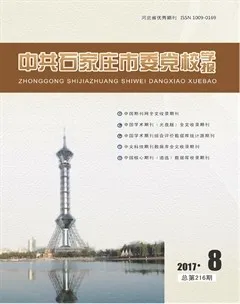產生、轉型與發展:中國政黨的歷史進程
[摘要]當今世界政黨政治成為各國政治現代化的主流,作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產生于近代西方國家,被認為是國家——社會二元分離的產物。在中國的政治秩序的變革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主導力量,革命成功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根本性轉變問題。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發展,民主建設、黨與國家的關系、黨與社會的關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政黨;產生;轉型;發展
[中圖分類號] D2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0169(2017)08-0019-05
一、政黨的產生:國家——社會二元分離的產物
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誕生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最早的政黨萌芽出現在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英國議會在王位繼承問題上發展爭執,形成了矛盾尖銳的兩派:以限制王權、擁護議會制度為宗旨的輝格黨;以擁護王權、贊成王位繼承為宗旨的托利黨。二者針鋒相對,構成了現代政黨最早的雛形。
中國“政黨”的概念是近代西方思潮傳入后才出現的,而“黨”在中國古代已經存在。《周禮·地官》提到:“五族為黨”,意思是說五百家都是親族姻戚,互相協助,體現了親疏遠近的關系。“黨”經常與“朋”連用,“朋黨”就是黨同伐異的一個政治小團體,這是皇權統治非常厭惡和排斥的。由此看來,朋黨是和宗派有著大抵相同的意思。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政黨與政黨體制》一書中梳理了博林布魯克、休謨、柏克等人對宗派(faction)和政黨(party)的區別,可以說“宗派”和“政黨”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因為政黨(party)一詞本身就來源于部分(part),直到后來“宗派”和“政黨”才在定義上被嚴格加以區分。
從中西方歷史發展來看,宗派、朋黨都有著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的某些影子,但又不同于政黨,甚至有著根本的區別。那么二者到底應該如何區分?從抽象意義的角度探求政黨的產生是一個很好的分水嶺:政黨的產生也就區分了宗派或者朋黨與政黨的概念。按照林尚立教授的觀點,政黨的產生有兩種條件。第一,國家的權力體系向社會的開放;第二,國家—社會的二元分離。在林尚立教授看來,第一種觀點只能作為政黨產生的充分條件。而政黨產生的充要條件則是國家—社會的二元分離。因為,在古希臘雅典城邦的統治中,民主思想萌生,雅典公民的政治參與已經表明國家權力體系向社會開放,但古希臘雅典并未出現政黨。而在中西方政治發展歷程中,無論是英國的光榮革命還是中國的辛亥革命都能夠充分說明政黨是國家—社會二元分離的產物。在英國光榮革命以前,無論是輝格黨還是托利黨的活動都僅限于議會內部的辯論、協商,無行動綱領和組織紀律,因此它們還僅限于政治團體或者宗派。光榮革命爆發后,代表新貴族和資產階級利益的輝格黨成為執政黨,要求限制王權、組建內閣,真正意義的政黨才得以產生,開啟了政黨政治的歷史篇章。以光榮革命為標志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表明,英國已不再是皇室的天下,腐朽的專制統治已經不能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社會新興力量逐步脫胎于國家權力體系,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統治階級。不同于英國的源生型,中國的政黨政治屬于次生型。清朝末年,隨著清政府內憂外患加重、民族危機加深、民族資產階級興起、西方思潮的引入,戊戌變法期間出現了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等政治團體,但在作為當局的清政府來看,這些所謂的政治團體是否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值得懷疑。中國同盟會于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誕生,它具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政治目標,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的。在推翻清政府、結束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過程中,同盟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并成立了作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中華民國。我們看到無論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還是我國近代發展歷史,一個共性就是社會團體或者政治集團不斷發展壯大,王室已經不再是國家的代言人,國家的大門開始向社會開放,社會的力量逐步脫胎于國家,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周淑真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基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政治發展是各國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目標是政治民主化。政治發展中最基本的是社會主體的成長與成熟。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主體不再像前資本主義那樣,只是社會中的某一階層或某一集團構成的社會精英,而是享有同等政治權利的社會公民所構成的社會大眾。對于現代政治發展來講,社會主體的成長與成熟,是社會大眾的成長與成熟”[1]。在這樣的發展背景和趨勢下,國家—社會實現了二元的分離,政黨及政黨政治成為了歷史的主旋律。
二、政黨的轉型:從革命黨到執政黨
革命是一個動態過程,即對舊的統治秩序、價值觀念、社會階級進行變革、改造、重塑的過程。從歷史發展、時代變革的角度來看,革命往往具有歷史進步性,時代發展性的特征,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等等,這些歷史上的革命大都伴隨著流血犧牲,顛覆了舊的統治,重塑了社會秩序。縱觀世界歷史發展,每一次革命不外乎由某一政黨或組織主導、推動、斗爭直至勝利或者失敗。對于一個革命黨來說,當舊的秩序被推翻,新的秩序構建后,就面臨轉型的問題。這樣的轉型即是外部環境變化的要求也是內部自身發展的需要。
民國初年,同盟會進行了改組,實現了由革命黨向政黨的轉變,之后更是集合五大政黨為國民黨,目的是為了爭取國會席位、監督政府。國民黨的主要籌建人宋教仁曾說:“國民黨與同盟會所持態度與手段雖有不合,然犧牲的進取精神則始終一貫,不能更易也。從前對于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斗;現在對于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斗。”[2]孫中山反復強調,同盟會是“革命黨”,而國民黨是“政黨”,“革命黨”與“政黨”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黨。革命黨“所抱持之惟一宗旨,則為三民主義”,“終能打破反對者之壓制而建設中華民國”。而“政黨”的要義在于“為國家造幸福,為人民謀樂利”。他還說,政黨的具體作用在于:其一,“養成多數者政治上之智識,而使人民有對于政治上之興味”;其二“組織政黨內閣,直行其政策”;其三“監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不溢乎正規”[3]。宋教仁案的發生,標志著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破產,孫中山深感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的渙散,提出要革命必須要有一個革命黨。孫中山把軍政、訓政兩個時期和憲政時期的一定階段稱之為革命時期,這一時期孫中山吸取民國年初的政黨政治實踐失敗的教訓,對革命黨在建立和鞏固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視,同時也形成了“革命時期”以黨治國的思想:國家必須由革命黨來造成,革命黨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根本;革命黨不僅要創立國家政權,領導國家,更重要的是要鞏固國家政權[4]。這里孫中山用了“革命黨”的概念,實質上對革命黨后期變為執政黨已經做了初步的設想與安排。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再到二次革命失敗后的革命時期主張以黨治國的思想,基本已經勾勒出了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基本邏輯:由變革、顛覆到管理、統治的轉型過程。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今走過96年的風雨歷程,經歷了土地革命時期、國共合作時期、建國初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等歷史階段,從一個成立之初僅有50多名黨員,到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再到今天擁有8800多萬黨員,掌舵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黨,基本清晰地展現了從革命性質的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變。這樣的角色轉變或者轉型是黨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做出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黨為加強自身建設發展所尋求的有效途徑。從政黨的類別來看,分為內生型(原生型)政黨和外生型(次生型)政黨,西方國家多為前者,即議會民主政黨,而后者則多為推翻舊的統治,建立新政權,特征多為暴力革命及武裝斗爭。這樣的政黨在執掌國家政權后,必然面臨轉型發展的重要歷史課題。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合法的執政黨后,中國共產黨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嘗試,總體呈現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不可否認的是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時期,我們黨的轉型進度較為緩慢。革命、斗爭、動員的思維模式、價值理念大量地體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領域,革命時期的慣性思維依然影響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訓,證明了革命黨必須不斷轉型,適應并遵循客觀規律。黨要實現轉型發展就不能回避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個是合法性問題,另外一個是代表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三個代表”理論、“兩個先鋒隊”表述的提出,做了更為科學合理、更富時代特征的回答。
黨的執政合法性問題。任何一個政權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于本國人民對政權的認同和支持。按照社會契約理論和代議民主理論,這樣的認同和支持即體現了權力的讓渡和委托。黨在反對外來侵略和國內反動勢力壓迫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成為了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然而人民的選擇常常具有特定性,即在不同時期體現出不同的特征,革命戰爭年代人民的選擇往往反映出要求翻身做主人的愿望,和平建設年代人民的選擇往往反映出要求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階級斗爭,實行改革開放,把黨和國家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領域,經濟水平保持了30年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日益富足,黨的執政合法性得到了鞏固與提升。
黨的執政代表性問題。縱觀世界歷史的發展,僅僅靠經濟發展來維系執政合法性,仍略顯單薄。一些威權主義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往往與經濟發展掛鉤,通過經濟增長率來換取民眾的認同和支持,這樣導致的結果即是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就會導致執政合法性危機。歷史上的法國大革命、2000年臺灣大選國民黨的失敗,這些歷史事件都發生在經濟高度增長時期,但高速的經濟增長并沒有帶來人民或民眾對政權的擁護與支持,反而帶來的是政權的喪失和崩潰。面對外部環境發生的變化和政治現代化,黨必須在代表性問題上作適時調整。薩托利在《政黨與政黨體制》一書中給出了作為部分的政黨和作為整體的政黨的分析框架,并嚴格區分了政黨與宗派的差別:作為部分的政黨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是多元的,表達著多元利益,是服務多元整體的表達工具。“政黨是代表整體的部分并服務于整體,而宗派僅是代表自身的部分”[5]。亨廷頓認為,政治現代化通常表現為廣泛的社會動員與政治參與,更多的社會成員和利益群體進入政治體系是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轉變的顯著標識。“政黨擴大了傳統政府所容納的政治參與的范圍,從而使這些制度適應了現代政體的要求”[6]90。“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黨的十六大對《黨章》作了修改“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都在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由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代表部分的政黨向整體性、代表普遍利益的執政黨轉型歷程中愈加清晰地認識到,獲取政權只是服務于整體的普遍利益這一目的的手段,重要的是獲取政權后如何代表多元、表達多元。當今國內外環境正發生深刻變化,過去我們強調“階級”這一概念,現在“階級”這一概念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階層”,這也印證了黨在轉型過程中在合法性方面如何由以經濟為基礎向更高層面的民主為保障來轉變;在代表性方面如何由以單一階級為根本向多元階層為導向來轉變。
三、政黨的發展:多元環境中的未來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始終在探索一條科學合理的、符合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治國理政之路。雖然黨在發展歷程中經歷過“左”或右的錯誤,但在復雜多變的執政環境中,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縱觀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開啟了改革進程中的新局面,特別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說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總的航向標。“國家治理”從概念上體現出了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即改變了過去管理或統治中權力的單向、強制運行。而“現代化”在經濟上體現出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在資源配置中從起基礎性作用轉變為起決定性作用;在政治上體現出多元社會階層的出現,政治參與、政治互動的多樣性。可以說,“現代化”要求必須進行“國家治理”,而“國家治理”則體現出“現代化”,二者高度統一、相互協調。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提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的信心和決心,同時也成為了今后一個時期黨建工作的總依據、總方略。中國共產黨的未來發展要在全面從嚴治黨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頂層設計下加以審視,其中發展民主、黨與國家、黨與社會三個問題要重點加以審視。
發展民主問題。可以說民主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的動力源泉,民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價值理念。黨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一多元環境背景下,要通過民主建設有效擴大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進一步筑牢執政根基。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發展民主就要實行多黨制或者兩黨制。事實上,政黨制度只是一種制度安排,并不能代替民主,民主的精髓在于人民能否有效選擇自己的政府,政府能否充分反映民意。古希臘雅典,并沒有多黨制或者兩黨制,卻有了最早的民主雛形。因此發展民主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現有符合中國國情實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大前提下,探討中國民主的發展。當前,以黨內民主示范、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作為發展民主的主要路徑。示范、帶動就說明了黨內民主要發展,人民民主也要發展,二者應該是相互影響、協同推進的關系。這就要在充分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以制度來保障黨員的權力和利益,進而平等地參與黨內政治生活這一基礎之上,同步帶動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制度載體的人民民主發展,特別要注重基層自治,加強基層民主建設。
黨與國家的問題。黨與國家的關系實質上就是黨與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之間的關系。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非常明確: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重要作用。因此,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首要前提。亨廷頓認為,強有力的政黨及政黨制度是維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不可或缺的要素。作為發展中國家,強大的政黨更是實現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的根本保障。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實踐也表明擁有強大政黨的國家比政黨軟弱的國家更具有穩定性。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增強執政權威性,實現政治穩定,推進政治發展是其肩負的重要歷史責任。這其中,黨要處理好與國家政權的邊界關系,找準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吸取蘇聯黨國不分、以黨代國、黨在國上的經驗教訓。以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為總路徑,堅持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合理進行分工合作,特別要注重法律在黨與國家政權機構間的制約、調節作用,黨要帶頭遵守法律,依法辦事,黨與國家機構間要依照法律程序、法律規定行使各自職能,做到黨的領導和國家政權機構的有機整合、有效互動。
黨與社會的問題。一般認為政黨來源于社會的成長成熟,政黨以奪取政權為目標,逐步發展壯大,登上政治舞臺。對于革命黨而言,在革命戰爭時期,社會結構單一,其社會動員、組織成為首要目的;進入和平時期,社會新興階層不斷發展,呈現出多元利益取向,政黨的凝聚、整合變為首要目的。亨廷頓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發展的目標是政治現代化、政治穩定和政治制度化。他認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參與、政治意識應同步發展,這是保持政治穩定的關鍵。要在擴大政治參與的同時,適時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政黨和政黨制度。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大致為由沖突走向一致的過程,政治制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新興階層相繼發展的國家,各種(下轉第27頁)(上接第22頁)社會力量不斷變化,“社會越復雜,異質性越強,政治共同體的建立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功用,這種政治制度可以調節、限制、疏導各個社會群體的權力,以便使一種社會勢力的統治與許多其他社會勢力的共同體和諧共存”[6]9-10。這對我們黨處理好同社會的關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是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共同體。我們黨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如果套用亨廷頓的觀點,那么中國共產黨與其它民主黨派就是政治共同體的關系,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就是亨廷頓所謂的政治制度。這樣來看,中國共產黨就要以構建共同體政治制度為導向,疏導、調節與各民主黨派間的關系,廣泛凝聚、整合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及其它社會團體、階層的利益,達到共同體和諧共存。其次是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一個有群眾參與的政黨制度比脫離群眾、失去群眾基礎的政黨制度要強大。動員和組織政治參與是黨擴大執政基礎的關鍵,同時也是黨加強自身力量的途徑。保持干群魚水關系是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重要法寶,現代化的今天,在社會多元的大環境下,黨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廣泛吸納社會力量進行政治動員和政治參與,擴大執政基礎,永葆黨的執政根基。
參考文獻:
[1]周淑真.政黨和政黨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1-42.
[2]宋教仁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456.
[3]孫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147.
[4]孫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400.
[5](意)G·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一種分析框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53.
[6](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聯書店,1989.
責任編輯:孫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