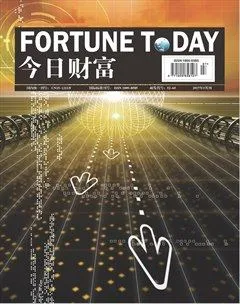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動力機(jī)制、企業(yè)家精神與文化屬性


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是在相當(dāng)長時期內(nèi)連續(xù)實施新的項目,并實現(xiàn)效益增長的過程。從定義的內(nèi)涵就強(qiáng)調(diào)時間持續(xù)性、效益增長持續(xù)性和企業(yè)發(fā)展持續(xù)性三個基本特性。中外企業(yè)實現(xiàn)持續(xù)創(chuàng)新,最初大多由特定的企業(yè)家推進(jìn)。這種持續(xù)創(chuàng)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彼得·德魯克指出:“機(jī)制比所有制更重要”。持續(xù)創(chuàng)新最終同樣需要形成一種有效的機(jī)制,既能激勵企業(yè)家不斷推動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又能培育創(chuàng)新的文化與人才,使企業(yè)家精神真正成為“基業(yè)長青”的靈魂。
在中國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下,中小企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的方向就是培育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就是將企業(yè)競爭的關(guān)鍵要素從生產(chǎn)、營銷轉(zhuǎn)向持續(xù)創(chuàng)新,使創(chuàng)新精神習(xí)慣化和制度化(Freeman,1982)。而企業(yè)創(chuàng)新動力則來自于對超額利潤的追求和企業(yè)家精神(熊彼特,1942)。從這個意思層面上講,企業(yè)家精神的根本特征表現(xiàn)為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造力。創(chuàng)造力可分解為創(chuàng)造性精神、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創(chuàng)造性能力。其中創(chuàng)造性精神是改造心智模式(Mind set),創(chuàng)造力思維是超越框架思考(Think out of box),創(chuàng)造性能力是創(chuàng)造性做事的能力。
一、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動力機(jī)制分析
(一)企業(yè)家精神的核心驅(qū)動要素
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精神作為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內(nèi)部驅(qū)動因素,對企業(yè)發(fā)展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 一是企業(yè)家的市場預(yù)見力,能夠發(fā)現(xiàn)潛在利潤。企業(yè)家精神中的創(chuàng)新意識,促使企業(yè)家不滿足固有體系的優(yōu)勢,主動根據(jù)外部信息,確定企業(yè)變革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方向。可以說企業(yè)家精神是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最主要的動力之一,是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精髓。與此同時,企業(yè)家通過管理權(quán)力、人格感召力,建立使企業(yè)全員渴望新事物、渴求變革的制度體系,從而其企業(yè)內(nèi)部建立永不滿足的企業(yè)文化。這樣的創(chuàng)新文化,包括整個企業(yè)對企業(yè)家創(chuàng)新意識、精神和價值觀的認(rèn)同。有了共識的企業(yè)文化,就是企業(yè)長期生存與發(fā)展的根本保障,可以形成強(qiáng)大的創(chuàng)新氛圍;還可以產(chǎn)生激勵效應(yīng),調(diào)節(jié)企業(yè)內(nèi)部矛盾,創(chuàng)造凝聚力和團(tuán)隊精神。
(二)長期利益目標(biāo)的現(xiàn)實驅(qū)動要素
企業(yè)利益目標(biāo)驅(qū)動,將使企業(yè)家不斷開發(fā)具有潛在需求且利潤豐厚的新產(chǎn)品,也會使企業(yè)處于不滿足競爭地位而尋求改變市場競爭狀況。這種求變活動導(dǎo)致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現(xiàn),同樣當(dāng)創(chuàng)新產(chǎn)品給企業(yè)帶來巨大的利潤和領(lǐng)先的市場競爭優(yōu)勢時,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精神再次被激發(fā)。企業(yè)家將更為積極倡導(dǎo)創(chuàng)新和冒險,則內(nèi)部的激勵機(jī)制必定是獎新罰舊、尊重創(chuàng)新活動和承認(rèn)創(chuàng)新成果,因而對創(chuàng)新成功者給予豐厚的精神和物質(zhì)獎勵。這種獎勵機(jī)制又會引導(dǎo)企業(yè)員工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進(jìn)而成為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習(xí)慣與創(chuàng)新文化的形成。
從上圖中可以看出,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動力機(jī)制的企業(yè)家精神、利益目標(biāo)和企業(yè)文化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其中企業(yè)家精神是核心驅(qū)動要素,企業(yè)在企業(yè)家精神的作用下,形成企業(yè)內(nèi)部的創(chuàng)新能力與組織學(xué)習(xí)能力、社會網(wǎng)絡(luò)能力;企業(yè)外部的政治和科技、社會經(jīng)濟(jì)相互作用并為企業(yè)內(nèi)部動力要素的形成,最終形成有利于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動力。要保持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動力,就必須把利潤增長和全體成員的切身物質(zhì)利益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形成持續(xù)創(chuàng)新的企業(yè)全體成員的物質(zhì)利益驅(qū)動。企業(yè)家持續(xù)創(chuàng)新精神與創(chuàng)新意識以及企業(yè)創(chuàng)新文化對推動企業(yè)的持續(xù)創(chuàng)新具有重要作用。企業(yè)創(chuàng)新文化最核心的要素就是共享的核心價值觀念,它使企業(yè)的全體員工保持共同的信念和團(tuán)結(jié)協(xié)作的氛圍,進(jìn)行持續(xù)創(chuàng)新。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機(jī)制的形成,主要受到來自企業(yè)內(nèi)部與企業(yè)外部兩方面因素的影響(Robert & Daniel, 2015 )。企業(yè)家精神有利于企業(yè)核心競爭優(yōu)勢的形成,并且形成企業(yè)的動態(tài)能力VRIN資源 (Valuable, Rare, Imperfectly Irritable, Non-Substitutable)(Teece,2014 )。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能力、組織學(xué)習(xí)能力、社會網(wǎng)絡(luò)能力在促進(jìn)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同時,會不斷地將中小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革新性的、具有價值的信息反饋給企業(yè),從而塑造新的企業(yè)家精神,使企業(yè)家精神與企業(yè)行為形成一個從內(nèi)化到外化,再到內(nèi)化的循環(huán)。
二、影響企業(yè)家精神的文化屬性
存在于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之中的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活動,必然會受到企業(yè)家文化屬性的制約。在中小企業(yè)內(nèi)部方面,企業(yè)家的人格特質(zhì)是企業(yè)獨(dú)特的“烙印”(imprint) (Ilouga ,Sahut & Marta, 2014 )。
(一)江浙粵民營企業(yè)家的文化根緣
浙江的制造業(yè)和經(jīng)商傳統(tǒng), 是浙商存在的基礎(chǔ)。也創(chuàng)造了義烏小商品、大唐襪業(yè)、蒼南標(biāo)牌包裝、海寧皮革服裝、永康五金、溫州塑料業(yè)和寧波小家電等專業(yè)化產(chǎn)業(yè)區(qū)。 在專業(yè)化產(chǎn)業(yè)區(qū)內(nèi),形成了“低技術(shù)部門的高技術(shù)”(high-tech in low-tech sector)的競爭優(yōu)勢;并且以宗主經(jīng)濟(jì)為紐帶的成組企業(yè)有序結(jié)成了一組“無形網(wǎng)絡(luò)”,并由經(jīng)濟(jì)性產(chǎn)業(yè)網(wǎng)絡(luò)延伸為社會性的網(wǎng)絡(luò),自然形成了浙江地區(qū)目前穩(wěn)定而可持續(xù)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基礎(chǔ)。浙江這種“塊狀經(jīng)濟(jì)模式”適應(yīng)“家族經(jīng)濟(jì)”和自立“宗主經(jīng)濟(jì)文化基因,具有與規(guī)模經(jīng)濟(jì)相沖突的內(nèi)在動力。家族經(jīng)濟(jì)由核心企業(yè)家的性質(zhì)決定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jì)增長模式,由此浙江中小企業(yè)普遍具有“低附加值、低檔次和基本粗放式”的民用消費(fèi)品生產(chǎn)與集散的特點(diǎn),其結(jié)果產(chǎn)生了一種具有較大局限性的創(chuàng)新文化。這種局限性集中地反映由私營經(jīng)濟(jì)支撐的“封閉性+ 自我保護(hù)性”。從客觀上看,浙江企業(yè)家能夠從經(jīng)商傳統(tǒng)中找到創(chuàng)新文化的調(diào)和點(diǎn),即以社會群體需求作為經(jīng)商基礎(chǔ), 并由滿足消費(fèi)者群體的核心文化, 但是這種持續(xù)創(chuàng)新具有短暫性、功用性。浙江持續(xù)創(chuàng)新是企業(yè)開始乃至后續(xù)的學(xué)校、科研機(jī)構(gòu)和政府跟進(jìn)創(chuàng)新循環(huán)模式。
與浙江企業(yè)家不同,江蘇企業(yè)家成長在長江文化、運(yùn)河文化和故都文化的歷史積淀之中, 形成了一種“對外開放的拿來主義” 與“小富即安的封閉主義”的文化格局。表現(xiàn)為蘇南園區(qū)經(jīng)濟(jì)模式創(chuàng)造以蘇州為代表的強(qiáng)縣域經(jīng)濟(jì)。這種面向全球范圍內(nèi)積極尋求科技人才,營造國家級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快速的財富積累。由FDI帶來的西方企業(yè)管理以及西方文化生活概念,融入了江蘇地方文化及其衍生相對廣泛的“拿來主義”。江浙民企營業(yè)都在傳統(tǒng)行業(yè)處于領(lǐng)先,兩省的百強(qiáng)民企多以制造業(yè)和建筑業(yè)企業(yè)為主。江浙2015年民營企業(yè)共有9家企業(yè)營業(yè)收入超過千億元,江蘇民企營業(yè)收入遠(yuǎn)高于浙江企業(yè),如蘇寧控股集團(tuán)營業(yè)收入超過3000億元,居全國第三位;恒力集團(tuán)和江蘇沙鋼集團(tuán)超過2000億元。浙江企業(yè)沒有超過2000億元大關(guān)。但是江蘇民企過分依賴政府政策主導(dǎo),博弈機(jī)制缺失,造成江蘇民企一種普遍的弱原創(chuàng)性。這也是江蘇總體經(jīng)濟(jì)增速放緩的內(nèi)在原因。
與江浙民營企業(yè)所處的行業(yè)不同,廣東企業(yè)主要分布在計算機(jī)通信、制造以及批發(fā)等行業(yè)。2016年有50家粵企跨進(jìn)中國民營企業(yè)500強(qiáng)榜單,粵企的華為、正威國際和萬科居榜單前十名的前三席。截至2014年底,廣東省民營經(jīng)濟(jì)單位達(dá)657.44萬戶,私營企業(yè)達(dá)到194.83萬戶,其中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超過9000 家,大部分是科技型中小型企業(yè)。特別是以專業(yè)鎮(zhèn)的產(chǎn)業(yè)集群,衍生出電子信息、創(chuàng)意設(shè)計、電子商務(wù)、生態(tài)旅游等新興產(chǎn)業(yè),成為廣東適應(yīng)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和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的重要載體。廣東經(jīng)濟(jì)與江浙經(jīng)濟(jì)發(fā)展路徑的差異,也與廣東企業(yè)家的文化個性有關(guān)。廣東企業(yè)家特別是潮汕商幫具有敢冒險、行事作風(fēng)兇悍和專注精細(xì)的共同特點(diǎn),造就了2015年34位潮汕籍貫企業(yè)家登陸福布斯全球華人富豪榜。這種文化特質(zhì)也有助于廣東企業(yè)進(jìn)入電子信息、生物醫(yī)藥、新能源、節(jié)能環(huán)保、新材料、機(jī)械裝備等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
(二)浙江企業(yè)家精神的文化弱性
浙江塊狀經(jīng)濟(jì)分布,單體企業(yè)規(guī)模普遍較小,缺乏大型龍頭企業(yè)。因此,大量中小企業(yè)的學(xué)習(xí)、創(chuàng)新活動依賴“模仿”方式,無法形成集群創(chuàng)新活動的正外部效應(yīng)。這種傳統(tǒng)創(chuàng)新模式中存在保守的家族制經(jīng)濟(jì)觀念, 決定了具有創(chuàng)新轉(zhuǎn)化力, 但是“創(chuàng)新壓強(qiáng)” 較低。特別是溫州的家族企業(yè)以親緣、人緣、地緣等關(guān)系組織起來的企業(yè)形式,往往以企業(yè)創(chuàng)始人(家長)為經(jīng)營核心,企業(yè)結(jié)構(gòu)以維系企業(yè)對家長權(quán)威的向心力和對家族價值的認(rèn)同為運(yùn)行體系。企業(yè)各項管理職能的運(yùn)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家族成員之間在長期生活中形成的非正式行為機(jī)制、情感聯(lián)系和溝通模式等。這種家族企業(yè)經(jīng)營上關(guān)系主義、家長權(quán)威至上和家族間信任特征,極大地阻礙了企業(yè)的人力資源、管理資源等創(chuàng)新要素的規(guī)模聚集,也造成企業(yè)興衰的偶然性。
相對浙江市場誘發(fā)型的模式,江蘇民營企業(yè)發(fā)端于政府引導(dǎo)的國有和 “蘇南模式”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改制。特別是江蘇省用財政資金來推進(jìn)新興產(chǎn)業(yè),使規(guī)模較大的旗艦型民營企業(yè)集團(tuán)脫穎而出。廣東企業(yè)在國家創(chuàng)新和電子行業(yè)創(chuàng)業(yè)基礎(chǔ)廣泛的環(huán)境,大型企業(yè)的集聚效應(yīng)和溢出效應(yīng)顯著。浙江省企業(yè)生態(tài)群以中小企業(yè)為主,缺乏大平臺的支撐、大項目的支持、大產(chǎn)業(yè)的配套和大企業(yè)的龍頭作用。浙商在天生資源稟賦缺失下求生存的無奈,培養(yǎng)出“追利生存模式”。近年面對人均GDP趨近發(fā)達(dá)國家(地區(qū))水平,開放的邊際效益遞減和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軟肋暴露,部分企業(yè)家便用熱錢圍獵地產(chǎn)、股市期貨等非實體經(jīng)濟(jì)。又疊加創(chuàng)二代“接班鴻溝”和“代際風(fēng)險”,高端創(chuàng)新要素被滬蘇發(fā)達(dá)省市吸走。這是浙江企業(yè)的實際,也是與江蘇、廣東企業(yè)的差距所在。(作者單位為 寧波大紅鷹學(xué)院)
本文為浙江省社會科學(xué)界聯(lián)合會研究課題“浙江中小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發(fā)展模式與機(jī)制研究(2017B05)”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