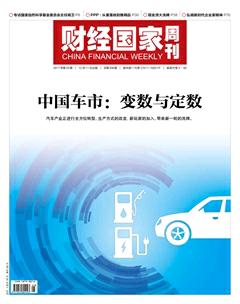金融去杠桿:被動還是主動?
黃文濤
金融去杠桿還未結束,債市調整可能也尚未完成。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其中,金融去杠桿概念自提出以來,已然采取了諸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

當前,繼續推進金融去杠桿的“天時、地利”均已具備,且下半場“強監管+中性貨幣”將成主基調。金融機構應盡早優化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盤活存量和增量資金,避免后續被動調整而遭受更大的損失,爭取以較小的成本盡早釋放風險。
不過,金融機構對此的認知還存在一定偏差,有的甚至依然遵循既有業務模式,主動去杠桿的意愿和力度明顯不足。待政策走向明晰之后,或最終導致市場陷入較為劇烈的被動去杠桿境地。
主動意愿不足
時至今日,金融去杠桿已歷時一年有余,但金融機構主動去杠桿的意愿還不夠強,金融去杠桿更多表現為存量資產的博弈。
盡管政策部門通過“資金成本剛性”、強化金融監管等方式逐步引導金融機構主動去杠桿,但從市場反應看,除4-5月份金融機構經歷了一輪較強的被動去杠桿以外,其余時段金融機構去杠桿意愿不強,甚至在監管協調之際,部分金融機構還選擇了重新加杠桿。
今年以來,股權及其他投資增長明顯放緩,1-9月份僅增加50億元,同比少增7.3萬億,但9月末余額仍高達22.1萬億元,遠高于2016年初的15.8萬億元和2015年初的7.3萬億元。
而且,同業存單發行量和發行價格普遍較高,市場主體對資金的剛性需求依然旺盛。今年前9個月,同業存單月均凈融資額達到16.6萬億元,較2016年同期多增7萬億元,同業存單平均發行利率較上年同期提高157BP左右。也就是說,雖然金融機構過度加杠桿的行為在逐步減少,但部分機構資產負債調整仍以存量資產博弈為主,主動去杠桿的動力和意愿明顯不足。
不僅如此,金融機構對接下來“強監管+中性貨幣”政策組合的預期亦不足,但可以預計,這將成為我國實體經濟和金融部門去杠桿的最重要政策組合。
國內外經驗看,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部門,主動去杠桿都離不開監管和貨幣部門的配合。強化金融監管將是未來金融市場穩定與發展的主旋律。同時,為配合主動去杠桿的政策目標,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基調或是最優選擇。期間,央行出于“削峰填谷”和結構性調整需要,在部分時段可能會增加或減少流動性投放量,但這主要是邊際上的變化,并不改變穩健中性的政策基調。
但從現實情況看,市場主體對“強監管+中性貨幣”政策組合的認識存在明顯偏差,依然遵循已有思維來理解和認識本輪金融去杠桿。

比如,在很多金融機構看來,大量政策判斷都是基于2013年金融去杠桿的調控經驗,但與2013年相比,本輪金融去杠桿耗時更長、涉及領域更廣,影響也更為久遠,不僅涉及到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等根本制度建設,同時也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國家戰略高度協同,應以全局性的眼光去衡量和判斷本輪政策基調。
這些預期偏差,將使得部分金融機構危機意識單薄,以觀望甚至“樂觀”心態看待本輪金融去杠桿。
隨著“強監管+中性貨幣”政策組合進一步明晰,此前偏“樂觀”的心態出現逆轉,或將造成一致性預期的修正和集體式被動調整,導致市場陷入較為劇烈的被動去杠桿境地。
認識偏差
不僅是對政策預期存在分歧,大量金融機構對于國內經濟與美聯儲加息等境內外因素的認知,也存在偏差。
在境內因素上,近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發揮作用,我國經濟呈現出總量穩定和結構優化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經濟短期內很難出現大幅回落,另一方面也難以輕易明顯回升,經濟運行表現出較強的韌性和回旋余地。
應當看到,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未來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都離不開一個健康有效的金融市場。這意味著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將是近期一系列金融政策的重點。
然而,金融市場通常更關注短期經濟波動,也常常通過短期視野判斷長期政策走向。對于短期經濟波動與長期趨勢同向運行時,短期分析視角確實非常有效;而當經濟或政策存在重大戰略調整時,過于依賴短期波動可能會忽視經濟和政策演化的核心邏輯。尤其是市場長期處在僵持階段時,經濟和政策預期偏差很容易形成一致性心理預期和集體性行為。即使經濟數據的一些微小變化,也足以造成市場的巨大波動,這既是市場對此前一致性預期偏差的修正,同時也是市場回歸經濟基本面的必要調整。
在境外因素上,2015年以來,隨著美聯儲開啟新一輪加息周期,美元指數和美國債收益率走勢就一直備受全球金融市場關注。
然而,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并未跟隨美聯儲加息同步上行,即使美聯儲公布了縮表計劃,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幅度也相當有限。因此,很多觀點都以“格林斯潘”之謎解釋該現象,弱化了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對全球經濟體可能造成的潛在沖擊。
但應當看到,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遠未結束,后續美聯儲還會綜合運用“縮表+加息”政策組合推進正常化。這些都可能對全球金融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巨大沖擊。
對中國而言,隨著匯率彈性的增強和資本項目改革的穩步推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操作空間已有明顯提高,但資本流出壓力和匯率貶值壓力依然存在。而且,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具有較強的示范效應和溢出效應。在中美國債利差高度相關的情況下,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邊際效應的逐步顯現,美國債收益率上行壓力對國內債券市場也構成了一定的潛在壓力。
大幕剛剛開啟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但卻并非重現。
近期的債市被動去杠桿與4-5月份的過程十分相似,但兩者之間卻存在本質的區別。
首先,本輪債市被動去杠桿是在長時間僵持之后,金融市場對金融去杠桿政策、經濟增長等預期偏差修正后的集體調整,未來金融市場可能會因預期變化而出現一定的分化;而此前被動去杠桿更多是監管強化的沖擊所致,監管沖擊之后金融市場依舊處在觀望之中,并逐漸演化為一致性預期之下的僵持格局。
其次,本輪被動去杠桿是金融去杠桿行至下半場后,打破長期僵持格局的一次突破,隨著金融機構預期和行為的變化,金融市場的調整可能會加快,債市也有望重回經濟基本面。而此前被動去杠桿主要是金融去杠桿政策的一次調整,是繼續推動金融去杠桿的一次政策探索。
再者,本輪被動去杠桿之后,金融市場的風險已明顯釋放,政策部門常態化監管機制可能會相繼落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也會得到明顯提升;而此前的調整僅僅只是開始,對于下一步政策如何變化仍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那么,被動去杠桿將走向何方?
可能肯定的是,金融去杠桿還未結束,債市調整可能也尚未完成。此次被動去杠桿之后,金融機構主動去杠桿的意愿可能會進一步增強,加之基本面總體穩定、監管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持續,債市很可能還處在一個相對艱難的調整階段。經過調整之后,長期僵持局面正在破局之中,債市的配置價值更加凸顯,但交易性行情可能尚需等待。
下一階段,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深入推進,金融市場將在以下幾個方面有顯著改善。
一是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目前抑制資金“脫實向虛”的成效已有所顯現,但遠沒有達到預期目標。隨著去杠桿的深入推進,金融機構同業加杠桿與資產部門之間的正反饋機制將會得到遏制,通過加杠桿獲取的超額收益將成為過去式。期間,證券類投資科目將告別高速增長的時代,調整完成后大概率會回歸至一個合理水平;M2與社會融資總量之間持續的背離也會逐步得到改善,并最終恢復至相對均衡的狀態。
二是金融系統性風險有效緩解。當前市場處在相對脆弱的狀態。隨著相關監管政策的出臺,金融機構通過同業加杠桿、多層嵌套的監管套利將得到緩解,從而有助于降低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以及交叉傳染風險。同時,金融產品剛性兌付等問題有望得到部分解決,同業業務也將逐步回歸本源。
三是資產負債定價回歸基本面。隨著去杠桿進程的不斷推進,“負債成本剛性”和“資產收益鈍化”并存的現象會逐步扭轉,資產負債將逐步回歸基本面。屆時融資成本(如7天回購利率)與資產收益率(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間維持相對穩定的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