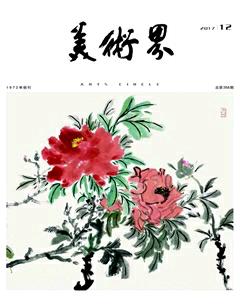民族與人文精神的形塑
我來廣西工作生活已有九年了,入鄉隨俗,便開始不自覺地了解起這里獨特的少數民族文化來,并以此為創作題材進行雕塑創作。第一件少數民族題材作品是2012年創作的《黑衣壯的女人》。2010年,我來到位于中越邊境廣西那坡縣一個叫做“黑衣壯”的壯族古村落,村里的青壯年男子大都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務工,只剩老人、婦女和兒童。勤勞樸實的婦女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至今仍保持著原始的勞作方式及傳統的風俗習慣,穿著的服飾是以黑為主,凸顯出黑衣壯族強大的氣場,這件作品試圖去表現這些內容。作品采用群雕的構圖來表現,塑造出七位不同年齡段黑衣壯女人向前行走的姿態。人物分為前后兩排,前排為身形弱小的老人和孩子,后排則是體形高大的中青年婦女,這種穿插錯落的布置在視覺上既有層次又互不遮擋。運用這樣緊湊的構圖表現并排行走的人群,人物相互之間沒有言語和眼神的溝通,但能體會到一種默契,展現出壯族女人彼此之間的友愛與團結。作品表現出一種少數民族文化神秘感的同時,力圖捕捉出不同年齡段少數民族女性內心的世界與情感。作品中衣紋的塑造保留了不經意間留下來有意味的塑痕,以此來展現少數民族人物淳樸、粗獷、活力的一面。這件作品不僅僅強調塑痕在空間中的恣意揮舞,形散而神聚,更是追求一股氣度和張力,追求一種對遠山民族的情懷釋放。今天,現代社會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對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形成了強烈沖擊,作品《黑衣壯的女人》對仍堅守著本民族文化的人們給予贊頌,也對鄉土文明被城市文明的強勢沖擊與滲透懷著一絲悲憫情懷。
由于對黑衣壯文化懷有特別的情感,三年之后我再次來到黑衣壯族村落,卻只能一聲嘆息,整個村落的傳統干欄式建筑幾乎已被混凝土筒子樓所替代,只剩兩三戶貧困人家的破舊木樓未拆。村落里少見中年婦女和孩子,只有三三兩兩湊在一起的高齡老人并排坐在長木凳上,彼此沒有任何交流,目視遠方,一條老狗作陪在旁。見此情景我深感無奈,決定當天返程,這一路上我陷入了沉思,覺得自己應該尋找一種方式發泄心中的吶喊。這種吶喊唯有靠雕塑來表達,這才有了雕塑作品《遠山的風》。《遠山的風》打破了以前作品固定的表現方式,首先從材質上運用木質材料與泥土相結合;其次是木質材料的高低穿插榫卯,把人物錯落的擱置在不同空間位置上。作品由木結構和泥塑人物兩部分組成,木結構吸取了古代建筑傳統榫卯形態,在人物塑造上運用寫意的手法,不拘泥于細節,追求印象中的神韻。作品中年邁的老人呆滯地望著子女歸來的方向,身下的木結構顯然已經腐朽與殘破不堪,仿佛下一秒鐘一切即將坍塌,但仍然凝聚著最后的一股勁兒默默堅守著。《遠山的風》悲情式地塑造了幾位老人與狗的孤獨狀態,從表面看似是對留守老人的關注與同情,思考之后不難發現作品是對即將被城市文化吞噬的少數民族文化命運與前途的人文關懷。
《遠山的風》以一種悲情的方式完成,我總覺得有些遺憾,畢竟人總是向往和追求美好,于是時常在心中勾勒出少數民族文化繁衍不息的場景,為了一了心愿,2016年創作了第三件關于黑衣壯的作品《壯山煙云》。《壯山煙云》將中國傳統雕塑與西方寫實雕塑的美學風格相結合,展現出既傳統又不失現代的藝術語境,既寫實又寫意的藝術手法,既西方又本土化的藝術面貌。通過對壯鄉壯族的多元化、民俗化、生活化、樸實化等民族歷史文脈的提煉,以人物內心精神面貌的傳達作為作品的支撐點,刻畫出具有濃郁、獨特的地域特征的主題雕塑作品。作品選用傳統少數民族題材為創作主題,從具象提煉到意象表現,以普通壯家三口最平凡的生活為作品的切入點并加以提煉。充分考慮作品的構圖,強調雕塑的整體構思,人物如山的歸納,一高一矮、一寬一窄,在空間上把握和傳達雕塑的美感。在把握整體構圖的同時也兼顧了作品的藝術塑造手法,注重掌控整體與局部的關系,考究每一個表情、動作、衣紋的塑造在合理的基礎上為雕塑的主題服務,使其更加生動,更富有表現力。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化獨特且深刻的理解與對雕塑藝術形式的創作研究,創作出與真實場景不同的藝術面貌,使雕塑創作來源于生活本身,又高于生活。這件作品力求表達壯族人骨子里流露出來的樸實、堅韌、積極、向上、頑強的優良傳統和高尚品質。以《壯山煙云》為題的雕塑作品,用具象寫實的雕塑方式塑造了壯族的三口之家迎面走在大路上的和諧畫面,正是對這些優秀傳統和高尚品質的藝術升華。作品關注于普通壯家三口最平凡不過的行走,沒有過多的粉飾,沒有常見表現少數民族幸福生活中勞動與載歌載舞的場面。從生活中提煉出具象性的動作姿態,表現出具有平凡性、儀式性、莊重性、精神性,使創作脫離表現臨摹式的塑造。作品在平凡中展現美感相比之下更加含蓄、耐人尋味,用這樣的藝術處理深刻地彰顯出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對民族夢和中國夢的美好追求。
在我創作的少數民族題材中,作品《日出》《苗山之后》兩件作品值得一提。這兩件均是表現廣西隆林素苗(苗族的支系)女人的作品。2014年創作的《日出》塑造了三位苗族姐妹站在山坡上唱著思念阿哥的苗山調子等待阿哥歸來的真實場面。作品運用圓雕和浮雕相結合的手法,巧妙的把腿腳與山坡空間壓縮,放棄使用傳統的底座展示。人物表現概括性的拋棄了部分細節,使雕塑的三個人物融為一體,疏密有致,傳達出三姐妹默契和聲的同時心中卻揣著對阿哥各自不一樣的思念,仿佛期待光明等待日出。《日出》看似描寫少數民族婦女關于愛情的命題,實則是在鄉村勞動力向城市輸出的社會背景下對留守婦女的關注。
如果說《日出》屬于現實主義的表現方式,那么2015年創作的《苗山之后》更具浪漫主義色彩,一次夢境仿佛回到了古代素苗寨子,透過煙霧朦朧,遠遠地看見一位騎馬的苗族王后靜靜地張開手臂,頗具儀式感……。醒來之后難以釋懷,草草勾勒,感覺已是一件雕塑了。這件作品想法來得最快,但創作經歷了一年,這一年使我開始從新認識中國傳統雕塑之美,這一年痛并快樂著。因為要表現古代苗族王后的氣質,初次嘗試了漢代的木雕手法來創作作品。漢代雕塑渾厚深沉,粗放豪邁,簡練傳神,風格粗獷古樸、氣勢豪放,看似簡單但蘊藏了漢人深厚的文脈積淀,每根線條的歸納都能感受古人追求氣韻的愿望。《苗山之后》的創作是學習與否定交錯的糾結過程,作品在斷斷續續的節奏中完成。作品《苗山之后》雕刻了一位少數民族王后騎馬的形象,運用原始的榫卯處理把作品各個部分榫接起來,吸收漢代木雕的以形寫意的思想雕刻人物與馬的形象。整件作品古樸、莊嚴、氣勢澎湃,具有儀式感。作品一方面通過藝術化的處理,呈現出一位莊嚴、高貴、自信的古代苗族部落王后的騎馬像,彰顯出昔日苗族部落文化的繁盛與自信;另一方面,借古喻今,當下社會文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逆轉,面對沒落的少數民族古代文化,我們不應該是嘆息,而應思考在當下如何復興少數民族文化。
這些年來,我除了連續創作了一批表現當代少數民族風貌的雕塑作品外,還應社會的需求創作了一批肖像雕塑作品,如:《馬三立像》《沈從文像》《禾下乘涼夢——袁隆平像》《洪松泉的傳說》《風蕭蕭兮易水寒——荊軻》等作品。這批雕塑作品的創作手法不一,在創作之前反復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在力求還原人物和時代賦予的精神之外,添加我個人對于人物的解讀,選擇最佳的表現形式。這些作品在社會上也得到了一致好評。不論任何題材的創作,我個人追求“力圖凝練民族與時代的偉大精神,追求人文與審美的和諧統一。”這可能是一個藝術家終生的目標。
國家藝術基金2016年度青年藝術創作人才資助項目雕塑《壯山煙云》證書編號:20163148
劉宇航
1985年生于湖南沅陵。2009年畢業于天津美術學院雕塑系并獲學士學位,2012年畢業于廣西藝術學院雕塑系并獲碩士學位。2012年至今任教于廣西藝術學院造型藝術學院雕塑系,講師。中國雕塑學會會員,廣西美術家協會會員,廣西青年美術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