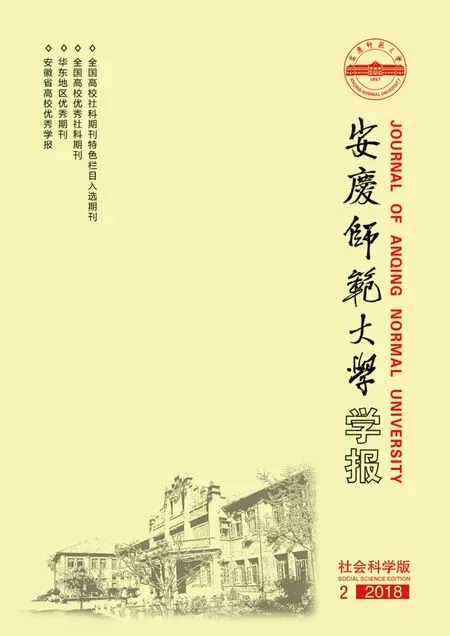士人交結與文本書寫:東漢游學士人文化活動考察
楊霞霞
(安徽廣播電視大學 文法學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游學是東漢士人重要的文化活動。史書記載其時“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1]2588,順帝時更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1]2547。近年來學界對這一史實的研究多集中于這三個領域:此期游學的發生、特點與社會影響,某一區域士人的游學活動帶來的學術繁榮,游學與文學的關聯特別是游學背景下五言詩的興盛。對東漢士人游學中具體的文化活動則少有提及,對這一時期游學士人文化活動類型也鮮有總結。當是時,游學者日眾,京城太學士子們秉持著“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1]2481的新游學理念,彼此交結、互相題拂,逐漸呈現出大規模交結、進而形成群落的態勢。士人下行民間、游學成風,又引發了士人間政治、學術、思想層面的多重交流,并進一步促成了文章書寫的繁興,遂有“自東京以降,迄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2]的新局面之形成。士人交結、文本書寫正是東漢游學士人的兩大文化活動類型,本文擬對這兩種文化現象進行具體分析,嘗試勾勒出東漢一代士人的活動影像。
一、游學士人的交結
“學宦一體”是東漢的學術政治生態。從小處看,是業師、弟子,同時又是舉主、故吏的關系;從大處看,則是學術與政治的彼此滲透。東漢游學者日眾,并逐漸呈現出大規模交結、進而形成群落的態勢。這與其時“學宦一體”的政治、學術形態密切相關。正是士人學宦一體的天然聯系和志士交結的有意為之加速士人的聚合,促進了士人群落的生成。
(一)學宦一體
“漢世,業師門生,恩同君父,關系至重。”[3]無論官學、私學都強調師長的權威和學生的服從。在學術上,學生恪守師法家法。在日常生活中,學生對師長負有各種義務。師長去世,弟子門生無論身處何方、居何職,均有奔喪服喪的義務。樂恢、樓望、鄭玄等去世,弟子門生會葬達數百人至數千人。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東海申君卒,輒送喪至東海。
同時,弟子與業師、故吏與舉主,這兩組關系又糾纏一起,形成業師亦為舉主、門生成為故吏的局面,即“學宦一體”的政治學術生態。
東漢經學大儒往往被朝廷所用,出任職官,如陳留劉昆通曉《施氏易》,“征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1]2550;南陽洼丹,“《易》家宗之,稱為大儒”[1]2551,先后為博士、大鴻臚;京兆楊政“善說經書”,“官至左中郎將”[1]2551;潁川張興,為梁丘家宗,先后為博士、“遷侍中祭酒”、“拜太子少傅”[1]2552;扶風平陵魯恭、魯丕兄弟二人“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1]873,后,魯恭拜博士,遷侍中、拜議郎、官至司徒,魯丕以明經篤學而屢次被舉。此外,東漢帝王為太子時亦需受業于師(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當太子登基,其師多以太傅身份錄尚書事,完成由學術名師向朝中重臣的身份轉變。
這些以儒學入仕者又大多為學術名師,或在入仕之前就已開館授徒,如劉昆曾教授于江陵,洼丹有弟子數百人,張興著錄弟子達萬人;或居官期間兼以教授,如崔瑗、周防、符融、蔡邕、劉表分別師從時為侍中的賈逵、徐州刺史蓋豫、少府李膺、太傅胡廣、南陽太守王暢。更有太子少傅張興、趙相魯丕、河內太守牟長在任期間,授徒數百至萬人者。
既為朝中大員,則擁有舉足輕重的薦舉權。如魯恭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1]882魯丕任東郡太守則“數薦達幽隱名士”[1]884。那么,兼為經師,其弟子無疑有更多機會受到推薦。例如:汝南鐘興少師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1]2579除鐘興憑借業師入仕之外,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亦受業于丁恭。桓榮為明帝師,其“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余門徒多至公卿”[1]1253。
又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1]1239至于位高權重者,其門生、故吏不計其數。最典型事例莫過于汝南袁氏,其家族五公三卿,“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于天下。”[1]2375當然,當舉主獲罪,其門生故吏亦罹其禍。東漢初期,楚王劉英謀反,事泄,朝廷詔捕同黨,會稽太守尹興獲罪,其“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勛及掾史五百余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1]2682漢末黨錮禍起,朝廷幾次下詔“諸附從者錮及五屬”,“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1]2189游學者因此牽連甚廣。例如靈帝建寧二年(169年),黨錮復起,大學者鄭玄“與同郡孫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錮”[1]1207。鄭玄一生向學,無意仕途,其遭黨禁,最有可能是因為與杜密的關聯。鄭玄曾為鄉佐,時為太山太守、北海相的杜密“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1]2198杜密于鄭玄有賞識、提攜之恩,兩者即成舉主、故吏關系。黨錮禍起,杜密下獄死,鄭玄作為故吏也遭禁錮。
這種學宦一體現象的形成與東漢社會的學術背景和政治現實有關,究其根源,正是東漢政府大力推行的明經入仕的人才錄用機制促成了學術、政治密不可分的結果,即學術政治化的必然產物。
(二)志士結交
在政府誘之以利祿、太學興盛的背景下,大量士人涌入洛陽。學子們自四海而來,共聚一地,在學業上共同進步,在生活中彼此照顧,漸漸形成深厚的同學情誼。
如東漢初期朱暉與張堪舊事:起初張堪有名于太學,以朱暉為友,并“欲以妻子托朱生”。后張堪去世,朱暉聽聞其家人貧困,則前往救濟。朱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1]1453此外又有和帝時期濟北戴封為同學石敬平送喪歸故里、山陽范式與汝南張劭的“雞黍之交”的故事,皆顯示出學子們重友情、講信義的道德品質。
中后期的東漢太學,隨著游學群體擴張、經書繁雜、仕進艱難,士子之間彌漫著輕學問、重結交的風氣。這種結交染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符融與仇覽的對話可為一例。“(仇)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1]2481有名望的太學領袖也注重獎掖士人。如,太原郭泰出身微寒,不欲為吏而辭家游學,“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于洛陽。”[1]2225在洛陽經符融引薦,與其時被奉為“天下楷模”的名士、時為河南尹的李膺友善,于是名震京師,為太學三萬諸生之領袖。郭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1]2225。史書記載,鄉人賈淑、陳留江原、扶風宋果受其感召而改過自厲;陳留茅容、巨鹿孟敏、潁川庾乘因勸令學,終有所成。
靈帝熹平四年(175年),朝廷“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1]336“后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1]1345這是一次較大規模的官藏圖籍的公布活動,促進了士人的流動。士人的這一觀視、摹寫行為,并不僅是簡單的抄錄文獻,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在交通設施落后、信息傳播不發達的東漢社會,士人大量涌入洛陽,又恰逢清議之風的興起,其背后必然是士人之間的更深層次的文化交流。
(三)士人群落生成
學宦一體的天然聯系與志士交結的有意為之最終都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所謂士人群落,是指聚集一地的士人因共同的生存環境、學術背景和政治理想而自發結合在一起的組織形式。這一群體平時聯系并不緊密,多是政府監督、指導下的共同體。當然,也包括具有學術傳承關系,由經師、弟子組成的師生群體。
1.東漢中央機構士人群落
歷史上的洛陽自秦至隋唐,一直都是民眾道路可達的核心區域。早在周代,“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洛,以此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4]而在東漢,洛陽作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成為士人們向往的圣地。“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洛陽成為中心點,具有最優的通達性,洛陽成為歷史上中心性最穩定的城市,持續了1100多年。”[5]
清代學者趙翼以“兩漢時受業者皆赴京師”[6]一語概括漢代游學者的地域流向。的確,作為學術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時的都城洛陽具有多重優勢,吸引了大批士人朝此間流動。而大批游學者因洛陽的學術向心力而輻輳至此,又加速了洛陽取代長安舊都成為各類學術思想交流新中心的進程。這一時期東漢中央機構主要士人群落依次有:
仁壽闥士人群落。有馬嚴、班固、杜撫。“永平十五年……顯宗召見,(馬)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1]859
蘭臺士人群落。光武、明、章時期,聚集洛陽的士人大多集中在蘭臺,如班固曾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后又撰成“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1]1334。除修史之外,蘭臺士人還以校書為職。如傅毅、班固、賈逵曾共同校書。其他蘭臺士人又有班超、孔僖、楊終、李尤等。
東觀士人群落。東觀是東漢最重要的文化機構,也是洛陽士人薈萃之所。和帝時期東觀士人群體,以班昭、馬續、馬融等十余高才郎為主;安帝時期先后有劉珍、竇章、劉毅、劉騊駼、馬融、許慎、蔡倫、李尤、王逸以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等五十余人進入東觀;順帝時期,張衡、伏無忌、黃景、崔寔進入東觀;桓帝時期,延篤、朱穆、邊韶、伏無忌、黃景、崔寔、馬融、延篤、張奐;靈帝時期,蔡邕、盧植、馬日磾、楊彪、韓說、單飏。
鴻都士人群落。鴻都門集中了大量“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1]1991-1992,其中可考者有樂松、任芝、賈護、江覽、郄儉、梁鵠、師宜官。
2.東漢地方主要士人群落
東漢地方士人群落集中表現在漢末荊州襄陽士人群落與冀州鄴城士人群落。這與漢末中央權力式微、地方勢力興起有關。
漢末的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谷獨登”[1]2124,同時在荊州牧劉表治理下,“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1]2421大量士民流入荊州,僅關中一地,“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余家。”[7]610來此避亂的名士有王粲、宋忠、隗禧、禰衡、繁欽、邯鄲淳、諸葛亮、傅巽、潁容、趙岐、裴潛、司馬芝、孫嵩、和洽、劉廙、杜夔、劉巴等,“皆海內之俊杰也”[7]598。其中,既有依附劉表為其幕僚者,也有僅以荊州為避難之所而不問政治者。
鄴城士人群落在喜好詩文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倡導下逐漸興起,并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文人集團。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鄴城,此后直至曹丕定都洛陽,鄴城一直是曹魏政權中心。大量士人匯聚于此,形成以三曹七子為主體的鄴下士人集團。山陽王粲、北海徐干、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玚、東平劉楨、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廣平劉劭、陳留蘇林、濟陰吳質等都是這一群落的代表人物。
3.東漢重要幕府士人群落
大量士人供職于幕府是東漢重要的文化現象。這一時期幕府士人群落主要有:以傅毅、崔骃、班固為主體的竇憲幕府士人群體;以馬融、楊震、朱寵、陳禪為主體的鄧騭幕府士人群體;以巨覽、陳龜、李固、周舉、馬融為主體的梁商幕府士人群體;以朱穆、周景、崔寔、趙岐、應奉、吳佑、楊賜、馬融為主體的梁冀幕府士人群體。
4.東漢著名師生群落
“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8]因此,由經師、弟子組成的師生群體也是不可忽略的文化群落。此期著名的師生群落有杜子春與弟子鄭眾、鄭興、賈逵等;賈逵與弟子許慎、崔瑗、高才生二十余人;馬融與弟子鄭玄、盧植、延篤等;鄭玄與弟子國淵、趙商、王基、郗慮、任嘏、孫炎等;胡廣與弟子蔡邕等;蔡邕與弟子阮瑀、路粹、蘇林等。在這些師生群落中,弟子從經師處聽講、抄錄、答問,經師為弟子傳道、授業、解惑,二者奇文共賞、疑義辨析、教學相長,共同推進了學術的薪火相傳。
二、游學士人的書寫
東漢各地域間大規模的士人流動促成了士人群落的出現,并進一步促成了文章寫作群體的生成。這些寫作群體的書寫,既包括以修史、定經、獻賦為主體的官方行為,也有私人性質的個體書寫。在共同的書寫中,東漢士人們相互啟發、彼此競爭,共同促進了東漢文章的發展。
(一)《東觀漢記》的踵續而成
“中興之史,出自東觀。”[9]196大批學者陸續進入東觀,合作書寫、踵續而成《東觀漢記》。這一修史活動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明帝永平年間,明帝召見扶風馬嚴,“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1]859又據文獻記載,班固又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后又撰成“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1]1334其他同時期身在蘭臺,極有可能參與這次著述的士人有:魯國孔僖,“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1]2560;蜀郡楊終,“顯宗時,征詣蘭臺,拜校書郎”[1]1597;廣漢李尤,“少以文章顯……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李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1]2616
安帝永寧年間,“鄧太后詔(劉)毅及劉騊駼入東觀,與謁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1]558。除劉毅、劉騊駼、劉珍三人外,此時活動在東觀的文人另有馬融、李尤、王逸、馬融等。李尤,“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仆射劉珍等俱撰《漢記》”[1]2616;南郡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拜為校書郎,很有可能參加這次修史活動。此次修史的成果是撰成《建武以來名臣傳》,乃“《漢記》之初續也。”[10]
桓帝在位期間,延篤、朱穆、邊韶、伏無忌、黃景、崔寔、馬融等亦進入東觀續修《漢紀》。南陽延篤,“桓帝以博士征,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1]2103;伏無忌、黃景,“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1]898;涿郡崔寔,“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1]1726。此外,延熹二年(159年),馬融“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1]1972;敦煌張奐因上書獻《章句》被詔下東觀,因此也有可能參加這次活動。
靈帝熹平年間,朝廷詔令增補《漢記》,“復征拜(盧植)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1]2113此次活動續寫“帝紀”和“列傳”,增設“志”的部分。至此,《東觀漢記》基本成型。
嚴格意義上,這里所論述的寫作群體已不屬于前文考察的游學者之列。然而,以上身在蘭臺、東觀修史的士人多有游學經歷;并且,蘭臺、東觀士人多為郎官,而“迄乎東漢……三署諸郎多郡吏與經生,貴族豪富之子弟較少”[11],郡吏、經生又是東漢游學主體。這些著作者受察舉或辟除而集中于此,這也是廣泛意義上的游學活動。因此,這里可視為對東漢游學群體的后續文化活動的研究。
(二)經學文獻的師生撰述
東漢游風盛行,士人輾轉各地求學問道,多以學習經傳為主要目的。在不斷的學習中,士人溫故知新,常且述且作。翻檢文獻,可以發現,東漢時期具有學術傳承關系的經師和儒生間的經學撰述較為常見。其中,著名的經學師生撰述有:
杜子春與鄭眾、賈逵師生的撰述。杜子春,曾受《周禮》于劉歆,并為《周禮》作注。史書記載:“《周禮》一書,當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緱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讀,頗識其說”,大儒鄭眾、賈逵“往受業焉”[12]。承師所學,鄭眾著有《周禮鄭司農解詁》,賈逵著有《周禮賈氏解詁》《周禮賈氏注》。
賈逵與許慎師生的撰述。賈逵除師從杜子春之外,還悉傳父業(其父賈徽曾師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亦為當時大儒)。此外,賈逵自幼常在太學,見識廣闊,兼通五經,世稱通儒。除撰注《周禮》之外,賈逵對《易》、《書》《詩》《春秋》亦多有研究,“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1]1240。其弟子眾多,而以許慎最為知名。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13]498,亦精通諸經,有“《五經》無雙許叔重”[1]2588的盛譽。其著作有《春秋左傳許氏注》《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不僅如此,許慎經典之作《說文解字》在問世之前,還“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逵”[13]498,可見亦受益于其師賈逵,方成《說文解字》。
馬融與鄭玄、盧植、延篤師生的撰述。馬融、鄭玄是東漢經學史上最著名的一對師生組合。二者皆博學多聞,兼通五經。盧植、延篤也是馬融高足。這一師生群體著作頗豐,且大體相類。如:馬融作《易傳》,鄭玄作《易注》;馬融作《禮記馬氏注》,鄭玄作《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圖》《三禮目錄》,盧植作《禮記盧氏注》;馬融作《春秋三傳異同說》,鄭玄作《春秋公羊傳鄭氏義》《春秋左傳鄭氏義》,延篤著有《春秋左氏傳延氏注》;馬融作《毛詩馬氏傳》,鄭玄作《毛詩鄭箋》《詩譜》;馬融有《尚書馬氏傳》《尚書中候馬注》,鄭玄作《尚書注》《尚書五行傳注》;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注》;馬融作《孝經馬氏注》,鄭玄作《孝經注》。
上述師生群體是東漢時期最著名、最典型的學術群體。他們基本都有游學各地、轉益多師的學習經歷,在傳道、受業之際,他們苦心著述,體現了士這一群體的傳承、傳播文化的最基本屬性,也大大提升了游學這一文化活動的學術價值。
(三)詩文的文士并作
東漢中后期,隨著游學者數量的增多,一些描寫游子生活和情感的作品也不斷涌現。
“居窮衣單薄,腸中常苦饑”[14]514“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14]518“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15]“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14]442,這是游子的衣食住行;“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同心離居,絕我中腸”[16]180“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16]186“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13]551“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17],這是思念親人、思念故鄉的游子;“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14]539“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14]540“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1]2631,這是游學中見棄于世人的精神苦痛;“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14]538“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14]541“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14]541,這是游子行走天地間發現的殘酷真相。
與家人的書信往來是游學士人的心靈慰藉。在與家人的書信往來中,以夫妻書信往來居多。最為后人稱道的東漢時期夫妻兩地書是秦嘉與徐淑的往來書信。《兩漢全書》記載了秦嘉與妻書有《與妻書》《重報妻書》《贈婦詩》《答婦詩》等;徐淑有《答夫秦嘉書》《又報嘉書》《答秦嘉詩》。秦嘉,隴西人。桓帝時期仕于州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其妻徐淑因病滯留故里。后秦嘉病逝,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9]240。兩人分在洛陽與隴西,書信往復,道盡思念之情。描寫夫妻書信往來的詩句還有很多,例如“客從遠方來”:“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余里,故人心尚爾。”[16]330“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16]192這些都是描寫妻子收到丈夫書信、禮物心情的詩句,由此也可見東漢游學風氣對家書寫作的影響。
此外,士子們自各地而來,輻輳一地,在共同的游學生涯中結下深厚友情。當他們分別后,書信便成為彼此交流的最好方式。《全后漢文》中記載了不少朋友間的往來書信。如張奐、延篤曾共同著作東觀。張奐作書與延篤,言“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又言“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13]651延篤亦感念張奐,謂“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13]629孔融交游甚廣,朋友眾多。他曾致信張纮:“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睹其人也”[13]838;寫信給韋端,臨末不忘贊其二子元將、仲將:“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復來,懿性真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由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13]838
三、結語
士人交結與文本書寫是東漢游學士人最重要的文化活動,兩者引發了不同領域的喧嘩與騷動。士人交結激起了政治的動蕩:士人聚集于一地、彼此交結,發展到一定程度,便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特別是積聚于洛陽這一各種政治勢力糾纏、諸多敏感事件的高發地,士人群落更易轉變為政治性(特別是不合作)的集團,并因其在士林、鄉里乃至官場的影響力而使得這種政治傾向蔓延全國。東漢后期,“官非其人,政以賄成”[1]3297的政治現實促使太學諸生與朝中清流士大夫走到一起,他們還“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1]2187,彼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遂卷起漢末政壇風云。文本書寫則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它是士人游學活動中較為溫和、內斂的表達方式,在文章史上卻具有重大意義:士人的游學逐漸打破地域之限,士人既可共同受詔作賦、奉命撰史、合作校經,又能私下詩文唱和、書信往來, 引發不同時空的文章書寫,并促成個體書寫的流行,遂“一世之士,各相慕習”[18],最終帶來了東漢文學的繁興局面。最后,士人交結與文本書寫這兩類文化活動又不是孤立并行的,士人交結中多有文本的交流,文本書寫中又多有士人結交的影像。而關于此二者關系,待另文再論。
[1]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書店,1988:85.
[3]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C]//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秦漢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1224.
[4]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2119.
[5]王成金、王偉、張夢天.中國道路網絡的通達性評價與演化機理[J].地理學報,2014(10).
[6]趙翼.陔余叢考[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295.
[7]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1959:88.
[9]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石家莊: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361.
[11]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M]//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329.
[12]賈公彥.序周禮廢興[M].北京:中華書局,1980:635-636.
[13]嚴可均.全后漢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4]蕭統.六臣注文選[M].李善,等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
[15]歐陽詢.藝文類聚[M].汪紹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15.
[16]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7]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896.
[18]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