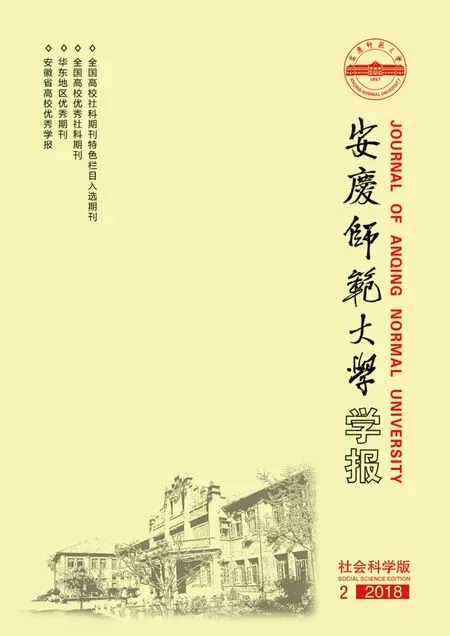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困境、成因與破解
——兼談實質性公眾參與
范華斌
(廣東警官學院 公共管理系,廣東 廣州 510230)
一、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困境
工業化、城市化在驅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亦衍生出眾多威脅公眾安全與健康的負面后果。生態環境持續惡化便是這一后果的突出表現。水源污染、霧霾肆虐、固體廢棄物以及輻射已經成為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日常生活風險的一部分。為了遏制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央和地方政府除了從制度層面對各種排放物的排放標準做出嚴格規定,從組織層面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從政策層面出臺各種激勵/懲罰措施來規制企業行為外,還試圖采取更為積極的行動,如加強環保類項目建設,降低和消解生態壓力。這類項目建設通常具有公益性,涉及大多數人的環境權益,但通常會給項目所在社區帶來安全與健康風險。垃圾焚燒項目建設,雖然減輕了周邊較遠區域的垃圾吸收壓力及其他次生風險,但對項目所在地而言,這一風險是額外的。也正因為潛在風險的不公平分配,環保類項目選址通常會遭到所在社區公眾的普遍反對,以致項目遲遲不能落地,或只能遷址。以垃圾焚燒項目選址為例,僅2016年4—6月發生在浙江海鹽、海南萬寧、江西贛縣、湖北仙桃、廣東肇慶的抗爭性群體事件,均以選址擱置或搬遷為結果,無一例外。垃圾焚燒項目建設屢屢出現“項目選址—公眾反對—項目擱淺或遷址”的怪圈,陷入一鬧就停、一鬧就遷的零和博弈困境。
二、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困境的生成
要想解析選址困境是如何生成的,必須就傳統選址決策模式固有的內在張力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進行全方位的審視。垃圾焚燒項目選址的傳統決策過程為“項目預選址—風險評估(環評)—政府宣布”。這一模式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從決策結構看,選址決策屬于地方政府內部事務,決策主體是單一的政府選址機構,即便是項目風險受眾也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二是對項目建設風險的評估,包括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后果”“可接受程度”等的研判,建立在科學的風險分析基礎上。這就決定了技術專家(官僚)在風險評估中的核心地位。從理論上講,只要科學的風險知識能保證項目風險得到客觀準確的評估,同時作為決策主體的政府選址機構以公眾的利益作為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能客觀公正進行科學決策,這一選址模式就能獲得較為滿意的結果。然而,這一決策模式在垃圾焚燒項目選址中的實際運作存在如下問題。
(一)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客觀的風險評估存在困難
科學知識存在“不確定性”和“滯后性”特點,不是所有項目風險都能通過科學的風險分析方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垃圾焚燒產生的“二惡英”是有毒有害氣體,但這種毒性是否可控即便在科學上也充滿爭議。為了防止垃圾焚燒的有毒氣體擴散,需設置垃圾焚燒廠與公眾的安全距離,那多大距離是安全距離?《生活垃圾焚燒污染可控制標準》(2016修訂版)規定:“應依據環境影響評價結論確定生活垃圾焚燒廠廠址的位置及其與周圍人群的距離”。但該《標準》并沒有標示出明確的量化范圍。并非不想,而是很難給出科學、可信的依據。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特征意味著垃圾焚燒項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后果”“可接受水平”等判斷,即便在專家系統內部也會存在爭議。一旦預選址所在社區的公眾知曉這一風險認知分歧,特別是風險評估結論與公眾的切身感受背道而馳時,“風險社會的環境異議”[1]便會產生,立足于科學評估結果的政府選址決策就會受到挑戰。
(二)封閉式、精英型決策結構引發公眾信任危機
“項目預選址—風險評估(環評)—政府宣布”這一決策模式是一種封閉式、精英型的決策結構。主要體現在決策主體單一、決策過程不公開、信息不透明。從垃圾焚燒項目選址、環評到開工的整個過程缺少公眾或第三方機構的有效參與。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減少項目選址阻力,要么在政府官網不顯眼位置靜悄悄地發布選址信息,公眾并不知情。如湖北仙桃垃圾焚燒廠項目選址中,官方表示曾在環保官網進行過項目公示,但多數公眾表示從項目選址到招標建設的兩年內,地方政府刻意隱瞞相關信息,周邊社區對正在建設的垃圾焚燒廠并不知情;要么突然公開,等一切已成定局再公布。根據《南方周末》報道,2014年惠州垃圾焚燒廠選址一直在封鎖消息中進行,定址后突然公布,引發了公眾的激烈反對,直至換址,風波才平息。從眾多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引發的抗爭性行動案例可以看出,全程隱瞞信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一旦公眾了解到相關信息,即便選址機構會采取一些解釋、溝通措施,這種“臨時抱佛腳”的做法也只會適得其反,失去的是公眾對選址機構的信任,甚至選址機構的一些規范化行為也會受到連帶影響而被公眾否決。選址決策過程不透明、信息不公開會引發公眾對這一“暗箱操作”的異議。而不時見諸報端的利益共謀案例則進一步加劇了公眾對選址機構的不信任。2010年1月30日,《亞洲周刊》的一篇《燒不掉的垃圾真相,中國環保公害揭秘》就曾揭示了以海歸人士為核心的、由學者、企業家、國外設備供應商、投資者所組成的利益集團,通過先說服地方高官,后撬動環保局長的方式,形成龐大的利益鏈,共謀獲利。
(三)風險受眾-技術專家風險認知分歧
選址社區公眾與技術專家圍繞垃圾焚燒項目風險的認知分歧是引發選址失敗的抗爭性行動發生的先決條件。這一分歧與上述兩因素相關,即公眾對立足于科學知識的風險評估的懷疑,以及對封閉式、精英型決策過程的不信任和利益共謀的擔憂。但分歧的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兩者認知風險的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別。道格拉斯和威爾德韋斯認為,普羅大眾的風險認知與其歸屬的文化類型或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當風險威脅到現有生活方式時,人們傾向于重視和高估風險,當風險沒有影響到或是維持現有生活方式所必須之物時,人們傾向于低估或有意忽視風險[2]。風險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大眾傳媒、個體經驗和生活閱歷、本地記憶、道德信念以及個人判斷的話語為依據而建構起來的[3]。一些關鍵性的地方因素如對麻煩的體驗、感覺污染物的存在、對污染物的熟悉感、擔心經濟下滑及是否相信地方官員保護健康和福祉的能力等,卷入了風險解讀的復雜過程,特別是社區環境通常成為風險認知和行動的重要依據[4]。由此可見,在一般民眾眼中,風險一詞并非單純的技術概念,更多的是社會生活概念。公眾通常在風險與社會生活(秩序)的關系中來建構這一概念的具體內涵。這一風險認知方式與專家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風險評估方式在邏輯上存在根本差別,且這一差別成為雙方認知分歧甚或矛盾的認識論根源。當傳統選址模式在選址實踐中遭遇抵制時,選址機構通過各種渠道臨時性地普及科學知識來設法抹平認知分歧。這種做法雖意識到了認知分歧這一事實,卻對分歧產生的原因沒有深刻的認知,無法取得預期成效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三、突破選址困境:反思科學精神,調整決策結構,尊重公眾認知
上述三個因素中前兩個因素是傳統選址模式本身固有的張力,后一個因素則凸顯了引發公眾抗爭行動的風險認知分歧的認識論根源。這一根源——風險認知方式差異與傳統選址模式所反映出的科學崇拜理念(否認公眾風險認知的合理性)是一致的。因此,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失敗的根源應歸咎于選址決策結構及其背后反映出的一般理念。結構性問題當然要通過調整決策結構和轉變理念來解決。
(一)正視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反思科學精神
傳統的項目選址模式與我們生活和工作日常提倡的“科學崇拜”精神是相吻合的,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則必須考慮到科學知識本身的不確定性可能引發的負面后果。這一不確定性不但會引發專家與公眾的認知分歧,甚至在專家群體內部也會引發分裂。由于認知分歧與分裂會產生導致選址失敗的抗爭性行為,選址決策機構有必要反思選址進程中所秉持的科學精神。反思并不是說要否定科學知識在風險評估中的作用,而是要認識到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和滯后性會使風險評估偏離科學評估要求的客觀、精確。為了降低這一不確定性,減少相關負面后果,選址決策機構有必要考慮引進或參考其他領域的知識,使選址決策顯得更加合理。比如面對垃圾焚燒產生的有害氣體“二惡英”是否可控這一在科學上充滿爭議的問題,決策時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在垃圾焚燒項目立項、建設和建成運作中是否發生與“二惡英”不可控相關事件、發生率是多少等實踐經驗。同樣,垃圾焚燒項目與居民區的合理距離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獲取較為準確、可信的參考標準。當然,面對選址所在社區對風險評估的懷疑,在普及科學知識的基礎上,選址機構有必要客觀陳述垃圾焚燒項目風險及風險評估中存在的不確定性,認真聽取所在社區的利益訴求,合理尊重公眾風險認知,與公眾協商解決風險的措施和應對這一不確定性的方法,以消除疑慮、取得信任。
(二)調整決策結構,引導公眾參與,提升公眾信任水平
結構性的問題必須通過結構優化才能得以解決,面對選址決策結構帶來的決策過程不透明、信息不公開引發的公眾信任危機,最為普遍性的建議是制度性的緩解機制——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決策意味著決策主體多元化,潛在的風險受眾、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或個體參與到選址決策進程中,能有效避免傳統決策結構的封閉性,減少認知分歧。多元主體間的風險溝通對于達成一致的選址目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風險溝通的目的并非徹底抹平(也無法抹平)專家與公眾的風險認知分歧,而是將風險認知差異降低到可以接受選址的程度,即求同存異。由于垃圾焚燒項目建設給所在社區帶來額外風險是不爭的事實,風險溝通的議題通常不局限于或者說并不主要在于是否存在風險,而且包括風險評估議題,如對項目所在地的長期保護與補償機制、各社區間的義務均攤、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等。議題拓展有利于釋放因風險不平等分配引發的選址社區公眾的“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憤懣情緒,也有利于彌合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礎上的風險評估與立足于社會理性的公眾風險認知之間的差異,在尊重這一差異基礎上達成妥協與共識,最大限度避免基于認知差異的“鄰避運動”,以減少項目選址的實質性阻力。另一方面,公眾參與選址決策也是有效的監督機制,能避免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共謀行為,確保選址決策合理、科學。
一旦公眾參與成為選址實踐的必要環節,就意味選址社區的風險受眾被“賦權”,成為影響選址決策的因素。這一賦權過程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公眾基于決策過程開放、信息透明的對選址機構的信任和信心。信任是合作關系中永恒的話題。作為公眾參與主導機構的選址部門必須認識到,社會信任的缺失是一個寬泛的、根本性的社會現象[5]。因選址機構在過往選址實踐中欺瞞甚至訴諸暴力的表現,以及監管機構對環保企業超排、偷排及環保產業項目運營過程監管不力等歷史因素所形成的較為低下的信任關系要想在選址時間框架內得到根本性扭轉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是當選址遭遇阻力時,通過各種途徑釋放的官方話語不能取得成效的關鍵。如何在不完全信任的情境下完成有效的風險溝通,便成為公眾參與中選址機構所面臨的重要任務。卡斯帕森等人認為,在不完全信任情境下,“風險溝通者的關鍵任務在于,培育一個使得信息和觀點能以有意義的方式進行交換的環境,便于利益相關的參與者可以作出自己的評判和決定。”[5]當然,在選址過程中,信任問題從來就不是單向的。單向度地強調決策的“科學崇拜”,忽視公眾參與,無疑阻礙了利益相關方達成妥協的可能性,不利于形成共識。
(三)正確認識公眾與專家的風險認知分歧,承認公眾風險認知的合理性
公眾與專家的風險認知分歧源于兩者認知方式差異,這一差異的合乎邏輯的后果即選址決策得不到社區公眾的認同,會引發公眾的環境抗爭行為。基于認知方式差異的風險認知分歧是很難抹平的,從眾多垃圾焚燒項目選址案例中可以看到,當項目遭遇公眾的反對時,選址機構較為普遍的處理手法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在公眾中普及科學知識,但均以失敗告終,公眾并不認同選址機構的官方話語。這一處理方式的實質是否認公眾風險認知的合理性。選址決策要想獲得公眾的認可,簡單地將科學理性凌駕于生活理性之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風險認知中必須承認知識體系是多元的,知識一方面固然來自于科學研究,而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知識與生活(方式)之間的聯系;允許不同于專家觀點的存在,甚至承認不同認識論或可替代認知的合法性[6]。人們關于環境的觀點是被諸如自主性、自我確定、公平公正和人類權利等概念所框定,要尊重不同民族、群體文化[6]。說到底,就是要承認在風險的認知過程中專家和公眾的相對平等地位,不因專家的專業地位和社會地位而確保其在特定風險的理解過程中的特權地位,將其觀點看成是凌駕于他人觀點之上的特殊話語。進一步說是要承認認知方式的多樣化,認可和尊重草根知識。而這正是實質性公眾參與的前提條件。
四、邁向實質性公眾參與
無論是承認公眾風險認知的合理性,還是正視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反思科學精神,抑或是調整決策結構,引導公眾參與,提升公眾信任水平,最終均以公眾參與選址實踐為指向。實際上,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實踐中的公眾參與是存在的,但沒有發揮解決認知分歧之功能,主要原因在于這一參與在現實中往往流于形式,只有參與之外殼,失去了參與的實質內容。為了促進形式化參與向實質性參與轉向,實踐中還需要解決好如下問題:
1.參與雙方要具備相對平等的參與地位
不可否認,與選址機構相比,公眾因風險認知途徑相對有限,風險信息來源缺乏,信息搜集、處理手段缺失,風險溝通渠道不暢等造成的弱勢地位,客觀上造成公眾無法擁有足夠的能力,平等參與風險評估的協商過程。要避免這一不平等局面,在選址機構充分認識到公眾風險認知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互尊重意識之外,提高公眾的博弈能力是關鍵。這一能力提升有賴于公眾自身努力,如公眾應該學法、懂法和用法,努力做到依法參與;公眾應該提高自組織能力,將碎片化個體有機聯結起來,以組織方式參與對話過程,避免出現個體直接面對組織這一不利局面;與公益性非政府組織合作,降低信息搜集等市場化行為成本。在現有體制下,風險博弈中的平等地位的確立僅靠公眾自身努力尚不夠。選址機構有義務通過信息公開等方式來降低公眾信息搜集成本,搭建有效的博弈平臺,不斷提升公眾的參與意識,提高其參與能力,在實踐中探索形成公平公正的博弈規則和運轉有效的參與機制。
2.有效區分利益相關者群體,避免參與人員結構不合理
韋爾巴(Verba)和尼爾(Nie)在《美國的參與:政治民主與社會平等》一書中,在實證數據的基礎上,根據態度和行為取向,將公眾參與者區分為非活躍者、專業投票者、狹義參與者、社群主義者、活動者和完全活躍者六個理想類型[7]。在案例分析基礎上,何艷玲和陳曉運根據風險認知和行為取向,將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劃分為無知者、隱忍者、從眾者與抗爭者四種類型,深刻地闡述了存在眾多而非單一的公眾參與群體[8]。垃圾焚燒項目風險協商中同樣存在不同性質的群體,在普遍的安全與健康訴求外,不同性質群體有自身獨特的關注和需求,如根據“接近性假設”,離選址地空間距離不同的群體對項目的反對程度不一樣;同一空間距離的不同社會經濟特征群體關注的問題優先等次不同、對選址機構的信任度有差別、參與的積極性程度有差異、博弈能力高低不同[9]。從邏輯上講,在各種形式(如聽證會、座談會)的公眾參與中,應根據實際情況選擇有代表性的個體組成參與群體,但公眾參與實踐則很少做到這一點,因為這需要作為主導方的選址機構在前期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將不同群體訴求進行類別化區分,在風險溝通中尋求不同的應對策略。而現實的參與個體選擇,通常遵循方便原則,忽視了參與群體的代表性問題。以較為普遍使用的網絡調查為例,因為技術或不知情等原因,其將相當一部分屬于被調查的利益相關者排除在外了。就垃圾焚燒項目選址實踐來說,尤其要注意弱勢群體,這部分人由于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匱乏,通常政治地位低下,參與機會缺乏且表達訴求的能力不足。一旦按照最小抵抗原則來選址,受到傷害的必定是這部分群體。從公平公正這個角度來說,參與活動的組織者在選擇參與組成人員時,務必要覆蓋所有群體,以保障參與人員結構合理。
3.合理設計公眾參與議題
垃圾焚燒項目風險所涉及的群體利益存在客觀差別,這一差別會帶來基本訴求、預期和選址態度的群體差異。在公眾參與方式設計階段,首先需要對公眾需求在調研的基礎上進行類別化區分,在風險溝通中盡可能考慮每一類需求,照顧多樣化的風險溝通議題,如固定資產貶值的補償、選址機構的角色定位、科技與倫理的關系等。這些議題通常超越簡單的技術風險評估范疇,需要選址機構、專家、項目承擔者與公眾進行充分的討論和雙向回應。而就這些實質性議題溝通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向公眾“賦權”,承認其對垃圾焚燒項目選址有實質性影響力的過程,這一過程有利于打破選址機構的“權力壟斷”,有效構建選址機構與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這種方法不一定能保證一項選址工程成功地被接受,但它的確向項目開發者與公眾提供了一個坐下來談判的機會,這正是瑞典各種核設施選址成功的核心所在[10]。
[1]郭巍青,陳曉運.風險社會的環境異議:以廣州市民反對垃圾焚燒廠建設為例[J].公共行政評論,2001(1):95-121.
[2]DOUGLAS M,WILDAVSK A.Risk and Culture[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3]MURDOC G,PETTS J,HORLICK J T.After Amplification: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C]//PIDGEON N.KASPERSON R E,SLOVIC P.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156-178.
[4]FITCHEN J M,HEATH J S,FESSENDEN R J.Risk Perception in Community Context:ACase Study[C]//JOHNSON B,COVELLO V.The Soci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isk,Dordrecht:Reidel,1987:31-54.
[5]羅杰·E·卡斯帕森,多米尼克·高爾丁,賽斯·圖勒.有害物質填埋場選址與風險溝通中的社會不信任因素[C]//珍妮·X·卡斯帕森,羅杰·E·卡斯帕森.風險的社會視野(上).童蘊芝,譯.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0:29-32.
[6]FAN M F.Justice,Community Knowledge and Waste Facility Siting in Taiwan[J].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0,21(4):418-431.
[7]VERBA S,NIE N H.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8]何艷玲,陳曉運.從“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鄰避沖突中如何形成抗爭動機[J].學術研究,2012(5):55-63.
[9]楊槿,朱竑.“鄰避主義”的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3(1):148-157.
[10]PARKER F L,KASPERSON R E,ANDERSON T L.Technical and Sociopolitical Issues in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M].Safety,Siting and Interim Storage:Volume I.Stockholm:Beijier Institute,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