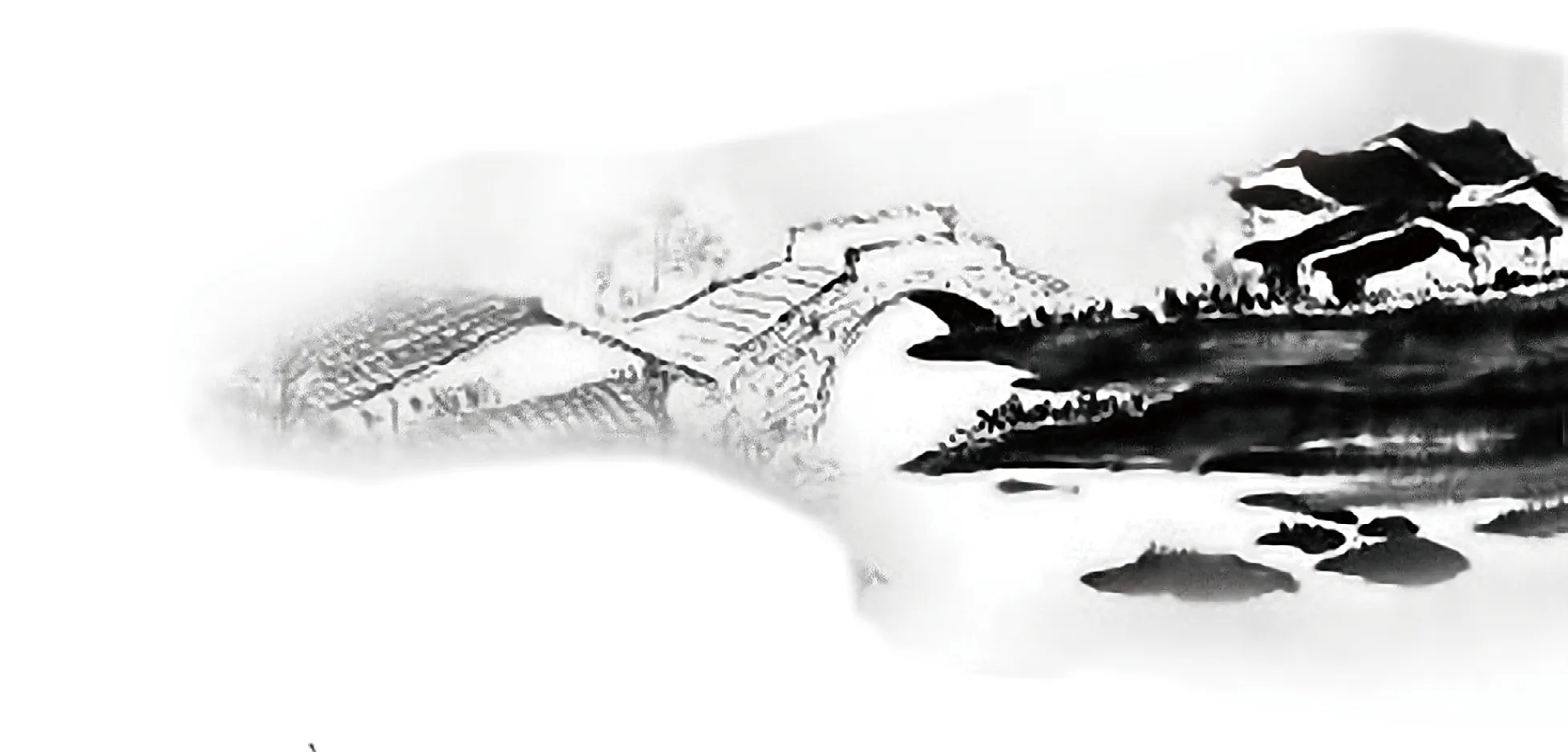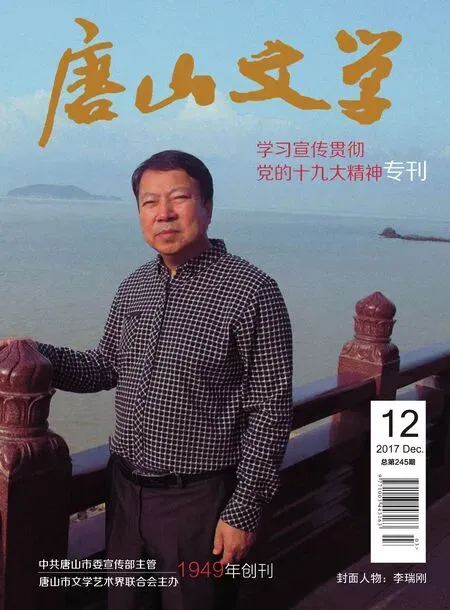社會主義文學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文學黨性原則
楊立元 楊春
社會主義文學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文學黨性原則
楊立元 楊春
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黨性學說在文藝領域中的貫徹和體現。它是社會主義時代作家創作的審美規范和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學的總的指導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是發展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在一個時期內,文學的黨性原則被淡化和削弱了。文壇上戳起的五光十色的旗幟掩蓋了文學的黨性原則當作庸俗社會學加以否定。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無可回避的命題:社會主義文學還要不要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文學的黨性原則是文學發展的桎梏,還是必須遵循的審美原則?對此,需要我們作出正確的回答。
社會主義文學必須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社會主義文學與其他階級文學的根本區別在于,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的,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作為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思想武器的。在對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審美觀照和藝術把握中,只有借助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透過生活表象,正確地揭示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規律,使文學達到歷史真實性和客觀真理性的高度統一。
今天,我們有必要站在時代高度,用歷史的眼光和現代意識,重新審視無產階級黨性原則的產生、發展以及在新時期的重要作用,以便對其做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判。
一、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中,為適應革命的需要,提出、發展并完善的,為無產階級的文藝工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和遵循的方向。
(一)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社會科學中的偉大革命,并為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中,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唯物史觀公諸于世。在馬克思、恩格斯多次闡明的唯物史觀中,不僅揭示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也科學地指出了文藝在社會結構中依存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經濟基礎的特殊地位。這一重大的科學發現,不僅揭示出文藝的本質及其產生和發展的規律,而且也科學地說明了文藝必然要成為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為無產階級把文藝作為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則提供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主張把文藝作為革命事業的一部分,認為文藝有巨大的社會改造意義,在階級斗爭和社會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審美作用。文藝作品通過“對現實關系的真實描寫”,可以“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主張“用最樸素的形式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1]在文藝服務的對象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文藝應描寫革命的人民群眾,特別是無產者。馬克思恩格斯批評了文學不表現無產者而專門歌頌“小人物”的傾向,主張文藝要表現先進的階級。馬克思指出:“農民和城市革命份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影。”[2]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希望通過“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寫表現“工人階級對他們四周的壓迫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甚至他還提出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革命的無產者”[3]。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已經提出了文藝要正確地表現工人階級,要正確地描寫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觀點。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文學的藝術性。馬克思指出作家在創作時要“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恩格斯認為,作品的思想和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4]。馬克思在總結了英國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不要“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而應該“更加莎士比亞化”[5]。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既強調文藝的傾向性,又特別要求藝術性,同時要求高度的藝術性與革命的傾向性的有機結合,黨性和審美性的完美統一。
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為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奠定了理論基礎,提出了文學黨性原則的雛形和最基本的內容。
(二)列寧對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理論的貢獻。
列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運用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學黨性學說的理論,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革命新時代的要求對文學的黨性原則,做了經典性的闡述,把文學的黨性原則發展為完整的形態,把文學的黨性問題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一偉大的經典性論文中,列寧深刻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反動腐朽的實質,尖銳地批評了所謂“無黨性”、“創作自由”的錯誤觀點,具體地闡述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他指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原則,發展這個原則,并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他精粹地歸結了文學黨性原則的兩個基本點:一是文學事業同黨的整個事業的關系問題,“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二是文學的服務對象問題,無產階級文學事業要“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他還認為無產階級政黨還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加強對文學的領導和監督。黨的領導和監督是實現兩個基本點的保證。列寧既規定了文學的性質,也解決了文學的服務對象問題。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進一步豐富了文學的黨性原則的內容,深刻地闡述了文學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和深化了文學為人民服務的原則。他說:“藝術屬于人民。它必須深深地扎根于廣大勞動群眾中間。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得到提高。它必須喚醒群眾中的藝術家并使之發展。”[6]列寧對文學的黨性原則的論述是對馬克思文藝理論的偉大貢獻,將馬克思主義文藝和美學理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三)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豐富和發展了列寧所規定的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
毛澤東同志從中國革命實際和文藝運動的具體實踐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美學思想和列寧的文學的黨性原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規定了正確的文藝方向,劃清了無產階級文學和資產階級文學的界限,解決了文藝的根本、原則的問題,即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
1.毛澤東同志重申了列寧提出的文學黨性原則的兩個基本點,并說明了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毛澤東同志把貫徹黨性原則的基本點視為“文藝運動中的”根本方向問題”。他在《講話》認為,我們“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做斗爭”。這就進一步明確了革命文藝工作和總的革命事業的關系。毛澤東同志更為具體地明確了“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干部”,要求“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還深刻地闡述了兩個基本點的內在聯系:一方面,整個革命事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另一方面,人民又是整個革命的領導力量的主力軍和參加者。即工人是“領導革命的階級”,農民是“革命的同盟者”,人民武裝是“革命戰爭的主力”,其他群眾則是“革命的同盟軍”。文學黨生原則的兩個基本點就是這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2.在黨如何領導、監督文藝實現這兩個基本點的問題上,毛澤東發展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同時也為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和繁榮指明了方向。
①黨要幫助作家解決為革命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問題。毛澤東特別強調作家的立場、作家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指示革命的文藝家應該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和進行創作。他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關鍵是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那么如何才能把立足點移到“這方面”來呢?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一方面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克服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所以,無產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實現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基礎和保證。同時,要學習魯迅,正確解決個人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②普及與提高的正確結合是達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目的的主要途徑。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上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的思想,指出了只有通過普及與提高正確結合的途徑才能達到為工農兵服務的目的。他首先明確了普及與提高的基礎“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普及”、“提高”。并規定了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并解決了普及與提高的方向問題,即“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和“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普及”、“提高”。
③引導作家認識社會生活與文學的辯證關系,掌握生活美轉化為藝術美的規律。
毛澤東同志具體地闡述了作家如何創造具有高度黨性的作品。首先是作家必須深入社會生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同時“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其次是作家審美情感的轉變和世界觀的改變。在生活積累的基礎上注意感情的積累,與工農兵有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語言。再次是生活美轉化為藝術美還必須對社會生活進行典型化,才能創作出“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的作品。除此之外,還要批判地繼承中外優秀文學遺產,解決好源和流的問題。
④建立文藝的統一戰線,團結可以團結的各種文藝工作者,堅持黨性和團結多數的一致性。為了擴大革命隊伍,調動文藝界的一切積極因素,更好地配合各個階段的革命任務。“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線上來。”
⑤開展文藝批評,通過文藝批評,開展文藝界的思想斗爭,來保證文學的黨性原則的實行。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他認為“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并提出了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并對這兩個標準以及兩者的關系做了明確的界說,正確、科學的規定。“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為了達到這個審美要求,要反對兩種傾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這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理論,有效地保證了文學黨性原則的實現。
(四)鄧小平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清算了“四人幫”的罪行,恢復、堅持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同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新時期文藝戰線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堅持應用和完善、充實了文學的黨性原則。
1、鄧小平同志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提出了文藝同整個革命事業的關系和文藝同人民關系的新內容。
①文藝要為四化建設服務。他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斗爭。要批判剝削階級思想和小生產守舊狹隘的心理的影響,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克服官僚主義。要恢復和發揚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培養和樹立優良的道德風尚,為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積極的貢獻。”[10]
②文藝要為人民服務。他說:“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11]這兩個基本點是鄧小平同志為黨中央制定“二為”的文藝方針所提供的理論依據和具體內容。這明確地指出了新時期的文學是社會主義的文學,社會主義的文學屬于人民。決定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
2、在黨如何領導文藝貫徹文學的黨性原則的兩個基本點方面,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藝思想。
①為社會主義文藝指出了一條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這就是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他指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12]
②為文藝制定了防止走“自由化”道路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批判了文藝界一些人宣揚“自我表現”,“一切向錢看”和無鑒別吸收西方文化的傾向,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更加繁榮昌盛的新局面”的“出現”提供了可靠的保證。[13]
③為防止文藝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指導作家在藝術上更加豐富自己,提出了文學藝術典型化的審美原則。在內容上,“要塑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創業者,表現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通過這些“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并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形式上,“文藝工作者還要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藝術形式”[14]。
④提出黨要按文藝特征和文藝發展規律來領導文藝。在黨對文藝的領導與監督問題上,黨組織既要加強領導,敢于領導;又要宏觀領導,把握大局。黨組織“要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來領導文藝,要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的條件。“要從各個方面,包括物質條件方面,保證文藝工作者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領導作風上,要發揚藝術民主,“衙門作風必須拋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要“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15]。
鄧小平的文藝思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的有力武器和指針,也是文學的黨性原則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發揮和發展。
(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習近平同志對無產階級文學黨性原則的繼承和發展
在進入新世紀以后,習近平結合文學發展形勢的需要,繼承和發展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他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新成果、新發展,深刻闡述了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為新的時代條件下做好文藝工作劃定了基本遵循的價值航向。
1.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創作原則。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命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根本命題及美學基石,也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常說常新的理論話題,對《講話》這條黨性原則進行了系統闡釋,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三個層次論述了人民與文藝的關系及其時代內涵。他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習近平強調:“有沒有感情,對誰有感情,決定著文藝創作的命運。”文藝工作者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做人民的孺子牛。文藝源于人民,為了人民,文藝作品的優劣也只能由人民來評判。“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人民需要文藝,文藝更需要人民。人民的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人民是文藝表現的主體、文藝服務的主體,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的憂樂傾注于筆端,是文藝家的神圣職責和歷史使命。
2.要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堅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那么如何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呢?《講話》指出:“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把握住兩條:一是要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各級黨委要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高度,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把文藝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貫徹好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把握文藝發展正確方向。”
3.指出優秀文藝作品的審美標準。《講話》指出: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作品“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秀作品”,“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秀作品。”這樣的作品,必須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好的作品應該是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4.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批評標準。《講話》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批評標準,要“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這是文藝批評的最高標準和最高境界,是提高審美的重要力量,是解剖文藝真相的“利器”,是引導的“方向盤”。“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
5.完善繼承與發展的關系。《講話》指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堅持和弘揚中國精神,并不排斥學習借鑒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繁榮發展起來,必須認真學習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藝。只有堅持洋為中用、開拓創新,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我國文藝才能更好發展繁榮起來。”
二、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是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學的正確原則,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文學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文學的黨性原則隨著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深入而誕生,并由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而豐富發展。它是人類最先進的文學——社會主義文學的指導原則。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產生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和眾多有成就的作家,對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100多年來的文學實踐證明,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是正確的原則。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的學說,對建立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學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奠定了社會主義文學的理論基礎和基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對最初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予以深切的期望和指導,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涌現了許多著名的革命詩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喬治·維爾特的詩歌被恩格斯稱贊為“社會主義和政治的詩歌”[7]。德國詩人海涅的《西里西亞織工之歌》,被恩格斯推崇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詩歌之一”,[8]因為它是“宣傳社會主義的”[9]。偉大的巴黎公社運動產生了第一批社會主義詩歌。偉大的無產階級歌手歐仁、鮑狄埃創作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國際歌》,為文學服務于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提供了光輝的范例。這些詩歌以全新的內容和飽滿的激情,鼓舞了千百萬無產者,開創了社會主義文學實踐的新路。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發表以后,社會主義文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代。列寧發展了文學的黨性原則,把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灌注到文學工作中,把文學改造成為一種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崇高的事業,成為整個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事業的一部分,為無產階級革命和推翻舊制度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社會主義文學也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它從原來被壓制、被排斥的地位上升為文學的主流,代表了文學發展的方向。高爾基的《母親》,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好》,法捷耶夫的《毀滅》《青年近衛軍》,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懇的處女地》《靜靜的頓河》,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作品,在世界各國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其主流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循著文學黨性原則的基本點發展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而不僅僅是在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后才出現了具有黨性的文學作品。我們認為凡是具備如下條件的文學作品都可以歸為具有黨性的文學作品。其一,符合人類歷史進步潮流,與社會發展趨勢相致的作品。其二,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和利益要求的文藝作品。其三,具有進行傾向和較高藝術性的作品。如魯迅的文學作品,他自稱其作品是“遵命文學”。他是遵了先進階級和人民的命,以其為“匕首”、“投槍”刺向反動階級的營壘。又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駱駝祥子》等小說都形象地顯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本質,揭示了黑暗社會的腐朽,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發表以后,極大地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發展。一大批革命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兵群眾和火熱的生活斗爭中去,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如《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作品,使文學的黨性與人民性、藝術性緊密融合,使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文學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全新時代。
(二)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文學仍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1.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以后,在文學黨性原則的指導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品。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的文學仍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是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必須堅持的普遍真理,也是衡量社會主義文藝成就的重要尺度。廣大作家遵循文學的黨性原則,以高度的革命激情參與偉大的歷史變革,不斷改變和調整創作心態,創作出了一大批代表著我國社會主義文學成就的作品,如小說《紅旗譜》《紅巖》《紅日》《李自成》(第一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山鄉巨變》《創業史》等,戲劇《關漢卿》《蔡文姬》《霓虹燈下的哨兵》《茶館》等,電影《林則徐》《我們村的年青人》《小兵張嗄》等,詩歌《雷鋒之歌》《復仇的火焰》《致青年公民》等都以昂揚的革命激情,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革命斗爭,塑造了閃耀著共產主義理想光輝的社會主義新人和無產階級英雄的形象,極大地鼓舞和推動了人們為社會主義事業而斗爭,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要,使文學事業成為黨所領導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事業。
2.10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幫”閹割篡改了文學的黨性原則,把黨性原則兩個基本點篡改為批判走資派、篡黨奪權和為他們樹碑立傳服務,造成了文藝界百花凋零的局面。把“文藝為政治服務”發展到極致,直接為他們的政治陰謀服務,在文壇上所充斥的是“陰謀文藝”,這就從反面證明了離開文學的黨性原則就會導致社會主義文學的毀滅。
3.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文學的黨性原則仍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文藝服務的對象更加擴大和廣泛,社會主義文學的內容也愈加豐富和多樣。“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提出,是文學的黨性原則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主義文學蓬勃發展的前提條件。“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突破了“樣板化”、“統一化”的創作模式,豐富性、多樣化成為新時期文學繁榮的審美特征。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拓寬了新時期文學的審美領域,塑造了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表現了富于現實意義和現代意識的主題。在藝術形式上,作家們不斷創新求變,從千篇一律板結狀的藝術模式和固定化的美學規范中掙脫出來,導致了審美范疇和藝術表現方式的不斷豐富和擴大,在藝術上呈現出不斷流變、多元互補和百花齊放的新格局。出現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塵埃落定》《抉擇》《長恨歌》《人民的名義》《天行者》等符合黨性原則的作品,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文學的發展。
三、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必須在文藝戰線開
展同各種錯誤傾向的斗爭。
社會主義文學是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時時刻刻都不能離開黨的領導。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證明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文學就進步、發展;離開了文學的黨性原則,文學就退步、蛻變。因此,在文藝戰線必須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對各種錯誤傾向加以抵制和批判。
1.在思想上,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做斗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在文藝領域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了重要的指示,對新時期文藝運動的經驗和前進中面臨的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科學的回答。但在一個時期內,由于當時的黨內負責同志主張“少干預,少介入”,放棄了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導致了文藝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自由化思潮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宣揚文學黨性原則“陳舊”、“過時”,否定文學的黨性原則。有人主張文學脫離人民,表現自我,實現個體生命價值;鼓吹文學脫離社會生活,切斷文學的“外部聯系”,讓“文學回歸自身”。這實質上是使文藝脫離為社會主義服務,脫離為人民服務,即脫離了文學的黨性原則。這樣使得一些作家遠離生活,走進了“象牙之塔”,爭當“精神貴族”;一些作家超脫現實迷戀于靈感和幻覺,面壁虛構,揚言為“下世紀人創作”;一些作家丟棄了文學的神圣,主張“玩文學”,在藝術的死胡同里欣賞陶醉;一些作家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自翔為“精英”,投入了國外反動勢力的懷抱。所以,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為指導,堅持文學的黨性原則,旗幟鮮明地展開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批判,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指導地位,促使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健康發展。
2.在藝術上,同粗制濫造,忽視藝術性的傾向進行斗爭。在一個時期內,一些作家在創作思想和實踐上放棄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丟棄了文藝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不講社會效益和社會責任感,不講藝術質量和藝術良心,使作品脫離、違背了人民大眾的審美需求,造成了背離社會發展的逆反狀態。在文學神圣的殿堂中所充斥的是宣揚色情淫穢、怪誕晦澀、兇殺暴力、封建迷信、庸俗低級的作品,使社會主義文學遭受了嚴重的沖擊。
其一、商品價值的沖擊。商品價值的沖擊使文學神圣化情感倒伏,使藝術品滑向商品,藝術價值被商品價值所覆蓋,藝術屬性商品屬性所取代,藝術創作規律被商品價值規律所滲透,藝術原則被商品原則所同化、軟化。一些作家以商品價值為創作取向,胡編亂寫,杜撰虛構。一些國家辦的刊物自負盈虧,慘淡經營,結果是逼良為娼,以求生存。更為痛心的是過去是由黨的宣傳部門把關的文學刊物有的一度竟由個體出版商定稿。這樣,文學的黨性原則也被商品化閹割了。
其二,通俗文學的沖擊。隨著改革開放,通俗文學應運而生。但一些作家淡化作品的嚴肅性,強調消遣性,忽視審美功隨,強調渲泄功能,所表現的內容不是床頭就是拳頭,使通俗文學成了庸俗文學,使文學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這些作品對讀者的審美心理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它潛移默化地改變著讀者的文化接受機制,降低了精神需求的品位,轉移了讀者的審美趣味,造成了文藝生態平衡的嚴重混亂和傾斜。
正是文藝的內外沖擊導致了作家審美心態的萎靡,讀者審美期待的疲軟以及文學內在精神的虛脫。削弱了社會主義文學的主旋律,窒息了文藝的生機和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這就為我們同各種不正確的創作傾向進行批評指明了方向,以便為人民創作出更美更好的作品來。
注釋:
[1]《馬克思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
[2]《〈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頁。
[3]《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頁。
[4]《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頁。
[5]《馬克思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
[6]克·蔡特金:《列寧印象記》,《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頁。
[7]恩格斯:《論喬治·維爾特》,《譯文》1965年8月號,第141頁。
[8][9]《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92頁,第93頁,
[10][11]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12]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頁。
[13]《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83~89頁。
[14]《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頁。
[15]《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頁。
楊立元,唐山師范學院教授(二級),碩士研究生導師,唐山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長期從事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工作。
楊春,唐山師范學院講師,碩士,從事唐山文化和體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