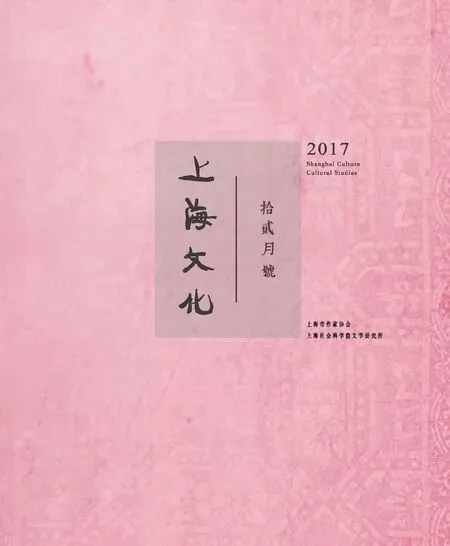陳鳴樹學案
符杰祥 黃喬飛
陳鳴樹學案
符杰祥 黃喬飛*
陳鳴樹先生為中國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專家、魯迅研究專家、文藝學研究專家。作為新中國學界的新生力量,其早期的魯迅研究文章可謂一個時代曲折艱難的見證。新時期以來,他高屋建瓴,視野寬廣,在繼續推出眾多魯迅研究成果的同時,亦在文藝學方法論領域先后提出兩極否定性原理、對應性原理等系列首創性概念,出色完成了一種跨學科、跨領域的開拓性探索。陳先生成就斐然,得益于他豐盛的文藝才情、深厚的理論修養與嚴謹的治學精神。無論何時,他的文章總能追隨時代,也總能超越時代。
陳鳴樹 魯迅研究 文藝學 方法論
陳鳴樹(1931—2014年),筆名澡雪,江蘇蘇州人。中國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專家、魯迅研究專家、文藝學研究專家。作為新中國學界的新生力量,其早期的魯迅研究文章可謂一個時代曲折艱難的見證。新時期以來,陳鳴樹高屋建瓴,視野寬廣,在繼續推出眾多魯迅研究成果的同時,亦在文藝學方法論領域先后提出兩極否定性原理、對應性原理等系列首創性概念,出色完成了一種跨學科、跨領域的開拓性探索。陳鳴樹在20世紀90年代主持編寫了《20世紀中國文學大典》,該著是20世紀學術史料整理工程的典型展現。除此之外,陳鳴樹在中國繪畫創作及理論研究上也頗有造詣,灑脫自由的筆力與深厚沉潛的學識相輔相成,水墨丹青亦可自成一家。
一
陳鳴樹先生于1931年10月,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市一個破落商戶家庭。早年喪父,因家貧中途被迫輟學。
1936年6歲,從報紙上剪下魯迅先生出殯時的畫像,以硬紙板粘貼放在床頭,畫像中“中國文壇巨子”的字樣為其早熟的心靈開啟了一扇啟蒙的窗戶,從而結下一生同魯迅的緣分。
1949年前夕,任工廠學徒。從工廠老工人手中獲得《魯迅自選集》,開始了其自學歷程。
1949年19歲,曾在蘇州公安局等部門服務。其間因病在市府機關干部療養所休養,廣泛閱讀文學書籍,并以《魯迅全集》作為重點研讀對象。
1954年24歲,結識江蘇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朱彤先生,在其鼓勵下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隨后。于1955年在《文藝月報》上發表了長文《評許杰的反現實主義的“小說論”——關于〈魯迅小說講話〉的文藝理論部分》。
1955年25歲,因表現突出,被指定為新中國學術界的“新生力量”,受到中宣部領導垂訪。之后被調入蘇州文聯,擔任執行委員兼秘書,同時擔任江蘇省文聯委員,華東作家協會會員(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后調至江蘇省《雨花》編輯部,負責理論組的工作。
同年,通過應試成為李何林教授的第一屆副博士研究生,主攻魯迅研究。李何林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對他的影響頗為深遠。
1956年26歲,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聽取周恩來、胡耀邦的報告,并加入上海作協,與唐弢結識,并自許為其私淑弟子。
1959年29歲,在副博士研究生在讀期間,陳鳴樹出版了其第一本專著《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該著是政治運動的典型產物。
同年,《論魯迅小說的藝術方法及其演變》在《上海文學》連載3期,受到王元化先生的贊賞,并推薦給籌拍《魯迅傳》的主角趙丹閱讀。上海文藝出版社文藝理論室周天寫信鼓勵其拓展成書,但最終并未落實。
1961年31歲,調入上海作協文學研究所。
“文革”期間,受到政治沖擊的陳鳴樹編寫了一本《魯迅的批儒反孔斗爭》,同時因身體狀況不佳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家協會看守大門,免于下鄉勞動改造。
1975年45歲,經李何林教授提名,調至北京魯迅研究室參與《魯迅年譜》的編寫工作。
1976年46歲,完成《論魯迅小說的典型化》一文,總計4萬字,分兩期發表于剛創刊的《社會科學戰線》上。自此,其學術道路回到正軌。
1977年47歲,陳鳴樹主動申請從北京調離,進入復旦大學任教。先在歷史系中國思想史研究室擔任蔡尚思先生的助手。在此期間發表文章《論魯迅“五四”時期的思想》,從思想史脈絡梳理魯迅的精神氣質。隨后在校黨委書記夏征農的建議下,在中文系成立魯迅研究室,后改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室,陳鳴樹在此擔任主任直至退休。
1981年51歲,出版魯迅研究代表作《魯迅小說論稿》(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年52歲,出版普及性質的《魯迅雜文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4年54歲,出版魯迅研究論文集《魯迅的思想和藝術》(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55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發表《魯迅研究史上的豐碩成果——三本魯迅專著的學習札記》。
1986年56歲,在《學術月刊》第10期發表論文《魯迅:中西文化沖突中的選擇》,該文在上海市紀念魯迅逝世50周年大會上宣讀,并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成果獎。
80年代末期,陳鳴樹在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進修素描。
90年代初期,與著名作家王小鷹拜國畫名家王康樂為師。
1991年61歲,在魯迅誕生110周年之際發表《論魯迅的智慧》一文,在《文化報》《魯迅研究月刊》《魯迅研究年刊》等多處轉載。
同年,《文藝學方法概論》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4年64歲,主編完成《20世紀中國文學大典》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同年,《現象學美學方法述評》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成果獎。
1996年66歲,《浩氣千秋民族之魂——紀念魯迅逝世60周年論文集》收錄其文章《20世紀初期魯迅的人文精神》。
2004年74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文藝學方法論》(第二版)。
2011年81歲,由上海魯迅紀念館和復旦大學出版社共同發起“《魯迅論集》首發式暨陳鳴樹教授80華誕慶祝會”,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召開。
2014年84歲,7月18日因病于上海逝世。
二
陳鳴樹年少成名,24歲便于《人民日報》發表了其關于魯迅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此后,他相繼編撰完成了14部學術著作,可謂成果豐碩。縱觀其學術發展脈絡,大體可以劃分為兩大領域和4個時期。兩大領域集中于魯迅研究和文藝學方法論研究;4個時期主要指50年代的成長期、60—70年代的沉寂期、80年代的高峰期、90年代以后的拓展期。
在1959年的特殊年月,尚在南開大學讀書的陳鳴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專著《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該書無可避免地具有政治運動的時代印痕,對此,陳鳴樹并不諱言,著文明確表示“悔其少作”,晚年也一直堅持自我批判。與巴金的《隨感錄》一樣,不回避歷史污穢的文字,反而能呈現出人格的高潔。但同時,書中亦不乏將魯迅文學自覺放置于審美維度上進行觀照的精美篇章,尤其是魯迅與拜倫的比較研究、魯迅與兒童文學的譯介研究,無論是文風還是觀念,對政治禁錮嚴峻的年代來說已是難能可貴的學術突破。在“文革”前后的極端年代,陷入沉寂期的陳鳴樹也在革命文化自我消解的大潮裹挾之下,編寫過兩本《魯迅批孔雜文選講》(1975年)、《魯迅批孔反儒的斗爭》(1976年)小冊子。
新時期以來,陳鳴樹的魯迅研究也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回歸正軌,完成了一系列魯迅研究成果,成績卓著。出版的著作包括《魯迅小說論稿》(1981年)、《魯迅雜文札記》(1982年)、《魯迅的思想和藝術》(1984年)。同時,作為年譜組召集人參與了《魯迅年譜》(1984年)的編撰工作。陳鳴樹的學術研究一方面注重對史料的征引發掘,一方面又保持著闊達的知識理念。從魯迅小說到魯迅雜文,再到魯迅思想和藝術價值,陳鳴樹通過一系列論著,將個人對魯迅的認知構建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些論著,擺脫了5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庸俗社會學的桎梏,顯示著新時代的思想深度與學術高度。在這其中,陳鳴樹關于魯迅小說典型化及藝術辯證法,魯迅美學思想與思想史地位、魯迅在中西文化沖突中的抉擇與中國主體性問題的探討,高瞻遠矚,思辨縝密,可謂巔峰之作。
在文藝學領域,陳鳴樹的專著有《文藝學方法概論》(1991年)和《文藝學方法論》(2004年)。《文藝學方法論》在2004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在修訂1991年《文藝學方法概論》的基礎上完成的。書中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文藝學方法論的原理與實踐問題,共分為三部分。上篇為“方法論:原理”,具體闡述了研究方法的對應性和兩極否定性原理、層次性原理、互補性原理;中篇為“方法論:中國與世界”,介紹并分析了社會學、心理學、新批評、原型批評、解構主義等10余種方法及其優劣;下篇為“方法論:實踐功能”,重點關注的是文藝學方法中的發現機制、資料的實證性與思維的超越性、理論框架的構建原理等問題。三部分由原理而實踐,并不滿足于西方理論的譯介,其中三大原理、三大功能,是陳鳴樹獨具創建的理論提升與學術歸納,顯示出其深厚的文史哲修養與中國問題意識。
90年代以后,陳鳴樹的學術思想基本成型,其主要的工作集中于學術思想的整合梳理。1994年,由陳鳴樹主持編寫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典》出版發行,這是20世紀學術史料整理工程的重要成果。2011年,《魯迅論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發行,該書收入了陳鳴樹不同時期魯迅研究的學術文章,既是一種個人研究成果的整理,也是一種魯迅研究史的總結。
90年代末至21世紀,陳鳴樹興趣轉移,重心移至書畫藝術,在中國繪畫創作和研究方面也頗有成績。陳鳴樹的生平事跡先后入選英國劍橋傳記中心《世界知識分子名人錄》《杰出的人》,美國傳記學會《世界5000名人錄》及國內《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多種辭書。
三
從50年代以魯迅研究年少成名,到新世紀結集出版《魯迅論集》,陳鳴樹畢生的魯迅研究,或起或伏,或興或止,貫穿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從歷史意義上說,陳鳴樹輾轉于不同時代的魯迅研究,可謂當代中國文化政治演變的縮影,也可謂當代中國學術發展曲折艱難的見證。
在陳鳴樹最早的著作《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中,包含有許多大批判文章,這無疑是政治運動裹挾中的產物。個人終究無法跳出時代的限制。就此而論,本書的局限,也是時代的局限;個人的學術悲劇,也是時代的學術悲劇。但同時,在一種時代的扭曲生長中,陳鳴樹的早期著作也顯示出無法壓抑的學術才華。在《論魯迅初期美學思想》一文中,陳鳴樹結合神話的溯源理論探索魯迅創作的審美源頭,對魯迅文學中“涵養人之神思”的美學情懷給予了高度關注。同時,他對魯迅筆下“溫煦”與“剛健”美學特質的提煉,深入肌理,部分超越了階級話語的刻板描述。新世紀以來,郜元寶的《魯迅六講》以對魯迅早期文章中的“神思”“白心”等概念的精彩闡發而備受贊譽,堪稱經典。對照陳鳴樹在思想高度統制時代對魯迅美學思想的艱難探索,其才華的敏銳與埋沒,不能不讓人心生感慨。
書中另一篇文章《魯迅與拜倫》亦值得注意。世界性的比較眼光、影響研究的范式,在這部早期著作中已有所體現。陳鳴樹探究的問題是:魯迅如何吸收拜倫的積極抗爭思想,并將其熔鑄在自己的精神品質和文學創作之中。他發現了拜倫式英雄反抗強力的高傲精神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心靈共鳴,指出拜倫與魯迅共同的反叛熱情不在于侵略弱小,而是“一方面擯斥侵略政策,一方面反對不抵抗主義”。①陳鳴樹:《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9年,第283頁。陳鳴樹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跨文化語境下魯迅的主體性特質。這是國內第一篇魯迅與拜倫的研究文章,這樣的發現無疑也是具有開創性的。在國外,較早研究魯迅與拜倫關系的是日本學者北岡正子,其首篇《〈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筆記》直到1972年10月才刊載于《野草》第9號上。其后,日本學者藤井省三發現了安德烈耶夫對魯迅和夏目漱石創作的影響,并認為魯迅關于拜倫的材源除了木村鷹太郎的《拜倫——文藝界之大魔王》之外,還受到了詩劇《該隱》中惡魔的影響。不過,這一研究也是遲至1985年才在《俄羅斯之影》上發表出來。就此而言,陳鳴樹的比較研究,即便在世界范圍內,也具有首創意義。再如《魯迅與兒童文學》一文,亦有先行性的價值。陳鳴樹較早將文學譯介引入研究范疇,發現魯迅在兒童文學譯介中并未堅持其一貫堅持的“硬譯”主張,這種差異與矛盾,其實是體現了“救救孩子”的熱愛與關懷的。
陳鳴樹在魯迅研究中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戰斗情懷和“保衛魯迅”的極大熱忱,這其中有政治語境的印痕,也有導師李何林學術精神的引導。在近60年的學術生涯中,李何林始終堅持“五四”新文學的戰斗傳統,矢志不渝地發揚魯迅精神。對李何林來說,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巨大的精神符號,既是研究對象,也是學術信仰。在兩部早期論著《中國文藝論戰》(1929年)和《魯迅論》(1930年)中,李何林即流露出鮮明的愛憎與是非,“保衛魯迅”的立場同時也形成了其最為突出的兩種學術特征:魯迅視點和論戰思維。在30年代,李何林曾公開發表兩篇論戰文章:《葉公超教授對魯迅的謾罵》與《為〈悼念魯迅先生〉——對大公報“短評”記者及其儕輩的憤言》,這在當時引起了極大轟動。在1939年出版的《近20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一書中,李何林更是言辭激烈地聲討了左翼陣營中的小團體作風,并將魯迅作為革命陣營的“代言人”,突出其至高地位。同樣,李何林在1959年發表的《十年來文藝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一文,也是因為堅持魯迅傳統而遭到批判。
《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一書中批判性的文風及充滿戰斗性的內容與李何林一脈相承。正如陳鳴樹在《李何林教授對魯迅研究的貢獻——為祝賀先生八十壽辰作》一文中所言:“先生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不計個人利害,以精衛填海的精神,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著、戰斗著、生活著。這也是先生的精神最令人感動、最值得后學師法的地方。”①陳鳴樹:《李何林教授對魯迅研究的貢獻》 ,《南開學報》1984年第5期。不過,陳鳴樹在早期的研究中僅僅關注到魯迅戰斗精神與政治語境中斗爭意志同構的表象,而沒有關注到其背后概念的替換以及政治掌控文學的問題所在。在這一點上,時為學生的他尚缺乏李何林更具前瞻性的問題意識與相對獨立的懷疑精神。這一時期的學術文章,許多是盲從政治運動的跟風書寫,理念化、口號化的意識形態色彩過于濃厚。在政治斗爭的糾纏與裹挾中,青年陳鳴樹并沒有完全擺脫時代的政治束縛,甚至迷失其中。在恩寵有加的鼓勵之中,他的文藝才華被彎曲與利用了。比如批判馮雪峰的那篇《一個個人主義心目中的魯迅》,就是在周揚的授意和葉以群的指派之下寫出來的。即便是在論述魯迅與拜倫關系這樣出色的文章中,陳鳴樹也存在諸多缺陷。比如認為魯迅筆下“孤獨者”失敗的原因是個人主義者的自我毀滅,而忽略了魯迅對拜倫式英雄的同情與贊美,這是以意識形態的偏見,遮蔽了魯迅文章自身的光華。
魯迅研究被意識形態所主導,甚至淪為一種政治斗爭的工具,是學人個體的迷失,也是時代集體的迷失。陳鳴樹有著超越于時代的才華,敏銳的學術觀察力使他能夠突破時代,發現文學的“人學”特性。1961年完成的《論魯迅小說的藝術方法及其演變》一文,是一篇代表性力作,因而得到王元化的贊賞和推崇。在高壓環境中,沒有人能夠確保自身不被異化,在異化的時代里保有最后一點人性之光,都是難能可貴的。在那個狂熱的年代,陳鳴樹的學術道路艱難而扭曲。一方面,被政治運動消磨了才華與熱情;另一方面,那難以扭曲或未曾消磨的一部分,也保留了政治風暴中最后一點學術才情與人格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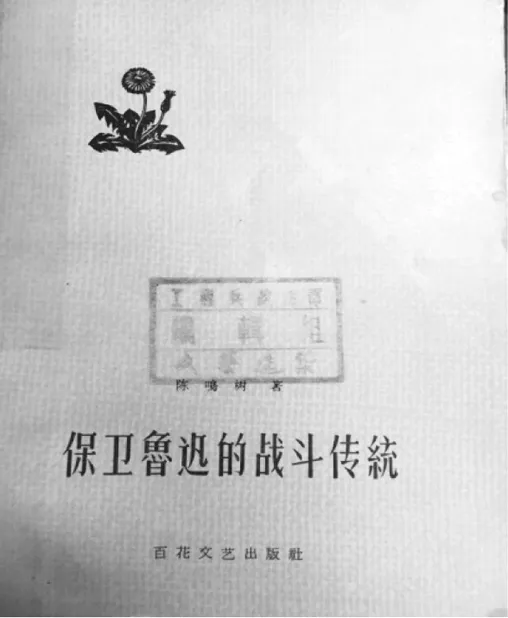
圖1 《保衛魯迅的戰斗傳統》
四
“文革”之后,陳鳴樹的學術研究逐漸回到正軌。1981年,他的《魯迅小說論稿》出版,有評價說:“它相當全面地觸及了魯迅小說的各個方面,自成系統,而且在體例上,兼得論文之深入與專著之系統兩方面之長。”①滕云:《對魯迅小說進行綜合研究的一本新著——評陳先生〈魯迅小說論稿〉》,《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該書在前人的基礎上,以更為嚴密的論證邏輯、更為深入的文思,構建了具有個人氣質的研究體系。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綜合研究法的運用。
綜合研究法最早的提出者是王元化。針對80年代譯介西方思潮中急功近利的理論熱與方法熱,王元化明確指出應當堅持“古今結合、中西結合、文史哲結合”。陳鳴樹吸收了其綜合思想的精華,在《魯迅小說論稿》中,他構建了兩組嵌套結合的分析模式。
其一,歷史視野。他將魯迅小說創作放置于宏觀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進程中,探索文本間的內在聯系。比如在探討《吶喊》和《彷徨》這兩本小說集時,他沒有將文本中農民命運的凄苦、知識分子的彷徨、革命青年的無助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而是將文本內容與時代特質相結合,創作風格與藝術方法相參照,從中得出的結論不是單面割裂的片段化呈現,而是具有史學視野的開放性總結。在《論魯迅小說的藝術辯證法》一文中,他認為:“魯迅小說的藝術方法的演變,正是標志著‘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向社會主義文學過渡的光輝范例;也就是帶有新民主主義革命色彩的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以及這兩者相結合的藝術方法,向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方法過渡的光輝范例。”②陳鳴樹:《魯迅小說論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37-138頁。這樣一種提法,讓我們關注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發端問題,是審美感受和理性邏輯相結合的產物。
其二,世界眼光。陳鳴樹關注的是魯迅將民族主體性與外來“新主義”相結合的辯證思考。書中提到:“他一刻也不離開中國的現實去思考‘新主義’。他特別著眼于中國人怎樣去接受‘新主義’。”①陳鳴樹:《魯迅小說論稿》,第7頁。陳鳴樹發現,魯迅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內省。魯迅贊頌俄國人民迎來新世紀的曙光,出發點不是以“新主義”作為全盤吸收的對象,而是借此反思中國的國民性問題。在陳鳴樹的論述中,魯迅看到了未來的光明,但并沒有脫離現實。再如解讀《理水》時,陳鳴樹發現,魯迅所塑造的大禹不再是個人式的英雄,而是有一群同向同心的伙伴,這顯示了魯迅晚年回歸本土、探求民族內部原生力量的一種新傾向。內外兩套分析模式相互融合,使得《魯迅小說論稿》突破傳統的文本解讀,走向更為圓融的綜合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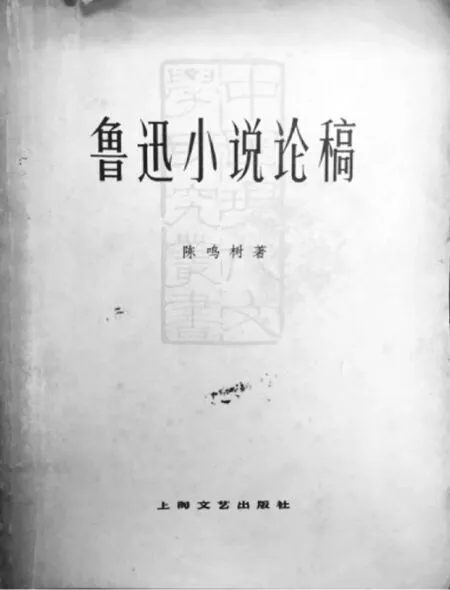
圖2 《魯迅小說論稿》
在80年代“解放思想”的啟蒙思潮中,李何林的另一位弟子王富仁教授率先提出“回到魯迅那里去”,可謂當時最響亮的啟蒙號角。陳鳴樹在1982年出版了新著《魯迅雜文札記》,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對回歸魯迅本體的一種南北呼應。《魯迅雜文札記》有意擺脫多年來將魯迅作為注腳的意識形態化表述,對過去的固有概念和陳腐的思維模式亦有所反撥。在書中,陳鳴樹概括了魯迅雜文的四大重要特質:“一、總結了革命斗爭的經驗;二、映照出‘時代的眉目’的‘史詩’;三、描述社會風貌和心理特征;四、參與文化思想的斗爭。”②陳鳴樹:《魯迅雜文札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2頁。同時,本書從文學史的意義揭示了魯迅雜文的諸多創造性,諸如古典散文與史筆傳統的發揚,史論、隨想錄、漫筆、日記、絮語等眾多形式的文體創新,文白雜糅、莊諧兼具等語體風格的原創等。這些研究和總結,極大地豐富了魯迅雜文研究的維度,從文體到筆法都進行了全面而自覺的歷史回溯。但正如他本人所言,限于普及性質,“這些概括,還不免皮相”,部分論述點到為止,尚待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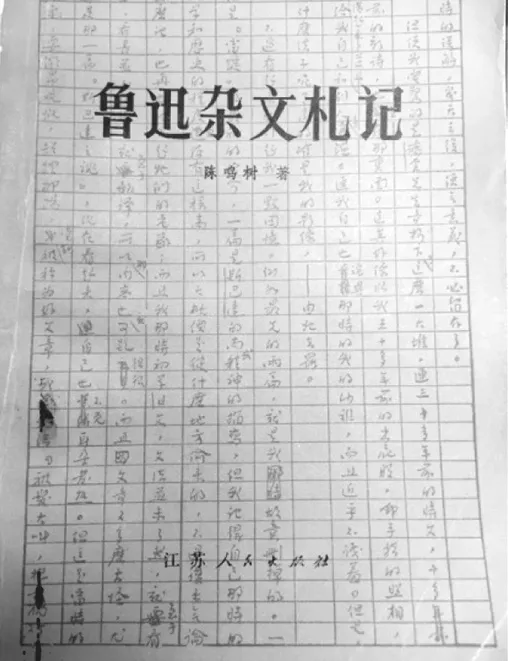
圖3 《魯迅雜文札記》
90年代以來,陳鳴樹的學術興趣發生轉移,但魯迅研究仍是其重心所在。相比于80年代的系列論著,這一時期并不高產,但思想更為成熟,視野也更為開闊。計劃中的《魯迅智慧論》無暇完成,但相繼發表了《論魯迅的智慧》《論魯迅初期的美學思想》《論魯迅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論魯迅的辯證法思想研究提綱》《魯迅:中西文化沖突中的選擇》等系列文章,皆立論高遠,視野宏闊。其中所提出的種種創見,如魯迅的智慧學、魯迅的“神思”說、魯迅的“中間物”等命題,高屋建瓴,洞幽燭微,眼光獨到,思辨深刻,對推動魯迅研究的深入發展,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王吉鵬等在2004年出版《魯迅的智慧》一書,便直言是在陳鳴樹《論魯迅的智慧》一文啟發之下完成的。如前所論,青年學者郜元寶教授在新世紀出版的《魯迅六講》,其中關于心學與神思的大力闡發,亦有陳鳴樹早年《論魯迅初期的美學思想》一文的觀點閃爍與思想呼應。
2011年,復旦大學出版社為陳鳴樹出版了72萬字的《魯迅論集》,陳鳴樹自視為“告別人生,謝奠學術”的“封筆之作”。①楊劍龍:《思想史、文學史視域中的獨特建樹——讀陳鳴樹先生的〈魯迅論集〉》,《上海魯迅研究》2012年第3期。這本書是陳鳴樹魯迅研究成果的完整結集,也是畢生心血的最后凝結。在評述魯迅的文化思想時,陳鳴樹曾指出:“如果說,魯迅在文化選擇上,早期有一種‘返顧舊鄉’的尋根意識,中期還有一種由返激力所引動的急遽心態,那么,在后期,就顯得從容周詳,應付裕如,完滿地體現了理性認知的主體意識。”②陳鳴樹:《魯迅:中西文化沖突中的選擇——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學術月刊》1986年第10期。以此來反顧陳鳴樹貫穿一生的魯迅研究,其文章境界由早年一種鋒芒畢露的批判論戰與自我迷失,最終實現一種理性升華與主體意識的完成,其文其人,也何嘗不是如此。
五
陳鳴樹在新時期以來另一重要領域是文藝學方法論。80年代的理論熱與方法熱,基本是西方文論的介紹與譯述。中國學者所面臨的一個最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不再亦步亦趨,轉而能夠從本土豐富的文藝史中攫取養分,在參透西方理論的同時建構符合當代中國實際的文藝學方法論。陳鳴樹是現代文學專業的學者,卻別具只眼,最早自覺意識到了文藝學領域的這一問題,跨界鉆研,孜孜以求。陳鳴樹最為重要的理論著作——《文藝學方法概論》是探索這一問題的最終成果,雖未完全解決問題,但卻率先從哲學高度探討了文藝學方法的內在邏輯與思維原理,其價值不可輕忽。
《文藝學方法概論》在199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在這部著作中,陳鳴樹縱橫揮灑,介紹了中西14種文藝學方法。這些理論在被中國學界接受幾十年后,現在看起來已不再陌生與新鮮,但陳鳴樹的超越之處就在于,他以自身深厚的文史哲修養,將文藝學方法論問題的討論,自覺提升到一種哲學層次。在從哲學層次探究文藝學方法背后的思維與機制問題過程中,陳鳴樹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系列原創性命題,比如“兩極否定性原理”“層次性原理”“發現機制的邏輯行程”等,這在“方法論熱”盛行的80年代,無疑是一股清流。
在該著中,陳鳴樹首先關注到的是方法背后的思維原理與機制問題,這對于以往習慣以經驗論的方式理解西方文論的中國學界來說,無疑是極大的突破。陳鳴樹在書中提出:“所謂文學本性,即是文學的客觀構成性。它的客觀構成性是一種事實而不是一種猜想。”①陳鳴樹:《文藝學方法論概論》,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1頁。因此,文學要回歸到生活之中,要從文本結構本身出發去設定其理論結構。從文學本體論出發,該著引出了3種范式:文學本體的本質分析演衍了文藝理論方法,文學的歷史發展演衍了文學史方法,文學的社會影響的判斷行為演衍成文藝批評方法。②黃昌勇編:《陳鳴樹先生紀念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0頁。這就使文藝學方法論的思考,重新回到理論衍生的內在層次,即是什么促成了不同方法的出現,方法出現過程中的思維模式是怎樣的,呈現出怎樣的特質等問題。該書中的上篇《方法論:原理》和下篇《方法論:實踐功能》,都對這些問題提供了建設性的論證。從該書的結構也不難看出,陳鳴樹并不滿足于14種文藝學方法的評述,而試圖要提供一種新的思想維度,探究原則性或原理性問題。
在陳鳴樹看來,唯有界定方法的屬性,才能夠判定和選擇一種恰當的方法。因此,他首先確立了“方法對應性兩極否定性原理”。在談到方法對應性時,他認為應當遵循對象第一義、方法第二義的準則。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批評總是跟它所判斷的現象相適應的,因此,它是對現實的認識。”③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滿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第575頁。因此,文藝學方法的運用,需要回歸到主體,從唯物主義的基點做出合理、恰當的判斷。但對象和方法的地位又不是絕對的先后順序,陳鳴樹在方法的否定性原則中補充說明了這一點。在他看來,文學的發現機制有其特殊性。新的邏輯起點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前人觀點的啟發,學術研究的目的一在整理前人成果,二在突破前人經驗,因此理論和方法是一種觸發的機制,不應當回避理論創造的可能性建構。在倡導思想解放的新時期,社會變革引發對庸俗社會學與教條主義的巨大沖擊,人們對大量涌現的新鮮理論成果如饑似渴,卻忽略了理論熱潮背后更為重要的理論建設及其機制原理問題。陳鳴樹的學理態度與學術觀念,對于80年代中國而言是難得一見的清醒與突破。
在陳鳴樹看來,經驗研究只能把握住規律的冰山一角,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經驗主義力求從經驗中,從外在和內心的當前經驗中去把握真理,以代替純思想本身去尋求真理……如果老是把知覺當作真理的基礎,普遍性和必然性便會成為不合法的,一種主觀的偶然性,一種單純的習慣,其內容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的。”④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16頁。因此,在進行理論運用及創造的過程中,邏輯的思維進程可以促成作品真諦的發掘,而思維需要3個層次——“感性、知性、理性”來完成一次旅行。感性,是針對個別對象,以最為深情的方式進行意義的豐富性拓展;知性則處在方法的中介位置,這是一種形成概念的能力;而理性則可以達到對對象最為深層的認識,它能夠增進思想的增值和擴容,同時促進思想群落的產生。對于這一問題的認知,陳鳴樹無疑走在時代的前列。他不僅看到了理論背后的思維層次問題,更提出了“理論熱”應該向何處去的思考。正如許明先生所言:“80年代文藝學方法論的討論匆匆略過,除了介紹幾種新方法外,似乎對方法問題的基本理論問題沒有什么觸及,在80年代末極少數有哲學素養的學者意識到了方法熱熱不下去的問題。陳鳴樹先生就是其中一位。”①許明:《渴望突破的契機》,黃昌勇編:《陳鳴樹先生紀念集》,第186、185頁。
作為一位跨界學者,陳鳴樹的文藝學理論也融入了魯迅關于“中間物”的思考。他將文藝學方法視為主體與客體間的“橋梁”,并指出:“由文學本性推演出的理論框架,是文藝學方法論確立的前提,是尋求文藝學方法論本體內涵的可靠方法。”②陳鳴樹:《文藝學方法概論》,第33、75、53頁。文藝學方法不再作為架空的理論,而是參與到完整思維過程的建構,它沒有凌駕于文本或讀者之上,而是作為貫通主客的“當下”存在,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陳鳴樹回顧了中西文藝學方法論的歷史,歸納出中國文藝理論的特質是內省、直覺、主情、鑒賞;而西方則是外察、體驗、主智、分析。這樣的總結是一種思維方法,也是一種歷史意識。
《文藝學方法概論》的出現,改變了以往文藝學專著對某一種外來方法的述評與譯介模式,轉而開始關注哲學思維方法的探索。陳鳴樹在書中提到文藝學研究的3個階梯:“即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體(個別)方法。一般方法是最高層的方法,即思維方法或稱哲學方法,特殊方法即運用到文學這個領域的各種方法,具體(個別)方法即適用于各別具體研究對象的方法,也可稱之為實用方法。”③陳鳴樹:《文藝學方法概論》,第33、75、53頁。3個階梯的研究方法如果缺失了第一層次的鋪墊,則無法建設更為牢固的理論主體,一部文藝學著作如果忽略了思維方法的指導,而單純停留在各種特殊理論的普及之上,無異于背離了理論研究的初衷。因此,陳鳴樹從黑格爾出發,以理性思維作為邏輯主線,延展至馬克思主義的理性思維模式,從哲學高度對文藝學方法論進行深入探討。陳鳴樹認為,文藝學方法論的展開必須以文學本體為據,因為文學來源于生活,所以無可避免地會同外部社會發生一系列聯系,從而產生歷史方法、傳記方法、社會學方法等研究模式。與此同時,文學具有相應的意識形態與語言結構、審美意蘊層,為結構主義、符號學、美學、心理學、語義學研究模式提供了活動園地。陳鳴樹打破方法之間新舊割裂的絕對化與簡單化,“主張從文學本性出發引申出方法論的多元化,并且認為,方法只要切合對象,就沒有新舊之別”。④陳鳴樹:《文藝學方法概論》,第33、75、53頁。這樣,陳鳴樹在《文藝學方法概論》中不但明確了文學研究方法的來源是文學本性的自由延展這一主張,同時讓傳統與現代理論找到一個平衡共處的開放空間,既大膽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同時又容納傳統理論的合理表達。該書出版之后,引發了學界熱烈的反響。石韞玉贊其“高屋建瓴,體大思精”,金學智譽其為是“一部‘智慧學’的書”。許明對該書的理論價值,則作出了更為系統的歸納與概括:
1. 在總體構思上,起點高。在研究意圖上,該書展開的是元方法(方法的出發點)探討,而不是某種方法的架構或運用。
2. 創造性地對文藝學方法的原理進行了設定,這是在文藝學研究中具有首創精神的。
3. 將知識增值和發現邏輯的問題引進了文藝學研究,并形成自己頗具吸引力的解釋。⑤許明:《渴望突破的契機》,黃昌勇編:《陳鳴樹先生紀念集》,第186、185頁。
2004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文藝學方法論》第二版,足見該書的學理價值與學術重量。過去主攻現代文學的陳鳴樹能夠在新的文藝學領域開花結果,這也再次說明:“一個人文學者必然要打破單一的學科分界,以廣泛的興趣貫通相關學科才會有所收獲。”①許明:《渴望突破的契機》,黃昌勇編:《陳鳴樹先生紀念集》,第187頁。只有打通學科之間的壁壘和屏障,拓寬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在交叉思維的互補中,才能更好實現學術研究的綜合提升。

圖4 《文藝學方法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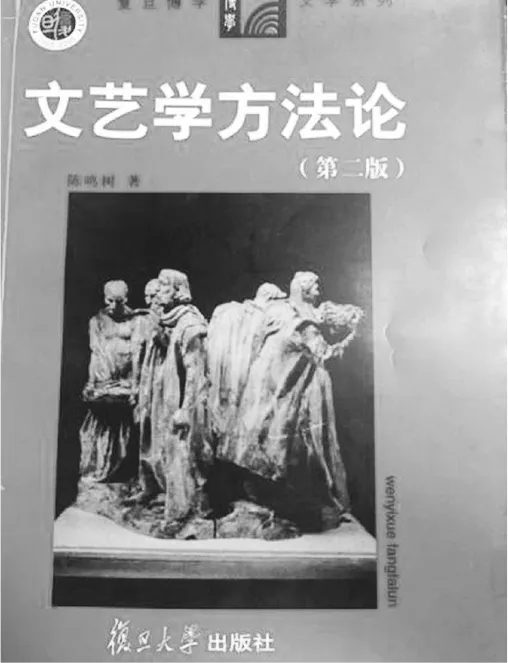
圖5 《文藝學方法論》
六
陳鳴樹成就斐然,得益于他豐盛的文藝才情、深厚的理論修養與嚴謹的治學精神。
陳鳴樹在著作中有一句評點魯迅的著名的話:“千古文章未盡才”,曾被錢理群先生大加欣賞而實行“拿來主義”,在致陳鳴樹70壽誕的賀信中加以引用。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作為陳鳴樹一生的寫照。從年少成名,到中年顛簸,再到晚年跨界,陳鳴樹的一生有眾多未盡之才,但也留下了許多妙筆佳作。在筆者的感覺中,陳鳴樹骨子里是一種浸染著江南文化的風流才子。只有風流才子,才會在不同時期展露文章才華,盡得時代風流。無論何時,陳鳴樹的文章總能追隨時代,也總能超越時代。即便在政治化的時代,先生的才情并未被完全束縛,他論魯迅的文章,如抒情篇章,現在看來仍有啟發。抒情論題近年被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大力發揮,認為是開辟了現代文學在啟蒙、革命之外的一條新路。看看陳鳴樹在那個革命化的時代,即有對魯迅文章抒情才華別有會心的發現與洞見,再看看王德威教授在后現代主義時代的異域研究,不能不佩服陳鳴樹的先見之明。先生無法掙脫時代的裹挾,但時代卻也無法完全裹挾先生。即使在現代學術普遍凋敗的年代,他仍然可以憑借個人一己的感悟寫出成功的文章。②參見符杰祥:《病中的先生》,黃昌勇編:《陳鳴樹先生紀念集》,第155頁。陳鳴樹后期由魯迅研究而文藝學、由方法論而書畫藝術,跨多種學科而各有成就,看似偶然,實乃必然。
*符杰祥,男,1972年生,山西臨猗人。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黃喬飛,男,1994年生,湖北赤壁市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魯迅手稿全集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2ZD167)的研究成果。
沈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