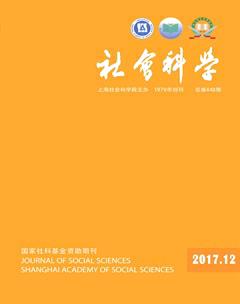新時代治國理政中的“概念先行”
周怡
摘 要:“概念先行”是當前政府的“話語體系建設”倡導下涌現的社會事實。盡管每一時代都不免有頂層的制度設計,但用話語概念,尤其用通俗易懂的百姓話語,而不是用規章規范,去動員和喚起行動卻是如今這個時代獨特的方面。這種現象一方面反映了國家意識形態的統領作用,另一方面,通過概念抑或觀念的動員、通過意義的合法化過程,把觀念下傳到社會組織、社會群體抑或個體層面,的確能夠獲得民眾的贊同,以形成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并指導行動。這種先于行動或鑲嵌于行動過程中的思想觀念之所以在我國特別有效,是因為(1)社會普遍存在的威權主義文化及其人格為“概念先行”鋪墊了綠色通道;(2)頂層設計中使用的民生話語、傳統文化話語及新知識話語,則為夯實概念與行動、上層規劃與基層響應間的一致性提供了長程的文化資源。因而,我國新時代治國理政過程中的“概念先行”現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現實社會基礎。
關鍵詞:概念先行;話語體系建設;治國理政;文化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G05; D6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7)12-0062-06
作者簡介:周 怡,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433)
一、話語體系建設與概念先行
加強話語體系建設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要倡導。2013年8月20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以增強國際話語權。那么,學理上什么是話語體系?話語(discourse),簡單的字面意思是人說出來或者寫出來的言語,是特定社會語境中人際間進行日常溝通的具體言語行為。福柯(Michel Foucault)終其一生的“知識權力觀”論述就非常重視話語與權力的分析,認為話語實際是社會權力的表演①;意指與社會權力關系相互纏繞的具體言語方式,反映復雜的具體社會形態②。話語體系(discourse system)則指話語運用的范式;既表達說話主體的意志及其思想建構,也包括說話主體與受話人、文本、語境等要素進行互動的整體模式。依這些學理去理解“話語體系建設”的國家政治內涵,就意味著每一個文明國家及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都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話語體系。其目標功能是:(1)對外展現國家軟實力的本土象征,在國際舞臺上“說好中國故事”;(2)借用話語體系指引、規范或折射本國具體的發展道路。顯然,十八大以來,作為中國話語體系文本要素、以“中國夢”開啟的系列標識性概念,已經成為當下中國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道路指示。近些年頻繁出現于媒體且完全出自“頂層設計”的標識性概念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層面:
上述這些緊隨“話語體系建設”之后出現的標識性概念是全新而先行的。姑且先不問概念的源頭抑或理據在哪里?現實告訴我們:這些概念一經提出并傳播,便頃刻成了中國人(受話人)參與治國理政的具體行動。如,“一帶一路”的概念推動中國依靠與相關國家既有的雙邊和多邊鄰里機制,借助區域合作平臺,發展了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及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既體現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傳統,又被賦予鮮明的時代特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和充分認同。又如,“智庫”和“大數據”的概念,促發了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智庫組織的迅猛發育和成長,催生出大數據分析技術及其“云產業”的勃勃生機。再如,在“共享經濟”的概念中,有了“共享單車”這樣一種分時租賃交通的新模式;也有了“共享民宿”的這種便捷經濟的旅舍等等。這些由概念驅使行動的種種現象,本研究稱之為“概念先行”。
很明顯,“概念先行”是中國新時代的話語體系建設倡導下涌現的社會事實。相比鄧小平時代用“摸著石頭過河”形容改革較多源自底層百姓試錯式的“邊緣革命”來說,當前的許多概念是“頂層設計”的直接結果,這也是“國家治理”取代“市場分化”的象征。盡管每一時代都不免有頂層的制度設計,但用話語概念,而不是用規章規范,去動員和喚起行動卻是如今這個時代獨特的方面。
二、觀念與行動:概念先行的理論依據
學界在處理思想觀念與社會行動時,一般取兩種簡化模型: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將思想觀念看作實際生活的反映;另一種是韋伯式的,將觀念當作社會行動的原因。然而,這兩種簡化都忽略了二者互動的事實Swidler, Ann,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 No.2, 1986, pp.273-286; Vaisey, Stephen, “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4, No.6, 2009, pp.1675-1715.。如何能結合馬克思和韋伯去研討觀念與行動之間的互動?困難不僅在缺乏清晰的概念來操作這種互動,還在于人類一直以來特有的對觀念價值的健忘。即任何概念抑或觀念一旦內化于心就會成為想當然的潛在力量去支配人的行動,并不為行動者所察覺——“觀念先于行動,有如閃電先于雷聲”(海涅)轉引自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被喻為閃電的觀念與作為雷聲的行動,不僅有先后關系,也具有互不可分的毗連關系。但現實中諸多社會發展與治理的研究,大多側重行動作為歷史事件雷聲的長程影響,而忽略支配行動的觀念,即觀念容易在學者的研究視線中如閃電般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使得揭示這種先于行動或鑲嵌于行動過程中的思想觀念變得十分重要,它構成文化社會學研究的目標之一。因而,這里“概念先行”的理論依據大都出自文化社會學的界說。
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有關“食物作為象征符號”的經典研究認為,日常飲食的可食與不可食性,并不以物的有用性來裁定,而是取決于物對人的意義。人對物的情感及其業已形成的觀念支配著美國人的飲食習慣。意義不僅決定生產什么食品,也決定全球的食品市場價格。如,不食也不能生產狗肉,因為認知情感中狗為美國人心中的寵物;豬肉比牛肉便宜是因為美國人觀念中牛比豬更親近一些。這種標識性概念抑或意義符碼決定了人的飲食行為。Sahlins, Marshall, “Food as Symbolic Code”,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p.94-104.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在《社會生活的意義》一書中,以水門事件、大屠殺、總統選舉、電腦科技等一系列經驗的個案研究為例,看到也強調了話語體系,尤其是深嵌人們頭腦中的二元符碼等無形的文化結構,對美國社會的政治事件、社會制度以及群體行動的建構和支配Alexander, C. Jeffrey,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顯然,他們的研究都高度肯定了觀念、概念抑或話語文本能夠對人的行動產生支配抑或積極的干預作用;在因果解釋鏈上他們置“概念”為因,“行動”為果;概念或者觀念作為自變量而先于行動得到了闡釋。endprint
其實,正如閃電和雷聲總相伴發生那樣,任何一種社會行動都是觀念支配下的行動,同時,價值觀念的追求一定會通過行動加以表現,觀念和行動本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大凡觀念總歸咎為思想,研究思想與社會的互動模式應該是當前中國社會話語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在這方面,作為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就涉及了支配與被支配之間如何達成“思想共識”而付諸行動的互動議題。像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樣,葛蘭西贊同上層可以對下層階級行使至高無上的統治權;但他認為這個上層統治權是通過贏得下層許可而獲得的,即需要有下層的“贊同”;只有上層和下層達成共識的思想才可能真正組織起整個國家或社會的整合。他的分析首先將國家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守夜人國家”(night-watchman state),作為一種依賴于軍隊、警察和司法系統的壓迫工具;另一類是“倫理國家”(ethical state),在公民形成和贏得同意中發揮教育和形塑的角色。接著,他把統治亦一分為二:一種叫控制或支配,通過使用軍隊、警察的暴力控制;另一種被稱作霸權,為構建合法性、發展共同理念和共享價值而組織起贊同的霸權。葛蘭西始終強調教育和贏得同意的霸權,而不是野蠻暴力的控制權力;因為在他看來,雖然暴力仍然是社會控制的一種重要手段,但在穩定時期暴力控制讓位于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一部分)的統領作用:(1)意識形態提供給人們實踐行為和道德行為的準則。意識形態是生活的經驗,也是觀念的體系,其作用是組織并整合各種不同的社會元素,以形成霸權集團和反霸權集團。這里,霸權和反霸權是通過一系列話語建構的主體和利益群眾的戰略性聯盟形成的。(2)意識形態植根于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意識形態霸權涉及意義的決策過程。人們會通過常識、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來組織他們的生活和經驗;這些常識和流行文化往往成為意識形態論爭的重要場所。(3)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動員及其組織起大眾中發揮重要的作用。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8; [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孔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顯然,葛蘭西文化霸權觀從倫理國家的意識形態統領民眾的角度,為我國新時代倡導“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經典意義上的理據。盡管葛蘭西強調的是意識形態而非本文論述的話語體系,但在福柯的權力知識觀看來,意識形態等同于“各層次社會權力關系中具有特定后果的話語”,或可以被理解為“對政治、對任何社會組織、社會群體起凝聚和合法性作用的觀念系統”[英]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孔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頁。。國家通過觀念系統(話語體系)向民眾提供一套建構社會秩序、實現社會整合的原則[美]華特金斯·克拉姆尼克:《意識形態的時代:近代政治思想簡史》,章必功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回到本文關注的議題,葛蘭西給當代中國“概念先行”現象所提供的理論支點可簡括為:(1)“概念先行”的話語體系建設反映國家意識形態的統領作用;(2)概念抑或觀念可以通過動員、通過意義的合法化過程,下傳到社會組織、社會群體抑或個體層面,獲得民眾的贊同,以形成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及其行動;(3)在以“科學知識概念”為說服工具的互動過程中知識分子會扮演重要角色。
三、概念先行的社會文化基礎
概念抑或話語先行在中國何以可能?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基礎,歸納起來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中國人心靈深處業已固化了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文化及其人格。在談論中國傳統的本土特征時基本有兩種說法已然成為共識:一種說法認為“家國同構”塑造的家長制國家(patrimonial state)歷來是中國社會的制度性結構; 另一則說自漢代始“儒家思想”就被尊為國家意識形態而長期執掌中國文化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作為結構要素的“家國同構政體”與作為文化價值要素的“儒家思想”合為一體,生成了所謂“制度化儒學”制度化儒學意指“儒學被提升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與濃重的法家色彩的政治結構結為一體,即制度與文化的復合體”。參見金耀基《中國政治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頁。的國家治理體系。這種體系使得中國人在道德倫理上長期受威權主義順從文化的影響楊國樞:《中國人的蛻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具體來說,當中國人將一個個分散的個體組織、整合起來時,首先考慮的就是血緣關系,親代對子代的撫育中就蘊含使之服從的因素。早期的人類利用血緣關系實現初民社會統治乃屬天然之事。逐漸地,隨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天然的恩賜由家拓展到家族及家族外群體,由宗法制度延展進今天的科層制度,復制或衍生到了國家的統治或支配模式。不少研究證實,“家”與“國”同構作為儒家社會倫理中存在的對偶現象之一Schwartz, Benjamin, “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David S. Nivison, Arthur F. 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50-62.,長期左右著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文化政治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中國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制度化儒學型塑出中國人普遍存在的威權人格和心態。這就是,在君臣權力關系中,臣子對君主的“忠信”及順服歷來被當作重要的個人美德,而被內化于心,再付之于行動的。中國百姓習慣于順從政府的統一分配和安排,對國家、對單位組織具有極強的依附。改革開放后,盡管社會的主導理念已經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幾乎每個人都被推入相對自主的市場環境,但現實告訴我們,發生任何大小事情或任何社會問題時,國人第一時間呼吁的是“政府為啥不管”、“政府應該出面采取措施”等,基本沒有主動或自主的參與意識。說到底,他們還是習慣了對政府、對國家及其組織的強烈依賴和順從。近期一些研究也表明:政府的意識形態、政府的社會動員依舊起支配性的強作用力量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另據全球愛德曼公關公司2011年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達到88%,位居全球第一位,之后幾年中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80%左右徘徊,居全球前三位。政府持有穩定而強有力的社會動員力量,以及民眾居高不下的政府信任,其實以兩個當下的社會事實呼應了中國人一以貫之的順從權威、依附權威的深層文化特質。顯然,社會成員具備這類文化特質,容易通過崇尚“‘國是‘家”、“個人應該服從集體、服從國家”的思想理念,將自上而下的新觀念、新概念、新話語視作當然的制度安排而付諸實際的行動。endprint
第二,話語體系建構中的民間流行元素。顯然,由概念抑或觀念組成的話語體系需要有“接地氣”的民間元素才更易于產生實際的影響和秩序。話語體現民間元素通常有兩種路徑:一是與民生需求元素相對應的路徑,叫民生路徑;二是與文化傳統元素相對接的路徑,稱之為傳統路徑。兩種路徑說到底都是社會動員過程中必要的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策略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也就是把百姓需要的、熟悉的文化資源加以整合,用定位在民生的話語體系,來為社會建設、社會整合服務。讓民眾深感政府的話語概念及其政策是傾向于改善百姓生活質量的明示努力,即正在發生的和將要努力去做的一切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是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這樣一種文化定位,一直明顯出現在中國社會。如,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在想“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市化道路”時,首先把制度建構的參照點放在“農民需要富裕,向往成為城市人”這樣的民間話語層面Zhou,Yi,“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armers City in Wenzhou the Early Reform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81, No.22, 2013,pp.476-498.。又如,當前體恤民生的概念包括“打通中間(最后)一公里”、“精準扶貧”等。在“打通中間(最后)一公里”的觀念下,我們看到截至2016年2月國務院取消了272項職業資格,還取消了152項中央制定地方實施的行政審批事項。而在“精準扶貧”概念下,我們讀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圍繞此概念所做的具體闡釋:“立下愚公志,心中常思百姓疾苦”(2015.3.6),“扶貧需要少搞些盆景,多搞些實惠”,“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2015.3.8),“民生工作要一諾千金,不要狗熊掰棒子”(2015.3.9)。再有,用“打贏藍天保衛戰”這樣通俗易懂的百姓語言代替了“治理污染”等學究語言。總之,概念抑或話語從國家主席直接就到了老百姓,語言上沒有任何“中間商”。這樣定位于民生的話語加上領袖的親民形象顯然有喚起民眾積極響應的強大力量,可以使“概念先行”的行動如期達成。同樣,在改革和建設的任何時期,傳統文化被納入中國話語體系的實例亦屢見不鮮。因為歷史上中華民族產生過儒、釋、道、墨、名、法等各家學說,涌現過老子、孔子、莊子、孟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善于利用傳統文化、符碼和習俗來動員群眾,讓群眾感到中國的改革及其建設是“中國的”,更容易獲得接受和認可。比如,作為詮釋中華文明復興的“中國夢”概念,其傳導的價值觀“國是家、善作魂、勤為本”,“儉養德、誠立身、孝為先、和為貴”均出自儒家典籍。而習近平2013年11月對曲阜孔府的訪問,以及他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典句的直接引用,如,在從嚴治黨的論述中他用到“明制度于先,重威刑于后”出自《尉繚子·重刑令第十三》;“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典出先秦《韓非子·喻老》等等,都通過“重訪”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向民眾傳遞出當代中國政治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強調,語義是中國人在以自己的本土文化符碼解決中國的事情。本土符碼的語義表達顯然能引起民眾的共鳴。
第三,概念能夠先于行動,還在于由概念建構的話語體系與新知識、新技術的結合。用民間流行話語去建構話語體系所處的民粹立場,一旦被過度使用,則可能導致或加速文化世俗化的趨勢[德]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譯,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在現代化發展的市場利益面前,源于商品市場發展的文化世俗化與國家主導的政治文化之間會產生矛盾與沖突。大多數國家會通過強調復雜社會世俗化的變化來實現改善人民生活的諾言;而世俗化的變化取決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新知識和新技術;其中,新知識和新技術概念的提出卻源于知識精英的參與和詮釋。假如把“話語權”分為政治話語權(即意識形態領導權)和學術話語權(即構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兩類的話,今天的中國社會更常見的是政治與學術話語權的兩相結合抑或兩相合作,更強調知識與國家治理的結合關系。“智庫”的風起云涌、“大數據”的實際參與、“供給側改革”概念的提出等都充分反映了政治政策話語與學術研究話語的聯手。比如,“供給側”屬于普通老百姓很難理解的經濟學學術話語,但該概念一經提出,在供給方面就出現了簡政放權、金融改革、放松管制及其國企、土地改革等政策行動,使老百姓得到實惠及市場利益。再比如,“一帶一路”概念是新時代中央政府在全球化市場中給出的新概念、新表述,同時也是提煉于歷史、經濟、地理學科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即它今天的意涵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個概念及其論證是政治文化與學術新科技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因為在“一帶一路”的倡導下,我們看到了新型“中歐班列火車”的啟動、“新靈渠”對中亞鄰國的連接、全球100多個國家的參與和支持等等。很顯然這一作為中國高層推動的國家理念已經成為行動。知識與權力相結合的理念,容易被普通民眾在不假思索的無意識中加以接受和認同的事實,這一點早在福柯的“知識權力觀”[法]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里有過生動的闡發。而對中國革命、中國政治有深度關切的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Jean Perry)亦看到,革命初期中國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身份出現在老百姓中,把他們的新理念、新知識帶給鄉村的上層紳士,通過他們讓下層的老百姓接受。即她看到了知識分子把教育及其知識從大學傳導到民間的參與革命的過程,并認為沒有一個國家的地方革命,能像中國這樣強調革命家作為教育家的功能Perry, Elizabeth Jean,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相對文化定位來說,裴宜理稱這樣的新文化傳導為文化援助(cultural patronage)策略,國家主動去操控文化、“培育同意”(cultivating consent)文化Rodriguez-Muniz,Michael, “Cultivating Consent: Nonstate Leaders and the Orchestration of State Legi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23, No.2, 2017, pp.385-425.,構建新文化符碼和形象,并使之深入到日常生活層面。其中,文化援助的手段來自新知識或新技術。毫無疑問,今天我們的國家經過近40年的巨變,新媒體、網絡支付、新金融等新技術的普及應用遠超發達國家,這種創新驅動能夠如此之廣泛,與知識分子參與話語體系建設密切相關。知識分子用科學技術去告訴老百姓“這是科學的、實用的,應該這么做,不應該那樣做”等等這番界說,與其革命時期傳播新思想而發生的文化援助如出一轍。endprint
如果說,社會普遍存在的威權主義文化及其人格為話語體系建設中“概念先行”鋪墊了綠色通道,那么,頂層設計時使用民生話語、傳統文化話語、知識話語,則為夯實概念與行動、頂層設計與基層響應間的一致性提供了長程資源。因而,我國新時期治國理政過程中的“概念先行”現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現實的社會基礎。
(責任編輯:薛立勇)
Abstract:One emerging social fact of the current practices of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precedence of conceptions. Although institutional designs from top to bottom is comm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i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current times to use discourse conceptions (especially the rank and file discourses) rather than formal regulations to mobilize individuals.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leading role of national ideology, but also the fact that the mobilization based on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cy of meaning can popularize and send ideas down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groups, or even individuals.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the mass, a society-wide “ideological consensus” is established, which subsequently directs peoples action. This type of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that are precedent to or embedded in the action process brings about societal consequences. That is because 1) the prevalent authoritarian culture and its embodiment pave the way for “conception precedence”; 2)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peopl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w knowledge that is used by the from-top-to-bottom institutional design provides long-term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ideology and action, and between top design and grass-roots resonance. Hence, the phenomenon of “conception precedence” in the new-era governance, reasonably and legitimately, has its social foundations.
Keywords: Conception Precedence;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Cultural Sociolog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