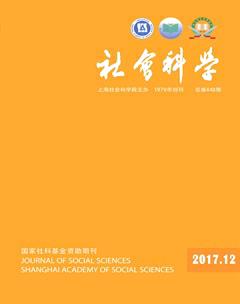生育醫療待遇:政策演變、人群差異及優化策略
摘 要:生育醫療待遇是包括產前檢查、住院分娩、生育并發癥、計劃生育手術及并發癥等費用報銷的一攬子政策,它是母嬰保健、“全面二孩”生育配套服務、全民生育保障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回顧相關政策演進過程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后生育醫療待遇是按戶籍、職業區分參保對象的,城鎮職工的生育保障起步較早,也相對成熟,而靈活就業人員、職工未就業配偶、農村廣大婦女的生育醫療待遇則起步較晚。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從住院分娩費用報銷這一主要方面來反映生育醫療待遇總體情況,結果表明,不同人口學特征、政策時期和從業性質的母親在分娩費用報銷方面存在顯著性差異。由于在分析期間1989-2010年內母親生育醫療待遇主要是職工的權益,來自于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因此,女性就業非正規化將弱化職工的生育醫療待遇這一政策的保障作用。改變這一狀況我們需要:將生育保險中的生育醫療待遇納入醫療保險中,打破就業身份對生育保障的限制,建立全民性的生育福利制度;推廣孕前檢查、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等服務,擴展生育醫療待遇項目,深化孕產婦保健工作;規范生育的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和整合現有法規。
關鍵詞:生育醫療待遇;分娩費用;生育保險;非正規就業;城鎮職工
中圖分類號:C913.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7)12-0079-10
作者簡介:莊渝霞,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上海 200020)
“生育醫療待遇”指的是女性在妊娠、分娩和產后所發生的醫療費用,它包括生育的醫療費用和計劃生育的醫療費用。其中,生育的醫療費用包括流產和正常生產的支出,是指女職工的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藥費等生育醫療費用。計劃生育的醫療費用是指職工因實行計劃生育需要,實施放置(取出)宮內節育器、流產術、引產術、絕育及復通術所發生的費用。此外,女職工生育出院后,因生育引起疾病的醫療費,也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同時,各省市也出臺了生育并發癥的范圍和支付標準的相關規定。因此,生育醫療待遇是包括產前檢查、流產、分娩、生育并發癥、計劃生育手術和并發癥等多項費用的總和。隨著醫療費用的不斷上漲,生育的費用不可避免成為產婦及其家庭的一項重要經濟負擔①。生育醫療待遇直接關系到母嬰健康,有利于減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孕前檢查、產前檢查、分娩以及產后并發癥支持是孕育過程的重要方面,也是生殖健康進行監測的重要環節。所以,保障婦女在孕期、產時和產后得到基本的醫療保健服務,有利于保障婦女的生殖健康,在某程度上也能促進“全面兩孩”生育政策的落實。因此,對“生育醫療待遇”進行研究具有現實意義和迫切性。
由于生育醫療待遇和生育津貼是生育保險待遇的兩項基本內容,現有文獻較少將二者區分開,而是籠統地就生育保險這一主題展開。生育保險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諸多,比如,生育保險覆蓋面較窄、待遇水平低、未能實現全部社會統籌、基金結余較多、立法滯后、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等等。其中關鍵性問題是如何拓展覆蓋面,具體做法和建議有:加強生育基金的社會統籌,拓寬基金收繳渠道,加大政府的財政投入,建立政府、雇主和個人三方負擔機制,注重男性生育角色,對招聘女工和產后女性的企業給予補償和獎勵,彌補“產假成本”,等等。建立一個全民性的生育保障制度是研究者達成的共識,生育保險應該逐漸從城鎮正規職業女性擴展至城鎮非正規職業女性,逐步將農村婦女和未就業女性也納入,同時著手于將男性和外籍人員、境外人員也納入相關研究可參見潘錦棠:《生育社會保險中的女性利益、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浙江學刊》2011年第6期;孫啟泮:《生育保險法制建設初探》,《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張瑩:《建立城市流動人口生育保險制度的探討》,《衛生軟科學》2007年第8期;馮祥武:《流動婦女生育保險問題新論》,《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班曉娜:《中國農村地區育齡勞動婦女生育保險制度探析》,《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唐芳:《論靈活就業群體的生育保險制度》,《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當然,要建立全民性的生育保障,制度設計非常關鍵。主要的建議是區分生育保險的待遇,將生育保險中的生育醫療費用并入醫療保險,以簡化管理并確保廣覆蓋的主張張翠娥、楊政怡:《我國生育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與改革路徑》,《衛生經濟研究》2013年第1期;蔣永萍:《社會性別視角下的生育保險制度改革與完善》,《婦女研究論叢》2013年第1期。,同時,保留生育保險的獨立性和規范生育保險待遇的基本內容張永英、李線玲:《新形勢下進一步改革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探討》,《婦女研究論叢》2015年第6期。,這樣,將有利于我國建立廣覆蓋的生育福利制度。
至今為止,并沒有文獻直接探討生育醫療待遇,相關研究主要是分析住院分娩費用的構成、城鄉差異及影響因素,指出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生育的醫療費用絕對支出在不斷增加、上漲過快。為了控制過度醫療問題,有學者指出應該推廣醫療保險預付制度,采取“單病種付費為主,多種付費方式并存”的方式與醫療機構進行結算相關研究參見李曉燕等:《1998—2003 年中國婦女住院分娩費用分析》,《中國初級衛生保健》2005年第11 期;方良欣、何秋苑、鄧群娣:《基于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影響產科住院分娩費用的因素》,《現代醫院》2011年第3期;張勁妮:《生育保險醫療待遇付費方式改革研究》,《就業與保障》2014年第4期;姜玉:《當前婦女住院分娩費用分析》,《中國婦幼保健》2016年第 19 期。。流動人口和農村孕產婦是必須關注的重要人群,為她們提供分娩的基本服務,有利于保證母嬰健康沈汝木岡、王燕等:《流動人口孕產婦住院分娩費用研究》,《中國婦幼保健》2006年第8期;邢利霞、裴菊英:《農村貧困孕產婦住院分娩費用補償狀況調查》,《中國婦幼保健》2011年第24期。。上述研究多側重于醫學角度,數據大多來自于某一特定醫院或某一地區住院分娩的人群,影響因素主要與醫療和生育自身有關,比如,醫療級別、醫療項目、生育方式、支付方式和患者體癥。endprint
由于生育醫療待遇的費用報銷渠道是不一樣的,本文先是介紹不同人群的政策依據。繼之,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數據,側重于社會人口學角度,全面考察1989-2010年期間女性享受生育醫療待遇的情況。生育醫療待遇是包括產前檢查、住院分娩、生育并發癥治療、計劃生育手術和并發癥治療等費用報銷的一攬子政策,本文主要選取住院分娩費用報銷這一主要方面來反映生育醫療待遇總體情況;在了解生育醫療待遇的人群分化基礎上,本文將提出相關政策改進建議,指出今后生育醫療待遇改革途徑及完善方向。
一、生育醫療待遇的政策演變
改革開放后,生育醫療待遇按戶籍、職業區分參保對象,城鎮職工的生育保障起步較早,也相對成熟,費用報銷是通過生育保險基金或所在單位支付。靈活就業人員、職工未就業配偶、城鄉居民生育醫療待遇則起步較晚。
一是城鎮就業婦女。1988年,《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和《關于女職工生育待遇若干問題的通知》出臺,規定了女職工在生育時享有醫療待遇、產假及生育津貼,要求用人單位在女職工“產假期間,工資照發”、女職工懷孕檢查和分娩時,“其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藥費由所在單位負擔,費用由原醫療經費渠道開支”。為了消除生育保險費用完全由“單位負責”所造成的企業之間競爭的不平等,“均衡企業間生育保險費用的負擔”,1994年,《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頒布,要求“城鎮企業及其職工”的“生育保險費用采取社會統籌”的方式,讓更多用人單位積極參保。其中,第六條對女職工生育醫療待遇作出具體規定,“女職工生育的檢查費、接生費、手術費、住院費和藥費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超出規定的醫療服務費和藥費由職工個人負擔”;“女職工生育出院后,因生育引起疾病的醫療費,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2010年,《社會保險法》出臺,從法律層面上對生育醫療待遇給予保障。2012年,《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通過,對就業婦女生育醫療待遇作出進一步補充,第六條強調“女職工生育或者流產的醫療費用,按照生育保險規定的項目和標準,對已經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對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支付”。
二是城鎮非就業婦女或職工未就業配偶。200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妥善解決城鎮居民生育醫療費用的通知》(人社廳發〔2009〕97號),要求“各地要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住院分娩發生的、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納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范圍。開展門診統籌的地區,可將參保居民符合規定的產前檢查費用納入基金支付范圍”。次年,《社會保險法》將職工未就業配偶也納入享受生育醫療費用報銷待遇的范圍,第54條作出明確規定,“職工未就業配偶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生育醫療費用待遇,所需資金從生育保險基金中支付”。這意味著,只要非就業婦女的配偶參加了生育保險,這部分婦女生育的醫療費用就可以從生育保險基金中報銷。其實,早在《社會保險法》出臺之前,有些省份,比如,江蘇(1999)、上海(2001)、新疆(2004)、吉林(2006)、河北(2007)、寧夏(2007)、山東(2007)、西藏(2007)、河南(2008),在首次生育保險立法中就已經將職工未就業配偶納入生育保險范疇。各地報銷政策各異,較多是采取一次性補償,補償費用為女職工生育醫療費用報銷的一半。
三是農村廣大婦女。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中發〔2002〕13號),在該決定中明確提出“做好農村婦幼保健工作”,具體目標是“加強農村孕產婦和兒童保健工作,提高住院分娩率,改善兒童營養狀況”;“到2010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要比2000年分別下降25%和20%”;“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質”。自此,我國逐步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加強對農村貧困家庭實行醫療救助。2009年,衛生部、財政部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實施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政策,探索將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醫療救助補助進行統籌管理。具體要求是“對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所需費用予以財政補助,補助標準由各省(區、市)財政部門會同衛生部門制定。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村孕產婦在財政補助之外的住院分娩費用,可按當地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規定給予補償。對個人負擔較重的貧困孕產婦,可由農村醫療救助制度按規定給予救助”。同年,兩部門又印發了《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專項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持續推進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專項補助資金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統籌管理。自此,農村孕產婦的生育保障逐步建立起來,資金來源于農村孕產婦住院分娩補助資金和新農村合作醫療資金。
二、生育醫療待遇的人群差異——以分娩費用為例
我們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調查數據庫,按照政策規定,截止至調查時點,大部分城鄉居民還是享受不到分娩費用報銷待遇的。因此,我們的分析對象為有就業單位的女性,她們的分娩費用報銷來自于生育保險基金或由所在單位承擔。但是,基于以下兩點考慮:一是不少地方要求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生育保險,二是部分省份規定只要職工所在單位繳納了生育保險,其未就業配偶就享有部分報銷生育費用的權益,因此,我們將分析對象擴展到所有母親。選取了分娩費用進行分析,是由于分娩費用報銷是生育醫療待遇諸多項目中的一項重要支出,它可以反映生育醫療待遇實施的總體情況。
(一)數據說明及變量設置
1、數據來源
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是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繼1990、2000年第一、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后組織的又一次全國規模的調查。數據庫分為個人主卷、流動、高層、兒童、老年五部分,本研究只利用個人主卷這一調查數據庫,共有26166個樣本,其中,男性樣本為12659份,女性樣本為13507份。endprint
2、研究對象界定
我們以1989-2010年“生育最后一孩”的母親作為分析對象,時間界定為1989-2010年,主要與這一階段全國和各地生育保險政策的陸續出臺有關。起始時間定為1989年,是因為我國于1988年出臺《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和《關于女職工生育待遇若干問題的通知》,于1989年執行,明確提出女職工的檢查費用和分娩費用由所在單位負責。之前的相關規定一并被廢除。1994年出臺《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于1995年執行,要求單位為女職工繳納生育保險費用,女職工生育的醫療費用則由生育保險基金結算。此后,我國各地不斷探索和出臺地方生育保險辦法。結束于2010年,是因為第三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是在2010年底進行,可以得到的母親生育最后一孩的數據止于2010年。按照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辦法》和各地生育保險辦法的頒布情況,我們將母親的生育年份劃分為四個時期(如表1所示),既代表母親生育的時期,也代表政策出臺的4個時期,把其命名為“同期群”。
3、數據的特殊處理
由于第三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提供的是橫截面數據,我們無法確切獲知生育最后一孩時母親的人口學特征。因此,我們選擇了“工作沒有發生變動”的母親作為分析對象,從而可以科學、合理地推斷出她生育最后一孩時的一些重要人口學特征。使用stata軟件處理數據,對戶口、城鄉、職業、單位類型和單位所有制5個變量進行嚴格的推斷,最終獲取生育最后一孩時母親的戶口、城鄉、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是按調查時點的情況進行測量的,因為大部分婦女一般是在完成受教育過程后進行生育的,這是一種合理的近似估計。參見郭志剛主編《社會統計分析方法——SPSS軟件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417頁。、同期群、職業、單位所有制、單位類型等7個人口學變量。
如表2所示,1989-2010年生育最后一孩的所有母親樣本共有7665份,在就業的7285份中,工作沒有變動的有3875份,占53.2%,此外,還有380份從未就業的母親樣本。受數據結構限制,我們將工作沒有變動的4255(3875+380)份樣本作為分析對象。由于第三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是有提供母親產前檢查以及分娩費用報銷情況的非常寶貴的全國性調查數據,我們認為,雖然沒有將工作發生變動1次、2次及以上的母親納入分析,這一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嘗試。期待2020年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的完善,屆時能將所有母親納入分析。
4、變量設置
本文將母親是否報銷分娩費用作為分析對象,分娩費用報銷情況分為“全部免費/報銷”、“定額補貼”、“部分報銷”和“全部自費”四種。同時將戶口、城鄉、受教育程度、同期群、職業、單位類型、單位所有制這七個重要因素作為其重要人口學特征。交叉表的變量分類設置如表3。為了了解從未就業者和農業從業人員的情況,我們對職業、單位類型、單位所有制這些變量進行擴展,納入了個體工商戶、自營勞動者和家庭幫工、農業生產人員、從未就業者等分類。
(二)分娩費用報銷情況及其人群差異
從總體上來看,在我們所限定的于1989-2010年生育最后一孩時工作沒有發生變動的4255份母親樣本中,缺失63份,共有4192份作出回答。其中,全部免費或全部報銷的比例僅為9.9%,定額補貼的為2.7%,部分報銷的占13.6%,需要全部自費的占73.8%。由于在我們的分析對象中(工作沒有發生變動的母親)農業生產人員和從未就業人員所占比例較大。因此,我們又對比了1989-2010年生育最后一孩時所有7665份母親(包括工作沒有變動的母親和工作變動的母親)的分娩費用報銷情況,結果發現,分娩費用報銷比例與上述相近,全部免費/報銷、定額補貼、部分報銷、全部自費的比例分別為9.8%、2.5%、15%和72.7%。所以,雖然我們將分析對象限定為工作沒有發生變動的母親時,仍具有一定代表性。如表4所示,不同的人口學特征、在不同的政策時期和不同從業特征的母親在分娩費用報銷待遇上存在較大差異。
1、不同人口學特征。農業戶口或農村人口分娩費用自費的比例很高,近85%,只有15%左右的農業戶口或農村居民是可以享受到生育醫療待遇的。非農業戶口或城鎮人口分娩費用報銷的比例較高,將近一半。其中,全部報銷或部分報銷是較常見的報銷形式,定額補貼的比例極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母親分娩費用報銷的差異較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報銷,但是,就大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母親而言,仍有37.3%的人需要全部自費。
2、不同政策時期。在不同政策時期母親生育的醫療費用報銷待遇存在顯著性差異。隨著我國各地生育保險辦法的不斷出臺,以及對城鄉居民生育保障的關注,女性分娩費用報銷的比例有所增長。在1989-1994年、1995-2000年、2001-2005年這三個時期,需要全部自費的比例高達75%左右。在2006-2010年這一時期,全部自費的比例降為50%。具體而言,于1989-1994年生育的母親,分娩的費用需要自費可能性最高,接著是1995-2000年和2001-2005年這兩個時期,最后才是2006-2010年這一時期。這一趨勢與政策規定以及費用報銷管理方式有關。按照1988年《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的政策要求,1989-1994年期間母親分娩費用由所在用人單位支付。1994年《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出臺后,開始實行生育費用社會統籌。較之于“單位負責制”,社會統籌均衡了企業間的負擔,顯然更有利于促進企業繳納生育保險費,為女性提供“生育醫療待遇”。因此,在1995-2005年生育的母親分娩費用報銷的可能性提高了。在2006-2010年期間,分娩費用報銷的可能性最高,有可能是因為2009年城鄉居民生育保障政策剛好在該時期出臺,拓寬了分娩費用報銷的人群。
3、不同從業特征。從職業來看,農民和從未就業女性分娩幾乎是需要全部自費的,只有10%左右的母親分娩費用可以報銷。這部分人群有可能與其配偶單位參加生育保險有關,作為男職工的未就業配偶,她們能夠享受生育醫療待遇。此外,近四分之三的商業服務人員分娩費用需要全部自費,其它職業的母親,比如,各類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工人,分娩時需要全部自費的比例也不小,為50%左右。從單位類型來看,分娩費用報銷情況最好的是大型企業,只有26%的母親需要全部自費,繼之是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和中型企業,需要全部自費的比例近45%,小型企業全部自費的比例更高,為62.8%。民辦非企業、社會團體全部自費的比例為70%以上。個體工商戶、自營及幫工、農業生產人員和從未就業人員這些群體,分娩時一般都是自費。從單位所有制性質和就業身份來看,除70%左右的國有正式員工分娩費用能夠報銷外,在港澳臺/外商投資企業和集體企業中,仍有47.1%的女性分娩時需要全部自費,國有非正式員工和在集體、私營企業中就業的女性,分娩費用需要全部自費的比例很高,分別為80.2%、63.5%和68.1%。endprint
(三) 研究結論及發現
從本文的描述性結果來看,農村地區、農業戶口、受教育程度較低、政策早期、非正規從業者分娩費用需要全部自費的比例較高,而城鎮地區、非農業戶口、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是靠近政策后期、正規從業者,更有可能享受分娩費用報銷的待遇。我們可以推測,在1989-2010年期間,影響女性分娩費用能否報銷的兩大因素是:
一是政策的影響力。隨著職工、職業未就業配偶、城鄉居民不同人群的生育醫療待遇政策的出臺,相應群體的生育福利得到了有效改善。表4所表現出來的城鄉差異和同期群差異,與我國對生育醫療待遇的政策對象限定和頒布時期直接相關。可以推測,隨著城鄉居民生育保障制度建設的推進,非職工女性能夠享受分娩費用報銷待遇的比例將大幅度提高。同時,費用管理方式也很關鍵。對于職工生育保險而言,社會統籌模式較之于“單位負責制”,更有效地保障了職工享受生育醫療待遇的權益。
二是就業身份的影響。在城鄉居民生育醫療待遇相關政策出臺之前,生育醫療待遇列支渠道主要是生育保險基金,它最突出的問題是受就業身份的影響。在體制內正規就業的母親更有可能享受到生育醫療待遇,在體制外、非正規就業的,特別是在私營企業和小企業中,以及個體工商戶、自營及幫工等靈活就業人員,享受生育醫療待遇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諸多研究證明,在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女性就業的非正規化都是不爭的事實宋秀巖、甄硯:《新時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究》,中國婦女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頁。,在非國有單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采用非正規雇用的個體私人經濟組織,女性勞動力比較集中蔡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城鄉就業、問題與對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頁。,而且,非國有制單位女性勞動力比例高于男性金一虹:《女性非正規就業:現狀與對策》,《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因此,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女性就業非正規化以及規模化,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女性在體制外進行經濟活動,那么,假若生育醫療待遇仍受限于就業身份的影響,將極大地影響女性享受生育醫療待遇。
三、生育醫療待遇的優化策略
當前,職工生育醫療待遇仍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城鎮未就業女性和農村女性分別從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或農村孕產婦住院費用補助的方式獲得部分補償。但是,其報銷比例及待遇水平遠不及職工的生育醫療待遇。從我們的分析來看,女性就業模式是決定她們能否享受職工的生育醫療待遇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隨著女性就業非正規化,女性就業模式的變化將弱化針對職工的生育保險政策的作用力。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考察政策的時效性,杜絕女性因就業身份改變而無法享受到職工的生育醫療待遇。那么,如何完善生育醫療待遇的政策,才能讓全體母親分享到生育保障的好處呢?
建議一,打破從業性質,如職業、行業、單位類型、單位所有制、就業身份對享受生育醫療待遇的影響,建立一個讓所有人員(不管是正規、非正規就業還是沒有就業的母親)都可以享有的生育保障制度。2016年初,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實施,二險合并后如何運營顯得非常關鍵。我們認為今后的發展方向是將生育保險待遇中的生育醫療待遇和生育津貼兩項基本內容分開管理,將生育醫療待遇納入基本醫療保險。一是先整合城鎮職工、靈活就業人員和城鄉居民生育醫療待遇,進行統一管理、統一運營,從而形成“不管是否就業都可享有生育福利”的制度。二是保留生育保險中的生育津貼功能,并且“由國家財政建立普惠式生育津貼,擴大生育津貼的發放范圍并逐漸演變成家庭津貼”張翠娥、楊政怡:《我國生育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與改革路徑》,《衛生經濟研究》2013年第1期。。
建議二是拓展生育醫療待遇項目,深化孕產婦保健工作。我國現有各級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高度重視育齡婦女的保健工作,主要包括產前檢查、流產、住院分娩、產后訪視、生育并發癥、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等服務。目前,生育保險辦法主要是對流產和住院分娩費用的報銷作出詳細規定。但是,還有以下工作可以繼續推進:(1)婚前檢查和孕前檢查及相關費用報銷事宜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2010年,財政部人口計生委印發了《國家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項目試點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試行)》,不斷推廣孕前檢查試點并提高覆蓋面,部分農村孕產婦也享受到了該政策的福利。我們認為,為了降低出生嬰兒缺陷率,保障母嬰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質,應將孕前檢查費用納入生育醫療待遇中,加以推廣和普及。(2)在繼續推進產前檢查和住院分娩生育服務的基礎上,重視生育并發癥和計劃生育并發癥的治療和費用報銷事宜,做好宣傳服務工作。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其它部門發布了《關于妥善解決城鎮職工計劃生育手術費用問題的通知》,將計劃生育手術費用納入了生育保險基金的支付范疇。2011年,國家人口計生委印發了《計劃生育手術并發癥鑒定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要求對計劃生育并發癥實行免費定點治療。
建議三是規范生育的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和整合現有法規。在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還有很多省市并未對生育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作出詳細的規定。一類是有法可依,可以參照現有的法規條例進行支付,但是在生育保險辦法中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比如,安徽省在《安徽省職工生育保險暫行規定》(2007年首次立法)中規定“生育保險醫療費用支付范圍按照《安徽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藥品目錄》、《安徽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診療項目》、《安徽省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服務設施范圍和支付標準》的范圍確定”;一類是沒有明確的支付方式,也沒有具體條例和辦法可依,需要另行制定支付標準。比如,天津市在《天津市城鎮職工生育保險規定》(2005年首次立法,2016年修正)中規定,“產前檢查費、生育醫療費和計劃生育手術醫療費等費用的支付標準和結算辦法,由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另行制定”。可見,生育醫療待遇散見于各類政策文件中,給受益者帶來很大的不便。我們建議,在將生育醫療待遇納入醫療保險后,必須統一待遇項目、待遇標準及整合現有法規。endprint
本文的工作在于把握不同人群的生育醫療待遇的政策依據,據此分析了1989-2010年女性分娩費用報銷情況,對女性的生育醫療待遇有個總體的把握。研究結果表明,生育醫療待遇政策具有強大的政策效應,它表現為一定的地區差異、時期差異和就業身份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就業非正規化會弱化針對職工的生育醫療待遇的保障性和覆蓋面。但是,城鄉居民生育保障為非正規就業者、未就業者構建了享受生育醫療待遇的安全網。本文研究的局限在于受數據結構制約,沒能納入工作變動的母親樣本,也沒有分城鄉進行更深入的比較,希望今后的工作能彌補這一不足。
(責任編輯:薛立勇)
Abstract: Medical reimbursement of childbirth expens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fertility support services of two-children policy, and the universal reproductive protec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of medical treatment of childbirth, detail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three groups of urban workers, urban non-employed women and rural women. Then, based on the data of social status survey of Chinese women in 201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imbursement of mothers' childbirth expen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imbursement of childbirth expenses between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olicy period and nature of employ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ormalization of female employment will weak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female workers.
It is proposed to break the barriers of employment status, to expand the medical treatment items and coverage of maternity protection, thus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of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medical reimbursement of maternity expenses, and then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maternity welfare system.
Key words: Medical Reimbursement of Childbirth Expenses; Cost of Childbirth; Maternity Insurance; Informal Employment; Urban Worker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