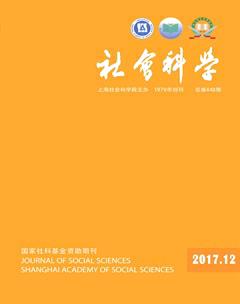初唐儒家話語下的三教關系
摘 要:貞觀之治的基本治國方略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體現。唐太宗的三教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學界一般認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釋、道三足鼎立,這種說法稍嫌籠統。事實上,唐太宗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總體政策,具體即重儒以尋求道統的合法性,確立治國理政的主體;崇道以尋求血統的正統性,為提升皇權合法性的基礎;尊佛以重建精神信仰,以為歸化民心的工具。在確立儒學官學正統地位和國家民族主體信仰地位的前提下,逐漸形成了以儒為主,以佛、道補充和輔助,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思想格局。
關鍵詞:初唐;儒家話語;三教關系
中圖分類號:B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7)12-0109-06
作者簡介:韓 星,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872)
一、貞觀之治: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體現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在其執政的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經濟發展很快,百姓豐衣足食,社會秩序安定、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大同之世的景象,史稱“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所采取的基本治國方略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典型體現。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臣合治,儒家君臣之道的完美體現。太宗豁達大度,嘉言懿行,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可稱媲美三代之盛;其賢臣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感其知遇,相與獻替可否,竭忠盡智。“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齊一努力之精神,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①
第二,選賢任能,是儒家賢能政治的集中體現。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曾先后五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以使更多的人才得以顯露出來。正是這些棟梁之才,為“貞觀之治”的形成提供了條件。
第三,以民為本,儒家民本思想的實踐。太宗從農民戰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重視百姓的生活,強調以民為本,他說:“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②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他反復引用荀子的話來告誡臣下和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卷4《教戒太子諸王》。他把民眾看作是國家的根本,把從民意、順民心的重民思想作為制定國策方略的出發點。
第四,文治太平,儒家治道的主體精神。太宗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認識到“武以克敵,文以致治”,因此他一即位就提出了為國之道,安靜為務的方針,推行仁政,宣布“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才能實現“中國既安,天下大寧”《資治通鑒》卷192。。所以,對外,他盡量避免戰事;對內,他提倡文治。還沒有即位之前,他就廣招文人學士進入秦王府,形成十八學士作為他的智囊團,后來就成為貞觀宰相的主要班底。他在即位第一天的群臣大會上就提出了“偃革興文”,隨后就廣招文臣,貞觀元年至四年,以文人入相而充實政事堂的詔令和任免即達18次之多,他不斷精選儒士補充進中央和地方的官吏班子,逐步形成了穩固的文人掌權的政治局面。
第五,建章立制,儒家制度化的完善。在制度建設方面,太宗君臣論政講民主諫諍,皇權帝制改革,輔之以均田、府兵、科舉、刑律、義倉、政事堂等制度建設與改革,盡可能地實現對權力的合理配置和制約體系,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民主精神。這是貞觀之治得以出現的關鍵,也是唐代在經濟、法制、文化、軍事方面逐步走向繁盛的重要條件。
第六,禮法兼治,儒家的法律化。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洞悉隋煬帝濫刑濫殺之弊,吸取了其教訓,認為只有把德禮與法治結合起來,才能移風易俗,治理好國家。他說:“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貞觀政要》卷5《仁義》。這里的“撫之以仁義”,就是推行仁義禮教,“示之以威信”,就是施行刑罰。這樣幾年之后,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唐太宗處理儒道釋三教關系的政策是其治理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三教關系方面,太宗盡管注意三教排列次序,但他深層關注的是國家政治與社會發展二元結構的平衡與穩定,一直在尋求國家意識形態與社會民眾信仰的合理結構。漢代以來意識形態方面成熟的經驗是以儒為主,以佛、道為補充和輔助,這點唐太宗繼承下來了。在初唐他需要進一步宏觀調控的是如何使三教形成合理的分工,構建立體的國家意識形態體系和國民信仰體系。
二、重 儒
唐太宗很清楚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他認為,立國之后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讓儒家出場。唐初朝廷都非常重視復興儒教,主要是為了尋求道統的合法性,借以確立儒學作為治國理政的主體。兩晉以及隋代政治秩序混亂,社會分裂動蕩,其主要原因在于重文輕儒,儒道淪喪,而唐朝廷吸取了歷史教訓,重新重視儒教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高祖就極為重視儒家。據《舊唐書》載:“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并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秘書外省別立小學。”《舊唐書》卷139儒學上》。武德二年高祖下詔在太學建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并博求其后,具以名聞,詳考所宜,以加爵土。這一興儒的舉動使學者慕向,儒教聿興。《舊唐書》卷139《儒學上》。武德七年,高祖親赴國子學祭奠先圣,下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配享,又令徐文遠在國子學講《孝經》,親臨聽諸生講解經義,以示對儒學的重視。高祖又下《興學敕》:“自古為政,莫不以學為先。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深博。朕今欲崇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謨。”《唐大詔令集》卷105《興學敕》。在高祖看來,儒教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價值的教育對國家政治的積極作用深遠,與道、佛比較起來,儒教是本,道、佛二教是末,他要崇本息末,崇尚儒宗。endprint
太宗還為秦王時就“銳意經籍”。武德三年,戰爭基本結束,李世民在秦王府開文學館,廣泛招引天下文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給五品的待遇。即位以后,就在正殿左面設弘文館,精選天下的儒者,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讓他們以本官兼任學士。并讓學士們在其中輪流值班,在政務閑暇時,皇帝就和學士們討論經義,商量政事,有時一直討論到深夜。又讓功臣、賢者和三品以上的子孫為弘文館學生。這樣的討論,使李世民本人也對儒學有了很深的造詣。
李世民在《遺蕭德言書》中說:“自隋季板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涂,《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所以太宗非常重視復興儒家。貞觀二年,大征天下儒士為學官。親自多次到國學館,令祭酒、博士講論儒學。學生能通一大經以上,就授予署吏。又于國學增筑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也增置生員,達到三千二百六十多人。這樣的重儒政策,使各地儒士抱負典籍,云會京師,就連吐蕃、高昌、高麗、新羅等地的貴族子弟也前來學儒,一時“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舊唐書》卷139《儒學上》。。
太宗善于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貞觀二年他就形成了關于儒、釋、道三教的歷史觀。他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于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為萬紐于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摯。庾信亦嘆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21《慎所好》。可見他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是否興儒是一個王朝生死存亡的關鍵,如果沒有儒家居中制衡,佞佛佞道,就會導致亡國之禍,故而重儒。唐太宗在《帝范·崇文》中開篇就指出:“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鮮明地表達了以儒為本,高揚儒家道統的明確意識。
儒學的傳承要靠經學。鑒于儒家典籍流傳久遠,文字多有訛謬,貞觀四年太宗就詔顏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正義》,并詔令天下傳習。除了經籍,唐太宗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設館修史,這就是《群書治要》與《隋書·經籍志》的編撰。《群書治要》是唐初著名諫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為唐太宗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書中擷取經典要義,闡明古圣先賢以德為本、修己為要的治國大綱;甄選歷代史實,既有明君用賢、忠良輔國達致天下太平的經驗,也有昏主寵佞、奸臣欺主導致朝政危亡的實錄;該書以儒家為主體,整合諸子百家,是中國古代治國安邦、匡政利民的治道思想的集大成。韓星:《<群書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現代意義》,《觀察與思考》2014年第11期。《隋書·經籍志》是以儒家為主,融合三教,在各種典籍的排列次序上,以儒家經典放在第一位,即依次為 經、史、子、集四大類,道、佛經籍置于集后的附錄位置,并說明道:“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遠致也。俗士為之,不通其指,多離以迂怪,假讬變幻亂于世,斯所以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這明確指出了道、佛為出世宗教,但與圣賢之教也有一致之處,只是世俗之人不通其深意,往往背離原有的宗旨,走入迂、怪、假、幻的歧路,造成了許多弊端。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為指導,抑其弊而不誣其利,所以就把有關佛教的資料作為四部的附錄收錄在子部雜家部分。
值得提及的是唐太宗“貞觀之治”時期的儒學是在文化多元,三教并存情形下以儒為治國的主導思想,盡管李世民都主張效法西漢的以儒治國,對董仲舒也持肯定態度,但并沒有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相反,唐太宗對非主流思想都采取寬容、兼和的態度,既在國家意識形態和民族主體信仰方面上堅持以儒家為主,兼容百家的同時,又在社會上奉行信仰自由,兼容道佛的基本國策。
四、崇 道
隋唐之際天下大亂,民間流傳“天道將改,將有老子子孫治世”等宣揚改朝換代的讖語和預言。李淵也開始利用讖語為自己的起兵反隋造勢。隋末道士中許多人認為李淵父子能取得天下,便紛紛投其麾下,為建立李家王朝效勞。如樓觀道士歧暉(558-630),在大業七年即對弟子說:“天道將改,吾猶及之,不過數歲矣。”弟子問他今后誰可能做皇帝,他說:“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后吾教大興。”《混元圣紀》卷8。大業十三年,當李淵起兵反隋入關時,他非常興奮:“此真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發道士八十余人至蒲津關接應,盡以觀中糧資唐軍。李淵稱帝后,認為歧暉資助興唐有功,“武德二年,高祖下令修繕樓觀臺,營造老君殿、天尊堂、尹真人廟,并賜田十頃,任命歧暉為觀主”《混元圣紀》卷8。。武德三年再臨樓觀臺祭祀老子并召見歧暉說:“朕之遠祖,親來降此。朕為社稷主,其可無興建乎?”《混元圣紀》卷8。于是下詔改樓觀臺為宗圣觀,并賜予帛、米以供觀中使用。李淵稱帝后,曾一再宣稱“李氏將興,天祚有應”,“歷數有歸,實惟天命”。這樣既可借神權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以宣稱李氏取代隋朝為“奉天承運”,為李唐王朝王權的正統性、合法性奠定了基礎。
李世民還為秦王時,在洛陽剛剛平息王世充,便與房玄齡微服謁見道士王遠知,王預言他會作太平天子。李世民登基后,即對王遠知特加優寵,詔在茅山建太平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太宗“玄武門之變”也得到道士的支持,所以他登基后對道士備加禮遇,稟承高祖遺業,崇道抑佛。唐初道佛二教互相攻擊,都想贏得統治者的青睞和重視,而唐初社會上則有重佛輕道的風氣。貞觀六年(632),詔令修訂《氏族志》,原因是修訂人員將山東崔姓和李氏同列一起,這使太宗感到門第輕重失宜。為了重新肯定自己的出身,并進一步明確了李氏王朝與老子的祖孫關系,他指示在重修《氏族志》時必應“崇重今朝冠冕”的撰修原則,追贈老子為始祖。貞觀十一年(637)繼李淵之后再次下詔,規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稱:“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后,齋供行立,至于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詔令集》卷113《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這個詔書表達了明確的崇道抑佛傾向,反映了唐在宗教方面的基本國策。endprint
據相關史實可以看出,高祖,特別是太宗是有清醒的政治理性的,并不真的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們之所以抬升老子,杜編祖系,拔高道教的地位,不過是借以確立自己的血緣的正統性,作為提升皇權合法性的基礎,是一種很強功利性的政治運作,還談不到信仰道教。
五、尊 佛
李淵最初因為個人原因也曾信過佛,在他為隋朝鄭州刺吏時,兒子李世民得了重病,他親自到當地大海寺廟里燒香祈愿。不過,從李淵本人的宗教觀來看,他總體上是比較理性的,其親信溫大雅曾記述李淵對待佛道的態度說:“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質疑,未之深信。”《大唐創業起居注》卷2。唐朝建立之初面臨著如何解決隋朝過度崇佛導致的僧尼劇增,寺院財富激聚,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同時太宗身邊的一些道教出身的官員對佛教的強烈批評,也逐漸使其對佛教采取了限制措施。武德九年發布詔書曰:“諸僧、尼、道士、女寇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并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舊唐書》卷1《高祖本紀》。他首先說明他的本意還是要“興隆教法”,并沒有完全否定宗教的教化作用,只是要區分真正的信仰者與混進佛道的偽爛之徒,所以不得不限制二教。從具體限制措施看,似乎佛道均衡,甚至在京城還留寺三所、觀二所,但如果考慮到當時佛道二教規模非常懸殊,對佛教來說無疑是更大的打擊。這鮮明地表現了李淵崇道限佛的基本政策。不過,由于武德九年五月發生了“玄武門之變”,李淵的詔令還沒來得及實行。李世民繼位后宣布廢止這一詔令,開始“度僧立寺,廣事弘持”。
對于唐太宗與佛教的關系,學界歷來有兩種相反的說法:一謂太宗弘贊佛教,一謂太宗實不以信佛見稱。其實唐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前后是有變化的,其佛教政策應在三教關系互動中動態把握。
太宗從小就有與佛教打交道的經歷,前述李淵到當地大海寺廟里燒香祈愿之事就是例子。太宗在平定各地割據勢力的戰爭中,也得到過地方僧侶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圍攻據守洛陽的王世充這一關鍵性戰役中,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曇宗等主動協助破城,并俘獲王世充的侄子仁則。這段經歷使他對佛教產生了某種特殊的感情。
太宗對佛教早先是肯定其正面價值,利用其教化作用輔助國家治理。在創建唐王朝的過程中,太宗勇猛善戰,軍功顯赫,同時也必然手上沾滿鮮血。即位后,他就在戰陣處廣立寺廟,超度戰爭亡靈。在相關詔書中他說:“釋教慈心,均異同于平等。……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視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陑,曾無寧歲。老弱被其桀犬,愚惑嬰此湯羅。……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于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兇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災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全唐文·為戰陣處立寺詔》。“釋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殺害為最重,承言此理,彌增悔懼。……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滅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廣弘明集》卷28《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他也檢討自己“自征討以來手,所誅翦前后之數將近一千。”《廣弘明集》卷28《唐太宗為戰亡人設齋行道詔》。他認識到佛教慈悲為懷,崇尚仁慈,能夠平等對待眾生,倡議在交兵作戰,死亡慘重的地方各建佛寺,延招僧侶,讓那些死難的亡魂,聞到晨鐘暮鼓之聲,能夠變炎火為青蓮,易苦海為甘露;他自己在戰爭中殺人太多,怕受到懲罰,以至于心懷憂懼。所以試圖通過佛教使那些游魂有所歸宿,同時對自己犯下的殺孽懺悔,借以解脫內疚之苦,使自己的心靈也得以安頓。
貞觀三年,太宗為報親恩,將自己舊宅,改建為興圣寺。貞觀四年,有詔命上宮,繡了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釋迦文佛圣像,安奉在勝光寺。佛像安座時,還設千僧大齋,供養大眾。貞觀五年,太宗又為穆太后,在慶善宮內造慈德寺,昭陵建瑤臺寺。并請玄琬法師在禁內德業寺,為皇太后寫佛藏經。貞觀八年(634)為追念穆太后,在臺城以西,真安城內建弘福寺,太宗曾親自到弘福寺為佛像開眼。在太宗為太穆皇后的追福手疏里他說:“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蓼莪》之念,何日忘之?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朕每痛一月之中……欲報靡因,唯資冥助,敬以絹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儻至誠有感,冀銷過去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后緣之慶。”《全唐文·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這里顯然是以佛教的途徑表達其孝敬感恩之情,一定程度上有某種信仰情懷。
唐太宗即位后相繼頒行度僧的詔令,因為當時經過戰亂佛教衰落,所以允許度僧來一定程度復興佛教。史料記載:“昔隋委失御,天下分崩,……朕屬當戟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全唐文·諸州寺度僧詔》。但從詔令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對僧人數量有控制,只是允許佛教有限制地復興。同時他也注重以法治教。鑒于社會上長期以來有些僧徒戒律松弛,不思佛法;假托神通,招搖撞騙;借善男信女的信佛之心,大斂不義之財等。這些違背了佛教慈悲為懷,濟世度人的根本精神。為了凈化佛門,太宗制定了一些律令,以規范寺僧。“朕情深持護,必無寬舍,已令依附內律,參以金科,具陳條制,務使法門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檢察。其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者,所司錄狀奏聞,庶善者必采,惡者必斤。伽藍凈土,咸知法味;菩提覺路,絕諸意垢。”《全唐文·度僧于天下詔》。這些措施說明太宗允許佛教發展,但這種發展不是沒有節制,而是要遵循國家基本的政策法令,即合法發展。
結 語
學界一般認為,唐初三教政策是儒、釋、道三足鼎立,這種說法稍嫌籠統。歷史地看,南北朝中后期的三教并存是一種自然發展,到了唐代,統治者對儒、佛、道采取的基本政策是三教并用。當然并用不是平均使用,而是根據三教各自的歷史淵源、思想特點、不同功能,立足于朝廷與國家的穩定,帝王的政治理性,以及帝王個人的喜好與信仰,采取了重儒、崇道、尊佛的總體政策。具體即重儒以尋求道統的合法性,確立治國理政的主體;崇道以尋求血統的正統性,為提升皇權合法性的基礎;尊佛以重建精神世界信仰,以為歸化民心的工具。大致格局是在確立儒學意識形態正統和國家民族主體信仰地位的前提下,以儒為主,以佛、道補充和輔助,逐漸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行,三元和合的局面,其中儒教居中制衡,具有主體地位,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指導和支配政治生活、公共領域的一切方面及個人生活的某些領域。后來,在面對景教等其他多元宗教的形勢下,又不斷調整,形成了以儒為主,整合多元文化,構建立體的國家意識形態體系和國民信仰體系。這充分表明唐在總體治理體系確立后,處理三教關系的方法和手段開始成熟起來。這一格局由隋代開啟,唐初高祖和唐太宗二帝奠基,歷經高宗、武周、唐中宗、睿宗的發展,到了唐玄宗開元時期最終完成。endprint
(責任編輯:周小玲)
Abstract: The Confucianism is the basic strategy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the Benign Administration of the Zhenguan Reign Period,which illustrates a typical way of Confucian governance. Tang Taizong's policy of Confucianism,Buddhism and Taois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ay of Tang Taizong's governance. Nowadays,scholar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policy was to keep the balance am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is somewhat overbroa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overall policy of Tang Taizong is reverenced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a. In particular, Tang Taizong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of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seek the orthodox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governance. He also established the legitimacy of Taoism to seek the origin, to enhance the basic imperial legitimacy. Tang Taizong showed respect to Buddha in order to rebuild spiritual belief among people, and use this spiritual belief to win peoples support. In the 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ing Confucianism as an official orthodox status and national belief subject status, the society of Tang Dynasty gradually formed the thought pattern thattreated the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body and treated Buddhism and Taoism as supplements. This pattern also can be descried a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operated in a parallel and harmony way.
Keywords: Early Tang Dynasty; Confucianism;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