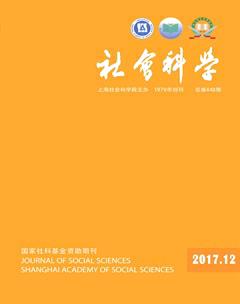論“聽”與“圣”的關系
摘 要:在“圣”達成的過程中,“聽”展現為一種能力,它具體表現為能聽、會聽、善聽等多個面向。一方面,具備高超的“聽”的能力,是成圣的必要條件之一;另一方面,凡為圣者,皆在“聽”上達到至臻境地。“聽”既是一種“德性”,又展現為一種“德行”,圣者在“聽”上具備完善的“聽德”。這不僅體現在成圣之后,也內在于主體通由“聽”而成圣的過程中。“圣”作為一種理想人格形態,具有正面價值,“聽”于是在成圣的過程中體現為一種價值訴求,對其不斷地追求與努力,使得主體在“聽”上呈現出不同的人格境界。要達成一言出,而天下莫不聽從的效果,需以“天下”為聽之對象,以公正為依據,信任為內在要求,兼顧各方面的利益,這同時也是由“聽”而“圣”的方法。
關鍵詞:聽;圣;先秦;理想人格
中圖分類號: B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7)12-0124-09
作者簡介:伍 龍,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博士后 (上海 200234)
隨著歷史的發展,“圣”作為一種理想人格形態已逐步隱退,但人們在人格的完善和境界的提升上,卻始終沒有停止自覺的追尋。當前,伴隨著經濟收入的提高,人們更加期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受人尊重的人。于是,新時期理想人格如何培塑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任何現實的問題都可以從歷史的思想積淀中尋找可供借鑒的資源。“圣”作為一種理想人格形態雖已隱退,但其實質的內涵,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內在驅動性與吸引力,卻并未完全隱退。“聽”作為一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圣”聯系最為密切的認知方式,與“圣”存在著密切的關聯。立足先秦思想的資源,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能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圣”,在當下培塑理想人格,提供重要的啟發與借鑒。
一、“聽”:“圣”的一種能力
“聽”之于“圣”首先展現為,個體在達成“圣”的過程中,所應具備的一種能力,其具體表現為能聽、會聽、善聽等多個方面。
“能聽”涉及“聽”的發生,即聽者能聽得進去,能通過耳或其他媒介將聽的內容迎接到主體的認知過程中,促使聽的產生。“能聽”和聽之“德性”有關:唯有塑造、培養耐心聆聽的品德,才能具備“能聽”的能力。圣者因具備高超的“聽德”,所以“能聽”,即對于各種聲音都能合理地予以吸納。
“會聽”涉及“聽”的方法,即聽者懂得如何運用正確的方法,踐行“聽”的行為。在“聽”的過程中,聽者往往容易受到自然性等方面的影響,從而無法正確踐行“聽”的行為。要想做到正確的“聽”,必須秉持一定的原則,堅持一貫的態度,運用相應的方法,如兼聽、衡聽等。可以看到,要想正確地踐行“聽”,需經過一番努力,這既涉及對于“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自覺,也關涉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了解、掌握以及運用關于“聽”的正確方法。
圣者在“會聽”方面,具體展現為嫻熟、自如地運用“聽”的方法,幾近完美地踐行“聽”的行為。一方面,針對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內容,圣者能靈活自如地運用相應的“聽”的方法來踐行“聽”的行為;另一方面,在完善的“聽”的行為背后,是圣者對于“聽”的方法深入而透徹的掌握。換言之,前一方面涉及的是,圣者在踐行“聽”的行為時所展現的實踐智慧,即將抽象的方法與實際的具體情境相結合,促使“聽”完美地實現。要知“實踐智慧不僅考慮普遍,而且考慮特殊”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42a10-15, in 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1, p. 1030.。它“指向具體事物,同時也意味著普遍原則與特定情境的溝通” 楊國榮:《論實踐智慧》,《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后一方面則關涉對“聽”的方法本身的理解和把握。兩者不可分割:正是因為對“聽”的方法有了深入而透徹的把握,圣者才能運用實踐智慧,正確踐行“聽”的行為。
“聽”的過程中所蘊含的實踐智慧,又具體表現為一種“善聽”的能力。所謂“善聽”是指圣者善于運用“聽”的方法,完成“聽”的行為。這里的“善”一方面體現為上面所提及的實踐智慧,即善于將方法與情境結合,促使“聽”的行為完美實現;另一方面還表現為一種積極、自覺的態度,即圣者因對于“聽”各方面的意義和價值都十分了解,故而能積極主動地促使“聽”,由“聽到”向“做到”轉化。在這一轉化的過程中,“聽”的作用才真正得以發揮和落實。
“聽”的能力所表現的上述不同面向,促使圣者在“聽”的方面達至“聰”的境地。在先秦時期,一般認為,“目”追求的是“明”的狀態,“聽”則要趨向于“聰”的境地。“視思明,聽思聰。” 《論語·季氏篇》。“目貴明,聽貴聰。” 《管子·九守》。如何算是“聰”呢?“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 《管子·宙合》。順乎中正之道地去聽,對聽聞的內容,依據一定的標準加以審查和反思,便是“聰”,否則便是“不聰”,便會“繆”。“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 《管子·宙合》。
圣者作為一種至高的理想人格,在“聽”上自然已達至了“聰”的狀態。換言之,“聰”可以說是“聽”所能達成的至臻狀態。“聰,察也。” (漢)許慎,(宋)徐鉉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0頁。“圣,通也。”(漢)許慎,(宋)徐鉉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50頁。圣即圣。因此兩字都從“耳”部。其中“察者,覆審也。”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339頁。從“圣”的“通”之意反觀“聰”,可以看到圣者在“聽”上所達成的“聰”具體表現為,圣者在“聽”上達至了“至察至明”的通達境地。立足于“能聽”、“會聽”、“善聽”來反觀“聰”,將呈現更為豐富的內容。事實上,“聽”的能力所展現的三個面向本密不可分,在相互關聯的同時,呈現出“聰”所具備的品質。endprint
首先,“能聽”是基礎,涉及“聽”的發生,唯有外在的內容被“聽”進去,才能談及“聽”的其他階段。其次,“會聽”是手段,涉及“聽”的方法,它為踐行“聽”,促使“聽”的內容向實際行動轉化提供指導。沒有“聽”的方法,便無從論及“聽”的實踐智慧。最后,“善聽”是目的,關涉“聽”的最終實現,以及將聽到的內容,積極轉化為富有成效的行動的過程。“善聽”既以前兩者為基礎,又是前兩者努力達成的方向。立足于三者的關聯,可以看到,“聰”不僅是某一方面達成與呈現“聽”,而是貫穿于“聽”的整個發生、發展以及最終實現、完成的過程。換言之,包括能聽、會聽、善聽等多個方面在內的“聽”的能力,都應達成“聰”的狀態,它不僅體現在“能聽”的階段,具備高超的“聽德”,而且展現為靈活、自如地運用聽的方法指導聽的正確實踐,故而,“聰”又與“聽”在實現過程中,主體應具備的實踐智慧緊密相關。基于此,“聰”體現出多面而豐富的意義。
“聽”作為一種“圣”的能力,并非僅僅指向成圣之后,從成圣的過程來看,“聽”作為一種能力,所蘊含的上述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已經為個體不斷培養和趨近“圣”這一理想人格助力。具而言之,“能聽”是培養個體耐下性子聆聽、聽取外在的聲音,使得“聽”的內容能夠進入聽者的認知過程,促使“聽”的發生,這一過程即是培養“聽德”的過程。個體在此階段已經通由“聽”在塑造自身的品德,并不斷培養起高超的“聽德”。“會聽”則要求聽者不斷地了解和掌握“聽”的方法,并能靈活地運用它們。在這一過程中,聽者亦逐步對“聽”的方法所具備的意義和價值予以自覺,從而將其自覺運用于實際行動。如何才能運用方法正確地踐行“聽”的行為,是“善聽”所涉及的問題,在不斷面對和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主體逐步獲得了關于“聽”的實踐智慧。與此同時,聽者也對“聽”自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自覺。
可見,在運用上述能力(能聽、善聽、會聽)的過程中,聽者不斷成為一個具備高超“聽德”,能耐心而全面地迎來“聽”的內容,對“聽”的方法既有透徹的了解、掌握,又能積極、主動、正確地將其運用于實際行動,指導“聽”的行為的實現和完善,充分掌握了“聽”意義上的實踐智慧,并對“聽”自身的意義和價值有充分自覺的人。這樣的人在“聽”上即趨向于“圣人”的狀態。換言之,正是對“聽”的上述能力的掌握和運用,個體才得以不斷地向“圣”這一理想人格邁進。此外,從“圣”的字型來看,“聽”是“圣”最為基本而原初的重要能力 參見貢華南《中國早期思想史中的感官與認知》,《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由此看來,“聽”的上述能力的培養,可以說是成圣的內在要求:要成為圣者,就應具備完善的“聽”的能力。可以說,“聽”的能力的培養和煅造,成為了“圣”達成過程中的必經階段。
二、具備“聽德”的“圣”
“聽”作為“圣”具備的一種能力,同時造就了其高超的“聽德”,這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圣者既有高超的聽之德性,又展現出完善的聽之德行;另一方面,在不斷由“聽”達成“圣”的過程中,借助“聽”,主體得以具備完備的“聽德”,從而成“圣”。前者體現出“聽德”是“圣”的內在品質與要求,后者則展現出在由聽塑德,進而成圣的過程中,“聽”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聽”作為“圣”的一種能力,首先表現為“能聽”,而“能聽”簡而言之即指能聽得進去。進言之,是指能由“聽”將外在的內容,迎入聽者的認知過程,這一點即與“聽德”相聯系。圣者作為理想的人格形態,其在“聽”上具備高超的“聽德”,無論是稱贊的、肯定的意見,還是批評的、反對的聲音,都能通過自身的理性判斷,被合理地吸納。“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賢圣莫能聽。” 《韓非子·難言》。真摯、懇切的言語,多是忤耳、逆心的,唯有圣者、賢者才能合理地由聽予以吸納。圣者所具備的高超“聽德”,從來源上確保了“聽”之內容的全面和完整,從而為“聽”的正確踐行提供基礎。可以看到,這里的“聽德”涉及兩個方面,即德性和德行。圣者正是因為在“聽”上具備很高的德性,才能對聽之內容予以合理而全面的聽取。與之相應,這一正確的“聽”的行為因其內在德性的支撐,使其展現為一種德行。
不僅是聽的發生(能聽),而且運用聽的方法踐行、實現聽的行為(會聽、善聽),都彰顯著圣者所具備的“聽德”。如前所述,“聽”的方法,涉及聽的態度和原則,以及具體的“兼聽”、“衡聽” 對“衡聽”與“兼聽”,《荀子》一書有較為豐富而深入的闡述。參見伍龍《論荀子哲學中的“聽”》,《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都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了判斷和篩選,并最終被最大限度的廣泛聽取,從而使得聽到的內容在轉化為實際行為后,能最大可能地兼顧各方面的利益。可以看到,在這一過程中,圣者能靈活地運用“聽”的方法,完善地踐行“聽”的行為,他能運用一定的標準對“聽”的內容進行判斷,并實現“兼聽”和“衡聽”,從而最大程度地實現公平正義,這些“聽”的行為同時也是一種德行,彰顯著圣者所具備的“聽德”。
與“聽”作為一種能力存在一樣,“聽德”并不僅僅是在“圣”這一理想人格達成之后,才具備的一種品質。在“圣”不斷達成的過程中,“聽德”一樣起到著重要的作用。在不斷修己之德性,善己之德行的過程中,個體才能不斷地趨近“圣”這一理想人格。具體來說,當我們面對不同的聲音時,因為自然性的驅使,總會對肯定的、贊揚的意見有所偏愛,而反感于批評、否定的聲音。在克服這一自然性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了解并掌握了“聽”的標準,且對標準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有所自覺;另一方面,我們會主動地運用這樣的標準,兼而聽之,避免偏聽偏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努力做到“兼聽”和“衡聽”。
在這一過程中,首先,個體將自己的自然性不斷向社會性歸正,促使自然性更好地存在。進言之,個體得以在博弈自然性和社會性的基礎上,使得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而非僅僅服從于自然性的動物性存在,從而使自己更好地在世。其次,個體對于“聽”之標準,即禮義、正道都有了了解和把握,對其所具備的意義和價值有了充分的自覺,進而運用這一標準對“聽”的內容進行判斷和篩選,真正做到正確的兼聽和衡聽。第三,“聽”并不僅僅停留于“口”之上,即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并不僅僅表現為聽取并予以口頭上的承諾,而且通過將聽到的內容貫徹于實際的行為,最終落實“聽”的作用和意義,如此便實現了從“聽”到“言”,再到“行”的轉化。這一意義上的“行”,以“聽”為依托,又將“聽”行為本身予以推進、擴展,安置于更為廣泛的行為中。不難看到,上述三點都促使個體不斷由“聽”達成“圣”:博弈自身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對禮、道等標準予以了解和把握,做到兼聽、衡聽,實現言行一致等。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不斷地由“聽”修習自己的德性,完善自己的德行,促使人格狀態向“圣”趨近。endprint
三、價值訴求的“聽”和人格境界的“圣”
“聽”在一般情況下,被理解為一種認知途徑和手段,而“聽德”之“聽”則更多地展現為一種道德能力。 參見伍龍《論“聽”與“德”的關系 ——立足先秦視域的考察》,《應用倫理研究》2016年第1期。相較而言,“聽”在與“圣”的關聯中,則呈現為一種價值訴求。
“圣”作為一種最高的理想人格,一直是中國古人不斷追求和趨近的目標,孔子便被后人視為“圣人”的典型代表,他既有深厚的仁德,又在各方面趨近智慧之境,“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基于此,“圣”被賦予積極而正面的價值,“成圣”則被視為一種有意義,有價值的努力。在這一過程中,個體不斷地趨近和獲得正面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聽”展現為一種價值訴求,它是獲得“圣”這一具有正面價值的有效途徑之一,亦貫穿于個體對“圣”這一理想人格狀態不斷訴求,并積極趨近的過程中。
一般而言,一個人總是希望成為在德性和德行上有修養的人,通過不斷地努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趨近理想的人格狀態。在這一過程中,“圣”作為最高的人格狀態和精神境界,無疑具有指向性和目標性。基于人的這一自發自愿的內在要求,“成圣”就展現為一種自覺自愿的行為,同時,“聽”又是成圣的重要途徑之一,所以這一過程便表現為個體自覺、主動地運用“聽”達成“圣”。因為自覺、主動,所以,“聽”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可靠而富有成效。一方面,主體會積極運用“思”的能力對“聽”的內容,依據一定的標準予以取舍;另一方面,主體也會將“聽”的方法運用于“聽”的具體行為,并進一步促使“聽”的內容向實際行動轉化。
不難看到,在這一過程中,“聽”已不再僅僅只是一種認知手段,同時還成為了追求“圣”這一目標的途徑,于是,“聽”呈現為一種內在的價值訴求,即要通過“聽”來積極主動、自覺自愿地訴求“圣”這一具有正面、最高價值的理想狀態,它并非來自于外在的強迫,而是出自于內心的追求和趨向。立足于“聽”的作用來看,個體之所以通由“聽”來修德,培養自己能聽、會聽、善聽等能力,從而向“圣”靠近,乃是因為它可以幫助個體,不斷地追求和獲得“圣”所具有的正面價值,幫助個體逐步向“圣”趨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聽”本身也被賦予了價值內涵,成為一種具備正面意義和價值的行為。具言之,作為通向“圣”的途徑之一,它為個體成“圣”提供了可能,聽者可以通過“聽”來修己之“聽德”,不斷煅造德性,完善德行,自覺“聽”的標準,收獲“聽”的智慧,這都體現著“聽”的正面價值。“聽”在幫助個體成圣這一點上,同時證明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當我們反觀當下,這一問題的思考將可能面臨一個困境:現今是否還存在對“圣”這一理想人格,自覺自愿地不斷追求?換言之,當下,是否還有一個所謂的“圣”的人格理想,在指引著人們不斷地向其靠攏,以此為目標引領人們不斷在人格上努力前行?這便涉及到“后圣賢時代” 所謂“后圣賢時代”,是指“圣賢”作為一種理想人格和價值目標,被人們自覺自愿追求的時代已不復存在,但當下,依然會涉及到理想人格的培養和塑造等問題,故而,以“后圣賢時代”這一名稱來指示,當前時代在這一問題上的特點。的成圣問題 在這里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如果“圣”的追求在當下已經不再可能和必要,那么“圣”與“聽”關系的討論將失去現實的意義,由此相關論述的必要性亦將受到質疑。,涉及到當下我們如何培養理想人格的問題。一方面,現今,“圣”作為一種最高的價值目標和至臻的理想人格,隨著歷史的發展已逐步隱退。與古人迥異,他們樹立了一個孔子那樣的圣人,作為生活中的楷模,讓有志者不斷地趨近和奮進。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當下,以“圣”的內在、本質的意義為指向,不斷地修習自身的德行,完善自身的行為,使其成為具備德性的德行,進而在修習的過程中,提升自己的人格水平和精神境界,讓自己成為一個品德高尚,彬彬有禮,有人格魅力的人,依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標。換言之,從人的自我要求來看,個體總是希望成為一個在精神層面和行為舉止上,更完善、更優秀的人,這樣的修習在幫助我們更好地與他人、自然相處的同時,也幫助自身更好地在世。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雖然沒有了古代嚴格意義上的“圣”的概念,也沒有樹立起一個如“孔子”那樣的圣之楷模,但人們依然在實質層面上,有一種向“圣”靠攏的自發要求,故而在這樣一個后圣賢時代,一樣有成就圣賢人格的問題。只是這個“圣賢人格”的追求過程,已不再像古代所說的,成為像孔子那樣的人,而是轉變為更為廣義的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培養和樹立理想人格的問題。“與古代要使人成為圣賢、成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過努力都可以達到的。” 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頁。對新時代,人們如何塑造理想人格這一重要問題,馮契先生做出了自己的理論回應,提出了“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論”。
借助這一理論,“聽”與“圣”的關系得以呈現更為豐富的內容。首先,如前所述,通過“聽”,我們可以不斷塑德,進而提升德性、完善德行,并逐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塑造理想的人格狀態。“聽”在這里作為一種路徑所提供的可能性,并非虛無縹緲,玄乎不定,而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因為“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認知行為,經常被我們使用和實踐。我們常能通過“聽”迎來外在的“聲”,并對其加以認知。在踐行“聽”的過程中,更好地認知自己和外在世界,由此向“圣”靠攏。這一靠攏具體表現為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狀態,包括內在人格和外在行為。總而言之,作為一種提升精神境界,塑造理想人格的途徑和方式,“聽”是切實可行,亦是觸手可及的,它具有實踐層面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前者源自“聽”作為一種日常的認識方式,常被人踐行;后者則因為“聽”在展開過程中,具體的實踐方法。所以,通過“聽”而成就理想人格,亦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過努力都可以達到的”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頁。。endprint
其次,在通過“聽”而成“圣”的過程中,顯然內蘊著一個“由聽塑德”的環節。從結果上看,圣者應具備高超的德性和德行;從過程上來看,要想成為圣者,需要在“德”上下功夫,修習德性,完善德行。“聽”作為一種行為,在不斷踐行的過程中,同時也為聽者在“德”上趨近完善,進而為“塑德成圣”提供了契機和可能:個體在不斷修習聽之德性的同時,也踐行著聽之德行,這從“德”的角度促進個體成圣。馮契先生在構建“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論的過程中,反復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在考察培養實現這一人格的基本途徑時,馮先生便指出“實踐和教育相結合是培養自由人格的根本途徑”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311頁。。他進一步認為“實踐是人和自然、主體和環境的交互作用”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頁。。在這一過程中,主體并非是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地將外在的環境、自然等對象化,從而由自在走向自為。“聽”作為一種行為,首先是實踐的。在踐行“聽”的過程中,個體不斷地通過“聽”將外在的自然之聲,人為之聲,以及聲所造就的環境,迎入到自我的認知過程中來,通過不斷地消化和理解,完成“由聽塑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聽”并非是被動地聽取,而是主動地“聽納”,即主體積極主動地運用“聽”來“塑德”,逐步塑造理想人格。因為如前所述,對于廣義的“圣”的追求,是每個人內心的愿望,為了達成這一理想人格狀態,主體的行為是主動而自覺自愿的。在這一過程中,最終實現的亦是外在自然、環境的對象化,而主體本身也逐步由自在走向自為。
“圣”展現的不僅是一種存在狀態,而且呈現為一種人格境界。從這一意義出發,“聽”又與境界的提升相關:在不斷修習“聽德”的過程中,個體也達成了不同境界的“聽”。在最初階段,聽者可能需要耐住性子去聽,克服某些自然性,并將其向社會性歸正,但是隨著“聽”的行為的不斷展開,聽者對于“聽”的意義、價值都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和自覺,對于“聽”的方法有所探索和把握,于是,聽者不再是克制、強迫自己去聽,而是逐步自覺、自愿地去“聽”,更為理性地將聽的方法運用于聽的行為,促使“聽”的真正、正確地實現。可以看到,從強迫、克制到自覺、自愿,聽者提升著自己“聽”的境界。待到至臻于圣的時候,則一方面“不勉而中” 《禮記·中庸》。,即不用勉強地去聽(如克制自己的自然性去聽等),便可自然而正確地踐行聽的行為,達成聽的效果;另一方面,從抽象方法到具體行為的過程中,圣者亦能靈活地將兩者結合,促使“聽”的實現。在“圣”之境界中,聽者可能已忘卻了“聽”之方法的規定,包括相應的標準、態度,以及具體的措施,但其聽的行為皆能正確,符合標準,達成“聽”最好的效用,這便體現為“聽”上的“從心所欲不逾矩” 《論語·為政》。的狀態。
縱觀整個過程,可以看到,在個體通由“聽”向“圣”邁進的過程中,聽者自身的精神境界也在不斷提升。雖然要達成最高的“聽”之境界相當艱難,但個體在踐行“聽”的過程中,正逐步地提升著自身的德性,包括人格狀態和精神境界等,完善著自己的德行,向著這一目標趨近。可以看到,正是通過“聽”這一實踐行為,一些準則和規范,如耐下性子去聽,將聽之方法與聽之行為結合等,才最終“習以成性”,形成了人的品德,這也是馮契先生在“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論中強調的。 參見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頁。可以看到,這一過程,實質上表現為“真誠地、鍥而不舍地在言論、行動、社會交往中貫徹理論,以至習以成性,理論化為自己內在德性,成就了自己的人格” 馮契:《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的過程。
最后,由“聽”而圣的過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不斷反復,循序展開的過程。在不斷地通過“聽”來修德性,善德行,從而提高人格境界的過程中,聽者總是會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和干擾,比如自然性的驅使、影響,總會對贊賞的言辭有所偏愛,總想不顧具體情境地聆聽美妙的“樂”。有時,自然性能因為理性的作用,得以克服,并被歸正,但有時,可能呈現更為復雜的情況,即自然性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壓倒社會性,占據上風。正因為如此,所以才需要個體不斷地通過“聽”來修習自身的德性。德性的提升本身呈現為一個過程,德行的完善需要逐步實現,這都決定了“聽”的行為需持續性的展開。事實上,也唯有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夠在不斷運用“聽”修德的過程中,逐步成圣。馮契先生也指出:“人的自在而自為不是說一旦歸于自然就完成了,它是不斷地反復的,人的才能、智慧和德性是不斷提高的,是一個無限前進的運動。” 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頁。而這樣反復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說,源自于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及個體自身的多面性與復雜性,后者(世界與個體的具體、真實的存在狀態)是前者(反復的過程)的本體論根據。也正因為如此,“聽”要真正成為成“圣”的切實可行的途徑,就需要聽者在將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過程中,持之以恒,堅持不斷,這是個體通由“聽”錘煉出的意志力,它同樣是成“圣”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質。
可以看到,借助馮契先生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論,“聽”與“圣”的關系得以在多個層面豐富地呈現。這一方面體現出馮先生理論自身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彰顯了“聽”作為趨近廣義“圣”(一種理想人格狀態)的一種途徑,所具備的有效性。理想人格狀態,既是指達到人格的自由,實現真善美、知情意的統一,又是指實現個體由自在到自為的轉變。“由聽塑德”的過程,促使主體德性不斷提升,在化理論 這里可以具體理解為“聽”的具體方法。為德性的過程中,成就自由的人格。“聽”外在之聲,包括自然之聲和人為之聲,所獲得的美感、享受,以及實現的與他者的和諧共在,幫助主體逐步實現真善美、知情意統一的理想人格。在這一過程中,主體并非總是被動而為,“聽”更多地展現為“一種主動的賦予創造性” 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頁。的實踐行為。通由它實現的是,“聽”之主體在迎接不同之“聲”后,形成的在“聽”之層面的個性,這一“個性”幫助主體不斷地達成理想人格,在轉化外在之聲的過程中,由自在走向自為。endprint
四、圣而后天下聽之
“聽”可以被理解為聽取、聆聽之意,由此出發,其展現為認知途徑、道德能力和價值訴求,但同時“聽”還可以被詮釋為“聽從”、“服從”。前一種意義使得“聽”一方面成為達成“圣”的重要路經,另一方面成為“圣”所應具備的重要能力。后一種意義,使得“圣”在達成之后,其所言之語,所踐之行,都極具說服力和規范性,使得他者愿意聽取,進而聽從,并以此為楷模和目標,不斷趨近。當“圣”和“王”相結合,即王者亦是圣者時,其所言之命令,皆會被聽從、服從。消極地說,若不聽從這樣的言論,則可能導致嚴重的后果。“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圣之言也。” 《管子·霸言》。圣者之言辭一出,聽之則國家長久,不聽則有亡國的危險。并非僅僅是出于消極后果的被動壓迫,而且因為圣者自身具備的高超德性和德行,使其在道德意義上成為了模范,個體出于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和追求,自覺自愿地向這一目標趨近,付出努力。聽者一方面對不聽所導致的嚴重后果有所了解和警覺,另一方面也是發自內心的甘愿聽從,并積極效仿。基于此,圣者能達成“遠不不聽,近無不服” 《管子·霸言》。的效果。如果說,前面所言及的“圣”更多地表現為個體的理想人格狀態,那么,這里的“圣”則與政治實踐相聯系,從“圣”轉變為“圣王”,所以,“聽”的意義也從聽取、聆聽擴展到了聽從、服從,從而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 這里亦涉及到前面所論及的問題:當下的時代已不再有“圣”這樣一個角色設定,即我們的時代沒有一個如孔子那樣的圣者,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物,讓人們學習和趨近,但不可否認的是,如在“聽”和“德”的關系所提及的那樣,當一個人在通過“聽”不斷提升了自己的德性,完善了自己的德行后,其所說之言,所踐之行,則具有不同尋常的說服力和范導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因為如此,個體才要不斷的錘煉自己的“聽德”,包括德性和德行兩個方面,從而在提升自我品性、品行的同時,使自己具有話語權和權威性。所以,由此出發,雖然不再有“圣”之具體人物的設定,以及由此而引來的追求和努力,但是從個體自身角度來說,依然存在一個提升自我之“德”,從而使得自己之言、行,能夠被人“聽”的維度。
那么,聽者應通過怎樣的方法,才能達成“圣者之言”呢?首先,需做到“合而聽之”。“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圣。” 《管子·君臣上》。個體在聽取內容的時候,不能任由自然性的驅使而偏聽偏信,應努力做到“聽”意義上的“合”,因為“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否相濟” 黎鳳翔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65頁。。唯有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才能權衡各種得失,為正確而理想的決策提供保障,這一內涵與前面所提及的“兼聽”相通。這里予以“合”的對象應指向天下,換言之,“合”并不僅僅是指多聽幾個人的意見和聲音,而應以“天下”為懷,廣泛聽取百姓的呼聲,兼顧天下民眾的利益。“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 《韓非子·奸劫弒臣》。一個圣明的君主,以天下百姓的呼聲為自己聽的內容。事實上,也唯有如此,圣者才能做到“無所不聞”,從而在“聽”上達至超凡的境界,“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 《管子·九守》。。通過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個體不再局限于自己之獨耳,而得以擴展到天下百姓之眾耳。如此一來,天下百姓所聽到的聲音,都能被我聽到,聽者于是做到“無所不聞”,這個時候的“聽”已趨向于“聰”的狀態,“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 《韓非子·法定》。。
以天下為聽的對象,展現“聽”之內容廣博性的同時,其行為本身還應遵循一定的態度,這便是“信”。其具體表現為,在“聽”的過程中,聽者應從內心給予“聽”的對象以信任,《管子》已有鑒于此。圣者是對天地四時之“道”有深入把握的人,“唯圣人知四時” 《管子·四時》。,因順乎天地之道而行,故其行為皆“正”,在用人方面亦能知人善任。如何可知君王已進入“明”、“圣”之境了呢?“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圣” 《管子·四時》。。這里的“聽信”,一方面是指在選賢舉能的基礎上,廣泛聽取他們的正確意見;另一方面,要求聽者應對聽之對象報以“信任”的態度,“即聽其言,又信其事,所謂為圣” 黎鳳翔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38頁。。從一般意義上說,在聽的過程中,如果僅僅只是“聽”,但并不“信”,那么,面對言說的對象,聽者將可能報以一種敷衍的“聽”。唯有加入了內在的信任,才能促使言說者更為誠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將促使聽者更好地通過“聽”,收獲更多真誠的意見。
從君臣關系來看,這種“信”亦具互動性,即不僅君上應“信”其臣,而且臣下應“忠”其君,唯有如此,臣子才能獲得君主的信任。否則,將導致其言不被聽,危及國之社稷。“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 《管子·匡君大匡》。此外,圣者以天下為懷,達成“無所不聞”的“聰”之境地,在“聽”的層面呈現圣人之境,這種以“天下”為聽之對象的態度,內在地涉及“公”,展現出“天下為公”的氣象。“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管子·內業》。圣者之所以能夠一言出而天下定,乃是因為其言以“公”為基礎,即所說之言,建立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之上,這體現出“公正”。這里的“公”,可以說是“合而聽之”、“兼聽”、“衡聽”等方法在“聽”的過程中運用的結果。換言之,“合”天下之聲音而聽之,兼而聽取廣泛的意見和建議,都是為了實現“聽”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基于此,不僅圣者之言能為天下聽之,而且其行亦極具說服力和范導性,讓他者自覺自愿地向其靠攏。
《尚書》中曾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尚書·周書·泰誓中》。天之所聽,乃源自民之所聽。換言之,聽取百姓的聲音,實際就是在聽天之呼喚。百姓之聲,指向天下民眾之生存疾苦。作為圣者,在自我修身的過程中,并不僅僅以個體的完善為目標,同時也應心懷天下。遵從天之召喚而行,在這里即表現為遵循百姓的聲音而行:唯有廣泛聽取百姓的呼聲,才能在言說、行動時,得到百姓的聽從、服從與擁護,“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將聽民而已矣” 《韓非子·顯學》。。所謂“先聽天下,而后天下聽之”。進言之,這里的“天聽”更多地與“天道”相涉,是由“聽”接續、體味、把握天之大道。與之相對,“民聽”則更多地關涉“人道”,是通過聽取百姓的呼聲,體察民情、事理。從“民聽”到“天聽”,體現的是人道與天道的相通、融貫。從這一理解出發,天道的體察,不再那樣神秘,而是在聽取民聲,體察民情,體味人道的過程中迎來。由此亦可發現,“聽”不僅與“德”、“圣”,而且與“道”存在密切關聯,“聽”也由此而彰顯出其形上意蘊。 “聽”與“道”的關系是另一個重要問題,當另做文單獨述之,此處不贅。endprint
綜上所述,通過“聽”個體不斷地趨近“圣”的狀態。當我們將“圣”做廣義的理解,放在當下時代,具體予以考察時,不難看到,“聽”作為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徑,其所具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有效性。在這一過程中,聽之主體不斷地把握“聽之道”,一方面正確地實踐“聽”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在這一過程中生成和獲得智慧。在馮契看來“智慧使人獲得自由” 馮契:《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這具體表現在“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馮契:《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頁。上。由此可見,主體通由“聽”達成“圣”的過程,同時也是通過“聽”獲得智慧的過程,個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獲得自由,包括勞動自由,人格自由等,最終成就理想人格。在這個過程中,主體將“聽”之理論轉化為“聽”之方法,又將這一方法最終內化為自身的“聽德”(包括聽之德性與聽之德行),從而實現廣義的“圣”,即所謂的“理想人格”。于是,“由聽成圣”的問題同時可以理解為“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的問題,這從一個側面體現出“聽”所蘊含的意義與價值。
(責任編輯:周小玲)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heng”, “Listening” as a kind of ability which express many aspects such as can listening, know how to listening and good at listening.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skill of listening is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become “Sheng”.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e people who become “Sheng” will have the perfect skill of listening. “Listening” also reflects a kind of virtue. Stand on this point, “Sheng” will have a perfect virtue about listening which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Sheng” , but also embodies in holiness. “Sheng” as a kind of ideal personality which has the valuable, so listening becomes a kind of value pursuit in the process of “Sheng”. The constant pursuit and efforts to make the people reflects different realms of personality in “Listening”. To reach the condition which the people say, all the world will be object to listen to, people should listen the world firstly, basic on the justice, trust a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get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this is also the way to reach the “Sheng” through the listening.
Keywords: Listening; Sheng; Pre-Qin; Ideal Personal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