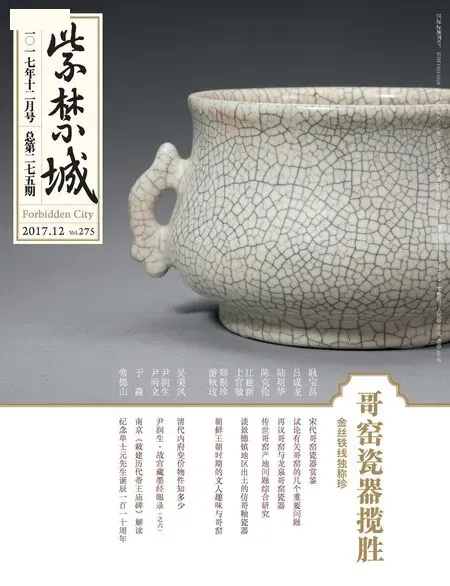南京《敕建歷代帝王廟碑》解讀
于 淼
南京《敕建歷代帝王廟碑》解讀
于 淼
南京歷代帝王廟于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初創,正殿崇祀歷代開國之君共十七人。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年)再建于欽天山(雞鳴山)之陽,立有《敕建歷代帝王廟碑》(以下簡稱《帝王廟碑》)一通,時任國子監祭酒的宋訥奉命撰寫碑文。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南京歷代帝王廟廟祀停罷,后因朝代更迭,廟址被毀,石碑亦下落不明。其外觀形制雖不可考,但所幸碑文內容被載于明代文獻中得以保存。
南京歷代帝王廟為歷代帝王廟之祖型,北京歷代帝王廟是其延續。清朝歷代帝王廟的帝王祭祀體系進一步發展完善,與南京舊廟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對南京《帝王廟碑》的研究與解讀,是探尋歷代帝王廟歷史變遷及明清兩朝統治者帝王觀的重要內容。
《帝王廟碑》概述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一舉結束了宋元時期北方少數民族貴族集團持續統治中國北部和全中國長達四百余年的歷史,重新恢復了華夏漢民族的統治地位。在這一背景下,為了彰顯中華一統帝系的歷史傳承,標榜明朝的正統地位,洪武六年八月,朱元璋決定在南京修建一座歷代帝王廟,集中奉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世祖,共十七位帝王。
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命人于欽天山之南對歷代帝王廟進行重建。至于為何棄舊蓋新,原因有二:其一,廟址不佳,褻慢神靈。結合碑文「相舊廟地介
乎通衢,褻而弗嚴」,「帝王功德,于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等語可知,帝王的功績與德行,昭彰于天下,
應該有一座清凈高潔的廟宇,將他們的神靈供奉在內,以展示后人對他們的崇敬。但舊廟所在地臨近街衢,環境嘈雜,既不莊重,也不嚴肅,可以說是對神靈的輕慢與褻瀆。其二,意外遭火,建筑被毀。據《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十一年二月戊辰日,「歷代帝王廟及上元縣
治火,延燒官民居室。詔賜被災者鈔有差」。(《鈔本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九,線裝書局,二〇〇五年,頁一七二)文
中雖未說明起火原因及損毀情況,但通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仍對歷代帝王廟進行祭祀的情況來看,廟宇并未完全燒毀。不過對于以木結構為主的中國古建筑來說,這場火災無疑令廟貌受損,有礙觀瞻。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新廟開始動工,朱元璋親命開國大將崇山侯李新前去督建,于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年)五月建成。時任工部尚書的秦逵于當月三日
上奏明太祖朱元璋,請撰文以記之,并將文章鐫刻于石碑。隨后,朱元璋敕命國子監祭酒宋訥為再建歷代帝王廟一事作文記述,遂成《帝王廟碑》。
南京歷代帝王廟現已不存,《帝王廟碑》實物更難尋蹤跡。但碑文在《西隱集》與《皇明經世文編》(以下簡稱《皇編》)均有錄入。其內容:第一,交代了歷代帝王廟初創及宋訥奉敕撰記的背景,并記錄了新廟建成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第二,通過與上古時期祭祀制度相對比,突出歷代帝王廟恭嚴其祀,正名定統的特點,還對廟內祭祀場景進行了描寫;第三,闡述了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說明入祀及弗祀的緣由,以「大公至正」、「度越百王」等語彰顯明太祖朱元璋的光輝形象;第四,以四言詩句贊恭作結,贊美歷代帝王的功德,祈求諸神護佑大明,永治天下。從而達到事神以誠,人神致喜的目的。
宋訥其人
宋訥(一三一一年~一三九〇年),字

雞鳴山圖采自《洪武京城圖志》南京歷代帝王廟屬“十廟”之一
仲敏,北直隸滑縣(今河南滑縣)人。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學習刻苦,經史子集無不披閱。元至正年間中進士,為鹽
山(今河北省東南部)知縣。后為避兵燹而辭官歸家。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朱元璋下令征召名儒十八人,編修《禮》、《樂》等書籍,宋訥參與了編撰工作,任務完成后不愿擔任官職而歸鄉。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年)十月,在杜敩的舉薦下,宋訥出任國子助教。在任教期間,宋訥講授儒家經典,不僅條理清楚,語言簡明,生動形象,又能深入淺出,融會貫通,為當時就學者所推崇。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宋訥被晉升為翰林學士,奉命撰寫《宣圣廟碑》。朱元璋看后對碑文大加贊賞,對宋訥本人也贊不絕口。同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南京歷代帝王廟圖采自《大明會典》

宋訥像采自《古圣賢像傳略》
明初,國子監數任祭酒皆治監不利,致使業績萎靡。在此情況下,以文辭莊重,責任感強著稱的宋訥便成為了朱元璋心目中祭酒一職的不二人選。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五年)正月,宋訥被升為國子監祭酒,朱元璋敕諭,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特命為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一,頁五二~五三)
朱元璋把明初人才培養的重任交與宋訥,足見對其德行、學識的信任與肯定。而宋訥也沒有辜負朱元璋的信任,很好的秉承了朱元璋的意志,以「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一六四,《西隱集》卷七,頁九〇七)為教學方針,逐漸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學方法。宋訥工作惟日孜孜,以校為家。《明史·宋訥傳》中記載:「(訥)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
恒止學舍。」《皇明開國臣傳》云:「上簡用公,特賜敕,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并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明書》(《罪惟錄》)載:「訥身言并教,寢食學廂,不輟,一時士皆適用。」翰林學士劉三吾在宋訥的墓志銘中稱:「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家。」
(《西隱集》 附錄 《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宋先生墓志銘》頁九二七)
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年),宋訥卒于任內,終年八十歲,朱元璋十分痛惜,親作祭文,還命官員在沿途進行祭奠。正德年間,追封謚號文恪。
「天命」論在社會生產力落后的古代,人們對于「天」的敬畏和信仰具有社會普遍性,因此新舊王朝交替之際,統治者總是想方設法證明自己受命于天,用來籠絡人心。早在西周時期便出現了「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的「天命」思想,漢
關于碑文的一些思考
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晉人干寶在《晉紀》中稱:「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茍有代謝,非人事也。」由此可見,古人認為人世間君王的權力皆來自于「天」,即君權神授。而帝王作為「天」的代理人,自稱「天子」,是遵奉天命,治理天下。
作為「天命」論的信仰者,朱元璋在元末的農民戰爭中就將「天命」論作為戰爭指導思想之一,用「天」的「權威」來動員反元隊伍,鼓舞士氣。但當江山坐穩,奪取皇權后,「天命」論的作用就發生了轉變。作為證明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依據,朱元璋曾多次強調,元明鼎革是「天命」所致,順天應人,以此標榜自己受命之正,進一步取得政治認同。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御奉天殿大宴群臣時宣稱:「朕本布衣,以有天

國子祭酒宋公(宋訥)像采自《三才圖會》
下,實由天命!」洪武七年八月,朱元璋親祭歷代帝王廟時稱:「元璋本元之
農民,遭時多艱,憫烝黎于涂炭,建義
聚兵,圖以保全生靈,初無黃屋左纛之意,豈期天佑人助,來歸者眾,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師北征,遂定于一。乃不揆菲德,繼承正統,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明太祖實錄》卷九二,頁四三一)

明人繪 明太祖朱元璋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廟碑》碑文開篇稱「粵自上古,神圣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即自遠古時代開始,歷代帝王相繼興起,天子作為「天」的代理人,管理人間事物,得以開創太平天下。又以「欽惟圣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受命代興,或禪或繼承」等語闡釋,無論是君王整頓綱紀,樹立準則,還是朝代交替興起,有序更迭,都是秉承于「天命」。又言:「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后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所謂「官天下」是指傳說中的五帝禪讓,而「家天下」則是自夏商周三代開始的世襲傳承。但無論是禪讓還是世襲,實際都是「天」的意志,是不可抗的客觀必然。
宋訥以「天命」思想,與朱元璋的「天命」論相呼應。將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相統一,論證以明代元是「天命」授予,順從天意,將朝代的更迭歸結于「天命」轉移,從而加強對中央政權的敬畏感,極力強調大明政權的正統性、合法性和神圣性。這一做法在鞏固政權,收攏人心,調節社會關系,穩定政治局面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以滿足統治者在政治上的需要。
「大一統」論中國歷史久遠,帝王眾多,歷代帝王廟入祀帝王應如何甄選,自然要有一個選祀標準。這一問題在碑文中并未直接回答,但通過解讀,我們便可發現其中規律。
《帝王廟碑》碑文載:「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即三皇、五帝、三王的相繼更替,漢、唐、宋的交替興起,直到元朝,都能夠一統天下,將大統接續傳承下來,皆是上天的庇護和保佑。三皇、五帝、三王作為古圣賢王,自然要進入歷代帝王廟,無需贅述,余下的漢、唐、宋、元則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王朝,而分裂及割據時期王朝皆不在入祀之列。由此可見,「大一統」乃是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之一。
從中國歷史進程來看,中國古代最輝煌的治世和盛世多出自于統一王朝,創造了偉大的文化業績。從王朝享祚時間來看,自夏商周至元明清,大一統時期近三千六百余年,而分裂割據時期約七百一十余年,不到統一時期的五分之一,足可證明「大一統」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是主流與常態。「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中華文化最基本的思維觀念以及中國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和價值取向,一直是中華民族發展的總趨勢,中國歷史演進的主旋律。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國家統一的心理特質。
明太祖朱元璋將「大一統」作為入祀歷代帝王廟的標準,原因也許可分為以下幾點:第一,將「大一統」作為最基本的政治目標,從精神層面強調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宣揚其繼承帝統的合法性,履往圣賢君之足跡,將自己納入到「一統」之緒當中;第二,以「大一統」為由,將元朝合理的劃歸到中國正統系列之內,巧妙的避免了「華夷」之辯的民族觀問題,令元世祖忽必烈與中原歷朝圣君一體崇祀于廟中,這一做法對于當時尖銳的漢蒙民族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第三,希望在「大一統」思想的前提下,以中原華夏制度為核心,在政策、經濟、文化等方面,樹立起不分華夷、不分中外、皆是國人、皆是一家的觀念,進一步促進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的團結。
「功德」論在中國封建歷史中,曾經有一些在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后實現短暫統一的封建王朝,如秦、西晉及隋,他們也被史學家們歸入「大一統」王朝之內,但這三朝卻未能入祀歷代帝王廟,這又是為什么呢?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簡單了解一下朱元璋的帝王觀和歷史觀。
在寧王朱權奉敕所著的《通鑒博論》中,對于西晉有以下評價:「嗟乎!儲嗣庸才,公輔近局,藩鎮地大,法制不修,風俗衰頹,而禮度不立……司馬氏以陰賊廢弒,取人之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酒色,保養奸回。風俗尚虛浮,士大夫賤名檢,廉恥道喪,貨賂公行,罪積數世,而功德不及于民。」而在《明實錄》中也記載了朱元璋對秦、隋兩朝「失德」的抨擊與批評。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朱元璋曾命楊訓文、滕毅二人集古無道之君,如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并敕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鑒。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明太祖實錄》卷十七,頁七〇)洪武元年七月,朱元璋與侍臣一起觀看古代帝王畫像,當看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畫像時,再三觀看,久久不能離去,而到了隋煬帝及宋徽宗畫像前則一帶而過,言:「亂亡之主,不足觀也。」(《明太祖實錄》卷三四,頁一六四)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鑒于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明太祖實錄》卷三九,頁二一六)洪武九年五月,朱元璋稱:「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明太祖實錄》卷一〇六,頁四七四)洪武十五年九月,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進《太平治要》共十二條,朱元璋觀后甚為同意,其中便有「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
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明太祖實錄》卷一四八,頁四〇)的論點。
由以上文獻史料可見,朱元璋對秦、西晉、隋三朝抱有十分排斥的態度。《帝王廟碑》中,宋訥貫徹了朱元璋的帝王觀與歷史觀,以「視其功德,不能無愧」為由,將三朝帝王擯棄于廟門之外,不與祭祀。也就是說,入祀帝王不僅要有「一統」之功,更要有「配天」之德。朱元璋認為,政權初立之時,前幾代帝王的功德尤為關鍵,因為它直接關系著國運的長久以及后世子孫的命運。在他看來,秦、晉、隋雖為統一王朝,但開國之主皆以違背天理的手段奪取政權,有弒殺篡亂之舉,屬得國不正,所以國祚不長。從帝王德行和為政之道而論,他們或驕縱恣肆,胡作非為,或濫施暴政,嗜殺成性,或窮奢極欲,勞民傷財,可謂喪德失德,最終吞下國破家毀、人亡政息的惡果。
從維護明王朝統治的角度來看,將三朝弗祀的做法明顯帶有極重的鑒誡色彩。朱元璋作為大明王朝的建立者,深知創業艱難,守成尤難的道理,也期望這一政權能夠千秋萬代,堅如磐石。不過正所謂「德厚者其祚必遠」(【唐】虞世南,陳虎譯注《帝王略論》,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頁四一),他希望自己的子孫能夠以此三朝帝王及繼任者所行之事為誡,認真總結短命王朝的經驗教訓,強調以德為政,注重修身之德,從而達到國祚永昌,以傳萬世的目的。

北京歷代帝王廟全景
南京歷代帝王廟作為北京歷代帝王廟的祖型,為其后北京歷代帝王廟的發展奠定了開創性基礎,由宋訥撰寫的南京《帝王廟碑》為我們提供了寶貴史料,對于探索歷代帝王廟從南京到北京的歷史傳承和演變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如今,南京歷代帝王廟不存,北京歷代帝王廟成為全國唯一。就現有文獻和文物現狀來看,北京歷代帝王廟的等級更高,祭祀理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清康熙皇帝提出了「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的取舍底線,雍正皇帝特別強調了崇祀治國守業帝王的重要性、乾隆皇帝更以「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認識高度,進一步完善了歷代帝王的祭祀體系,最終將入祀帝王增加到了一百八十八位。其中,既有大一統王朝的帝王,也有部分割據時期的帝王;既有開國創業之主,也有治國守成之君;既有華夏漢民族帝王,也有北魏、遼金以及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帝王,使歷代帝王廟成為體現中國大歷史的帝王祭祀廟宇。

北京歷代帝王廟景德崇圣殿外景

北京歷代帝王廟景德崇圣殿內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