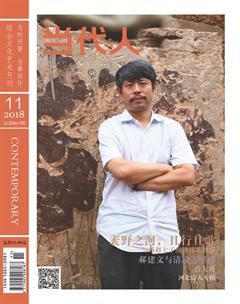給流失壁畫一個最好的歸宿
范玉蘭
2017年,對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員郝建文來說,是他的一個學習年。這一年,他兩次外出,一是去敦煌研究院參加國家文物局舉辦的《壁畫保護修復技術培訓班》,二是去中國藝術研究院工筆畫研究院,參加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中國古代壁畫摹制技法人才培訓》。50歲的人了,從年齡上說,在這兩個班里他都是“老大”,有的同學與他女兒同齡。但在他看來,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活到老,就要學到老。
兩次學習,時間安排都非常緊張。尤其在北京學習期間,工筆畫研究院教室的燈常常亮到深夜。回想起在北京的學習時光,郝建文覺得,臨摹壁畫太容易上癮,太容易投入,那些日子簡直是太瘋狂了。
有一天,他和江蘇理工學院王巖松先生微信聊天,得知王先生在做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千年壁畫,百年滄桑——古代壁畫暨流失海外珍貴壁畫再現傳播與展示》,這個項目要在國內5個城市巡回展覽。
郝建文馬上想到八年前他到行唐出差,在縣政府招待所墻上看到過清涼寺壁畫照片,畫面中的菩薩面部生動,姿態優美,造型和設色明顯不同于河北其他寺廟壁畫。縣里同行告訴他,原壁畫在1926年已經流失到英國了,而且壁畫很大,高度有4米。當時他吃了一驚,因為,單體人物這樣高的壁畫在河北非常罕見。
這么好的東西,流失到大英博物館,我們國人很難看到,這讓他很難過。當時他暗下決心,有機會一定等比例臨摹一幅,讓更多的人不出國門也能看到它。
他把清涼寺壁畫的情況告訴了王巖松先生。王先生馬上表示,希望郝建文親自臨摹清涼寺壁畫,參加國家藝術基金的巡展項目。
完成這么大一幅壁畫的臨摹,很耗時間,郝建文還有日常工作要做,要是靠業余時間,短短幾個月一個人難以完成。于是,他決定約幾位同學一起來做。
這次臨摹不尋常
郝建文從事文博工作30多年,做過很多寺廟和墓葬的壁畫臨摹工作,河北博物院《北朝壁畫》展中約400平方米壁畫摹本,便是由他負責完成的。
但這次清涼寺壁畫臨摹,非同尋常。一般來說,臨摹古代壁畫,最好是能看著原壁畫來做,古人的用筆和設色一覽無余。如果不能看著原壁畫,那么,有壁畫高清圖片也可以將就,臨摹過程中,要去經常觀摩原壁,感受古人氣息。
這次臨摹,壁畫實物在大英博物館,距中國萬里之遙,別說對著原壁臨摹了,就是去看上一眼都很難。為了壁畫高清圖,在北京學習期間,他讓女兒郝頡宇幫忙查找資料,又請中央美院的老師和朋友們幫忙,但一無所獲。
他只好求助朋友圈。河北博物院志愿者白肖紅老師非常熱情,托她在英國的朋友不止一次去大英博物館拍照攝像。因設備和拍攝環境的原因,片子清晰度不高。
正在一籌莫展時,一位朋友說,他女兒肖瀟正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讀書,讓她幫我們拍。
那天,郝建文下班回家,朋友來電話告訴他,女兒正在大英博物館拍清涼寺壁畫,問他拍攝要求。他非常激動,對朋友說:“盡量不要變形,壁畫很高,拍高處時,雙手把相機舉起來盲拍;把感光度提高到1000至2000。”那天晚上,他高興得失眠了。
第二天,片子就打包傳來了,他覺得在那樣的拍攝環境和光線條件下,片子的清晰度已經很不錯了,基本能滿足臨摹需要。
這時,離交稿時間已不足三個月。
很快,郝建文組織成立了清涼寺壁畫臨摹小組。這是一個特殊的小組,沒有工作經費,做畫板、買礦物顏料和紙張等,都要自己掏腰包,臨摹壁畫沒有任何報酬。
這個小組成員,除了他,還有長春大學教師桑蕾;吉林藝術學院教師邰浩然;河北師大教師田紅巖;唐山職業畫家王亞新。他們又各自帶幾位學生參加。
臨摹工作在長春、唐山和石家莊三地同時進行,最后,集中在石家莊調整畫面。
他根據畫面,分割為左中右三幅。根據每人特點和優勢,將畫面最清晰那幅,交給了桑蕾,整幅壁畫要靠這個人物出彩,她有實力;中間部分交給了王亞新,他出手快;最不清楚的畫面,留給自己和田紅巖。他覺得,田紅巖做事細心,他倆都在石家莊,有問題交流起來也方便。
打印的原大稿子不夠清楚,需要把局部照片放大后仔細觀察,來整理畫面。學生印稿很認真,粗線、細線以及墻體上的裂痕和脫落等一點不落。
為了接近原作,他們用百草霜(鍋底灰)調膠來勾線。著色基本都采用礦物質顏料。
七八月份的石家莊酷暑難當,石家莊組的十來個人在河北師大教室里,開著吊扇,白天晚上沒日沒夜地干著。這樣,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白紙上的顏色一點點鋪滿。
其他組情況也都差不多。長春的氣候涼快一些,從桑老師發來的照片看,大家時間抓得都很緊,都非常辛苦。
約定的交稿時間到了,長春組和唐山組的摹本通過物流運到了石家莊,三幅壁畫摹本匯集到河北博物院壁畫工作室,終于可以拼在一起觀察、調整了。
郝建文激動地打開包裝箱,把畫一幅幅擺在地上,通過對比才發現中間這幅畫面太黑了。右邊這幅色調沒問題,但線條顯弱,質感差些。
他通過蘋果電腦(在手機屏幕和普通電腦上有些形象不易看清楚)觀看壁畫圖片,發現有的細節沒有刻畫,有的形存在問題,色彩也不夠準確。
能看清楚的,好修改,那些看不清楚的,只能通過放大照片,一邊分析一邊找。
那些日子,不能影響日常工作。只能每天早來晚走,擠時間干;周六周日休息時間,放開手腳拼命干。
郝建文說,在調整階段,他的隊友們也常有新發現,時常能聽到這樣的對話:
“哎,這不是蓮蓬嗎?還有這么多蓮子呢。這么多豎線表現的是花蕊。”
“就是,原來沒有看出來。”
“這還是一串珠子呢,還都連著呢。”
接著,便是愉快的笑聲。
壁畫共分割了12塊,每尊菩薩分為4塊,大小不等。從壁畫現存情況看,當時,壁畫揭取的技術還不成熟,分割部位丟失的畫面較多,安裝后又進行了補繪。不過,在揭取壁畫前,倒是充分考慮了人物面部和手部的完整。
從畫面的內容來看,三尊菩薩,從左向右,所持法器分別為拂塵、佛珠和如意。中間為主尊,正面,身軀高大。兩側為脅侍,側身,面向主尊。經推測,這三尊菩薩,中間為觀音菩薩,左邊可能是普賢菩薩,結合與五臺山的關系,他覺得右邊可能是文殊菩薩。
右邊的文殊菩薩,面部呈深褐色,和另兩位菩薩的面部顏色明顯不同,仔細觀察,深褐色的面部有殘留的白顏色,和那兩尊菩薩色彩一致,郝建文這才猛然發現,現在看到的深褐色的面部以及五官,是里層的壁畫,白顏色那層畫面的五官已全部脫落。這和壁畫說明牌上提到的補繪正好吻合。
清涼寺已經不在了,據當地老鄉說,建筑的基礎部分在取土時也都挖掉了。文獻資料只見于縣志中的名稱和始建年代,寺內的碑刻也早已蕩然無存。
國際友人伸援手
在作品完成、裝箱郵寄前,郝建文心里還是有一絲遺憾,他總覺得未能看到清涼寺壁畫高清圖,如有高清圖片參照,臨摹效果可以更好。
抱著一線希望,他聯系敦煌研究院的李娜老師,她曾在英國攻讀壁畫保護專業博士。李娜幫忙查到了大英博物館申請館藏文物圖片信息,并把鏈接分享給他。
郝建文英語不熟,便請了美國朋友Chris Foster(中文名傅希明)幫忙翻譯。那天晚上,傅希明很激動地告訴他,大英博物館亞洲部中國書畫及版畫的負責人Yu-ping Luk(陸于平博士)把壁畫照片傳來了,供這次臨摹壁畫參考使用。聽到這個消息,郝建文激動壞了。
傅希明先生和他說:“我將《燕趙都市報》關于你們臨摹清涼寺壁畫的報道作為附件,發給了大英博物館陸博士,她就提供了清涼寺壁畫照片。”
他囑咐郝建文,片子僅供這次臨摹參考用,如果發表,需重新向大英博物館申請。
郝建文和傅希明先生開玩笑說,這次臨摹清涼寺壁畫鬧大了,還得到了國際友人的幫助,成了國際間合作項目。
將把摹本捐給行唐
網上有關行唐清涼寺的資料不少,不知是否可靠,郝建文向行唐縣文物保管所閻偉所長了解情況。當得知郝建文他們正在做清涼寺壁畫臨摹時,閻所長非常激動,他說:“前些日子,縣領導還說應該按原大小臨摹一幅清涼寺壁畫,將來放在博物館里,正準備和你聯系做這件事呢。”真是機緣巧合啊。
后來,閻所長特意來看臨摹的清涼寺壁畫,希望參加完國家藝術基金全國巡展后,縣里出資購買收藏。
郝建文經常下鄉,對縣里的經濟狀況比較了解,經慎重考慮,與幾位同學溝通,建議參加全國巡展后將這幅壁畫摹本留給行唐,將來在博物館展示。大家都覺得這是它最好的歸宿,都愿意捐獻。
這次清涼寺壁畫臨摹,頗受人們關注,牽動了好多人的心。先后有20多人參與,他們大多數是大學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對于他們來說,是一次非常好的社會實踐活動。
臨摹完成后,省會媒體紛紛報道,引起了人們對清涼寺壁畫的格外關注。
郝建文將臨摹作品照片和媒體報道傳給了中國美協副主席何家英先生。何先生說,這次臨摹太有意義了,而且臨摹得特別棒。
郝建文透露,他請何先生題寫了“郝建文壁畫工作室”。他覺得先生題字,就像給了他一面大旗,他要扛好這面旗,盡自己所能,在古代壁畫方面多做些事情,爭取做出成績。
九月份,這幅壁畫摹本在四川美院美術館舉辦的展覽上首次亮相,接下來還要去太原、南京和上海等地參加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古代壁畫暨流失海外珍貴壁畫再現傳播與展示的巡展。
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幅壁畫摹本,并通過它來了解河北,了解石家莊和行唐的歷史文化。
編輯:安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