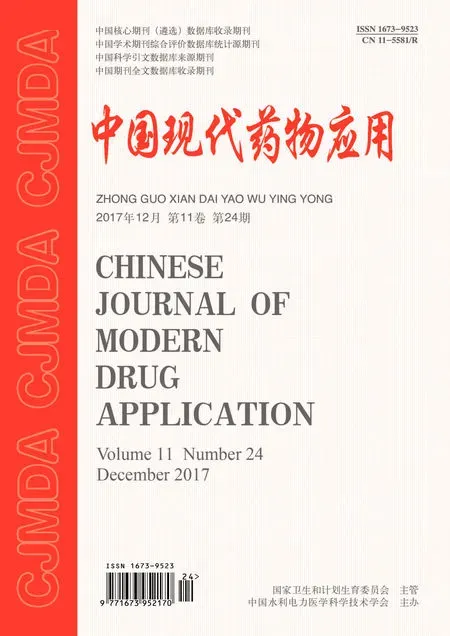嬰兒痙攣癥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的臨床研究
鐘向陽 李秋瓊
嬰兒痙攣癥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的臨床研究
鐘向陽 李秋瓊
目的研究嬰兒痙攣癥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的臨床效果。方法30例嬰兒痙攣癥患兒,隨機(jī)分為對照組與治療組, 各15例。對照組患兒給予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常規(guī)西醫(yī)治療, 治療組患兒給予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比較兩組患兒治療效果、不良反應(yīng)及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情況。結(jié)果治療組患兒治療總有效率為93.33%, 高于對照組的60.00%,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治療組患兒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6.67%、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率為13.33%, 均低于對照組患兒的40.00%、46.67%,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結(jié)論針對嬰兒痙攣癥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可以替代西藥常規(guī)治療手段, 減少西藥的不良反應(yīng), 便于患兒接受, 提高治療效果, 對嬰兒痙攣癥的早期發(fā)現(xiàn)和治療有很高的臨床研究價(jià)值。
嬰兒痙攣癥;分型治療;針灸醫(yī)藥結(jié)合
嬰兒痙攣癥又稱West綜合征, 患兒臨癥癥狀以鞠躬樣或點(diǎn)頭樣痙攣為主, 且多伴隨智力的改變。如不及時(shí)治療,不僅容易對患兒的成長造成影響, 同時(shí)也容易增加家庭的負(fù)擔(dān)。嬰兒痙攣癥預(yù)后不良, 發(fā)病率為活體嬰兒萬分之一至萬分之四, 屬于常見難治性癲癇, 西醫(yī)缺乏廣泛有效治療手段。中醫(yī)研究并未深入, 缺乏系統(tǒng)治療理論體系與臨床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本團(tuán)隊(duì)通過對數(shù)百病例追蹤調(diào)查, 發(fā)現(xiàn)此病患兒皆先就西醫(yī),長期未果而轉(zhuǎn)就中醫(yī), 因而多為虛證, 涉及臟腑為心、肝、脾、腎。然由于病程長, 病機(jī)復(fù)雜, 非一方加減化能囊括, 故擬定分型論治, 從肝脾不和、脾腎虛或兩虛、心腎陽虛、肝腎陰虛等類型, 分別制定基礎(chǔ)方, 以針灸結(jié)合醫(yī)藥之手段進(jìn)行治療。旨在通過本課題研究, 探討、確定、完善本癥治療之分型思路的實(shí)用性, 證實(shí)分型基礎(chǔ)方治療方案的可行性, 為臨床綜合療法治療嬰兒痙攣癥提供基礎(chǔ)理論體系與手段。現(xiàn)報(bào)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3月~2016年12月在河源市中醫(yī)院康復(fù)科、內(nèi)科住院和門診部治療以及網(wǎng)絡(luò)群體征集家長自愿的嬰兒痙攣癥患兒30例作為研究對象, 隨機(jī)分為對照組與治療組, 各15例。對照組患兒男7例, 女8例;年齡1.5~3.0歲, 平均年齡(2.13±0.29)歲。治療組患兒男8例,女7例;年齡2.0~3.5歲, 平均年齡(2.14±0.46)歲。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納入與排除標(biāo)準(zhǔn)
1. 2. 1 納入標(biāo)準(zhǔn) ①患兒均符合中醫(yī)對嬰兒痙攣癥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②患兒無其他系統(tǒng)重大疾病。③患兒家屬知情同意。
1. 2. 2 排除標(biāo)準(zhǔn) ①存在藥物過敏史者。②存在重要臟器嚴(yán)重功能損害者。③無法施行針灸者。
1. 3 方法
1. 3. 1 對照組 對照組患兒給予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治療:給予患兒20 U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5%葡萄糖溶液250 m l泵入, 泵入速度15~20 m l/h, 1次/d, 14 d為1個(gè)療程。視患兒病情的緩解情況, 考慮增加或減少藥量。病情未緩解者, 考慮將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劑量增加至40 U, 采用相同方法給藥。
1. 3. 2 治療組 治療組以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 藥物以醫(yī)院自制膏方便服用, 針灸由針灸科資深的治療師辨證施治。①中藥方劑1:太子參10 g、茯苓10 g、川芎6 g、熟地10 g、炒白術(shù)10 g、白芍10 g、山藥10 g、陳皮6 g、膽星5 g、神曲5 g、清夏5 g、枳殼 5 g、羌活5 g、蜈蚣 1條、石菖蒲5 g、飴糖20 g。②中藥方劑2:紫河車10 g、山萸肉10 g、山藥10 g、茯苓10 g、炒白術(shù)5 g、太子參 10 g、五味子5 g、生地10 g、黃精5 g、麥冬5 g、白芍5 g、肉蓯蓉5 g、肉桂 5 g、木糖醇15 g。一劑制成膏方100 m l, 2次/d, 50 m l/次, 飯后服用。③針灸方法:實(shí)證者, 針刺百會(huì)穴, 安神定志;針刺人中, 開竅醒腦;針刺內(nèi)管, 調(diào)理心神;針刺后溪, 統(tǒng)督陽氣;針刺涌泉, 營養(yǎng)腦神經(jīng)。虛證者, 針刺印堂, 調(diào)和陰陽;針刺鳩尾與間使, 安神定眠;針刺太沖, 益肝補(bǔ)腎;針刺太溪,平肝熄風(fēng)。風(fēng)痰閉阻型, 輔以風(fēng)池及合谷針刺;肝火痰熱型,輔以風(fēng)池、太沖、豐隆等穴位針刺;脾虛痰癥型, 輔以足三里及三陰交等穴位針刺;肝腎陰虛型, 輔以三陰交及照海等穴位針刺;氣虛血瘀型, 輔以血海及足三里等穴位針刺。
1. 4 觀察指標(biāo) 觀察比較兩組患兒的治療效果、不良反應(yīng)及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情況。
1. 5 療效判定標(biāo)準(zhǔn) 以中醫(yī)癥狀診斷為主、西醫(yī)腦電圖檢查結(jié)果為輔, 判定治療效果。痊愈:發(fā)作完全控制1年, 腦電圖恢復(fù)正常。顯效:發(fā)作頻率以及積分減少>75%, 或與治療前發(fā)作間隔時(shí)間比較, 延長>0.5年未發(fā)作, 腦電圖改變明顯好轉(zhuǎn)。有效:發(fā)作頻率以及積分減少50%~75%, 或發(fā)作癥狀明顯減輕, 持續(xù)時(shí)間縮短>1/2, 腦電圖改變有好轉(zhuǎn)。無效:發(fā)作頻率、程度、發(fā)作癥狀、腦電圖均無好轉(zhuǎn)或惡化。總有效率=(痊愈+顯效+有效)/總例數(shù)×100%。
1. 6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采用SPSS20.0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對研究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計(jì)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biāo)準(zhǔn)差(±s)表示, 采用t檢驗(yàn);計(jì)數(shù)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yàn)。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 1 兩組患兒治療效果比較 治療組患兒治療總有效率為93.33%, 高于對照組的60.00%,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1。
2. 2 兩組患兒不良反應(yīng)、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情況比較 治療組患兒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6.67%、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率為13.33%,均低于對照組患兒的40.00%、46.67%,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見表 2。

表1 兩組患兒治療效果比較[n(%)]

表2 兩組患兒不良反應(yīng)、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情況比較[n(%)]
3 討論
嬰兒痙攣癥為特殊類型的癲癇, 發(fā)病時(shí)間集中于1歲左右[1]。發(fā)病時(shí), 患兒頭部及軀干前屈, 上肢內(nèi)收, 下肢屈曲,握拳, 兩眼斜視, 且多伴隨意識(shí)障礙[2]。病情嚴(yán)重者, 發(fā)作次數(shù)可達(dá)每日幾十次[3]。患兒腦電圖檢查可見高峰(幅)失常, 臨床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顯示, 發(fā)病初期, 患兒家屬多尋西醫(yī)治療。西醫(yī)治療方法以給予患兒鎮(zhèn)靜劑、神經(jīng)阻斷劑及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為主[4]。藥物可有效刺激腎上腺皮質(zhì)的發(fā)育及機(jī)能,刺激糖皮質(zhì)類固醇的分泌, 達(dá)到緩解患兒痙攣的目的[5]。但易導(dǎo)致患兒體質(zhì)下降。本文研究發(fā)現(xiàn), 給予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治療后, 患兒治療總有效率為60.00%、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40.00%、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率為46.67%。
長期采用西醫(yī)方法治療者, 從臨床看, 先找到西醫(yī), 用了各種鎮(zhèn)靜劑、激素、神經(jīng)阻滯劑之后才尋求中醫(yī)。尋至中醫(yī)時(shí), 多已久病成癇。患兒面色多呈青、白或黑色, 舌淡苔白,內(nèi)臟于傷, 脾腎陽虛、肝氣不平。腦電圖可見高峰(幅)失律。祖國醫(yī)學(xué)認(rèn)為, 嬰兒痙攣癥發(fā)病原因有三:①嬰兒血?dú)馕闯洹⒓∧w不密、寒邪所感, 或久寒傷陰, 筋絡(luò)失其濡, 從而抽搐。又或入里化熱, 成白虎湯癥, 久之灼傷陰液。②護(hù)養(yǎng)不當(dāng), 汗出如漿, 不及更衣, 寒濕入里。③胎兒或嬰兒期間,母親或嬰兒有所大驚, 致陰陽分離, 氣血并行于上。除上述三者外, 先天不足、后天失養(yǎng)、產(chǎn)傷、瘀血, 同樣容易誘發(fā)嬰兒癲癇癥。
根據(jù)發(fā)病原因的不同, 可將其分為癇證虛實(shí)夾雜型及癇證虛證為主型等不同證型[6]。本組患兒證型以上述兩者為主。視患兒中醫(yī)證型的不同, 給予其不同的方劑治療, 可豁痰熄風(fēng)、健脾補(bǔ)腎、養(yǎng)血活血, 促進(jìn)患兒疾病的康復(fù)[7]。嬰兒痙攣癥針灸應(yīng)視患兒中醫(yī)辨證分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8],以達(dá)到降低痙攣發(fā)作次數(shù)的目的。本文研究發(fā)現(xiàn), 治療組患兒治療總有效率為93.33%, 高于對照組的60.00%,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治療組患兒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為6.67%、營養(yǎng)不良發(fā)生率為13.33%, 均低于對照組患兒的40.00%、46.67%, 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臨床研究顯示, 微熱對患兒抽搐等癥狀的緩解, 具有積極意義, 但機(jī)理尚不明確,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用藥常見不良反應(yīng)以肌萎縮、骨質(zhì)疏松、眼病及潰瘍等為主。本組給予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治療的患兒, 共發(fā)生不良反應(yīng)6例, 不良反應(yīng)發(fā)生率較高, 治療安全性較差。給予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的患兒, 僅1例發(fā)生了不良反應(yīng), 發(fā)生率低。對比發(fā)現(xiàn), 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治療嬰兒痙攣癥, 效果更佳。
綜上所述, 針對嬰兒痙攣癥采用針?biāo)幗Y(jié)合分型論治可以替代西藥常規(guī)治療手段, 減少西藥的不良反應(yīng), 便于患兒接受, 提高治療效果, 對嬰兒痙攣癥的早期發(fā)現(xiàn)和治療有很高的臨床研究價(jià)值。
[1] 梁倩, 馬融. 嬰兒痙攣癥驗(yàn)案1則. 四川中醫(yī), 2011, 29(7):102-103.
[2] Gaily E. Vigabatrin monotherapy for infantile spasms. Expert Rev Neurother, 2012, 12(3):275-286.
[3] 楊小林, 張曉青. 促腎上腺皮質(zhì)激素釋放激素及受體在嬰兒痙攣癥致癇組織中的表達(dá). 癲癇雜志, 2017, 3(1):3-14.
[4] 陳漢江, 張喜蓮, 馬融. 馬融治療嬰兒痙攣癥經(jīng)驗(yàn). 中醫(yī)雜志,2013, 54(18):1547-1549.
[5] 李燕. 1例嬰兒痙攣癥的藥物治療與藥學(xué)監(jiān)護(hù). 臨床醫(yī)藥文獻(xiàn)電子雜志, 2016, 3(2):373, 376.
[6] 王興宏. 嬰兒痙攣癥的治療和預(yù)后研究進(jìn)展. 中國實(shí)用醫(yī)藥,2015, 10(31):272-273.
[7] 趙慧, 劉智勝. 嬰兒痙攣癥的藥物治療進(jìn)展. 深圳中西醫(yī)結(jié)合雜志, 2015, 25(20):195-198.
[8] 李楠, 黨大勝. 臨床藥師對1例嬰兒痙攣癥患兒術(shù)后抗感染治療的藥學(xué)監(jiān)護(hù). 中國藥房, 2014, 25(34):3253-3255.
10.14164/j.cnki.cn11-5581/r.2017.24.072
517000 河源市中醫(yī)院
2017-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