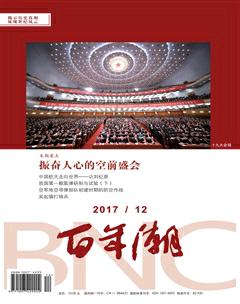遲到十余年的大學夢
周百新

1977年,30歲的我以一個孩子父親的身份,與全國幾百萬考生一起,參加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這距離我準備參加1966年高考,已經11年了。
11年前,即將高中畢業的我,滿懷對大學生活的憧憬,積極復習,準備迎接全國高考。那時,我在大別山鄂豫皖交界處的一個山區小縣城——商城讀高中。學校不大,三個畢業班,加起來不到90人,但那是全縣唯一一所高中,是我們的“最高學府”。能到這里讀書的學生,都是全縣的學習尖子。剛剛入校,校長就在大會上鼓勵我們:要為商城高中爭光!未來的大學生,就在你們這些人里產生!到了高中三年級時,學校將最好的任課老師、最好的班主任都放在畢業班。同學們懷揣大學夢,刻苦學習,希望能考進一所理想的高等學府。
1966年6月,距全國高考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了,同學們已經進入“臨戰狀態”。學校開會,言必稱為國爭光、為校爭光;走廊里貼滿勵志標語;同學們爭分奪秒,暗中攢足勁兒要大顯身手。
那時,我在班里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特別是數學、物理、化學,常常考滿分。老師經常鼓勵我:考不上清華、北大,至少也要到上海交大、北京理工這類大學。
然而,6月13日,縣委忽然派來工作組,召開由全校師生參加的動員大會,集中學習《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工作組要求學校先停課,學習領會中央文件,特別強調反對只專不紅的辦學路線,要求教師和學生做又紅又專的時代楷模,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奠定基礎。
由于當時并未明確高考是否如期進行,因此我們畢業班的復習絲毫沒有放松。學校根據同學們的成績組織輔導小組,對學生進行個別指導,還將閱覽室、圖書館及學生餐廳騰出來,為畢業班同學的復習創造條件。工作組雖然沒有公開反對學校安排的畢業班復習,但要求必須保證開會學習時間。我們心里不敢公開反對,但私底下都想方設法與工作組“打游擊”。
有一天,學校組織我們畢業班開會學文件,我和另一位同學打算溜到外面復習,結果看見大門有人把守,急中生智,我們爬上學校高高的圍墻,翻到后面鄰山的紅麻地里,躲在那里復習了一整天。這一天又悶又熱,出汗出到衣服都能擰出水來。中午我們不敢出去找飯吃,合伙吃了一個早飯省下的饅頭。
該來的終歸躲不過,7月6日清晨,學校大喇叭里播出了“推遲1966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消息,這對于我們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三年的努力在最后時刻化為泡影!剛開始時,我們還自欺欺人地懷疑消息的準確性,證實確有此事后,老師安慰我們:是“推遲”,不是“停止”,復習不要放松。我們抱著幻想,一刻也不敢丟下書本。但到年底,北京的學生陸續來校串連,一個又一個造反派組織粉墨登場,學校全面停課,教室內外貼滿大字報,校長和老師成了被批斗對象,恢復高考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1968年冬天,正是“文革”轟轟烈烈開展之時,我隨全縣第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到縣城北邊的河鳳橋鄉劉圍孜生產隊插隊。雖然到農村當了農民,一年四季“戰天斗地”,但我們這一批“老三屆”高中生始終沒有放棄大學夢。
1971年,全國高校終于恢復招生,青年隊的同學個個躍躍欲試,誰都想趁機跳出“農門”,去大城市讀書。我心想,自己是66屆高中生,青年隊里沒幾個同屆的,如果拼成績,上學應當有把握。與我要好的同學說我有希望,甚至私下向我表示祝賀。后來才知道,這時的高校招生不需要考試,而是由貧下中農“推薦”。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父親又是右派,只能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報名。
雖然政策上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視同仁,但后來我還是名落孫山。一打聽才知道,所謂“一視同仁”不過是一個幌子,就算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招錄,也只是一個點綴而已。這年,青年隊里與我一起下放來的低年級高中同學中,有兩三個人上了大學,而我這個66屆的高中生卻無緣讀書。形勢如此,無可奈何!
后來,青年隊的同學們或是去讀書,或是去當兵,或是被招工,陸續都離開了。再后來,包括我在內,只剩下三個同學。另外兩人和我一樣,家庭出身都不好。直到1972年底,河南舞陽鋼廠招工,經過爭取,我才得以離開下放五年的農村。
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煉鋼工人,在熊熊的爐火面前,大學夢就像投進爐中的焦炭,化作縷縷輕煙。我娶妻生女,一心考慮如何努力工作,怎么與遠在家鄉的妻女早日團圓……
1977年8月,家在北京的工友神神秘秘地告訴我們,鄧小平又出山了,今年有可能恢復高考。當時,我剛剛被調到工廠子弟中學教初中物理,雖然恢復高考的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確認,但在我心里,大學夢已像初春的草芽,漸漸萌發。與此同時,我也十分擔心:像我這樣已經30歲、結婚成家的人是否還有資格參加高考?
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其中特別提到,要注意招收1966、1967兩屆高中畢業生,婚否不限。我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放下了。由于時間倉促,前后只有一個月,我只是簡單看了看資料,就于12月8日,與一批比我年齡小十幾歲的年輕人一起走進了考場。
考場就在我任教的子弟中學。雖然已經很熟悉學校的環境了,但那天我還是起了個大早,擔心會出什么差錯。當我帶著文具盒走進學校大門時,看門大爺熱心地問:“你今天是來監考吧?”我沒敢告訴他我也是來參加高考的,害怕萬一落選,在學校里傳開,在學生面前影響不好。
這次考試我報的是理工科,考試科目是語文、政治、數學和理化,外語只是測驗,不計入總分。11年前,我的數理化在班里總是前幾名,雖然十來年沒有再摸過高中課本,但我在農村擔任過半年的初中物理教師,又在工廠子弟學校里教了半年書,早已遺忘的知識多少又撿回一些。我的語文、政治考得一般,但我感覺數理化不會差到哪兒去。
考完試后,剛好學校放寒假,我就回到幾百里外的家鄉商城,與母親、在縣醫院工作的妻子,還有不足一歲的女兒團聚。假期還沒有過完,廠里教育處打來長途電話,說我過了高考分數線,已經初選上,通知我趕快回廠里參加體檢。
體檢的過程并不順利,也許是由于心情激動,加上長途跋涉,我的血壓總是超標。給我量血壓的是位女醫生,她大約看我臉色赤紅,便在一邊不斷地安慰我:不要緊張,不要緊張!可是,她越安慰,我心里越著急,擔心身體過不了關,影響上大學。后來還是女醫生手下留情,給了個合格。
很快,我任教的子弟中學開學了,高考的最終結果卻遲遲沒有傳來,我又回到學校代課。同事們都認為我這位“老三屆”的高中生一定沒有問題,分配課程時叫我不要再代課了。我卻擔心錄取過程中有變數,一再堅持繼續代課,校長最終同意了,但不讓我代主課,因為他擔心我隨時可能離開學校。豈知到了1978年3月,廠里與我一起參加體檢的幾位初中畢業的年輕人先后接到錄取通知書,而我望穿秋水,也沒得到任何錄取消息。后來才知道,這年省招生辦規定,凡年齡超過25周歲的考生,要比別人高出100分才能錄取。
得到這個消息,我心里十分懊喪。之前,挑燈夜戰,本來有把握考上全國重點大學,結果因為一場“文革”,大學夢斷;下鄉期間,因家庭出身問題,屢屢喪失求學機會;粉碎“四人幫”后,終于有機會重圓大學夢,也達到了大學錄取分數線,結果又因為年齡問題名落孫山。學校同事看我情緒低落,紛紛過來勸我,說還有幾個月又要高考了,不如再試一試。
我想,再試一次吧!如果仍舊時運不濟,我就“認命”了。1978年6月,我又參加了全國高考。結果出來后,毫無懸念地過了分數線,還高出幾十分。汲取上次教訓,填報志愿時,我沒有選擇全國重點院校,而是報了家鄉新開辦的一所師范學院——河南信陽師范學院。
1978年9月1日,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走進了信陽師院數學系。31歲的我,帶著妻子和女兒的希望,帶著始終不渝的夢想,重新回到明亮的教室。同桌是一個比我小十幾歲的年輕人,看著他嘴唇上毛茸茸的胡子,我仿佛看見了12年前的我……(編輯 葉松)
作者:信陽市政府機關黨委原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