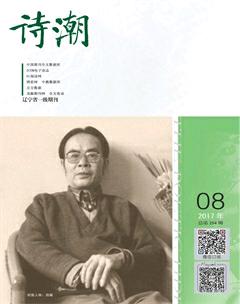榮光啟 認認真真用“廢話”寫出詩意
【主持人語】
口語詩的意義
口語詩是當代詩壇最有爭議的一種形態。本來新詩就已經為許多讀者詬病了,被認為沒有韻味沒有詩意……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新詩不同時期又會冒出“廢話詩”“下半身”“梨花體”“羊羔體”和“烏青體”等等形態的作品,這就更讓人受不了了。大家的疑問集中在語言和“詩意”上:這樣的大白話、“流水賬”也是詩?詩歌寫作咋會如此簡單?
中國詩歌三千年歷史,人們大約習慣了詩詞歌賦的關學風格,對詩意的期待是“關”的,這個“關”蘊藉在精致的詩歌結構和獨具匠心的語言和意象上,即使是對待新詩,人們常常也有這樣的關學期待。但是新詩不是舊詩,舊詩受篇幅和體式限制,必須要在語詞、意象和結構上下功夫,每一處都可能有詩意讓人眼睛一亮。但新詩的關學風格是整體性的,不一定要局部下功夫,新詩的一個可能是,你在局部打量它,它毫無趣味,但你讀完之后,就在結束的那一剎那,為之一振。
用最直白的語言,來表達生命的感動、感慨或感觸——口語詩的風格是:詩作處處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整體上卻明顯地呈現出一種生活里的真實,一種生命中的感動。我將許多喜歡用口語寫詩的人稱為一群認認真真用“廢話”寫出詩意的人。這一類詩歌,整首詩你看起來都會覺得廢話連篇,但讀完卻很讓人感動,它以最沒有詩意的語言在陳述生活中那些令人悵然若失的東西。其實這樣的詩作非常難寫。很多時候,你必須像寫古詩一樣,反復打磨,因為它不能有一處詞涪、描寫是無用的。與很多讀者所說的想法恰恰相反:這樣的詩,沒有一處是廢話!它追求的是一種蘊深意于無形的整體效果。口語詩的寫作者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一
“第三代詩人”韓東的詩大多數是非常口語化的,他在語言上的節制、簡潔甚至到了干枯(幾乎看不出什么“詩意”)的地步。這種詩歌語言看似“空無一物”,但事實并非如此。對韓東而言,“寫詩不單單是技巧和心智的活動,它和詩人的整個生命有關。因此,‘詩到語言為止的‘語言不是指某種與詩人無關的語法、單詞和行文特點。真正好的詩歌就是那種內心世界與語言的高度合一。”用《圣經·創世記》中知識樹(識別善惡樹)和生命樹的比喻,韓東的詩歌顯然是在追求“生命樹”,他不想延續前人的思維、審美習慣,把文化、歷史的符號與象征意蘊作為寫作的素材,他更愿意抓住當下個體生命的真實感受,在這種當下感受中體會永恒。他說的“內心世界與語言的高度合一”完全不是修辭的問題,而是一種生命的境界。也正因為此,他的許多看似無甚詩意的口語詩,讀來十分令人感動,像《我們的朋友》
我的好妻子
我們的朋友都會回來
朋友們會帶來更多沒見過面的朋友
我們的小屋子連坐都坐不下
我的好妻子
只要我們在一起
我們的好朋友就會回來
他們很多人還是單身漢
他們不愿去另一個單身漢小窩
他們到我們家來
只因為我們是非常親愛的夫妻
因為我們有一個漂亮的兒子
他們要用胡子扎我們兒子的小臉
他們擁到廚房里
瞧年輕的主婦給他們燒魚
他們和我沒碰上三杯就醉了
在雞湯面前痛哭流涕
然后搖搖擺擺去找多年不見的女友
說是連夜就要成親
得到的卻是一個痛快的大嘴巴
我的好妻子
我們的朋友都會回來
我們看到他們風塵仆仆的面容
看到他們混濁的眼淚
我們聽到屋后一記響亮的耳光
就原諒了他們
事實上對于口語詩的理解與接受是一種關于“詩意”的觀念問題。怎樣的詩才是有詩意的?是局部的美的累積呢,還是多處的“廢話”突然被一種力量照亮為詩?2013年6月,在潛江一次詩會上,楊黎、沈浩波、宋曉賢等人都在,我讀到一位來自北京的年輕女孩淺予的兩首詩,一首是《陽光照進來》:
陽光從窗戶照進來
照到31床
也照到
30床
離29床
還差一步的距離
陽光照到的兩張床
都顯得好亮好亮
白色的床單
打起反光
陽光沒照到的床
顯得真安靜
離陽光
就那么一步距離
另一首是:“一個男同學在扣扣上對我說/他深深體會到了北漂的孤獨/心里總是空落落的俄想要對他說點什么/但后來我沒有說,說什么都不及給他一對乳房溫暖/但是乳房,我不敢給”(《空落落》)。當我讀完《陽光照進來》,心里特別震驚,作者在言說對“醫院”“疾病”“死亡”(“安靜”)和“絕望”(“離陽光僦那么一步距離”)的感覺和經驗時,不露聲色,言辭簡潔到如同醫院的白色床單一樣,但詩歌整體上的詩意,卻如同那床單好亮好亮的“反光”一樣,叫人肅穆。《空落落》寫一個北漂青年的孤獨與另一個北漂青年無法安慰這種孤獨的遺憾,青春飽滿的肉體對應著“空落落”的心靈,意象之間滿有張力。毫無疑問,到這兒來,我乙經對口語濤肅然起敬。口語詩人大多是一群極有藝術追求的寫作者。
二
我想起湖北詩人大頭鴨鴨(魏理科)的詩。魏理科出道很早,初期出沒于“詩江湖”網站,紊來與韓東、楊黎、于堅、沈浩波等“民間立場”詩歌陣營關系密切。他的詩吸收了口語詩、廢話詩的長處:用最直白的語言,來表達生命的感動、感慨或感觸。這種詩作的風格是,詩作處處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整體上卻明顯地呈現出一種生活里的真實、一種生命中的感動。比如他的代表作之一《一個后湖農場的姑娘》:“巴士進入后湖農場時/一個姑娘上了車/坐在我前排左邊的座位上/她十八九歲的樣子/皮膚偏黑/穿暗紅的T恤衫/半截褲和塑料涼鞋/圓臉、圓手臂/肩膀也是圓的/乳房堅實/個子不高,不胖/卻顯得壯碩/過早地勞動/把她催熟/已經適合生育/和哺乳/這個大地的女兒/眼望車的前方,有時/也扭頭看下我/可能是感覺到了/我一直在后面看她”。
魏理科的詩讓我對口語詩、廢話詩刮目相看,對寫這一類詩的詩人充滿敬意,他們的寫作,要產生詩意,其實更難;因為這一類詩作的詩意來自于整體,所以對遣詞造句的要求其實更高,不能濫用抒情的詞匯,陳言套語更是禁忌,一切工作,要做到恰到好處、渾然天成。這是他的《大雪和烏鴉》:“把道路埋掉∥掩蓋事物的真相∥一場大雪∥卻無法把烏鴉變白∥風將它越吹越冷/更像一塊鐵∥一只烏鴉,在世界潔白的臉上/留下污點∥庀仿佛是故意的”。這首詩的結尾很讓人觸動。但這種詠物詩的模式只是魏理科錘煉口語詩詩意的一種方式。他更多的方式是錘煉詩歌整體的詩意,那種讀完了你會心一笑又悵然若失的詩意。
這幾年,魏理科讓我更肅然起敬的是他的理論文章,我發現他是一個愛讀書的人,一個對自己的寫作有自覺的詩人,他不是偶然地崛起于湖北潛江、聞名于全國,原來他是一個在“詩江湖”廝混多年、目標明確(寫口語詩)、有重大野心(改造口語詩)的詩人,他稱自己的詩作為“后口語”詩,為什么是“后”?這里的“后”既是post也是pass,因為他的寫作對當前的“口語詩”有超越性:“我是覺得自己基本克服了口語詩曾普遍存在的三個問題:一是段子化的問題。口語詩更依賴敘述和敘事,但必須講出詩意。很多口語詩只在講段子,根本沒詩意,只有‘實在,缺少‘空虛。二是自大的問題。即自我的真理化、圣人化和神話。我覺得好詩要徹底地摒棄個人英雄主義,詩人不是救世主,詩人不代表真理,詩人也不是道德模范。詩人只代表自己對語言的修煉以及個體的體驗與感知。詩人要有擔當,但更應該是對自己生活、命運與靈魂的擔當,是向內的擔當,而不是對外。要觀照自身,寫出自己的猶豫、搖擺、困惑、無奈、頹廢、脆弱、叛逆、羞恥、隱秘而.電微的愛、反思、懺悔、追問等等,并由此來趨近人{生的真善美。三是缺乏韻味的問題。很多口語詩太在乎一竿子戳到底的氣勢,語感和語式太簡單化;有的太沉溺于瑣碎的細節,詩歌打開的空間太狹窄;有的鐘情于場景的描繪而宣泄過度,失去了詩歌的可玩味性;有的主觀意圖太明顯直白,沒有一點料峭和崎嶇,導致沒有可發散的意味。”
魏理科坦言他對口語詩有自己的追求:“一是情緒飽滿。無論寫什么,無論言辭是熱還是冷,但詩里都有一顆熾熱的心。一首詩要寫得情緒飽滿,語言不失控,又飽有意味,我認為是挺難的。所以寫詩在我這里,是件很耗人氣力的事情,每一首詩都是自己生命的一種燃燒與轉移。我不是一個隨口就來的詩人,我寫一首詩,常常需要醞釀,主要是情緒與語境的醞釀,以及切入點的尋覓與比對。寫詩是件愉悅的事情,雖然寫作過程中有很多折磨,但每寫出一首詩來,給人的喜悅是巨大的。就像撓癢一樣,詩是心中的一種‘癢。二是各種‘度的把握與拿捏。直白又要留白、出奇又不離譜,既實在又空虛、內斂又赤忱,既濃烈又疏離、沉重又輕盈,顫動又寧靜,張揚而不宣泄,肆意而不亂方寸,淋漓而不輕浮,質樸而不呆板,簡潔而不簡單,錘煉而不留痕,順暢而不打滑,具有張力與摩擦力而又不能生硬,既在此處又在他處,既有形而下的質感,又有形而上的意味,等等。各種‘度的把握與拿捏,滲透在一首詩的全身,一個人的詩歌功夫怎么樣,就體現在各種‘度的拿捏上,我很少說別人的詩好,也是基于這方面的考察。再,我尤其看重一首詩的結尾,我認為一首詩的成敗,一半在于結尾。第三個長處是比較好玩、有趣。我一直想把詩寫得好玩一點,但還沒能得心應手。好玩的詩,太難得了。它既依賴詩人個人的性情,也更需要自由精神與創造力。好玩的詩,更能閃耀詩歌本身的智慧之光。閉目回想一下:我們能記得的詩、有印象的詩,大都是些有趣的詩,這是大腦自然記憶的結果。詩歌的趣味,有很多種……我對深度不太感冒,語言、語速、語感、語氣、語調、語式、語境、意味,才是我看重的。語言的準確、不枝不蔓,是第一步。平淡而出奇是第二步。語言松懈下來,平淡無奇卻饒有意味,是第三步。”
三
另一位湖北詩人平果,也是口語詩的高手。平果的許多作品,幾乎是零度的抒情,但是讀完卻叫人悵然若失,感覺詩作之中有一個旋渦,吸引人的心思意念,讓你無法對這樣的作品作一次性的消費:
咳嗽
那時候
父親總是最晚回家
聽到家門口
父親一聲咳嗽
母親說
你爸回來了
然后全家人
安然入睡
現在妻子總說我
你每次回家
一聲咳嗽
就把我吵醒了
我很茫然地問
我咳嗽了嗎
“那時候”與“現在”的對比,“父親”與“母親”之間的相互感應,“我”與“妻子”之間的齟齬,“我”與自我之間的茫然感……短短小詩,卻蘊藏了很多現代人的生活與情感的信息,在陳述上,作者沒有任何地方表現出抒情的態勢,但卻傳達出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自我的飄忽不定感。這是平果這樣的詩人在寫作上高明的地方,作品看似毫無抒情性,但細細品味,整體上卻言說了人的一種深切的生存體味。
有一次我在湖北某刊物歷數槐樹、黃沙子這些作品十分令人費解的詩人,尊稱他們為湖北的“先鋒詩人”,不想向來性情溫婉、言語不多的大頭鴨鴨向我開炮:“說這些人是湖北詩壇的先鋒派,那你太落伍了……我們才是湖北真正的先鋒!”現在我是贊同大頭鴨鴨他們的。他們就如美術界的抽象畫派,作品看起來令人費解,甚至讓人懷疑這也叫藝術,但其實作者內心有強大的觀念的支撐:什么是真正的藝術?我們認為這才是!對于“后口語”詩人,其觀念非常明確:用最簡單的、最不裝模作樣的語言來言說真實、呈現詩意。這種觀念也意味著一種艱難——對讀者來說,這是挑戰與戲弄:別告訴我這是詩歌……
同居
上世紀50年代末
一對五十出頭的男女同居了
在一個叫趙河的小村莊
一間低矮的茅草屋里
如今他們一百多歲了
仍然在一起同居
在一個水塘的坡坡上
青草覆蓋的土堆下面
為了方便找到他們
我立了一塊碑:
外公王家廉
外婆廖玉珍
之墓
這首詩也是這樣的效果,讀起來平淡無奇,但讀完之后,感動油然而生。1950年代的一對上了年紀的男女,他們相愛了,然后同居了(這是多么需要勇氣,也需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事情),然后他們的愛情至死不渝。這首詩凸顯的意象是“墓碑”,但題目卻是“同居”,它要言說的不是死亡,而是那永遠的愛情。簡短的詩行蘊藏著豐富的信息。我將大頭鴨鴨、平果他們稱為一群認真寫“廢話”的詩人。這一類詩歌,整首詩你看起來都會覺得廢話連篇,但讀完卻很讓人感動,它以最沒有詩意的語言在陳述生活中那些令人悵然若失的東西。大頭鴨鴨坦言,其實這樣的詩作非常難寫。很多時候,你必須像寫古詩一樣,反復打磨,因為它不能有一處詞語、描寫是無用的。與很多讀者所說的想法恰恰相反:這樣的詩,沒有一處是廢話。它追求的是一種蘊深意于無形的整體效果。
四
當代有許多優秀的口語詩的寫作者,他們的寫作是值得尊敬的。即使是趙麗華、烏青,你在當代漢語詩歌發展的脈絡當中,你在他們個人的寫作史當中,才可能對他們有正確的理解。當然,一般讀者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包含文化名人韓寒,也達不到。當代口語詩的寫作者,承繼了韓東的“詩到語言為止”和楊黎的“廢話”觀念,也吸收了“下半身”詩歌對當下現實的直接反映能力、詩歌敘述的“性感”之風,他們的作品,其實越來越好看。這種用最直白的語言來表達生命的感動、感慨或感觸的詩作,我們不能輕視。這種詩作,處處看起來平淡無奇,但整體上卻明顯地呈現出一種生活里的真實,一種生命中的感動。他們的寫作,要產生詩意,其實更難;因為這一類詩作的詩意來自于整體,所以對遣詞造句的要求其實更高,不能濫用抒情的詞匯,陳言套語、思想觀念上的“俗”更是禁忌,一切工作,要做到恰到好處、渾然天成。
我說他們是一群“認認真真用廢話寫出詩意”之人,我對他們充滿敬意。
口語詩的現代性和生命力
李佳鑫
口語詩是當代詩人以口語(相對于書面語)的形態進行的詩歌寫作,詩人們關注日常的生活經驗,以語感為詩歌節奏,著力于詩歌關懷社會現實的能力,為漢語詩歌帶來新的面貌與活力。口語詩就和它的名字一樣看似簡單,但實際上,口語詩的寫作對濤人的觀察力、想象力、表現力、創造力都有較高的要求,因為是“口語”,所以要營造出詩意就需要有另外的途徑。
口語詩自80年代到今天,已經蔚為大觀,在新詩史上有了立足之地,并且很有帶領新詩發展的勢頭。口語詩的現代性毋庸置疑,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口語詩發展對新詩發展產生的積極作用,不能因為某種身份的原因對它進行事實的屏蔽。施蟄存等現代派詩人認為具有現代性的詩歌“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情緒用現代的辭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我們也可以從詩歌語言(現代的辭藻)、詩歌經驗(現代情緒)和詩歌形式(現代的詩形)這三個方面來談論口語詩所體現的現代陛。
一、從書面回歸到口語
白話文運動提倡用白話代替文言的書寫,將人們從書面的文言中解救出來。雖然它的本初目的是服務于政治改革,但是也使文學獲得了更好的發展,這種發展一方面是適應了當時新思想、新觀念的表達,另一方面是便于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因此“吾手寫吾口”以及“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顯得意義非凡。如今口語在詩歌中的使用進而形成口語詩這樣的詩歌樣式,在詩歌發展中實際有同樣的意義。口語顧名思義就是大家在日常交往中實際實用的語言,和書面語相比,沒有文縐縐的書卷氣,但是顯然口語離生活離社會現實離生命的距離更近,因為它能夠更準確地表達出人的生活經驗和日常存在。由于歷史政治的原因,朦朧詩習慣于用暗喻、象征等方式,將詩人的情感隱藏在意象的屏障中,與朦朧詩的朦朦朧朧相比,口語顯得更加直白、形象,因此它能夠更通俗地表達出生活的趣味性,更簡易地表達出生活的復雜性。比如詩人蔣濤的《那一年,我們在西安當螳螂》:
西安人管
打的
叫
擋車
這讓
知識淵博的我
看見了
滿街揮舞的
螳螂
這首詩充滿了想象的趣味和生活的現場感,其實口語所帶來的并不是乏味,生活化的場面往往蘊藏著無限的詩意,讀到這首詩,大概每個人都會伸出胳膊揮一揮,然后會心一笑。
不論是言志還是抒情,詩歌都是依靠語言為演說方式的文學樣式,而語言恰恰又是一種思維方式的呈現,因此選擇口語作為詩歌語言,就意味著選擇了口語作為自己詩歌的思維方式。口語的思維方式是直線性的,這里的直線性并不是貶義,而是說詩人用口語直觀地準確地表達出自己身體各個部位的感受,這種感受既包括易于感知的視覺、味覺、觸覺等,更包括那些由視覺、味覺、觸覺所引起的心理感覺,但是口語詩人又往往不會直接像抒情詩人那樣說疼、痛這樣的籠統的感覺經驗。而是將身體的感覺敘述出來,讓閱讀的人參與到詩人由外到內的感覺形成過程中去。這就意味著他們的詩歌必須選擇具有及時性、瞬時性和敏感性的生活化口語,只有這樣,詩歌本身才能顯現出表意的鮮活性和表情的靈動性,才能夠達到自己感覺傳遞的目的。
口語詩也會出現富有情感性的意象,但是這些意象顯然和之前的朦朧詩中出現的意象有很大的不同。朦朧詩中的意象大多數是我們可以在古典詩歌中見到的自然類意象,比如大海、樹木、太陽、黑夜等,朦朧詩人們繼承了詩經中的比、興傳統,同時引進了西方新意象詩歌潮流中的某些元素,通過物象的排列表現自己思維的跳躍或者借助移情的方式表達自己個人的情緒。而口語詩中的詩歌意象顯然更具有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就是口語詩生命力的一種體現。詩人獨禽就可以讓爆米花入詩:
一枚炮彈一樣的機器
放在火上烤
里面裝著玉米
“嘭”
玉米花亂飛
一群孩子跟著飛出來
“玉米花亂飛,一群孩子跟著飛出來”這句真是厲害,讀者不自覺地想到玉米花飛在天上的情景,生活里便有了些許浪漫,但更讓人感到驚喜的是,玉米花帶給孩子們的情緒特征也被詩人巧妙地表達了出來,亂飛的不僅僅是好吃的爆米花,還有等待著的孩子們,聽到一聲響后帶著歡樂飛奔過去。一直以來沒有人可以冪定什么可以入詩什么不可以入詩,法國象征主義詩人波特萊爾以丑陋的意象入詩,是對詩歌的一次革命,擴大了詩歌可以包容的范圍,而在口語詩人這里,人的生活范圍,就是口語可以抵達的范圍,就是可以出現在口語詩中的意象的范圍。
二、從英雄回歸到個人
在現實中感動詩人的,并不是那些建立豐功偉績的人,而是在底層為了最基本的生活掙扎不放棄的他們,這就是大多數人生活的原貌,詩人看到了體會到了這個國家人民的辛酸和堅強,讀者讀到了悲憫和生活的力量。這就是大多數口語詩所關注到的并且愿意在詩歌中書寫的詩歌經驗。這是陳衍強的《感動我的中國2005年度人物》:
在館子門口抓潲水里的飯菜吃的聶老者
到單位收舊書舊報每斤賺5分錢的王大娘
爹媽死后蹲在街邊給人擦皮鞋的李小燕
為了養活全家午夜還在守著水果攤的趙大貴
每天挑著蜂窩煤往各單元樓層爬的張二娃
烈日下鋤草流的汗珠比收的玉米還多的我母親
天不亮就上學晚上10點鐘還在做作業的我兒子
進城賣雞蛋被小偷摸走12塊錢的我三嬸
被村長踢下身四處上訪被治安員攔截的馬德華
為給公公治病只要有人出30塊錢就脫褲子的劉玉蘭
現在一部分所謂的現代詩人打著朦朧的幌子,蜷縮在自己個人的天地中,用詩歌表達著一些私人小情緒,而讀者被排斥在用生硬的千奇百怪的個人化意象搭建的詩歌的門外,難以進入。到了最后詩歌變成了必須要由詩人自己進行解讀的東西,因此詩歌的內涵變得單薄,詩歌的場域變得狹窄,詩歌失去了傳播的意義,更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還有一部分詩人一直保持著回望歷史的姿態,企圖讓詩歌穿著歷史華美的外衣,展現自己神圣的光芒,這種姿態只會讓詩歌的生命力不斷萎縮。回顧歷史不如關注當下,因為當下本身就是歷史堆積的成果。
口語詩在詩歌經驗上就表現為是對當下社會現實、日常經驗、人的存在的一種關注,對傳統和歷史的一種背離,這種背離姿態表現為去除事物的歷史價值,還原于事物的本質特征。在詩人擺丟眼中,1985是這樣的:
不小心
把雞蛋打落
在光溜的黃泥路上
碎了
苗族奈媽懊惱自責
她俯下身
想把雞蛋收起來
帶走,沒成功
10歲的我
正挑禾谷回家
目睹了下面這
銘記一生的畫面
奈媽跪下
用嘴親吻大地
不,是雞蛋黃
嘖嚕幾聲
一吸而盡
我們并不需要恢宏的歷史畫面告知我們歷史是怎樣的,在口語詩中,歷史記憶就濃縮在“奈媽跪下吸雞蛋”的動作中,歷史就是這樣,由每個人組成,每個人都在過去的存在中留下了屬于自己不可取代的那個部分。
口語詩人直抵生活現場、直抵社會現場、直抵當下的歷史現場,是詩歌進入社會現實的一種途徑,是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人的一種細微卻深刻的表現。他們用生活的視角審視人的渺小,描寫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解讀當下人的存在困惑,發現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表現人性的豐富與復雜,擴大了詩歌的經驗內涵,使得詩歌能夠以言說事實的姿態,占據更大的傳播空間并且恢復了詩歌的教化功能。這種教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說理宣傳,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讓閱讀者由情的通達主動上升為理的認知。比如詩人劉川的《新年大衣柜》:
為新年買的新衣服
在大衣柜里
直挺挺地掛著
又直又挺
沒有一件
是彎曲的
它們如此筆直
真像是一個又一個
有骨氣的人
可新年這頭一天
我就要穿上它們
去給別人磕頭、鞠躬
新年買新衣一直是中國的節日傳統,詩人的眼光雖然在新衣上,但是詩人之所以能夠成為詩人,就在于思緒的深刻和跳躍,詩人并沒有沉浸在直挺的新衣所帶來的喜悅中,而是進一步,想到要穿著這些直挺的新衣踐行中國傳統中粗糙的成分,人的性格就表現了出來。人作為有思想的動物,竟然還不能像一件衣服一樣筆直地活著,必須向別人磕頭、跪拜。新衣與舊俗,詩人從大家共有的生活經驗出發,發現了別人不能發現的,但是又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從而引起讀者對傳統文化、對人當下悲劇性的存在的反思。這就是口語詩人的高明之處。
而在經驗表達上,與朦朧詩表達時代帶給人的個人苦悶或者說一類人的痛苦相比,口語詩顯然擴大了表達主體的概念,將一類人擴大為所有人,不管是所謂的大人物、知識分子,還是生活在社會底層艱難求生的人,每一個人都有愛恨情仇。口語詩人正是以發現生活的姿態,敞開自己的內心,細致地感知他人,認真地融入生活,潛心地與社會交流,在交流中使自己的存在得到更明確的感知,因此詩歌不再被限定在一個窄小的自我言說的空間里,詩人個人的生命縱深感和他的生命寬闊感都在這種敘述中被完全打開了。
在口語詩中,不僅僅是經驗表達主體獲得了擴充,不同種類的人都可以在詩中找到自己真實的身影,所表達的經驗內涵也有了相應的擴充。我們可以相對簡單地劃分出中國傳統詩歌所表達的經驗類別,但是很難把口語詩做種類的劃分,因為每一種經驗感受都可以被口語詩人寫在詩中。
另外,在經驗的表達方式上,口語詩人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口語詩并不是直接把“傷口”擺給讀者看,然后嘴里喊著“疼”“痛”,它是運用情景化的場景,事實的敘述,把受傷的過程展示給讀者,直擊你的腦部神經,調動你的想象力和身體的敏感性,不用詩人說痛,你便跟著他一起痛了,甚至可能比他感受到的還要痛!這種表達方式營造出來的是一種事實的詩意。朦朧詩用意象搭建起了詩歌的想象空間,產生的意境的美感和中國古典詩詞的美學特征相一致。而口語詩所發展的是詩經中“賦”的修辭手法,從以意象為骨架的結構中跳了出來,以口語為語言形式,直逼事件本身,使人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依靠事實的聯想,獲得體驗的快感和感情的生發,形成事實的詩意。事實的詩意和意象的詩意相比,顯然有更廣闊的生存境地。“人跡板橋霜”雖美,但這種美,也只是到美為止。但是事實的敘述不僅僅是美的享受,更是詩人感情生發的一個過程,那么讀者就能在閱讀中和詩人一起經歷。從而將詩人的經歷轉化為自己的體驗,達到情緒交流的目的。
的確,因為詩歌的待殊言說方式,很多人覺得詩歌離生活很遠,但事實并不是這樣,詩經中的風就是對生活的敘述描寫,只是在之后的發展中,詩經中的雅和頌得到了更壯大的發展。風便被逐漸擱淺了,這種擱淺使得詩歌離大眾越來越遠,甚至被部分人誤認為詩就是個人化的東西,這種詩歌觀念顯然不利于詩歌的長久發展。很顯然口語詩的出現改變了這樣一種有偏頗的詩歌發展局面,為詩歌注入了生命的活力,我們不應該輕視當下的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經驗,當下是由歷史匯聚到這里的,如果我們只記得回望歷史,而忽視了當下,那么還怎么從當下獲得向未來發展的動力?因此我認為,口語詩所表現的當下性,恰恰就是它的未來性,意味著口語詩有它掩蓋不住的生命力。
三、從韻律回歸到語感
詩歌的發展在歷史的長河中已經有了它自己的清晰脈絡,這條脈絡發展到胡適有了一個巨大的轉折,爾后由破至立,白話新詩不斷發展成熟,當今的口語詩又可以被視為一次突變。口語詩和其他詩歌的不同,還表現在詩歌的形式上。在本質上,詩歌的分行特征沒有改變,他們改變的是詩歌所依據的節奏特征。中國古典詩歌依靠平仄的概念掌控整首詩的韻律和節奏,達到一種朗誦或唱誦的和諧;白話新詩在萌芽和發展中不斷對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平仄概念進行反抗,不同的詩人提出了自己的詩歌主張,比如說聞一多先生以韻、節以及音尺的概念對白話新詩做出一系列的規范,毋庸置疑,在白話尚不成熟,新詩觀念仍處于建立的時期來看,這些理念的提出對新詩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之后戴望舒等現代詩人提出以情緒的節奏代替詩歌韻律的節奏,強調詩人要將詩寫得自然;卞之琳等詩人提出了新詩戲劇化的觀點,將具體化的情景、動作、對話作為材料,應用在詩歌創作中,認為詩的語言必須以日常的語言為基礎;廢名認為新詩應該是用散文化的語言自由地寫。這些現代詩人對新詩詩歌觀念的建立都立足于自己的詩歌創作和自覺的審美基礎上,不斷擴大了詩歌所能容納的范圍,避免了新詩剛剛打開中國古典詩歌的枷鎖就掉到西方詩歌的陷阱中,還詩歌以自由,還詩歌以生命。
對于口語詩人來說,他們所提倡的是依據詩人的語感來掌控詩歌的節奏。伊沙更是用“口氣”來為“語感”命名。語感來自于詩人對語言的敏感,口語詩人使用的的確是最普通的日常語言,但是怎么熟練地使用口語創造性地表達出自己的審美體驗?怎么使讀者在閱讀口語詩的過程中既有美的享受,又有生活的熟悉感?怎么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獲得高度的想象力和敏感意識?怎么用口語建立自己的詩歌節奏?一首優秀的口語詩必須解決這些苛刻的問題。比如“我攔不住你/我夠不著你/我替不了你/我叫不醒你”(王小龍《墜落》),這四句詩單獨成為一個小節,表現“女孩”墜落時“我”的反應,伸出了手卻拉不住、夠不著,想要替“你”一躍而下卻無能為力,想要叫醒沉睡迷茫蒙昧的“你”,可惜自己的力量太弱,“我”發出了動作、想法、聲音,仍然抵擋不住“你”墜落的悲慘結局,于是讀者在閱讀中仿佛能聽到墜落時耳邊呼呼的風聲,“我”的歇斯底里的呼喊、掙扎和內心瞬間的痛苦,感受到了“我”的緊張、急迫、無奈。這就是詩人獨一無二的語感,用最簡單的句子,表現出了情緒和現場的質感。
口語詩人必須使用這樣簡單的語言和句式,創造出一件件精美的藝術品,同時這些藝術品又能讓讀者產生這就是生活的感慨。是語感讓口語性的敘述仍能產生詩意的審美和感受,使詩歌成為詩歌而不是其他。一首優秀的口語詩只屬于某一個具體的作者,他是詩人具體的鮮活的生命印記和生活感受,別人無法套用,因此語感雖然是優秀的口語詩共同的標尺,但是又因人而異。
結語
口語的,日常的,語感的,這三個維度其實是一體的。詩歌既然是口語的,就意味著它是詩人心靈更直接的敞開,一方面它表達了詩人自己的言說態度和言說方式;另一方面,詩人從自身出發,密切關注口語能夠抵達的生活社會百態;而優秀的口語詩又必須依靠語感樹立起詩人鮮明的個人風格,表現獨立的詩歌美學特征,這樣才能顯現詩人與眾不同的創造性。優秀的口語詩正是三者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