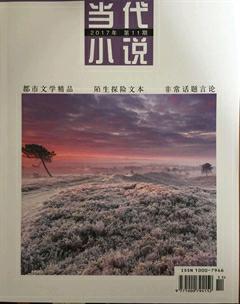生命如同花椒樹般堅強
張麗軍
生命如同花椒樹般堅強
劉仁杰
愛情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之一,它能凈化人們的思想,慰藉浮躁的靈魂。在金錢異化人心,肉欲橫流的時代背景之下,真摯單純的愛戀已經難以再尋蹤跡,給人留下一種內心深處的悲哀。文清麗的《綠萼梅》(《中國作家》2017年第7期)又名白梅,象征著純潔高雅。然而在愛情的背叛里,綠萼梅失去了她本來的色彩。由眼前的老干部聯想到多年前發生的愛情故事,至今讓人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唏噓不已。在劉平勇的《欲說還休》(《中國作家》2017年第7期)中,老一輩人的感情雖然很平淡,但是相守就是最大的幸福。爸媽在一起四十多年相互扶持,即使父親去世了,母親內心依然是溫暖的。主人公的婚姻是悲哀的,她不僅沒有一個相守的丈夫,而且因為他的賭債失去了自己的貞操。王手的小說《第三把手》(《收獲》2017年第3期)講了一個鞋廠的故事,金錢讓人的生活變得豐富,也在暗中侵蝕人心。在有些人的世界觀里,婚姻、愛情在金錢面前,顯得有些無足輕重。第三者的出現破壞了家庭,但這種事情卻似乎是當今社會有錢人必然會經歷的,不得不說這是時代的悲哀。薛憶溈的小說《母親》(《作家》2017年第8期)寫了婚姻出現了問題的一對夫妻,二人在生活和觀念方面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孩子成為他們婚姻的唯一紐帶。當青春年華逝去,母親和父親之間已經沒有太多共同話語,只留下深深的寂寞與懷疑。陳再見的《陵園舞者》(《作家》2017年第7期)講述了在當今社會中的丑陋一面,主人公出軌一個青年,丈夫與年輕店員之間私通,女兒被人輪奸卻又當作無事發生。最后主人公被變態殺死,為自己的出軌付出了代價,同時也折射出當今社會關系混亂、教育失衡的一面。李瑤音的《西施密令》(《中國作家》2017年第7期)講述了西施與范蠡隱居之處的保護性開發,既是對于千年愛情故事的贊頌,也是對于歷史的尊重。鐘求是的《街上的耳朵》(《收獲》2017年第3期)主人公式其步入老年,年輕時候的愛情和仇恨都成為回憶。但令式其最難忘的是那段青春的年輕時光,以及曾經的自己,只有時間能夠改變容顏,消解仇恨。在竇紅宇的《紅宵屋》(《十月》2017年第4期)中,愛情在金錢化的社會面前,顯得那么孱弱無力,同時在現代化大潮的進程中,土地的流逝與傳統的破壞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愛情、人性在金錢、權力的異化下變得可悲,拆遷日益成為人們生活中所關心的重要問題。秦眼鏡對于煤礦有著深厚的情感,夢想著有一天能夠重振煤礦昔日的熱鬧。張芬與秦眼鏡相互愛慕,無奈秦眼鏡沒有足夠的錢蓋房子,只能聯合幾個昔日的工友,在豬圈之上用廢舊材料蓋了一座屬于自己的房子。房子雖然很小,卻也是兩個人溫馨的愛巢。王小富從小喜歡張芬,張芬卻看不上他的邋遢形象,王小富因此懷恨在心。在拆遷的過程中,王小富不再理會張芬的請求,執意推倒秦眼鏡的房子來開發房地產。秦眼鏡和張芬的愛情,在現代化,工業化的進程中,顯得不值一提。拆遷過程中,人們為了金錢放棄自己的家園,同時也顯現了金錢成為衡量人們社會地位的唯一尺度。雙雪濤的《白鳥》(《收獲》2017年第3期)涉及到愛情故事,講述了那些存在于我們周圍的平凡愛情有著自己獨特的魅力,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世界觀,只有心存一只為愛人遮風避雨的白鳥,才能收獲真正的愛情。
贍養老人,尊敬父母,是每一個子女應盡的責任,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良傳統。對待父母不僅僅需要物質上的幫助,更需要精神上的陪伴。任曉雯的《別亦難》(《人民文學》2017年第7期)就寫道,兒女對于父母的養育之恩,要回報的不僅僅是金錢,更應該是陪伴。生活的苦難不斷壓向陶小小,丈夫年輕時候家暴,年老時收養的一只黑貓也離她而去。陶小小忙了一輩子都是為了別人,承受著重壓,然而在年老時,女兒卻不能在身邊陪伴,就連貓也離她而去,留下了兩個老人孤獨生活。烏鴉有反哺之意,羔羊知跪乳之恩,張不退的《負回憶》(《作家》2017年第7期)講述了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是每個人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每個人良心的體現。小說通過書寫家庭生活的瑣碎,披露了社會生活中的贍養老人問題,也展現了婚姻是一座圍城。王大進《快跑的聲音》(《作家》2017年第7期)展現了父母對于孩子的愛是可以超越極限的,脆弱的人在孩子面前也會變得無比堅強。阿大從小擅長跑步,也十分懦弱,曾經在一次次的考驗面前退縮,在小寒的病情惡化之時他再一次逃走。但是他最終還是回來了,奔跑在下雪的街道上,希望能追上開發商的小轎車,拿到小寒的救命錢。在寒冷的冬天,因為這份父愛的存在,顯得足夠溫暖。愛情的力量是偉大的,它可以令人有勇氣面對一切,同樣親情的力量也是偉大的,它可以在你受盡愛情摧殘的時候救贖心靈。貧苦的生活很容易將人心異化,只有愛和被愛才能撫慰內心。孟昭旺的《旅行》(《十月》2017年第4期)中李東與李紅是一對姐弟,從小李紅對李東呵護有加。年少時候李紅為了追求自己的愛人,甘愿與父親決裂。在結婚的時候,丁洋將李紅父親的肋骨砸斷,從此以后李紅不能踏進家門半步。在以后的日子里,丁洋因為生意的問題與人發生了沖突,從此拋妻棄子遠走他鄉,李紅苦苦地等待卻換來丁洋的背叛。李東出獄后,不忍看姐姐受欺負,便在夜里將侯三殺死,棄尸水塘。李紅帶著孩子滿懷希望地和李東一起南下尋找丁洋,而李東自知犯下了大罪,內心深處已不再平靜。
世事多變,如棋局般常新那是歷史的必然,社會中的人生本來就如同一場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舞臺,也都有自己的精彩。社會的發展總會有陰暗面的存在,在社會的陰暗面之中,更陰暗的是人心難測與虛偽,是權力的的失衡與濫用,是歷史的殘酷輪轉。夏天敏的小說《是誰埋了我》(《十月》2017年第4期)中提道,戰爭不僅對人肉體上產生了傷痛,更在社會、人性的層面留下來了許多陰影。在無奈的性愛與純潔的愛情之間,李水遭受了巨大的煎熬。如果不與匪首的女兒桃花交合,就永遠無法逃出匪窩。如果與她交合了,又該怎么樣對待家鄉的愛人玲子,這令李水陷入了糾結的境地。李水在欺騙了桃花,逃離了匪窩之后,帶人剿滅了這伙土匪。可是李水卻并沒有獲得心安,在家鄉他是一個不在了的人,在愛情里他親手埋葬了與玲子的純潔愛情。在內心深處他已經是個死過一次的人了,在戰爭的巨大漩渦里迷失了方向,良心久久不能平復,一份份榮譽獎章也無處安放。錢靜的《顯微鏡》(《作家》2017年第7期)用顯微鏡將生活中的酸楚放大,在城鄉巨變的過程中尋求自己的幸福,在顯微鏡中發現自己以前沒發現過的東西,尋求生活、愛情的真諦。第帶著冬的《灑之同志要來》(《中國作家》2017年第7期)寫出了政府基層工作者的悲哀,一方面要貫徹政策,不斷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一方面又要不斷處理各種各樣的上訪案件。電話里的灑之同志要來,其實是“傻子同志要來”,鄉鎮領導為了維持穩定,不得不將各個上訪重點戶控制起來,小說也展現了信訪部門的一些工作弊端。肖勤的《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人民文學》2017年第7期)小說涉及了當代社會中的權力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陰暗面,同時也展現了社會中依舊有心存正義、良心的人廣泛存在。黃梵的《報復》(《作家》2017年第8期)描述了何東與主人公之間相互詆毀,用卑劣的手段損壞對方的聲譽。主人公用廚藝的道理來解釋自己照抄別人著作的行為,又在夢中產生了陷害何東的想法,表現了現代知識分子虛偽卑鄙的一面。棉棉的《失蹤表演》(《收獲》2017年第3期)強調了人生本就如同一場大戲,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這場戲中,我們費盡心思的偽裝自己,生活充滿了浮躁、虛偽和欺騙,但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是有意義的,我們應該笑對人生,演好生活的這出戲。
網絡時代的到來,便利了人們之間的信息交流,同時也滋生了新型的違法犯罪行為。范小青的小說《千姿園》(《作家》2017年第8期)中的主人公利用微信騙取房客的信任,用各種手段牟取錢財。隨著同名同姓的一個王偉突然出現在自己視野之中,小說主人公仿佛看到了一個鏡中的自己,卑鄙猥瑣的靈魂受到了審視。快速發展的網絡社會讓知識的攝入變得簡單,牛健哲的小說《獅虎尚未相遇》(《作家》2017年第7期)講述了獅虎相交的故事,告訴人們在現實面前應該保持自然平衡的態度,尊重真正猛獸的尊嚴,不要把它們當作寵物或囚禁于牢籠。同時也折射出在網絡時代高校教育的一些弊端,強調應將知識應用于實踐。萬寧的《朋友圈,同學群》(《當代》2017年第4期)中的吳緒在喧鬧的社會生活中疲憊不堪,曾經純潔的戀情讓她回味無窮。“我們這個社會的階層與圈子,一直是隱形的”,或許只有在微信群里,每個人才能相對公平的說上幾句話,展現一下自己的生活。在微信的朋友圈,同學群背后,是對于青春年華易老的感嘆,是對社會生活的隱憂。微信方便了現代人之間的相互聯絡,讓故人有了重新相見的機會,滿足了精神層面的需求。但微信的朋友圈也讓現實的社會關系更加復雜,傳統中國式的人情往來在微信中消磨。
一個好的作家是有精神故鄉的,如魯迅的“魯鎮”,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同樣,“老實街”是作家王方晨的一個精神坐標,這里有著作家獨特的人生感悟與審美情懷。在小說《鵝》(《作家》2017年第8期)中,“鵝”神秘的懷孕后產下了一子,無論爹怎樣責備也不肯丟棄這個嬰兒。鵝后來與自己喜歡的男人們發生了關系,也因此受到了母親和兒子的譏諷。但無論在老實街遭受了怎么樣的苦樂,她都是一只屬于故鄉的鵝,這里才是她真正的歸宿。鄉村是當代人的精神之根,只有在鄉村之中,人們才能真正回歸自然,享受生命之間的心靈交流。鄉村與城市是有著內在深厚聯系的,然而城鄉之間的差距又是難以消除的,農村人在城市總是會受到各種歧視,農村總是作為犧牲品支撐城市的建設。方格子的《在豆莊》(《作家》2017年第8期)中豆安是一名記者,在世道人心巨變的當代社會,他見證了發展過程中的金錢問題與人心異變,同時也感受到了農村人在都市的辛酸無奈。鄉村一方面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開發利用,另一方面因為地理條件不便、政策落實不到位等因素,其自身發展也受到了許多限制,因而鄉村健康發展成為當下的一個焦點。在光盤的《抓捕路霸江自善》(《當代》2017年第4期)中就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江自善是一個心系村莊的普通村民,為了能有一條路而四處奔波,想要求助于政府,政府的官僚作風卻讓他屢屢受挫。最終他聯合村民,籌款60萬修了一條路,但是私設關卡,企圖用過路費來收回修路的投資。縣長的車被收了過路費以后,下令抓捕江自善,派出所長葉予嘉同情江自善,也同情鄉村命運,不愿抓捕他。最終江自善接受了礦粉廠的60萬,不再收取過路費,但是鄉村環境卻遭受了嚴重破壞,江自善為了鄉村命運,挺身而出炸毀了礦粉廠 ,卻也必須承受法律的制裁,成為了一個悲劇式的人物。王方晨的《鄉王》(《中國作家》2017年第8期)講述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土地進一步受到侵蝕,金錢利益改變了鄉村的本來面目,同時人們的精神故鄉也變得模糊不清。城市的喧鬧與繁華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卻不能為人提供精神的歸宿。孟昭旺的《尋羊記》(《十月》2017年第4期)中孟毛在尋找丟失的羊的過程中,發現了那個女人和父親所做的丑事。他為了尋找自己缺少的母愛,用鐮刀威脅她,想要那個女人擁抱自己,卻在女人懷抱自己的那一刻逃走,小說描繪了農村留守兒童的苦悶與鄉村道德的淪喪。胡學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學》2017年第7期)中的苦水淖是一個環境十分惡劣的地方,因為水質的原因,造成了這一方人的低矮身材與悲慘命運。喬果果是一個出身于苦水淖的純真女孩,雖然身材矮小,卻心靈手巧,而且頗有繪畫的天賦。主人公賞識喬果果的才能,希望果果能夠深造繪畫。然而單純的果果卻與人面獸心的許老師發生了關系,并且懷孕了。在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巨大,生于苦水的純潔之花,終于又在現代社會中遭受了更大的傷痛。
生與死是人類永恒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歷史長河中的國仇家恨面前,是像一朵煙花在空中綻放還是如落葉般安靜入土,這與每個人的人生觀有著密切聯系。房偉的《獵舌師》(《當代》2017年第4期)將個人的仇恨和歷史浮沉聯系在一起,在歷史大背景之下襯托個人命運的悲哀。在戰爭中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報國仇家恨,“軍人殺命,書生誅心,料理獵舌”,廚師下毒本是行業中最不齒的事情,但個人名譽、生死在歷史大潮中顯得微不足道,寧可轟轟烈烈的為了國家而死,絕不茍活于侵略者的腳下。宋尾的《隱身》(《人民文學》2017年第7期)中講的是在當代社會,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毫無愧疚的活著就是一種幸福。主人公因為自己的戀人被殺,留下了心理陰影,不愿意接受別的女性,卻一次次地在暗中跟蹤不同的女人。在這種變態的快感中尋找自己的安慰,然而最終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諦,在夜色與鐵銹中放空了自己。姚鄂梅的《兩棵花椒樹》(《人民文學》2017年第7期)中的倪可與主人公是在病房中結識的朋友,倪可年輕貌美,并且很有才華,卻無奈病魔纏身。倪可的讀者對她議論紛紛,一次次所謂的探望對她來說也只是變相的譏諷。主人公與丈夫分居,年輕時候的愛情火焰早已熄滅,突如其來的“癌癥”讓她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主人公一直安靜地等待死亡的到來,最后才發現這是一場誤診。而倪可卻沒有那么好的命運,她25歲就要走向人生的終點。在倆人分別之際,倪可送給主人公的兩棵花椒樹有了別樣的含義,一方面人生需要自我調味,一方面也要如同花椒樹那般堅強。即使人生路已經接近終點,也要留下屬于自己的美麗。劉汀《夜宴》(《十月》2017年第4期)中的胡燕云是當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類似于郁達夫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但小說中不僅僅有陰暗的部分,也有對于人生和命運的希望,他對于人生的看法正是千萬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
深沉的哲思與溫情的現實
妥 東
作家對生活的思考和想象往往基于一定的生活。在面對現實中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時,敏銳的作者總是試圖以最快捷、最銳利的目光將這些動人的生活畫面記錄下來,融入自己的情感體驗,將他的感受傳遞出來。在生活面前每一個懂得用熱情去欣賞的人,都會發現不一樣的風景,而善于思考的寫作者,更是如此。他們會在人們忽視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不一樣的故事,而在他們的講述中,這些故事往往透著對生活深刻的思考。
曹多勇的《出走》(《時代文學》2017年第7期)講述的是一個平凡生活中的女性,在面對生活的不盡如人意時選擇三次離家出走的經歷。這個故事最初看來,頗帶有方方的中篇小說《出門尋死》的味道,因為生活的沉重和不如意是她們共同出走的理由。相較而言,兩篇小說在敘述中所形成的線索大體是一致的,即通過出走這一行動,反觀現實的生活,在目睹人生中的艱辛之后,在外在的環境中,又得以把握生活的本質,從而做出自己新的選擇。從故事的結果來看,曹多勇的《出走》實際上還是形成了與方方一致的答案。小說中主人公宋雅琴的三次出走就好像三次不同階段的人生經歷一般,在沒有經濟能力的情況下,女性的出走面對的一個鐵定的事實就是——她還得回來。與曹多勇透過女性出走這一主體設置不同的是,李進祥的《三個女人》(《朔方》2017年第6期)則從正面寫出了現實生活中女性的不同生活境遇。小說的主要線索是通過敘述者的旅行串聯起來的。與曹多勇的《出走》相反,李進祥這里是敘述者的旅行之所見所聞。由此,在旅行的不同時段內,三個女性形象漸次進入敘述者的視野。小說中“我”遇到的三個女性分別是“吹葫蘆絲的女人”、“抱孩子的女人”、“開出租車的女人”。每個人的生活中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艱辛和苦澀。正所謂每一個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李進祥的敘述將三個女性平凡背后的故事娓娓道來,讓我們感受到生活溫情之外的現實,也體會到三位旅途之中的女性面對生活所表現出的堅強的意志。在生活面前永遠都有不平凡的強者。故事中三個女性雖然都有不同的人生遭際,但是在現實面前,在生活的艱辛面前,她們的臉上依然保留著信心和勇氣。李進祥同寧夏的許多作家一樣,在深入生活的現實面前從來不含糊。
與李進祥的《三個女人》同樣閃爍著濃濃的人間滋味的還有馬悅的《一根紅絲線》(《回族文學》2017年第3期)。故事講述的是一個回族老人的平凡生活,老伴去世后老人的生活狀況一天不如一天。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孤寂淹沒了一切,生活之中的動力和支撐就靠著細細的回憶勉強連接起來。在宗教洗禮的氛圍中,老人想到了“新生”。而單娃手上系著的那根紅絲線正像維系老人的寄托一般,不僅對來生充滿了希望,同樣表達了對于生命的強力的一種強烈渴求。關于宗教反思和救贖的升華讓這部小說超脫了以往的瑣碎,達到了更高的境界。透過這一切,反觀曾經的平凡和樸素,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又是那么合理,但又有著分外的沉重。
同樣在現實中足以給人的心靈沉重一擊的還有葉周的《布達佩斯奇遇》(《北京文學》2017年第6期)。小說講述了一對母子的境外遭遇。小說將敘述的目光轉向了經歷戰火的難民的遭遇。在小說中講述了一位美國華人女記者帶著女兒出游歐洲的經歷。她們在布達佩斯與浩浩蕩蕩的敘利亞外逃難民相遇,并目睹了逃難的一家四口在病亂中的生死抉擇。七歲的男孩原本跟隨母親和妹妹逃離戰火流落異國他鄉。但途中前路受阻,途中兩個女兒又相繼生病,為照顧更年幼且途中生病的女兒,母親不得不冒險忍痛將兒子托付給陌生路人,讓他跟陌生人繼續前往德國。在逃難面前,母子分離的場面讓人痛心。小說在女記者的視野和目光中見證了所發生的一切。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無數的悲劇永不停歇的在上演。流離失所痛失親人,這些在戰爭中顛沛流離的難民遭遇無疑又一次刺痛了我們的內心。戰爭給人們帶來的代價是慘痛的。女記者在布達佩斯所遇到的母子分離的抉擇,只是戰爭所波及到的極小的一瞥,更多的無辜的人正在被迫走上流亡的路途。
當然,在狂野的呼號和對生命不公正的反思和控訴之外,還有對平凡生活中樂觀幽默的表達。王凱的《沙漠中的葉綠素》(《青年文學》2017年第7期)就像一個不斷制造著生活趣味的裝置一般,將我們的視野帶向了一線軍人的愛情生活中。《沙漠中的葉綠素》講述的是三個青年大學生軍官在基層部隊的生活經歷。主要圍繞著主人公陳宇的愛情生活展開,將駐守沙漠邊關的軍人生活面貌呈現了出來。小說中陳宇、何勇和彭小偉三個年輕的軍校大學生畢業被分配到駐在沙漠的某空軍基地。在平凡枯燥的基層部隊,三個對生活有著理想的年輕人分別經歷了愛情的洗禮。王凱的描述中,原本枯燥的生活也變得有趣,他的語言和敘述節奏是我最喜歡的。在漫無邊際的講述背后幽默的情調和態度,將生活改裝成一輛裝備齊全的野戰車,游行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正如《青年文學》主編張菁所評論的那樣“王凱的作品有著中年男人的柔情和嬉笑下的真意。我在閱讀的時候,幾次忍住眼淚,生怕辜負了作者營造的歡樂。日常的生活真的只是把我們的感知磨鈍嗎,有時候我們看到的厭倦不過是因為表皮上的浮塵,還沒有被吹散罷了,但它并不妨礙我們內心的相信與堅持。《沙漠里的葉綠素》呈現著王凱骨子里的幽默和深情。”當然,小說中除了滋潤沙漠的愛情葉綠素之外,對生活無盡的幽默樂觀的態度,才是這部小說所帶給我們的最精當的物事。
生活的豐富性永遠是小說家對小說創作追求博遠的最夢寐的理由。也由此,在生活的不同層面上我們在作家的寫作中看到了不一樣的風景。尤鳳偉的《水墨》(《北京文學》2017年第6期)就讓我們領略到了當代畫壇的一系列不一樣的“風景”。小說講述的是一個不知名的畫家,在晚年卷入一場刑事案件之后面對相繼而來的各種人生問題所做出的選擇。小說中畫家坧泉原本是一位默默無聞的畫家,但隨著自己的畫作被盜,警方介入調查,他也因此有了可以讓自己畫作升值的炒作機會,但當他得知盜取畫作的人是小區物業的老邱時,他的內心面臨著一次重大的抉擇。老邱的家庭狀況他了解,考慮到自己的畫也不值幾錢,坧泉想就此息事,但是無奈他的弟子越東已將此事報告予警察局,案子進入司法程序,無法撤案。最終案件告破,老邱被關入監獄。坧泉一直想方設法彌補,但實際上這一切都是老邱對他的成全。小說通過坧泉畫作被盜警方隨之介入這一線索將做人的底線放置在考量之中,坧泉的選擇和他的弟子的選擇在這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小說還將當代畫壇的種種怪相展露畢盡。阿諛奉承,以次充好,無良炒作等等這一系列的事情在畫壇依舊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與尤鳳偉的《水墨》對生活群像的反映不同的是,潘靈的小說《偷影子的人》(《大家》2017年第4期)則將小說敘事中的哲思非常精妙地傳達了出來。小說講述的是云南邊陲的移民小鎮的故事。主人公韓家川原本是市文聯的一位創作員,因主動反映意見被安排到昭女坪移民社區掛職,創作一部反映移民生活現狀的報告文學。小說以韓家川在昭女坪的經歷為故事結構的線索,將昭女坪所發生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串連了起來,先是以陳三爺為首的“自救自五人小組”的“偷雞事件”,之后又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團來昭女坪參觀。這兩件事情串聯起來,將昭女坪的村風民俗,以及移民之后原始村民的生存狀況展現了出來。自救自五人小組表面上去錄公雞雞叫的聲音是為了睡眠不足的鐘老漢(鐘老漢聽不到雞叫的聲音無法入眠),實際上,它也同樣指向移民對于新環境極不適應的現實感受。這篇小說透過韓家川的視角所勾連起來的不光有歷史歲月里的恩怨情仇,還有新時代環境下,對國家移民工程的深刻反思。
杜光輝的《十四號病房》(《飛天》2017年第7期)講述的是一個關于寫作者之間的感人故事。身患肺癌的老作家魏繼青在生病住院期間,無意間看到與他同病房的年輕人胡孝坡以自己的真實經歷寫成的小說,于是他產生了幫助年輕人校訂小說并出版這部小說的想法,最終他得以完成這個目標,在魏繼青的努力之下,胡孝坡的小說成功出版。小說的故事節奏交替循環,一方面以作家魏繼青的視角進行著故事主線的串聯,另一方面,故事中又將小作者胡孝坡的小說故事情節穿插于其中,使得這個故事有了雙重的故事線索和敘事節奏。小說的故事雖然平凡,但是經過這樣的包裝處理,明顯地超越了故事已有的內核,不論是在寫作技巧還是情感傳達的層面上,這篇短小的作品都做到了精致又豐富的呈現。在常新港的《男孩子汪天洋》中(《延河》2017年第7期)小男孩汪天洋的世界同樣是豐富多彩的。作者常新港通過細膩的筆法將小男孩汪天洋的心靈世界的變化成長刻畫得十分美妙。展現了孩童世界那份純粹的童真與美好。這部小說在當下的現實語境中似乎有著十分濃烈的反襯意味。從更深層次上來討論的話,則可以將話題延展到成長過程中社會對一個孩子的影響。我們都樂于看到童真的美妙,但同樣在成人世界中,人作為個體的所作所為與孩童時期的一切都相去甚遠,此中的差異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在男孩子汪天洋的世界中,似乎每一個生存于世間的人,在他的成長中都對他有益。沒有利害關系也沒有親疏遠近,在他的心里所裝下的那丁點小事,對他來說都意味著一種不安,反觀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很多時候卻是選擇性地忽略著,絲毫不顧及他人的感受。
在聶鑫森的《世俗凡人》(小說三題)(《青島文學》2017年第7期)中,聶鑫森以小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他對個體生命的“文化性格”的一如既往的關注。三則小說故事結構雖然看起來非常簡單,取材也來自于普通的現實生活。但反復閱讀會發現,聶鑫森正是通過對不同的平凡人物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擾及其化解方式的探尋,并透過文化的照射,將他們的“頓悟”和“釋然”呈現了出來,從而找到了這種困擾背后的“文化癥結”。而化解的最終方式,則是“自信”與“釋然”的文化背后,所代表的那種“無為與有為”的文化性格。這種對日常生活中的突然發現,已然讓他在生活面前多了一份通達。聶鑫森從文化高度上去審視簡單生活的瑣事,不僅為這篇短小的小說注入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內涵,也打開了小說的外延,語言精簡而又不失文辭。與此相同,韋俊海的《接上一只異性的手》(《滿族文學》2017年第4期)似乎也是從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主題的,但是他所處理的是新時代的“父與子”的關系的話題。小說的敘述是從兒子的視角進行的。因此,在兒子的眼中父親的形象一步步呈現在讀者的面前,當我們閱讀完最后一句話的時候,父親的形象實際上已經無法立起來了,這就是這部小說所要表達的“新父親”形象。在兒子的眼中,他的父親成了貪戀無能自私自利的色情狂,他那因車禍而斷的那只手,在手術過后換成了一只女性的手,他開始用這只手瘋狂地謀劃一切事情,先是看上了美麗的麗麗,但是受到干擾最終未果,接著又開始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進行洗錢。最終他被關入監獄,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在兒子的眼中,父親儼然已經被結構得支離破碎,而從古至今的所謂的父權的強大的宰制力在這篇小說里蕩然無存。
現實生活有時候的感傷一方面是自己的情緒所受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時間的流逝中,似乎這種世事變遷之中已注定會有一種不一樣的思緒,它會在某一時刻擾亂你,讓你對現實變得不那么陽光自信。丁力的《重逢》(《中國作家》2017年第7期)從某種程度上將這種狀況呈現了出來。小說通過“我”重回馬鞍山與故友重逢,引開了一系列對過往歷史的追憶和反思。將特殊年代人們的生存環境和現在的生存境遇進行了對比,最后他似乎又回到了起點一樣回到了深圳。“別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擾,而自己也不愿意打擾別人。”小說的敘述氛圍多少帶著一點憂傷,讓人讀完難以釋懷。細思主人公所遇到的種種,實際上如果僅靠回憶去填補現實中的許多無奈是遠遠無法彌補的,很多時候,往事已經在逝去的時光中不可追了,所以,不論是置身于舊地的重返還是在記憶的深處重新回憶都需要巨大的勇氣和信心。
不論從哪個層面來談論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中短篇),一個比較明顯的事實是,作家們在面對生活的復雜性面前永遠沒有失去把握的能力和信心,這一點是現階段的創作者,尤其是創作新人表現出的顯著特點。
尋找失落的精神生命家園
袁 雪
人生往往是苦多樂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眷戀著生命。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有很多作品描寫了人生的苦難,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所以,書寫溫情的當代文學作品顯得尤為可貴,溫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人生的苦難和煩惱。王祥夫的兩篇小說《浜下》(《長江文藝》2017年第14期)和《半截兒》(《長江文藝》2017年第14期)是關注人情世故的力作,對細微情緒的描寫入木三分。《浜下》中的婆婆是位八十三歲的老人,身體矯健,生有兩兒兩女,在兒女們成家立業后,婆婆一直獨自生活。兒女忙于生計,平日里沒有時間去看望母親。當婆婆不小心吞下了半枚針后,引起了兒女的關心和自責,他們慌忙趕來照顧母親。婆婆看到子女齊聚一堂,內心一陣陣的興奮。然而,當她順利地將針排出體外后,兒女的關心也隨之消失了,他們各自散去,繼續奔波忙碌。沒有人想到要去照顧老人的情緒,母親與子女間的溫情被忽略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小說《半截兒》同樣講述了一個溫情的故事。蜘蛛和半截兒是一對夫妻,蜘蛛的身高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小時候得了一種怪病,導致四肢長而細。半截兒雖然是個正常男人,但是因為十六歲時扒火車,發生意外,失去了下肢。一開始,兩家鄰居對這對夫妻是冷漠的,他們的存在帶給了鄰居們一些不便。半截兒內心有愧,于是,便時常幫鄰居免費修鞋。漸漸地,鄰里之間的關系緩和了。中秋節時,鄰居會主動給夫妻倆送月餅。當蜘蛛懷孕待產時,雖然陌生人會投來不可思議的目光,但是,鄰居們紛紛獻上祝福。特別是當夫妻兩人充滿儀式般地步入病房時,發現鄰居們早已在焦急地等待著、擔心著。這兩篇小說對人們情緒的把握非常到位,緊貼人物的內心世界展開敘述,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每個人都有情緒,我們應該對身邊的人多一點關心,特別是身邊人的情緒波動,否則便容易釀成悲劇。貝加中篇小說《大爺》(《廣西文學》2017年第7期)中的馬博禮,四十五歲依然沒有成家立業,同事們看似關心他,實際上并非真正的了解他。特別是侯絮,一口一個“大爺”,叫得馬博禮心顫,他認為語言是一種能量的載體,而“大爺”這個詞則具有極強的破壞力。眾人都沒有在乎馬博禮的反感情緒,特別是侯絮,這就導致馬博禮對她心生怨恨,伴隨著情欲沖動,馬博禮陰差陽錯地殺死了她的雙胞胎妹妹。
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人們往往疲于奔命。遲子建的小說《最短的白日》(《長江文藝》2017年第14期),便講述了一位肛腸科醫生疲憊的一天。“我”的兒子因為吸毒進了戒毒所,為了幫兒子償還百萬元的“毒債”,“我”被迫進入自由度和收入更高的醫院。在冬至日這天,“我”從哈爾濱趕往大連做手術。在列車上,“我”遇到了一名年輕的技工,通過聊天,“我”了解到這個小伙子的年紀跟兒子差不多大,然而價值觀卻是迥異的。這名技工的家境并不富裕,卻樂觀向上,孝敬母親,喜歡善解人意、尊重他人的女孩子。而“我”的兒子從小便嬌生慣養,“我以為一棵不經修剪的樹,才能頂天立地。可我忘了,他生活的現實叢林,遠比真實的叢林要物質和險惡”。兒子從小懶于學業,考上了一所民辦大學,與女友租房住,這些女友都滿嘴臟話、奇裝異服,他卻把這種玩世不恭當作“活得明白”,終于在一位女友的誘惑下跌進了毒品的旋渦。這兩種價值觀的對比是鮮明的,生活不易,雖然我們都在奔向異鄉,充滿焦慮與無奈,但是陽光灑脫的心境無疑會減輕內心的負擔。
無獨有偶,在普玄《過生日別在外面喝茅臺》(《清明》2017年第4期)中,胖子陳在老牟的煤炭經銷部工作。老牟是老板,胖子陳是唯一的員工,他已經六個月沒拿到工資了。胖子陳的妻子面臨生產,為了養家糊口,他選擇在生日這天辭職。老牟卻讓他陪區長吃飯,因為今天也是區長的生日。胖子陳覺得很委屈,自己的生日無法慶祝,還得“裝孫子”,喝假茅臺酒。現代人的生活壓力與日俱增。北雁小說《梅河亂》(《滇池》2017年第7期)中,一家四口雖然生活在城市,卻沒有城市戶口,作為“房奴”,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再加上奇葩的鄰居們,生活更是雜亂無章。如今,房子是城市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談婚論嫁時的重要條件。比如在李東文的小說《夢見自己是條狗》(《廣州文藝》2017年第7期)中,“我”的父母與花花的父母因為彩禮和房子問題鬧得不歡而散。在嘈雜的都市生活中,保守內心的貞潔難能可貴,如官玉華《月光白》(《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里的女子,很多富豪喜歡茶葉,并非是為了品茶,而是囤積居奇,賺取利益。小說以自述的方式,娓娓道來,“我”拒絕了福哥的無理要求。
愛情永遠是文學永恒的主題,在作家的筆下,生長于都市生活中的愛情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姿態。在陳芳《櫻花爛漫》(《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中,塔塔作為現代女性,由于工作原因樂于應酬,丈夫向陽院心生芥蒂,最終導致二人婚姻破裂。在吳榮國《夜的誘惑》(《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中,阿星除了妻子之外,還和另外一位女人情意綿綿,終于在一個醉酒的夜晚,他看清了情人逢場作戲的本質,也懂得了妻子對他的一片深情。東巴夫《孤鳥》(《滇池》2017年第7期)這篇小說,則描述了現代都市人空虛寂寞的情感狀態,謝觀返鄉后與父母沒有共同語言,只想逃離故土,可是在城市中他也漂浮不定,難以扎根。寇洵《少了點什么》(《廣西文學》2017年第7期)同樣講述了都市年輕人的空虛之感,少了點什么呢?少了內心世界的安寧。都市男女在沒有情感對象的情況下,如何宣泄自己的感情呢?曹軍慶《我和小丹在一起》(《江南》2017年第4期)中,蘇長河斷然拒絕孫書蘭的追求,因為他愛上了充氣娃娃小丹。絕望之下,孫書蘭竟然按照蘇長河的模樣,也做了一個充氣娃娃。沒有愛情作為基礎的婚姻,往往是不牢靠的,就如游利華《錦夜行》(《廣州文藝》2017年第7期)中的大可與紅壁,兩人通過朋友介紹相識,彼此覺得合適,便結婚生子。紅壁覺察到大可對另一個女人存有幻想,她焦躁不安,但也知道人心是控制不住的。無獨有偶,李一楠《吳萸的告別晚宴》(《廣州文藝》2017年第7期)中,年輕時候的吳萸是位傲氣十足的美女,有著不食人間煙火的韻味,喜歡洋氣現代的事物。后來她主動結識上海女人藍青,藍青是位溫柔細膩的美人。在與藍青的接觸過程中,吳萸的丈夫鐘明出軌了。高傲的吳萸放棄這段婚姻,并操辦了二人的婚禮。婚姻歷程中,隨著歲月的流逝,夫妻間也漸漸失去激情,陷入中年危機,如巴克《善良的人是可恥的》(《上海文學》2017年第7期)中,姜洪國在事業風生水起時,包養女人。王新梅《生日快樂》(《清明》2017年第4期)中,艾柯在三十八歲生日這天,沒有收到丈夫的祝福,她便去往酒吧買醉,傷感時間飛逝之快。
阿袁在《他鄉》(《上海文學》2017年第8期)中,則描寫了另外一種都市情感。孟漁與姬元是一對“食友”,一開始,孟漁認為姬元是對他存有幻想,才故意接近。但是接觸久了,他發現姬元是個隨性的女子,在他面前從不裝扮,姬元善于傾聽,在她面前,孟漁不覺得拘謹,竟然可以放心地講述他的情人——朱茱的故事。小說結尾處,孟漁終于向姬元說出了自己的困惑,“為什么想和我一起吃飯”?“這一回她冷不丁又開口了,說他像某個人”。原來,兩個人都在向對方悼亡自己的愛情。阿袁在這篇小說中塑造了四類不同的女人,第一類女人是孟漁的妻子,長相粗糙,缺乏生活情趣,認為做女人是講究套路的,吃飯時矯揉造作,翹著蘭花指。表面做出柔弱婉轉的樣子,骨子里卻潑,作為校醫務所的女護士,講究養生,出軌后,竟然理直氣壯地說是為了追求陰陽協調,為了健康。第二類女人是姬元,性格隨性,不拘小節,有一種我行我素的潦草與簡慢。作為哲學系的教授,她喜歡讀書和思考。吃飯時是正常的吃法,只是食量“不秀氣”。第三類女人是朱茱,她是孟漁的情人,生性浪漫,溫柔多情,富有生活情趣,作為古典文學專業的教授,喜歡讀書,遠離煙火氣息。吃飯時非常秀氣,細嚼慢咽。第四類女人是蘇馮堇,鮮艷、心機重重,善于調戲男人,如果把丈夫以外的男人稱為魚的話,“蘇馮堇其實不吃魚。她愛的,是垂釣。釣上來,扔回去; 再釣上來,再扔回去,樂此不疲”,不僅自認為聰明,還自以為美。作者通過孟漁的視角,來觀察前三類女人的吃相,透過吃相展現她們的性格,趣味盎然。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在不幸中,有用的朋友更為必要;在幸運中,高尚的朋友更為必要。在不幸中,尋找朋友出于必需;在幸運中,尋找朋友出于高尚”。朋友,在人的一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孫鵬飛《如果我是塞林格》(《清明》2017年第4期)中,蔡凌格與老三之間的兄弟情,雖說不是出生入死,卻也是可以為了兄弟兩肋插刀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再見《抄家伙》(《長江文藝》2017年第13期),一場打架斗毆中,“我”遭到了兩個兄弟的陷害。在歐陽偉慶《遍地桃花》(《長江文藝》2017年第13期)中,肖天佑為了得到自己兄弟的女朋友,設計陷害關地龍,成為強奸犯。從監獄里出來后,關地龍開始設計報復,最終,肖天佑自殺身亡,用死亡來救贖自己的靈魂。面對物是人非的一切,關地龍也選擇了自殺。昔日的兄弟反目,結局讓人唏噓不已。
“惟孝順父母,可以解憂”,孝敬,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在張建春《素人(外一篇)》(《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的《老權》中,老權生得老相,心地善良,對岳父的孝敬,超過妻子三分,岳父在彌留之際,“留在人世間最后一句話:我的權兒……‘兒的音調顫抖,拉得長長的”。趙晏彪《張工和他的母親(外一篇)》(《安徽文學》2017年第7期)中,張工的父親去世后,張工的母親便只吃兒子做的菜,張工已經在水利廳的一個部門做了六年處長,“幾乎不出差,幾乎不參加任何應酬,一旦非出差不可,他會提前準備好菜,放在冰箱里,保姆每天熱一下飯菜即可。若是工作上有應酬必須前往,張工也要先回家給母親做好飯,才去赴約”。無獨有偶,曹多勇《看老子》(《滇池》2017年第7期)中的妻子,知道父親喜歡吃五花肉,每次去看望公公之前都會費一番心思和功夫,從挑肉到烹飪,事事親為。而黃絳《有福的六奶奶》(《廣西文學》2017年第7期)中,三兒媳對自己的婆婆則橫挑鼻子豎挑眼,眼里只有金錢。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家長忙于生計,往往會疏忽子女的健康成長。如袁有江《路上的故鄉》(《清明》2017年第4期)中,“我”和妻子在外打工,兒子成為留守兒童,讀高中后,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曠課逃學、打架鬧事,最終被學校開除,后因集體嫖娼被抓。兒子只對養育他長大的爺爺親近,從不開口叫“爸媽”。這種現象讓人寒心。包括陳柳金《綺川橋》(《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母親,段維維工作忙碌,將孩子交托給符雪芬照看。段維維因為應酬晚歸,一身酒氣,兒子蘇宇不喜歡讓她靠近,“媽媽每晚都喝酒,味道太惡心,我才不要跟她睡”。這些父母沒有照顧到孩子的情緒,親子關系岌岌可危。
在這一季的南方文學期刊中,眾多作品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官場的丑態。如龍建芬的《小小說二題》(《廣西文學》2017年第7期),第一篇《陳年老抽》中,恭城為了工作調動迎合領導喜好,“這個領導好一口煙,那個領導喜一口酒,另一位領導喜歡你陪他打打小牌”,如此這般,經過無數“游戲規則”的訓練,他才如愿以償。第二篇《上任》中,閆正三的工作能力差,常常玩忽職守,然而因為姐夫是組織部長,所以竟然莫名其妙地升為了副鎮長,連他自己都摸不著頭腦。很多官員更是在其位不謀其職,就像黃榮才《前方有座橋》(《清明》2017年第4期)中,副縣長和交通局長的對話,“我這個交通局長,你這個前交通局長,我們建了多少橋?不知道是否有人記住”,“想流芳千古了?關鍵是人家這進士爺,三百多年前建的石板橋,今天還能用。我們建的橋能用多久?千萬別流芳千古不成,反倒留下罵名”。這些官員眼里只有權勢利益,一些豆腐渣工程只會勞民傷財。當然,社會的運轉離不開那些兢兢業業的官員,如楊少衡《你可以相信》(《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遲可東。遲可東有句名言:“世間應有公正,你可以相信”,他知道世事紛繁復雜,卻依然相信世間應當有公正,無論作為理念,還是作為行事依據,都是需要的。所以,他敢于觸碰牽扯領導的企業,“為了讓河水干凈一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向本貴《族譜》(《清明》2017年第4期),在這篇小說中,劉書記為了升遷,竟然與鄉村企業家劉道喜沆瀣一氣,不顧農民的損失,一味破壞環境。更可悲的是,記者作為人民的喉舌,竟然也為了金錢利益亂寫文章。終于,河堤決裂,洪水襲來,將流傳百世的族譜卷入水中。正是因為官場黑暗,導致底層民眾的生活苦不堪言,送禮成風。如在李煥才《我是老鼠》(《天涯》2017年第4期)中,“我”作為運輸公司的業務經理,時常要打點廠長和鄭隊長,“鄭隊長拍拍我肩頭,意味深長地說,你很聰明,很會辦事,我也會做人呢”,收禮也是理直氣壯的。小說將底層民眾比喻成老鼠,將各類官員比喻成貓,“其實,誰都很難。無形中我們已經形成一條艱難的生物鏈,每個節點都是擠在夾縫中,但是又各有作用,不能斷開,只是越到后面的節點,越艱難”。無獨有偶,在曉蘇《撒謊記》(《長江文藝》2017年第13期)中,院長勸“我”撒謊,將兒子酒駕致傷的事實上報為意外傷害,這樣便可以得到合作醫療報銷。可是,為了開證明,“我”迫不得已請村長吃飯,為了感謝院長,“我”心甘情愿送禮。最后算下來,得益的并非老百姓,而是這些蠅營狗茍之徒。
無論環境如何變化,生而為人,我們不應該丟棄那顆赤子之心,在功成名就面前,做人依然是首要的。就像曹春雷《秘方》(《廣西文學》2017年第7期)中的那三個字,“心要正”。做菜適用,做人也適用。
本欄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