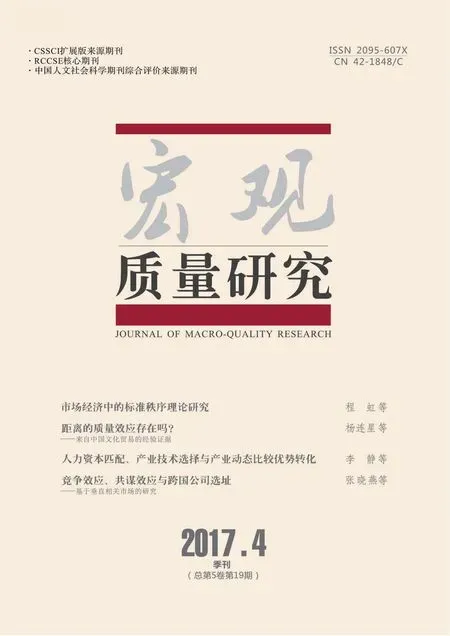人力資本匹配、產業技術選擇與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
李 靜,楠 玉
人力資本匹配、產業技術選擇與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
李 靜,楠 玉
一個國家最適宜的技術結構內生于其要素稟賦結構,國家產業技術選擇方向與要素稟賦本地化匹配程度可以解釋不同國家存在的比較優勢差異。因此,本文分析了人力資本匹配、產業技術選擇與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得出的結論:(1)一國在完成資本的初始積累后,如果鼓勵采取偏向原本稀缺要素的技術進步,可以跨越“比較優勢陷阱”,實現出口貿易的動態升級;(2)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與產業生產率的內生增長有關,而產業的技術選擇同國家人力資本結構匹配是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條件;(3)人力資本結構、技術選擇和產業升級之間是一個不斷匹配的動態過程,而技術的“本地化”是形成產業比較優勢動態演進的動力之源,因此,優化人力資本結構的同時,應加強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建設以及創新發展戰略的實施。
人力資本匹配;技術選擇;動態比較優勢;出口貿易升級
一、引言
一個國家最適宜的技術結構內生決定于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而產業技術選擇的“本地化”也將使得其與應用環境的要素條件間存在適宜與否的關系(Atkinson和Stiglitz,1969)。這意味著,如果發展中國家選擇與其人力資本結構相適宜的技術,其技術變遷的成本就會變得相對低一些。比如,中國與印度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印兩國的要素稟賦相似,但是兩國產業技術選擇方向不同,中國重在技術引進,印度重在自主創新,因而兩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存在顯著的差異,中國的比較優勢體現在制造業上,而印度的比較優勢在服務業(邵文波等,2015)。顯然,不同國家的貿易模式不能完全由要素稟賦來解釋,產業技術選擇與要素稟賦間“本地化”匹配與否可以作為解釋不同國家產業比較優勢差異的個中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服務貿易出口主要集中在運輸、旅游等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服務產品上,在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服務項目上發展較慢。張幼文(2013)認為,一國的貿易競爭力和貿易結構從源頭上看源自一國的要素結構。但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演進不僅源自要素稟賦豐裕情況,而且源自要素稟賦間(技術與人力資本)的匹配情況。總體而言,中國高端要素在要素結構中占比較低,服務貿易出口仍以勞動、資源密集型的傳統服務為主。因此,當前要素結構視角下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依然適用于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轉型問題研究(許和連和成麗紅,2015)。但是,在眾多要素稟賦中,人力資本在消化、吸收先進技術過程中起到主體性作用,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以及李靜等(2017)特別強調,人力資本的錯配阻礙了人力資本的有效使用,而優化人力資本的配置,提高人力資本定價的市場化程度,才能優化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遷的動力機制。邵文波等(2015)從勞動力技能匹配的角度進一步考察了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結構與比較優勢的關系,人力資本結構差異并不能單獨決定比較優勢,還需要考慮替代彈性不同的部門對于勞動力技能匹配的要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分布偏向于某部門特定技能范圍的國家在該部門具有比較優勢。李靜和楠玉(2017)研究也發現,人力資本錯配使得大規模的研發投入并沒有實現技術進步,導致產業動態比較優勢演進遲滯以及經濟穩定增長動力不足并存。在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引致人力資本適宜匹配,最大限度釋放人力資本規模增加所產生的人口質量紅利,從而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外學者,Duarte等.(2010)和Cuadrado等.(2011)則指出,源于非位似偏好產生的收入效應和部門技術差異帶來的替代效應所引發的勞動力錯配,使得農業部門勞動力逐漸減少,服務業部門勞動力不斷增加,而工業部門勞動力則會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駝峰”形狀。Asuyama(2012)進一步檢驗了中印兩國的人力資本分布差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他認為人力資本更為集中的中國在生產鏈更長的行業(比如制造業) 有比較優勢,反之,人力資本更為分散的印度則在生產鏈更短的行業(比如服務業) 具有比較優勢。Morrow(2010)把技能混合(Skill Mix) 同產出、收入分配、生產能力和出口聯系起來,將各部門生產技術的替代程度與要素密集度對應,把人力資本分布放到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下,重點考察了在價格給定條件下不同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決定以及對產出的影響,其實證研究發現,技能混合比自然稟賦或人力資本稟賦對于產業內貿易有著更強的解釋力。
在本文的研究中,將繼續沿著適宜技術理論探討人力資本匹配、產業技術選擇和產業動態比較優勢問題。具體而言,第一,本文集中考察一國產業技術選擇如何引致產業的動態比較優勢轉化,分析在完成資本的初始積累后,產業的技術選擇方向。第二,本文刻畫出人力資本結構和技術選擇動態匹配過程,以及二者的適宜匹配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機制。第三,結合適宜技術理論,檢驗一國技術的“本地化”是否可以引致產業的動態比較優勢和出口貿易的動態升級這一微觀命題。本文余下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為特征化事實與本文研究的理論邏輯;第三部門為理論分析;第四部分為實證檢驗與進一步分析;最后為主要結論與政策含義。
二、產業基本特征與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產業基本特征
表1刻畫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人力資本結構、產業比較優勢以及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等的各項特征。根據表1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相對出口競爭優勢指數、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勞動比和產業規模都顯現顯著的遞減趨勢,下降幅度分別為6.5%、6.1%、49%和1.2%。對應的,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力資本構成,即高技能人力資本與低技能人力資本的占比也呈現逐漸弱化的趨勢,下降幅度高達44%。由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基本特征的各項指標計算結果顯示,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不明顯,并呈現遞減的態勢,下降幅度為2.9%。但是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其他特征指標的變化趨勢都表現出明顯的一致遞增態勢。比如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遞增幅度為14%左右,資本勞動比和產業規模各自提升幅度約14%和1.5%。考慮到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情況,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垂直專業化指數上升幅度高達76%。與之伴隨的,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人力資本結構不斷優化,高技能人力資本與低技能人力資本的占比提升幅度約為11%左右。相比資本密集型產業,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其相對出口競爭優勢指數提升幅度高達34%,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幅度為6.6%左右,且其資本勞動比、產業規模和垂直專業化水平分別提升9%、35.7%和652.8%。而且,這段時間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人力資本結構發生明顯的優化,高技能人力資本與低技能人力資本的占比提升高達33%。

表1 產業的基本特征(1998-2012)
注:根據作者計算所得。
以上特征分析表明,隨著人口紅利將從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的轉變,中國人力資本結構也不斷優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升,為產業升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進而為出口產品的升級提供可能性。在高質量的人力資本推動下,帶動我國產業的動態規模經濟效應,自主創新效應和技術進步效應,實現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結構的動態演進,為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從數量型向質量型,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戰略性轉變,逐步實現我國外向型經濟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二)理論基礎
理論上,早期Acemoglu(2002)研究就表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對利潤刺激的反應,而這個刺激物主要是要素的稀缺和豐裕,當稀缺要素與豐裕要素的替代彈性較高時,技術進步就會更偏向于使用豐裕要素。但是,這種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不適合普通勞動力要素豐裕的國家。借用Acemoglu(2002)的理論,如果采用偏向豐裕的低技能勞動力的技術,就會增加大量低技能的勞動力需求,其結果就是擠出高技能的勞動力,并減少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其長期就是出現低技能替代高技能的技術進步方式。一個典型的事例發生在19世紀早期,由于當時有大量農村和愛爾蘭的農民涌入英格蘭城市,增加了英格蘭城市低技能勞動力的供給,結果是英格蘭出現低技能替代高技能的技術進步現象。但是,在完成資本的初始積累后,鼓勵產業采取偏向原本稀缺要素的技術進步則有利于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升級。但是,如果鼓勵產業采取偏向原本稀缺要素的技術進步,就會出現兩種驅動力:一是企業對初始人力資本的選擇以及對原有人力資本的投資;二,如果采取偏向原本稀缺要素的技術進步時,高技能勞動力就會需求緊俏,從而轉化為能夠直接誘發高技能高報酬的信號和預期,因此,隨之而來的就是人力資本自發的積累和升級。其直接結果:引致產業發展的技術選擇方向與其本地化的人力資本結構適宜匹配,進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與產業比較優勢過程的動態演進,具體如圖1所示。

圖1 人力資本水平、技術選擇和產業動態比較優勢
另一方面,在開放背景下,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般演化路徑為: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在追趕經濟驅使下,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迫切需要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演進,因此對于一個特定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技術選擇方向應該強調自主研發,即存在對潛在技術水平的追趕。這個潛在的技術水平一方面引致產業人力資本的升級(配置更高的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另一方面加快研發有效率的投入,進而促使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的有效互補。

圖2 潛在的技術引致和人力資本升級
根據圖2顯示,對潛在技術的獲取不像對現存的先進技術模仿和有方向性技術路徑的自主創新那樣,它引致人力資本升級和技術的跳躍式進步。其演化路徑是:開放背景下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內在驅動→潛在技術的獲取→人力資本升級和技術的跳躍式進步→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這意味著,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般演化路徑體現了在既有的參照系指引下,人力資本逐漸積累和技術不斷進步的過程,在這個參照系指引,體現在諸如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模仿,按照發達國家的增長軌跡所實現的一種循序漸進的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過程。而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追趕路徑則體現了在沒有任何參照系的情況下,對潛在技術水平的獲取如何引致人力資本升級和技術的躍遷,這是一個跳躍式的過程。
三、基本理論分析
(一)生產部門
假定一個經濟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的C-D形式:Y=AKαLβ且α+β=1 。其中,Y、K和L分別為經濟總產出,資本和勞動要素的投入,A為技術進步水平,α和β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由C-D生產函數得出生產函數的人均形式:


進一步,由(1)和(2)式可以得出整個經濟的資本勞動比率和各個產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見(3)式:

(二)技術選擇
林毅夫(2002)把一個產業的資本勞動比與地區的資本勞動比的比值作為技術選擇的替代指標,體現了該產業的經濟發展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偏離程度。為了反映不同產業的人力資本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并體現在產業升級過程中人力資本與技術選擇匹配關系,本文把一個產業的資本與該產業的人力資本的比率與地區的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比率的比值作為一個產業技術選擇能力的體現。首先,假定一個產業的人力資本是該產業的勞動人數的一個比率,即,Hi=λILi。同理,整個經濟的人力資本也是該經濟勞動人數的比例函數:H=λL。結合(3)式,則各個產業的技術選擇系數表述為如下:
對于一個產業長期發展來說,選擇合適的技術需要和該產業的人力資本水平相匹配。但是,通常意義來說,恰當衡量一個產業的人力資本水平不能用該產業的人力資本絕對量來衡量,而是用該產業的人力資本相對水平的高低來衡量*就絕對數量而言,像某些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能勞動者的數量并不少,甚至會超過很多比較小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但是考慮到某些大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龐大的勞動力基數,其人力資本水平是相當低的。。即一產業的技能勞動(人力資本)相對于該國非技能勞動的大小作為該產業人力資本水平體現。因此,本文定義一個產業的相對人力資本水平為hi=Hi/li。相應地,整個經濟的相對人力資本水平為h=H/l。這里li和l分別為各個產業及整個經濟的非技能勞動力,因此,hi和h為各個產業及整個經濟的相對人力資本水平。由于非技能勞動力和人力資本共同構成該產業或整個經濟的勞動力總數
li+Hi=Li;l+H=L(5)
(3)如果該食用堿在測定前已經受潮,則用甲同學的實驗方案測得的NaHCO3的質量分數會____(填“偏大”“偏小”或“無影響”)。
結合(5)式,得出如下表達式:

(6)式表達一個產業的相對人力資本水平在整個經濟中人力資本水平份額,體現了該產業人力資本在整個經濟中的結構。把(6)式帶入(4)式,得出如下反映產業人力資本與產業技術選擇的關系式:

由(7)式可以看出,一個產業的技術選擇同這個產業的人力資本水平相關,同時和該產業以及整個經濟的人均產出、技術進步水平相關。
(三)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
產業結構轉化和升級是一個動態過程,其本質是對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由于產業異質性特征,人力資本對不同產業的影響會存在差異,因此,這就需要人力資本結構和產業結構匹配的要求。當然,為了保證產業結構的轉化和升級,必須有技術上的支持,這樣的支持并不是什么樣的技術都可以擔當起來的,由于在數量、結構和類型上不同的人力資本一方面影響各種要素生產力發揮的差異,從而對技術選擇產生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選擇和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相匹配的技術將能更大限度的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化和升級。因此,應針對不同產業類型來選擇合適該產業人力資本水平相匹配的技術才能更大限度的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化和升級。接下來考察異質性人力資本、技術選擇和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之間的內在邏輯。由(7)式可以得出如下(8)和(9)式。

由(8)和(9)式可以看出,作為產業目標的人均產出以及體現產業結構的某個產業的人均產值和總產值的比重受到技術選擇和該產業的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為更清晰地展現他們之間的變動關系,對(9)式進行刻畫,見(10)式:

通過(10)式可以發現,技術選擇系數對產業結構有正影響,這說明對特定產業選擇超前技術和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都有助于增加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同時,如果特定產業采用較先進的技術,它不具備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和基礎,同時先進技術的引入,增加了其要素投入的負擔比率,這樣反而不利于其產業結構轉化和升級。也就是說,如果人力資本在數量、結構和類型上不能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技術要求,那么產業結構升級就會弱化,甚至阻礙了產業結構轉化和升級的速度。因此,選擇和產業人力資本結構相匹配的技術水平對于產業結構轉化的速度和效果至關重要。進一步,通過對(9)式的等價變形,得出(11)式。
本文得出結論為:技術選擇與人力資本的彼此匹配意味著技術與人力資本之間的有效契合,即實現技術與人力資本組合的邊際生產率最大化(姜雨和沈志漁,2012)。盡管技術選擇與人力資本的彼此匹配是產業結構的轉化和升級基礎條件,但是,技術選擇的外生性改變需要相應的人力資本與之匹配,這使得匹配關系下技術與人力資本都有增長變化,并且其匹配關系不再是一個相對靜態的過程,而是從某一點的相對靜態契合轉化為動態發展的持續匹配過程。基于此,產業技術選擇的實現,要求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升級,以實現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和出口貿易的動態升級。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樣本選取和計量模型
本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高技術產業統計分類目錄,選擇了化學藥品制造業、中藥材及中成藥加工、生物制品制造、飛機制造及修理、航天器制造、通信傳輸設備、通信交換設備、通信終端設備、雷達及配套設備制造、廣播電視設備制造、電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導體分立器件制造、集成電路制造、家用視聽設備制造、電子計算機整機制造、醫療設備及器械制造、電子計算機外部設備制造、其他電子設備制造、辦公設備制造、電子元件制造、儀器儀表制造等五大類23個行業的1998-2012年的數據作為實證分析的樣本。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Ri,t=controls+β1H_chari,t+β2H_MAi,t+ψ1H_chari,t×R&Di,t+ψ1H_chari,t×Letii,t+ci+ωt+εi,t(12)
以上各個變量設定如下:
(1)R為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標。數值越大表明產業競爭力越大,本文作為產業比較優勢動態演進的替代變量。用來度量產業國際競爭力水平的指標一般有出口交貨值、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國際市場占有率及國際競爭力指數等。鑒于可得數據的限制,本文選擇各產業歷年出口交貨值作為度量產業國際競爭力R的指標。
(2)H_char表示產業人力資本結構特征的指標,本文選取三類指標來刻畫產業人力資本的結構特征:1)高層次的人力資本(H1),用大型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與企業科技活動人數之比來表示;2)中等層次人力資本(H2),用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人數與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之比來表示;低層次人力資本(普通勞動力)(H3),用(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企業科技活動人員人數)/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來表示。
(3)H_MA表示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用以刻畫人力資本對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長期效應和即期效應。鑒于數據的局限,本文設定滯后4期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H_MA(4)作為刻畫人力資本對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長期效應,設定滯后0期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H_MA(0)作為刻畫人力資本對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即期效應。
(4)本文產業技術選擇主要體現自主研發和技術引進兩類方式,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資本結構特征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H_char×R&D)以及人力資本結構特征與技術引進的交互項(H_char×Leti),用以捕捉產業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技術選擇交互作用對產業比較優勢動態轉化的影響。
除此之外,還需要考慮一些外在因素對產業動態比較優勢的影響,比如對外依存度(D_open)、匯率(E_R)的變動以及產業的規模經濟(D_str)等。因此本文把對外依存度、匯率以及規模經濟作為控制變量(controls)引入到模型中。本文的數據的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及外匯管理局網站。以上各個變量的統計描述見表2。

表2 樣本的統計描述
(二)實證分析結果
首先,僅報告高層次人力資本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長期效應和即期效應的估計結果。由表3的第(1)列檢驗結果顯示,當控制產業規模經濟、對外依存度和匯率等變量之后,發現HMA(0)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負值,但是HMA(4)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值。這說明高層次人力資本雖然在當期不能立即引致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但是從長期來看,高層次人力資本能顯著引致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大幅度提升,實現產業比較優勢動態轉化。進一步,考察高層次人力資本與產業技術選擇的匹配對產業比較優勢的影響,因此在第(2)列和第(3)列引入了滯后4期的高層次人力資本移動平均過程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和技術引進的交互項。檢驗結果顯示,滯后4期的高層次人力資本移動平均過程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HMA(4)×R&D)系數以及滯后4期的高層次人力資本移動平均過程與技術引進的交互項(HMA(4)×LETI)系數都顯著為正值。這充分顯示了在長期高層次人力資本和自主研發以及技術引進之間存在互補作用。進一步考察中等層次人力資本與產業比較優勢動態變化之間的聯系,計量檢驗結果見第(4)-(6)列。檢驗結果顯示,中等層次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HMA(4)×R&D)系數以及與技術引進的交互項(HMA(4)×LETI)系數都顯著為正值,也顯示了在長期中等層次人力資本和自主研發以及技術引進之間也存在互補作用。為比較分析,在第(7)-(9)列考察了低層次人力資本與產業比較優勢動態變化之間的聯系。檢驗結果顯示,低層次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與自主研發的交互項(HMA(4)×R&D)系數以及低層次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與技術引進的交互項(H_MA(4)×LETI)系數都顯著為負值。因此,根據如上實證結果正好說明了長期依靠低層次人力資本獲得的競爭優勢不利于技術進步和新產品的研發,產業技術選擇以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化需要適宜人力資本結構之相匹配。

表3 計量估計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差,上標“***”、“**”和“*”分別表示1%、5%和10%顯著性水平。
基于實證結論穩健性檢驗的目的,本文進一步選擇把人力資本的移動平均過程的滯后期分別設定為滯后0期、滯后3期和滯后6期,分別把滯后0期、滯后3期和滯后6期移動平均過程的人力資本引入上述模型中以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
由表4的回歸結果顯示,選擇滯后0期,人力資本與自主研發以及技術引進的交互項系數分別為0.087和-0.004,并且不顯著;當選擇滯后3期時,人力資本與自主研發以及技術引進的交互項系數分別為增加到0.094和0.076;當選擇滯后6期時,人力資本與自主研發以及技術引進的交互項系數分別為增加到0.271和0.107。由此可見,隨著一國本地化人力資本結構的不斷優化,自主創新比技術引進的效果愈加明顯,這表明,產業技術選擇與人力資本匹配具有顯著的動態特征,因此,從國家產業政策來看,不僅需要關注人力資本縱向增長環境,還得選擇適宜的技術進步方向。這意味著,隨著一國本地化人力資本結構不斷優化,如果長期堅持的“市場換技術”的技術進步路徑,而不是堅持自主創新體系的建設,從長期來看并不必然引致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演進和外向型經濟方式的根本轉變。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差,上標“***”、“**”、“*”分別表示1%、5%和10%顯著性水平。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含義
過去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競爭模式,盡管使得我國一些產業具有短期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過多依靠低勞動力成本獲得產業競爭力,容易使得我國產業一直圍繞在低附加值環節上,從而產生“比較優勢陷阱”。本文基于適宜技術理論,分析了人力資本匹配、偏向性技術選擇與產業動態比較優勢轉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得出的結論是:一個產業的技術選擇方向需要同這個產業的人力資本結構相匹配,二者適宜匹配是促進產業結構轉化和升級的基礎條件。然而,這種匹配關系不是一個相對靜態的過程,一國在完成資本的初始積累后,隨著人力資本結構的不斷優化,長期堅持“市場換技術”的技術進步路徑并不必然實現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演進,但是加強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建設以及創新發展戰略的實施,可以有效克服“比較優勢陷阱”,實現出口貿易的動態升級。因而,技術的“本地化”是形成產業比較優勢動態演進的其中動力之源。
考慮到人口數量紅利已經結束,新型的人口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國建立自己的動態比較優勢,進而在長期中不斷地向高級產業擴張,就內在地要求人力資本的可得性以及人力資本結構的優化匹配。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議為:除了以多種方式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之外,還需要促進人力資本要素與先進技術的動態匹配。以趕超技術為路徑指向,通過創造自主創新的環境和條件,采取政策鼓勵和構建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充分利用技術選擇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持續積累自主創新能力,形成以技術引致和人力資本升級互動的傳導機制。除此之外,需要規制技術型生產部門,重塑技術型企業收益結構,使其向研發型轉變。因此,在激勵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同時,提高人力資本回報率,吸引高層次人才匯聚至研發部門,改善當前研發資源配置尤其是人力資本大量聚集并沉淀在非生產性和非創新性部門的現狀。
[1] 姜雨、沈志漁,2012:《技術選擇與人力資本的動態適配及其政策含義》,《經濟管理》第7期。[Jiang Yu and Shen Zhiyu,2012,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Dynamic Fit between Technological Selection and Human Capital,BusinessManagementJournal, 7.]
[2] 李靜、楠玉、劉霞輝,2017:《中國經濟穩增長難題:人力資本錯配及其解決途徑》,《經濟研究》第3期。[Li Jing, Nan Yu and Liu Xiahui,2017,China’s Economic Growth Stabilizing Conundrum, Misalloc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Solutions,EconomicResearchJournal, 3.]
[3] 李靜、楠玉,2017:《為何中國“人力資本紅利”釋放受阻?—人力資本錯配的視角》,《經濟體制改革》第2期。[Li Jing and Nan Yu,2017,Why is Human Capital Dividend Release Blocked?--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Mismatch,ReformofEconomicSystem, 2. ]
[4] 林毅夫,2002:《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經濟研究》第12期。[Lin Yifu,2002,Viability,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flections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EconomicResearchJournal, 12.]
[5] 邵文波、李坤望、王永進,2015:《人力資本結構、技能匹配與比較優勢》,《經濟評論》,第1期。[Shao Wenbo, Li Kunwang and Wang Yongjin,2015,Human Capital Structure, Skill Match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EconomicReview, 1.]
[6] 許和連、成麗紅,2015:《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適用于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轉型嗎—基于要素結構視角下的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分析》,《國際貿易問題》第1期。[Xu Helian and Cheng Lihong,2015,Application of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to Structural Transfromation of China’s Service Export: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Perspective of Factor Structure,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 1.]
[7] 張幼文,2013:《要素流動-全球化經濟學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Zhang Youwen,2013,The Flow of Factors-Principles of Global Economics,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ress.]
[8] 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2014:《中國經濟增長的低效率沖擊與減速治理》,《經濟研究》第12期。[Research Group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2014,The Shock of Low Inefficiency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Governance of Economic Slowdown,EconomicResearchJournal, 12.]
[9] Atkinson,B.A.and Stiglitz,E.J., 1969, A New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nge,TheEconomicJournal, 79(315):573-578.
[10] Acemoglu,D.,2002,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TheReviewofEconomic69:781-809.
[11] Acemoglu,D.,2003, Labor-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1-40
[12] Alverez Cuadrado,F.M.Poschke.,2011,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AmericanEconomicJournal.Macroeconomic, 3(3):127-158.
[13] Asuyama,Y., 2012, Skill Distribu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India,”WorldDevelopment, 40(5):956-969.
[14] Duerte,M.,D.Restucca., 2010, The Role of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ggregate Productiv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125(1):129-173.
[15] Morrow,J., 2010, Is Skill Dispersion a Source of Productivity and Expor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F.R.E.I.T.WorkingPaper, 134.
HumanCapitalMatching,IndustrialTechnologySelectionandIndustrial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s
LiJing1andNanYu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0;2.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most appropriate to a certain country depends on its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explained by considering the degrees of matching between their nation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and their factor endowment. In view of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matchi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selection and industrial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with a number of meaningful conclusions drawn as below.
1) After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initial capital, encouragement by the country on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favor the country’s scarce elements can help to overcom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p”, and therefore realize the dynamic upgrading of its export trade.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s related to endogenous growth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but the right technology selection of industr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3) The matching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echnology sele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 dynamic and gradual process. While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s being optimized,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Human Capital Matching; Technology Selection;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port Trade Upgrading
10.13948/j.cnki.hgzlyj.2017.12.003
* 李靜,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電子郵箱:skyli8406@163.com;楠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員,電子郵箱:nanyunanyu@yeah.net。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7YJC790070)和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AHSKQ2016D48)資助,感謝匿名評審人對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見,文責自負。
■責任編輯鄧 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