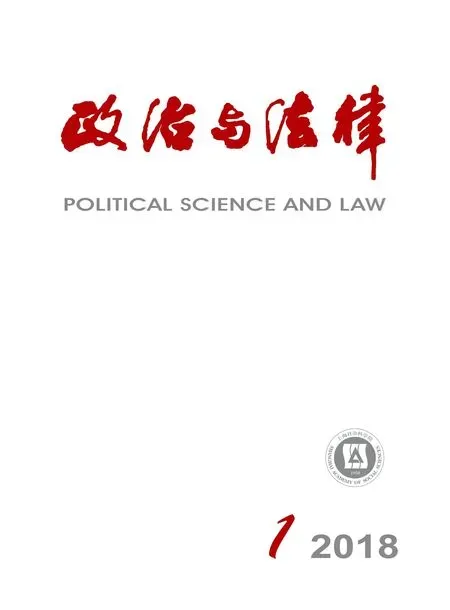侵權法上生存機會喪失理論的本土化構建
——以醫療損害案件為視角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浙江杭州 310008)
侵權法上生存機會喪失理論的本土化構建
——以醫療損害案件為視角
季若望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浙江杭州 310008)
侵權法中的生存機會喪失案件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尚屬少見,經剖析案例,可以發現該類案件中存在請求權基礎不明、賠償范圍不統一、客觀數據量化不足等問題。應當將生存機會喪失的保護納入生命權和健康權的體系加以保護,機會喪失的救濟不適用傳統人格權侵害的“全有或全無”模式而應適用“比例式賠償”模式。在賠償范圍層面,應當區分物質性損害賠償與非物質性損害賠償,且原則上將前者列入比例賠償范圍內。在賠償數額層面,應當力求客觀數據的多樣化與精確化,同時在計算方法上區分已發生損害和未來風險,分別采納“比例式計算法”和“多段結果計算法”。
生存機會喪失;請求權基礎;損害賠償;醫療過失;比例式賠償
機會喪失理論(Loss of Chance)是侵權法體系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重要理論,其對侵權法原有的因果關系理論僵化死板的缺陷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修補,對具體適用中的個案正義的衡平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因此為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中的諸多國家所采納。*Eva Steiner, French Law: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54.對于機會喪失理論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其一,機會喪失的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是什么;其二,賠償的范圍又應當如何劃定。當然,關注這些問題最終都是為了解決理論的應用問題。
機會喪失理論在我國曾引起若干關注,但在司法實務中卻暴露出請求權基礎不明、賠償范圍不統一、客觀量化數據匱乏等問題。與之前的研究不同,筆者擬從我國司法實務中的生存機會喪失案例出發,揭示司法實務中機會喪失理論的適用之困境及原因,并以我國現行法為基礎為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尋找到合適的理論基礎,提出具體的損害賠償計算之方法,以期為司法實務提供幫助。
一、司法案例之剖析
生存機會喪失在我國司法實務中并不多見,且其名稱也不統一。筆者分別以“生存機會”和“存活機會”為關鍵詞在北大法寶搜索相關裁判案例,將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外的民事案件統計整理為圖1和表1。

圖1 生存機會喪失案例整理

從圖1和表1可以看到,此類案件在2006年以前幾乎難覓蹤影,從2006年的南京腦科醫院等與宋小妹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開始陸續增加,*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2006)鼓民三初字第413號民事判決書;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07)寧民一終字第741號民事判決書。自2014年起呈現爆發式增長,2016年開始有所回落,2017年僅統計至7月15日,尚難判斷全年的情形。筆者在本文中主要針對醫療過失領域的生存機會喪失案件進行分析,因此還需要從這部分案件中剔除相關性不大的民事案例,剩余案件共計77件。從案例來看,我國司法實務中對機會喪失理論的運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一)生存機會之賠償請求權基礎不明
綜觀相關案件司法文書的行文表述,多數法官對于“生存機會”的描述僅有寥寥幾句,如“醫療過失與不良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這不良后果是指可能喪失的生存機會”*彭泳鈞等與溆浦縣康復醫院等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湖南省溆浦縣人民法院(2009)溆民一初字第997號民事判決書。,“嚴重違反疾病診治原則,將具有住院、PICU住院指征的患兒放置留觀,使白某喪失繼續生存機會”,*廖XX與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11)虹民一(民)初字第5121號民事判決書。“……在第二次住院期間的處理明顯違反診療常規,使患者喪失最后生存機會”,*牛某等與上海長海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2011)楊民一(民)初字第6823號民事判決書。“……使患者喪失生存機會,存在過錯且與患者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難以排除”,等等,*李良銀、王雪玉與樅陽縣人民醫院、安慶市立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安慶市迎江區人民法院(2015)迎民一初字第00307號民事判決書。它們不僅在用詞上各不相同,在論證和定性上也不具備參考意義,反而更像是用以證明醫方過錯行為的一種論述。僅在少數案件中法官作出了較為正面的肯定式回應并引用鑒定意見中的相關比例數據加以佐證。例如,“該過錯使患者喪失生存機會,被告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根據本案案情,本院酌定被告承擔70%的賠償責任”。*袁良珍與安徽省肥東縣中醫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肥東縣人民法院(2014)肥東民一初字第01653號民事判決書。又如,“該醫療過失行為使患者喪失了可能的生存機會,醫療過失的參與度擬為20-25%”。*林某某、邱某某、邱爐生、邱華生、林發金與上杭縣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福建省上杭縣人民法院(2013)杭民初字第65號民事判決書。再如,“醫療過錯行為在被鑒定人康英的病情緩解、生存機會喪失中的過錯參與度理論系數為25%(參與度系數值20%-40%)”。*李建國等與華北煤炭醫院學院附屬路南分院等醫療服務合同糾紛案,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區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973號民事判決書。另如,“……喪失了可能的生存機會,過錯參與度可考慮為25%”。*阿克蘇地區第一人民醫院與張弓長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4)新民申字第1397號民事裁定書。
如果拋開具體的生存機會數據來談機會喪失,恐怕不止在論證方面缺乏力度,也會給法官的判決帶來極大的障礙,或者從另一角度看,給了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從賠償項目來看,盡管法院在多數判決中采取了比例判決的思想并以“司法/醫療鑒定”確定的“參與度(過錯程度)”為計算依據,但其中是否包含了對生存機會的喪失以及何種賠償項目是對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卻語焉不詳,且“參與度”的概念也并未有統一認識。*僅有少數學者正面討論“參與度”的問題,如楊立新。參見楊立新:《論醫療過失賠償責任的原因力規則》,《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從援引的法律條文來看,法官一般引用的都是概括性較強的抽象性條文或已有賠償項目明確指向性的列舉式條文,而對請求權之性質本身并沒有太多涉及(除部分案件中援引了生命權的概念及相關條文外),如此一來,判決中的損害賠償之基礎就比較模糊,法官也似乎更加傾向于根據法律條文得出賠償結果,而并不關注法律條文所保護的權利究竟為何。這樣,機會喪失賠償的問題似乎就在這種“和稀泥”的判決中顯得更加難以判斷。
事實上,這也是在醫療侵權類型案件不斷發展的趨勢下勢必會出現的新型的權益保護與尚未作出反應的法律條文之間的矛盾。法官在判決中面臨著雙重困境:首先,在現行法的體系下,很難輕易找到“生存機會”直接賴以被涵攝的規范基礎(盡管有相應的損害賠償指導規范,如《醫療處理事故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三款),通過解釋的方法將其納入體系內仍存在較多困難(相關文獻理論研究的欠缺和既有權利的涵蓋界限模糊);其次,審判中法官所面對的是“醫療損害責任訴因”和“醫療損害責任鑒定”等方面的“雙軌制”帶來的實踐混亂,*我國醫療侵權責任領域原來面對的是“醫療損害責任訴因”“醫療損害賠償標準”和“醫療損害責任鑒定”三方面的“雙軌制”所交織而成的混亂處境,在我國《侵權責任法》及其司法解釋出臺以后,事實上“賠償標準”的混亂問題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盡管仍有案件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來處理(如禹城市人民醫院與彭桂芳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上訴案,山東省德州地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德中民終字第565號民事判決書),但大多數案件中已經不再存在“雙軌制”帶來的混亂。然而,在上述另兩個領域,“雙軌制”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參見楊立新:《中國醫療損害責任制度改革》,《法學研究》2009年第4期。醫療事故的分級制度與鑒定體系的混亂已經基本消除了法官進一步考量在判決中為新型權益的保護進行解釋乃至論證的空間,更多出現的是法官類似于工廠“流水線生產”一般的機械化適用法律條文。
相對而言,域外法上的判例就給出了較為明確的答案,比如直接在判決中指明生存機會是區別于過失醫療行為給患者造成的痛苦所對應的損害賠償之外的一種獨立的可賠償項目,在最后的賠償金額上也應做相應區分,僅對機會喪失的賠償采取比例式計算方式。*See 838 at Judgment of 890 N.E. 2d 819 (Mass, 2008).因此,需要進一步就判決思路進行分析,以求在兩個問題上得到明確的答案:其一,生存機會到底是否為法官意欲賠償之范圍內項目;其二,如答案肯定,則請求權基礎何在。數額的確定固然重要,但性質界定是必然前提,因為性質的界定決定了構成要件的苛刻程度和計算方式的合理性。
(二)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難以確定
在涉及生存機會喪失的案例中,精神損害撫慰金是一種重要的賠償形式,但在計算基礎上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否應當歸入比例賠償的范圍,有關案例中卻呈現出兩種意見:*對于其他費用,法官普遍認為應當列入比例賠償范圍,故此處筆者不討論。在大部分案例中,法官認為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屬于按比例賠償的損害賠償基礎,“關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對死者家屬(近親屬)的精神撫慰,不屬于醫療責任范圍內應劃分比例的賠償項目,應由侵害人全額向受害人的近親屬賠付”;*富裕縣中醫院與孟某某2等醫療損害賠償責任糾紛上訴案,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黑02民終1035號民事判決書;梁某某等與柳州市某某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魚峰區人民法院(2012)魚民初(一)字第355號民事判決書。在小部分案例中,法官則將精神損害撫慰金作為比例賠償的項目之一。這里可能涉及兩個問題。其一,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對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嗎?如果是,其賠償的是生存機會本身還是損害賠償的替代給付?請求權基礎何在?其二,如果是對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那么其計算依據應該是什么、是否應當有比例式計算的空間?
在個案中,法官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否列入以醫療過錯參與度來衡量的比例賠償計算范圍內存在如下不同見解(詳見表2、圖2、圖3)。

表2 精神損害撫慰金是否列入以醫療過錯參與度來衡量的比例賠償計算范圍

圖2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與否圖3是否按照參與度(過錯度)進行比例式賠償
另外,精神損害撫慰金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其一,沒有明確的方法可用于將無形的非金錢損害合理地轉化為金錢賠償;其二,精神損害的嚴重性(severity)在不同個體間差異較大,無法提出客觀衡量標準。*從醫學診斷層面來說,其標準體現為“受害人是否能在遭遇損害之初”(in the first instance)忍受下來;不僅如此,這種痛苦的經歷常趨于主觀,因為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對于刺激的意識感知能力”(conscious perception of a stimulus)。See Mark Geistfeld, Placing a Price on Pain and suffering: A Method for Helping Juries Determine Tort Damages for Nonmonetary Injurie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3, No. 3 (May, 1995), pp.781.有學者提出,應當從損害事實基礎、責任基礎、金錢評價三個重要因素出發,并結合損害類型、嚴重性程度、持續時間、因果關系貢獻度、當地生活水準等因素進行綜合權衡,在保障個案衡平的同時,兼顧法律安定性。*葉金強:《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解釋論框架》,《法學家》2011年第5期。然而,確定賠償標準的主觀因素太多并非好事,如何盡可能地在客觀因素的影響下確定精神賠償撫慰金的數額就成了關鍵問題。
(三)客觀量化數據匱乏
1.缺乏既定病情(preexisting condition)的影響分析
既定病情的概念在我國的法律法規中并非完全找不到蹤影,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三款就明確提到了“患者原有疾病狀況”,但可惜的是,這只是法官對于損害賠償的一個考量因素,而不包含請求權基礎。而且,在大多數涉及生存機會的判決中,法官對于既定病情的分析或是寥寥數句,含糊其辭,一筆帶過,或是直接得出“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雖給出數據比例,卻沒有相關佐證;*如羅某某等與宜賓縣李場鎮中心衛生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四川省宜賓縣人民法院(2014)宜賓民初字第700號民事判決書。僅有部分案例中法官給出正面回應,如“該醫療過失行為與患者死亡沒有直接因果關系,患者屬于急性重癥胰腺炎,病情兇險,死亡率較高,患者自身疾病與死亡存在直接因果關系,本院認定被告上杭縣醫院以承擔25%的賠償責任為宜”,*林某某、邱某某、邱爐生、邱華生、林發金與上杭縣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福建省上杭縣人民法院(2013)杭民初字第65號民事判決書。又如,“王某某自身病變是其最終死亡的根本原因”。*朱秀蘭、張四周等與樅陽縣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樅陽縣人民法院(2015)樅民一初字第01904號民事判決書。更為關鍵的是,既定病情對于最終的損害結果的影響力沒有定論,這會給生存機會的賠償帶來極大的困難。事實上,這也是我國類似案例中難以做到精確化比例判決的最大障礙,醫學鑒定結論的論證不充分,導致損害賠償的基礎不具備較強的說服力。
2.生存機會的客觀量化數據匱乏
在判例中,“生存機會”的喪失大多是作為一種主觀的描述性語詞出現,即使與數據相連,也只是在醫方過錯與最后的損害結果之間的參與度(過錯程度)之上有所連接,而無客觀量化的“生存幾率降低”的數據化體現,在這樣的論證基礎上對“生存機會”進行賠償實屬粗糙。在美國侵權法相關案例中,法官據以認定賠償的基礎無一不是具體的“生存機會”的概率的量化數據,即使不能得到精確的數據,也有較為可靠的概率范圍供法官參考,而非如我國實務中的司法鑒定,僅僅就整體的過錯診療行為對最后的損害結果的影響作出判定。
此外,還有部分案件的司法文書中明確出現的“生存機會無法量化”,*馬某甲等與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法院(2013)中區法民初字第02666號民事判決書;梁某某等與柳州市某某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魚峰區人民法院(2012)魚民初(一)字第355號民事判決書。“生存機會的浮動范圍”,*彭泳鈞等與溆浦縣康復醫院等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湖南省溆浦縣人民法院(2009)溆民一初字第997號民事判決書。“……使其喪失了一定的生存機會,與其死亡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但就現有材料,確切的參與度難以確定”等鑒定結論,*武連彩等與膠南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2013)膠南民初字第459號民事判決書。也給損害賠償的計算帶來了阻礙。在此類案件中,部分法官采取了“鑒定人出庭作證,給出比例”的方法來作為損害賠償的依據,但問題在于,鑒定結論尚無法認定生存機會的大小,那最后的認定是否具備正當性呢?另外,這種比例與生存機會的大小又非同一事項,對后者的認定或賠償仍然沒有正面客觀的數據加以支撐,讓人難以信服。
二、請求權基礎:生存機會喪失與人格權保護
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人格權的體系內加以保護,是生存機會在我國現行法的體系下得到救濟的一種思考路徑。*另外一種可能是,將機會喪失納入法益框架進行保護。事實上,英美法系正是以此思路將生存機會的喪失本身視為患者的利益受損并加以賠償的。這種做法的本土化雖然可行,但路徑復雜許多,若以“奧卡姆剃刀原理”考量,則不應采納。鑒于本文寫作重點在于為實務提供參考,對于法益保護理論上的構建思路,筆者在此不予探討。這種路徑的主要出發點是人格權(主要集中于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的保護屬于我國侵權法明確規定的人格權益,認定標準明確,舉證責任相對簡單,對患者及其近親屬利益的保護較為周全。在生存機會喪失的諸多案例中,法官都從這方面作出了嘗試。*在筆者于本文中考察的77件相關案件中,法官在判決中明確以生命權為請求權基礎并予以論證的,共計10件:吳樹曦等訴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2011)思民初字第5166號民事判決書;李某某等與富蘊縣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烏中少民終字第31號民事判決書;阮盛宗、陳眉姿等與福安市婦幼保健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4859號民事判決書;袁良珍訴安徽省肥東縣中醫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肥東縣人民法院(2014)肥東民一初字第01653號民事判決書;張庚來等訴中國石化集團中原石油勘探局第七社區管理中心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河南省濮陽縣人民法院(2014)濮民初字第2994號民事判決書;胡程家、邵溢姣、胡某、胡靜、胡建偉與被告周志剛生命權糾紛案,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初字第983號民事判決書;重慶市江津區中心醫院與廖勇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上訴案,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終字第01886號民事判決書;謝敬平、謝挺等與黃山市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皖10民終381號民事判決書。在此種討論前提下,生命權與健康權是主要的討論范疇。
(一)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生命權體系加以保護的路徑
這種路徑的主要出發點是生命權的本質在于對生命利益的尊重,而機會喪失(包括痊愈機會和生存機會)的實質恰恰是患者原本可能享有的生命利益由于醫方過錯醫療行為的侵害發生了人為的縮減。然而,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生命權體系加以保護并非順理成章,采用這種做法者至少需要回答兩個前提性問題:其一,生命權的保護實質是什么;其二,生存機會是否在其涵攝范圍以內。只有在生存機會的保護目的與生命權保護目的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將生存機會的保護納入生命權的體系的目標。因此,前者是對我國民法體系中生命權含義和目的的明晰,后者則是將生存機會納入生命權體系的嘗試。
1.生命權的保護
生命權為享受生命安全之人格的利益之權利。*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頁。在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生命權的享有主體自然是患者本人,可是患者一旦遭遇死亡,生命權即失去權利主體,不存在損害賠償問題。*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第102-103頁。而其近親屬則更不具備提起生命權侵害的主體條件,因而陷入權利遭侵害卻無適格主體的尷尬。事實上,生命權的保護問題一直是人格權中存在爭議較大的問題。從邏輯上來說,在生命權遭受侵害時,侵權法的矯正正義之目的和恢復原狀之目的因主體之缺失必定要落空,*張平華:《生命權價值的再探討》,《法學雜志》2008年第1期。因而,生命權是唯一對其侵害只能由第三人主張權利的利益。*[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張新寶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死亡賠償制度之目的不是對死者的生命價值進行賠償,而是救濟因受害死亡事件而受到利益影響的第三人。因為生命具備不可替代性,無法進行金錢評價,但生命損害具有彌漫性,*此處的彌漫性是指由于生命遭受侵害所帶來的死者生命權損害以外的一系列附帶損害,如對其近親屬、被扶養人等主體的生活造成的影響。生命權的法律保護主要是從經濟角度對這些附帶損害進行填補。所以民法雖可以拒絕對生命本身予以賠償,但對因生命喪失導致的相關損害,卻需要加以填補。*孫鵬:《“同命”真該“同價”?——對死亡損害賠償的民法思考》,《法學論壇》2007年第2期。這不僅是我國學者的共識,也是歐洲各國法律所認可的事實。*參見前注,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書,第70頁。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侵害生命權的損害賠償真正旨在填補的是受害人喪失生命所造成的社會關系的斷裂,以金錢賠償的方式來盡可能達到公平衡量受害人在世時形成的社會關系所代表的經濟價值,從經濟上實現“恢復原狀”的功能。
2.生存機會的保護實質
在生命權保護制度的功能得到確認后,方可探尋其權利內容,以期將對生存機會的保護納入其中。
從域外法看,美國侵權法的實務判例中對生存機會喪失的保護已有150余年的歷史,自1867年Craig v. Chambers案發生以來,*17 Ohio St. 253 (1867).理論的發展幾經波折,但在賠償的認定上卻始終采取了肯定的態度。直至1981年King教授對生存機會的賠償作出了經典定義:“……如果被告的侵權行為毀損或減少了原告獲取更有利結果的期待,那么原告就應該得到對所失期待的賠償。損害賠償的基礎是被告的侵權行為對原告得到更好結果的可能性的降低程度,且侵權行為是否真的降低此可能性并不影響損害賠償的認定。”*Joseph. H. King, “Reduction of Likelihood” Reformulation and Other Retrofitting of the Loss-of-a-Chance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Law Review, 1988, p492-493.這種對既定病情的激化/加速部分被King教授稱為“部分確定性損失”(partial/ less definitive losses),*Joseph. H. King, Causation, Valuation, and Chance in Personal Injury Torts Involving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1, Vol. 90: p1364, 1370, 1377.在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主要體現為生命存續期間的縮減。對此觀點,盡管反對者有之,但其亦認為,生存機會的實質是原告被剝奪的獲得更好結果的機會。*Todd S. Aagaard, Identifying and Valuing the Injury in Lost Chance Case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6, No. 5 (Mar 1998), p1339.
英國法上的Hotson v. East Berkshire Area Health Authority案中,盡管原告敗訴,但其原因并非機會喪失本身不可賠償,而是原告無法給出有力證明。*[1987] AC 750, [1988] UKHL 1, [1987] 2 All ER 909.該案中,法官對機會喪失的賠償作出了肯定回答。在Gregg v. Scott案中,法官Nicholls認為該案中出現了明確的醫學術語(存活率),*[2002] EWCA Civ 1471, [2005] 2 WLR 268 House of Lords.醫生并未履行他的保護義務,導致病人未得到及時救治而降低了存活率,病人應該得到相應賠償。也就是說,病人真正的損失是防止病情惡化和得到及時診療的機會喪失,而這種損失的形成是由醫生的過失所造成的,*Margaret Fordham, Loss of Chance-A Lost Opportunity?, 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5, p213.這才是患者能夠請求賠償的機會喪失的實質。
不難看出,盡管學者和法官可能在生存機會喪失的救濟基礎上見解不同,但普遍認可是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對既有病情惡化的助推導致了病人生命周期的不當縮短,故應認可損害賠償。
從筆者整理的我國案例來看,法官對于生存機會的見解也有相似之處,如“……被告福安市婦幼保健院的醫務人員未能履行上述義務,……以致鄭某某未能延緩生命期,喪失了生存機會”,*阮盛宗、陳眉姿等與福安市婦幼保健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4859號民事判決書。“……被告南華附一醫院診療方案不合理,治療措施不力,導致患者失去了長期的生存機會”,*劉檢告等與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等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人民法院(2014)石民一初字第159號民事判決書。“……診療過程中,未能盡到充分謹慎的注意義務,使患者失去了適當的治療機會,與患者的喪失生存機會(或生存期)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等等。*朱秀蘭、張四周等與樅陽縣人民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安徽省樅陽縣人民法院(2015)樅民一初字第01904號民事判決書。。也就是說,生存機會之所以在各個法律體系下均能得到救濟,是因為法官均認可其本質是患者的既定病情被激化導致生命周期的不當縮短。從這一層面來說,生存機會的保護實質上就是對生命存續權的保護,也是生命維護權的權能體現,*有關生命存續權和生命維護權的討論,參見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頁。將其納入生命權的保護體系并無障礙。
不過,值得注意的問題在于,筆者以上論述的基礎,是現有的案件都是在患者已經死亡的基礎上提起的訴訟。然而在美國法、英國法等域外法的案件中,生存機會喪失的案例不僅僅包括患者死亡后近親屬提起訴訟的情形,也包括存活患者本人提起訴訟的情形。*See 189-190 at Judgment of N.W.2d 174 (Iowa 2003).[2002] EWCA Civ 1471, [2005] 2 WLR 268 House of Lords.那么,一旦認定生存機會的實質是生命權的保護,對于仍然存活的患者本人提起的訴訟,人們將如何看待?同樣是生存機會的喪失,是否需要區別對待?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就需要利用身體權、健康權的理論框架加以探討了。
(二)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身體權體系加以保護的路徑
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身體權的體系予以保護主要是解決在患者并未遭遇死亡情況下的生存機會喪失之賠償問題。與前面的情形類似,在此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身體權的保護實質是什么;其二,生存機會喪失之賠償是否得以納入該體系。
1.身體權的保護
身體權是自然人維護其身體組織器官的完整性并支配其肢體、器官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其權利客體包含身體及其組成部分和身體的完整利益。*參見前注,王利明書,第342頁。在我國《民法總則》頒布之前,盡管我國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但多數學者傾向于認可我國民法上身體權的存在。*同前注,王利明書,第344-346頁;張俊浩:《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頁;施天濤:《生命健康權的損害賠償新論》,《政治與法律》1991年第5期;楊立新:《論公民身體權及其民法保護》,《法律科學》1994年第6期;柳春光:《身體權概念的再界定》,《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明確規定了身體權,從身體權的保護內容來看,其主要包括身體利益的享有權,*這種享有權一方面是指維持身體的完整的權利,另一方面是指維持身體利益的安全的權利,即對保有自身身體的各組織、器官并維持完整和安全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身體利益僅指生物學上(物理上)的客觀身體組織及利益,而不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層面的內容。與生命權一樣,身體利益的享有權是身體權人實現其他權能的基礎和來源。參見前注,王利明書,第350頁。身體完整和安全的維護權,*此即身體權人在遭受侵害之時有權請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救濟途徑。這種權能既體現為積極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措施,也體現為消極的人格權請求權的行使。這種完整性主要體現在身體的物理完整性方面,非法觸摸等行為應當被視為對人格尊嚴權的侵犯。參見前注,王利明書,第350-351頁;前注,柳春光文。一定限度內的處分權能。*這種處分權的支配性體現在身體權人對身體的組成部分(器官或組織)在符合法律或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的放棄、捐獻和對身體治療或麻醉、針刺等介入手段的拒絕權和同意權。參見前注,王利明書,第351-354頁。。據此,身體權保護的核心是身體組織的完全性,只有侵權行為損傷身體內部或外部之組織,方可認為是身體權遭侵害,比如毆打、非法搜查、不當手術、割須斷發等均屬之。*參見前注,王澤鑒書,第102-103頁。
2.生存機會喪失納入人身權保護體系的可能性
從我國實務來看,生存機會喪失的案件中,患者往往會因為醫生的過失行為受到身體上的損害,即使未遭遇死亡的結果,也可能會有殘疾或外傷等結果。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身體上的損害結果,確屬對身體權的侵犯,但并非生存機會的喪失,而是醫生的過失行為所帶來的身體損害。真正的機會喪失部分是患者因此而導致的生命期限的不當縮短,這種損害并不體現在身體的結果完整性上,而更多的體現于功能完整性上。即使患者僅僅因為醫生的誤診或漏診而錯失了治療的良機,導致病情惡化,也并未招致身體完整性的缺損,所以,將生存機會的賠償納入身體權的保護范圍實為不妥。
(三)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健康權體系加以保護的路徑
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健康權的體系予以保護,主要是為了解決在患者并未遭遇死亡情況下的生存機會喪失之賠償問題。與前面的情形類似,在此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健康權的保護實質是什么;其二,生存機會喪失之賠償是否得以納入該體系。
1.健康權的保護
健康權是自然人享有的以其器官乃至整體的功能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同前注,張俊浩書,第137頁。其權能主要包括健康享有權、健康維護權等。*健康享有權是指自然人享有保持其身心健康的權利,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兩方面。在生理層面,要求健康權人生理機能完整,各器官系統發育良好,功能正常,體質健壯且有良好的勞動能力;在心理層面,要求心理狀態良好。需要注意的是,健康并不是指無疾病狀態,僅指器官及系統乃至身心整體的安全運行,以及功能的正常發揮。參見前注,王利明書,第376頁;前注,張俊浩書,第137頁。健康權人在遭受侵害時可以采取各種合法手段來維護自身的健康并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險。這里的侵害包括身體方面的侵害(出售腐肉或私用毒藥以侵害人的健康、使人感染傳染病、散播有害健康之氣體或液體),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侵害(因名譽毀損或恐嚇引起精神衰弱、延誤懷孕確診期以使婦女“不斷地處于精神崩潰狀態中”)。參見前注,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書,第86頁;前注,史尚寬書,第148頁。健康權保護的核心是身體機能和心理健康的功能完整性,與身體權所保護的外部機體的完整性正好形成互補,從而實現對生命物理層面的全面保護,再輔以生命權的保護,對其社會關系加以維護。
2.生存機會納入體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本質是對患者生命因過失診療行為不當縮短的救濟。在患者死亡的情形下,其屬于對生命享有權和維護權的侵犯順理成章,但在患者尚未去世的情形下,不能借助生命權體系加以保護,此時健康權體系就是最好的保護傘。從健康權的角度來看,生存機會的喪失實質上同時意味著患者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受到侵犯。
從身體健康層面來看,生存機會的喪失無疑是對身體機能的破壞,因為這種喪失本身就是由既定病情的惡化/加速所帶來的(可歸責于過失診療行為的部分),當然影響了患者機體的功能完整性,且在某些情況下屬于嚴重的健康權的侵害(比如癌癥確診期的延誤可能會導致生存機會大幅度的降低,乃至從有治愈之希望變為無可醫治)。
從心理健康層面來看,生存機會的喪失所造成的心理打擊無疑是致命的。事實上,生存機會喪失的背后隱含的是患者對于生命延續的一種期待,這種合理期待由于非正常因素(醫方過錯)遭到破壞,從有治愈希望到希望渺茫乃至完全落空,患者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死亡提前來臨所帶來的恐懼等負面情緒)可能遠遠超出其身體上所遭受的痛苦,人世間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明知死期降臨卻無可奈何的精神狀態,很多死刑犯在面對死刑期限來臨時所展現的與其犯罪時的窮兇極惡極其不相稱的恐懼就是最好的寫照。這種對恐懼感的賠償絕非信口開河,德國法院就曾在某案判決中寫道:“因疏忽延誤了癌癥確診時間,由此而導致的病人對于腫瘤擴散的與日劇增的恐懼感構成了應當加以賠償的非財產損失。”*參見慕尼黑上訴法院1995年2月9日之判決,載NJW1995年,第2422頁。轉引自前注,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書,第86頁。
綜上所述,在患者仍然生存的情況下,將生存機會的喪失納入健康權的體系加以保護亦不存在障礙,且能夠和生命權體系形成互補,實現對生存機會的全面保障,真正體現對生命的尊重。
三、構成要件的檢討
雖然將生存機會的喪失納入生命權及健康權的體系中加以賠償從法理基礎上來說不存在論證障礙,但真正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研究者所作的努力僅僅是為了讓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有法可依、有據可循,為實務中的法官裁判提供便利,為患者的權益提供更為全面的救濟。從本質上而言,生存機會的喪失所賠償的僅僅應當是醫生的過失行為所造成的相對應的生命周期縮減帶來的損害,而非生命逝去的全部損害抑或其對健康造成的全部損害。然而,無論是侵害生命權的賠償抑或是健康權的賠償,從現行法上的條文來看“似乎”都是以“全有或全無”的形式來認可損害賠償的,*這些條文包括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一十九條,我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四條,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換言之,如果只是借用了“生命權”、“健康權”的框架體系加以救濟而不對“比例式”的賠償模式的正當化基礎加以闡述,則筆者本文中的結論難免有自相矛盾之嫌。那么,如何在現行法框架內合理化解此種矛盾呢?筆者認為,這無法繞過構成要件的探討。對于生存機會喪失的保護而言,應有以下構成要件。
第一,既定病情的存在。既定病情的存在是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侵害生命權/健康權案件的最大特征,也是生存機會喪失理論誕生的根本原因。在此類案件中,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激化了既定病情的發展,并與既定病情一同促成了最終損害結果的產生,因而無法將所有的損害結果歸責于醫生。盡管無法做到絕對精確化測定,但仍可以通過專業的鑒定數據來測定既定病情的影響力,以期盡可能使醫生承擔與其過失行為程度相當的損害賠償責任。從另一個側面來說,要區分某案件是否為筆者于本文中探討的生存機會喪失理論案件,就要確定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是否與既定病情相關聯,如果此損害結果的發生與既定病情存在與否并不相關,則此案件為普通的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不適用“比例式”賠償模式。*McMullen v. 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 88 Ohio St. 3d 332 (2000).
第二,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醫生的診療行為是否存在過失要以其是否違反既有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中所明確規定的注意義務為標準。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出于醫療活動的專業性和復雜性,為衡平醫患雙方利益,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中的“過錯”一般僅指“過失”。*張新寶:《中國醫療損害賠償案件的過失認定》,載朱柏松、詹森林等:《醫療過失舉證責任之比較》,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頁。在這一點上,生存機會喪失案件與一般的侵害生命權或健康權的案件并無差異。
第三,損害結果。在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對患者既定病情的激化而導致的生存機會的喪失或減少,而非最終損害結果,這是“比例式賠償”的核心要件。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區分最終損害結果中既定病情所影響的部分和過失診療行為所影響的部分。然而,正因為兩者相互促進,導致最終損害結果無法精確測定,所以通常將生存機會喪失的部分視為此時過失診療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也就是King教授所提出的“部分確定性損失”。*See Joseph. H. King, Causation, Valuation, and Chance in Personal Injury Torts Involving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1, Vol. 90: p1364, 1370, 1377.: p1364-1377.
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中,侵權人之所以要承擔全部的損害賠償責任,是因為其侵權行為對最終損害結果的作用力遠遠大于其他原因,基本上可以認為其導致了“全部的損害結果”。然而,在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既定病情的影響力完全超出“可以忽略”的范疇,不僅是造成損害結果的重要因素,而且在部分案件中甚至是“決定性因素”,而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只是起到了激化病情發展的作用,因此使其承擔“全有或全無”的賠償責任顯然并不合理。不過,如果能準確界定過失診療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部分(評估層面),那么再對此部分適用傳統的“全有或全無”規則(因果關系舉證層面),就不存在此種弊端了,因為醫生只是承擔了與其侵權行為原因力相當的損害賠償責任。舉例而言,如果該患者的生存幾率減少了30%,那么就針對損害總額的30%的部分適用“全有或全無”的賠償規則,從而達到實質上的“比例式賠償”效果。同時,如果仔細觀察現行法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保護的規范,就會發現其并未將“全有或全無”規則限定于全部的最終損害結果之中,而是法律僅僅存在于與侵權行為具有因果關系的損害結果之上。事實上,即使法律條文列舉了諸多賠償項目,法官也只能認可原告有證據證明因果關系存在的部分。從這個角度上說,法官通過過失診療行為對生存機會減少的概率部分適用“全有或全無”規則,就達到了“生存機會喪失理論”的效果,且并不違反現行法的規定,因為“機會喪失理論”的實質就是在“部分確定性損失”的因果關系上適用傳統規則。事實上,這種以原因力為損害賠償基礎的做法并非創新,類似的可見于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就是例證。
第四,過失診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生存機會喪失理論中的因果關系事實上沿用了傳統的“全有或全無”規則,所以與普通的侵害生命權和健康權案件并無二致,此處無需贅述。
綜上所述,盡管筆者在生存機會喪失的損害賠償上借助了生命權和健康權體系的框架,但在損害的評估和界定部分卻與傳統的侵害生命權和健康權案件相區分,這也是侵權責任中“個人僅對其過失行為所肇致之損害負責”的題中之義。*同前注,王澤鑒書,第12-13頁。通過構成要件的檢討,可以為生存機會喪失保護的“比例式賠償”模式提供正當化基礎。
四、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范圍及計算
(一)賠償范圍的確定:計算基礎
從美國侵權法的實務經驗上來看,其案例判決中對生存機會的賠償基本是按數據化、客觀化的路徑進行計算的,盡管賠償與否以及賠償的合理性摻雜了法官的價值判斷,但用于計算賠償金額的始終是科學數據(概率點或概率范圍),法官即以此為賠償依據,而不會徑直予以變更或拋棄不用。盡管數據本身未必絕對精準,但法官對此的嚴格遵守卻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判決結果的公平。而且,法官的判決中會明確指出賠償生存機會的金額部分,而非將之與過失醫療行為對患者造成的其他損害相混同。這樣一來,賠償的對象、賠償的原因和賠償的計算都有據可循,令人信服。
比較來看,由于法律體系的不同(我國法上須有明確的請求權基礎,而美國法上的判例雖依據了《錯誤死亡法》的規定,但有關規定僅為損害賠償項目,非請求權基礎),我國的法官一方面限于法律條文的匱乏而無法對生存機會喪失的救濟提出明確統一的適用規范,另一方面又在個案的判決中察覺到了對生存機會之喪失不予理會可能帶來的實質不公平,因此在判決中顯得猶豫不決,瞻前顧后。在對域外法予以借鑒且對生存機會在本土化背景下可能的救濟途徑進行探討后,還需要為賠償問題提供一些實際性的考量標準,以便對司法實務真正帶來幫助。由此,這種計算基礎中的考量因素應該盡量遵循一個標準:盡可能減少價值判斷因素,增加客觀化、精確化的科學數據及其他依據,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具體來看,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因素值得參考。
第一,客觀的生存概率。
生存概率是計算生存機會喪失最重要的客觀依據之一,生存概率的大小決定了當事人得到賠償數額的多少,因此其客觀化與精確化對于生存機會的損害賠償來說至關重要。事實上,這也是我國的司法案例中普遍缺乏的精細化的一環,主要體現為鑒定意見對生存機會的描述與過錯行為的描述沒有區分,數據參考也是以“參與度/過錯程度”的形式出現的,這讓人無法確定這一百分比到底是指醫生的過錯行為與患者的全部損害結果之間的原因力的大小,還是僅僅對生存機會喪失的原因力大小。
綜觀醫療鑒定和司法鑒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筆者并未發現與“參與度”相關的條文,僅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九條中發現與之可能類似的“責任程度”的描述,但在相關案例中出現的鑒定意見中,有接近半數的醫療/司法鑒定意見(37/77)采取了“參與度”的描述,其余的案例中則有“過錯參考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師北屯醫院與張修全等生命權糾紛上訴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農)十師中級人民法院(2012)農十民終字第00031號民事判決書。“關聯程度”,*尹寶禮等訴黃石市中心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湖北省黃石市黃石港區人民法院(2014)鄂黃石港民一初字第00071號民事判決書;中國貴航集團三〇二醫院與劉俊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上訴案,貴州省安順地區(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安市民終字第100號民事判決書。“原因力大小”等不同語詞。*莫紅燕等與浙江蕭山醫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市)人民法院(2015)杭蕭民初字第719號民事判決書。也就是說,在沒有法律法規明確支持的情況下,“參與度”已經作為一個通行概念在鑒定意見中出現。那么,“參與度”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呢?
有學者指出,“參與度”的概念來自法醫學鑒定中的損傷參與度,即在外傷與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諸因素共同作用導致某種后果,即暫時性損害、永久性功能障礙和死亡,外傷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定量分割(或因果比例關系),即外傷在該案件中的參與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法醫室傷與病關系研究組:《外傷在與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參與度的評判標準(草案)》,《法律與醫學雜志》1994年第2期。據此,醫療過錯行為中的“參與度”,指同時存在醫療過錯行為、患者疾病因素等眾多致害因素的醫療糾紛案件中判斷醫療過錯行為在患者發生的損害結果上的參與程度。*劉鑫:《醫療損害鑒定之因果關系研究》,《證據科學》2013年第3期。首先,這種來源的判定并未得到學者和法官的普遍認可,*就筆者參考過的文章而言,并沒有其他文章指出“參與度”概念的來源或法律基礎,而是直接在文中予以使用并論述。就筆者所研究的判例而言,盡管“參與度”的概念使用較為普遍(接近一半),但仍未達到“共識”的地步,也沒有法官對此概念加以詳述。也不具備現行法的支持,僅為筆者一家之言。其次,在我國醫學損害責任案件中,“醫療過錯”和“醫療過失”概念之混用頗為常見,有學者認為,“醫療過錯”行為之概念并不準確,因為“過錯”包含“故意”和“過失”,但在機會喪失案件乃至醫療侵權行為中,醫方行為普遍僅為“醫療過失”行為,否則構成刑事犯罪行為或一般侵權行為。*參見楊立新:《醫療損害責任概念研究》,《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3期。因此此處所用“參與度”之概念以“醫療過錯行為”為前置條件進行解釋,是否妥當值得商榷。退一步說,即使認可這一來源和概念的鑒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僅僅只有“參與度”的數據,而沒有既定病情的影響力數據或其他影響因素的數據,這種“參與度”的精確程度是否足夠直接作為判決所依賴的唯一依據。有學者指出,在參與度的基本理論中,當醫療過失、疾病等多種因素參與時,要同時分析諸因素的原因力,研究他們的相加之和,這樣才能使參與度的鑒定有理有據。*魯滌、唐田豐、常林:《醫療損害賠償案件因果關系的判定》,《中國醫院》2009年第8期。筆者贊同這種觀點。
筆者所搜集的案例的司法文書中,生存機會的數據不僅很少被明確提示,醫療過失行為在就診前后的數據對比也相當缺乏,無法由此得出生存機會實際減少的數額,只能得到醫療過失行為發生后的生存機會大小(甚至只有“參與度”的大小),與美國侵權法上有明確的生存機會大小的前后對比的差值提取模式相比,其說服力顯然不足。更有學者提出“參與度”的計算公式,明確“參與度”并非“機會喪失率”,而是“責任比例=25%×機會喪失率+10%”。*張四平、黃偉宣、程時和、李新、孫巖:《機會喪失醫療損害的鑒定》,《中國司法鑒定》2013年第3期。也就是說,如果法官確實依此公式予以判決,那么,損害賠償的數額不是對純粹機會喪失的賠償。
事實上,有學者已在數據量化層面作出努力,將參與度數值與因果關系的比例程度相聯系,作出了參考值的對應圖表,*彭書雅、夏文濤:《機會喪失醫療糾紛因果關系及參與程度鑒定分析》,《證據科學》,2013年第3期;同前注,劉鑫文。盡管在具體因素的列舉與數據全面性層面仍未臻完善,但與司法實務中僅提出“參與度”概念,未加分析即直接用于計算判決結果的粗糙做法相比,已經有所進步了。在不斷追求判決結果精確化、客觀化的方向下,應當努力做到在現有模式下將“參與度/過錯度”與生存機會比率掛鉤,乃至解釋為生存機會喪失率,這才能真正體現出對生存機會喪失的比例式賠償。
第二,既定病情的影響力。
在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中,最大的難點在于既定病情和醫療過錯行為共同促成了病情的惡化和最終的死亡結果,而對于具體的原因力大小,卻無法給出客觀化的準確依據。因此,在采納以實驗數據為基礎的生存率來考慮機會喪失的賠償之時,自然要將患者既定病情的影響考慮在內。如前所述,在既有的醫療損害責任案件基礎上,如欲將判決結果推向客觀化、精準化,則既定病情的影響力數據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條件。
事實上,按筆者對生存機會喪失賠償的實質定義,最合理的賠償方法應當是僅對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對既定病情的激化程度進行數值衡量,并予以直接賠償,而非將機會喪失的百分比與總損失額相乘,因為總損失額中包含既定病情對最終損害的影響,所以從最終結果上看,醫方承擔了高于其責任額度的損害賠償數額。*Todd S. Aagaard, Identifying and Valuing the Injury in Lost Chance Case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6, No. 5 (Mar 1998), p1351-1353.然而,生存機會喪失案件的難點恰恰是無法準確區分既定病情與過失診療行為對最終損害結果的影響,故就案件性質而言,目前的確認生存機會減少的百分比之方法仍屬首選。
在此基礎上,對既定病情影響力的評估就成了影響生存機會喪失百分比的一個關鍵因素了。筆者并無醫學知識背景,不敢對評判標準妄自揣測,但既然“參與度”之標準來源于《外傷在與疾病共同存在的案件中參與度的評判標準(草案)》(以下簡稱:《標準》),那么不妨以《標準》中的相關規定做類比參考。《標準》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較為詳細地規定了參與度的評判標準,以既定病情的癥狀/體征/器質性改變為標準加以界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資參考。同時,在既定病情對最終損害的貢獻度方面,可參照事件樹分析法或魚骨圖分析法做定性及定量分析。*參見前注,劉鑫文。
當然,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有證據表明,最終損害的產生與既定病情并無聯系,而純粹由過失診療行為引起,那么這就不是筆者于本文中指稱的“生存機會喪失”類型,而僅僅是單純的醫療損害責任案件,不適用本文的計算基礎及方法。
第三,損害的總額。
所謂損害的總額,就是指用于計算生存機會喪失所依據的總損失額應當包含哪些賠償項目,即比例式賠償范圍界限及于何處,這是計算基礎的核心內容。對于這個問題,不妨先看看積累了豐富判例的美國侵權法是如何處理的。
從美國侵權法的理論上來看,學者大多只在抽象的費用意義上給出方向,或是(因機會喪失而)增加的機體痛苦(physical pain)或其他身體損害(physical losses),情感損害(emotional losses)和間接損害(consequential damages,比如額外增加的醫療費用);*Todd S. Aagaard, Identifying and Valuing the Injury in Lost Chance Case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96, No. 5 (Mar 1998), p1344-1345.或是生存機會中所蘊含的未來收益(future benefits),即患者如果存活情況下可能獲得的利益,考量因素包括積極因素(年齡、身體健康狀況和收入能力)和消極因素(存活情況下的既有病情的影響);*Joseph. H. King, Causation, Valuation, and Chance in Personal Injury Torts Involving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Future Consequences, The Yale Law Journal, 1981, Vol. 90: p1382-1383.或是將生存機會喪失理論看做是一種單純的因果關系的判斷標準,適用于所失利潤(loss of profits),或從更廣義上來看,適用于根據通常情況下因果關系所采納的參數標準來看無法得到證明的損害。*See C. Castronovo, La Nuova Responsabilith Civile (3rd edition, Giuffrk, Milan 2006), p.545, note 212 and p.761-763. Supporting loss of chance as loss of profit within the domain of pre-contractual liability, in opposition to what is accepted by the author within the remaining domains of civil liability, see A. Sagna, Il Risarcimentodel Danno nella Responsabilita Precontrattuale(Giuffr6, Milan 2004), p.138 et seq. Never taking a stand on the definition of loss of chance, but taking note of the terms of controversy and hesitations among court decisions, see A. Baldassari, IlDannoPatrimoniale(CEDAM, Milan 2001), p.177-199; and T. Gualano, 'Perdita di chance', in G. Vettori (ed.), II DannoRisarcibile (Volume I,CEDAM, Padua 2004), p.121-190. Cited from Rui Carodna Ferreira, The Loss of Chance in Civil Law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Analysis,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 Comparative Law, 2013(20): 63.然而這些概念均無法對實務產生明確的指導性意義,就像是給法官一把無鋒之劍,難以適用。
從美國司法實務上來看,大多數判決也未涉及具體的賠償項目,僅是以總額的方式出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Matsuyama v. Birnbaum案中,有法官指出,總額應參照傳統的“全有或全無”規則下所產生的最終損害(ultimate harm)的總價值:如果患者死亡,則依照錯誤死亡法(wrongful death statue)的相關規定予以計算;如果患者未死亡,則根據醫療過失案件中對身體損害的規則進行計算)。*See 840 at Judgment of 890 N.E.2d 819 (Mass. 2008).在該案中,法官就引用《馬薩諸塞州一般法注釋》(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Annotated)第229章第2節的錯誤死亡(生存機會喪失被視為錯誤死亡的一種類型)中的損害計算方法,該節明確列舉了機會喪失案件中的賠償項目:(1)死者相對于有權代替其接受損害賠償的主體的價值,包括但不限于死者的預期凈收益(expected net income)、對有權接受此損害賠償的主體的服務(services)、保護(protection)、照料(care)、援助(assistance)、社會費用(society)、社會交往(companionship)、撫慰(comfort)、引導(guidance)、法律顧問(counsel)和建議(advice);(2)合理的喪葬費;(3)在死亡結果是由被告的惡意、故意或疏忽大意的行為或者重大過失行為造成時,原告可以請求不低于五千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在該案中,法官援引了第一條作為生存機會的計算基礎。*See 828 at Judgment of 890 N.E. 2d 819 (Mass, 2008).不過,也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各州的錯誤死亡法規定不同,損害總額的計算方法也有差異。*孫鵬:《英美死亡損害賠償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以死亡損害賠償額的計算為中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同時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過失診療行為中所產生的患者的實際痛苦和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和機會喪失的部分是否應當分開計算。在美國部分案例中,法官明確認為,應當予以界分,并對生存機會喪失部分進行比例式賠償,而不要將患者遭受的痛苦賠償列入其中。具體來說,患者遭遇的痛苦有兩種:其一,由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所引起的與機會喪失明顯背離的疼痛和煎熬(pain and suffering),對這部分的賠償與其他任一醫療過失案件遵循相同的規則,不列入比例賠償范圍;其二,最終損害結果隱含的疼痛和煎熬部分,比如胃癌的致死過程中所帶來的痛苦,這部分痛苦即使沒有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可能也會產生,因此醫生只需要對其過失行為所導致的患者避免這種痛苦結果的可能性的減損部分負責,這部分痛苦應當計入比例賠償范圍。*See 839 at Judgment of 890 N.E. 2d 819 (Mass, 2008).亦有法官明確指出,這樣的區分方式并不公平,因為其沒有考慮到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患者未死去的情形,同時亦與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比例式賠償模式出現的初衷(用以防止“全有或全無”的僵化,區分損害卻對痛苦部分的賠償予以全額賠償)相違背。*See 189-190 at Judgment of 670 N.W.2d 174 (Iowa 2003).筆者認為,是否應當區分,還是要回歸到生存機會的賠償本質上看,由于醫生僅對其過失診療行為造成的對既定病情的惡化部分負責,應當予以區分。
綜上所述,美國侵權法上對于生存機會喪失的損害賠償計算原則是,以生存機會的喪失率與傳統醫療案件中按照錯誤死亡法計算的損害賠償總額的乘積作為生存機會喪失的賠償金額。從法理上看,其意圖對過失診療行為造成生存機會的減損部分進行賠償,以使醫方應承擔的賠償責任與其對結果的原因力大小相匹配,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實質正義”。
在我國法的背景下,筆者認為,在將生存機會喪失納入生命權、健康權的體系加以賠償的基礎上,可以參考美國侵權法的損害賠償的思路,在傳統的侵害生命權和健康權案件的損害賠償總額的基礎上折算出醫生對其過失診療行為所應負責的部分即可。
1.生存機會喪失的物質損害賠償
以前述為基礎,此處的賠償項目應當根據侵害生命權所救濟的賠償項目展開。我國法就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處理方式區分了所受損害(具體損害)和所失利益(抽象損害),*從我國法上的現有條文的規定來看,對生命權遭受侵害的賠償條文主要有我國《民法通則》第九十八條、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一十九條,我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四條,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條。對于前者采取“差額賠償”的計算方法,對于后者采取了“定型化賠償”的方法。*參見張新寶主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法律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3]20號民事判決書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71頁。其中,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及其他預計收入和因誤工減少的收入主要包括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宿費、住院伙食補助費、必要的營養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和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從賠償項目來看,如果要納入生存機會的保護范圍,那么按照“差額說”應當是醫生實施過失診療行為前后的利益差值,即因此而增加的費用和減少的利益。
筆者以為,原則上,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應當列入比例賠償范圍。因為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等費用在患者既定病情被及時確診的情況下仍可能有所支出,真正與醫生的過失行為相關聯的是在正常的既定病情治療費用以外新增的、因過失行為導致的后續治療和康復支出的費用,比如因為醫生的誤診導致的病情惡化以后需要接受額外治療的費用(如及時發現即可避免接受的放療或化療)。對于這部分費用,有學者認為屬于客觀賠償范圍,應給予全額賠償,無機會喪失率之應用的余地和必要。*吳志正:《實證醫學數據于醫療事故損害賠償上之意義》,《臺大法學論叢》(臺北)第40卷第1期,2011年3月。筆者贊同這種觀點。然而,問題在于,生存機會喪失案件與普通人身侵害案件不同的地方是既定病情對于最終損害的影響無法精確判定,從上述相關費用的賠償規定來看,其各項費用的賠償依據應當是與侵權行為存在因果關系的部分,但在生存機會喪失的案例中,原告方所列舉的費用依據往往是患病前后的總費用,因此若予以全額賠償,則對醫方顯然不公平,而以生存機會喪失率為基準予以比例賠償,則真正體現了醫方對其過失診療行為所造成損害部分的責任。當然,如果患者能證明費用部分是由于醫生過失診療行為所造成的“增加的費用”,則應當認可其全額賠償,而不適用比例賠償原則。
對于因誤工減少的費用部分,應當以同樣的標準去看待,即“是否為過失診療行為所增加的必要費用”。事實上,由于既定病情因素的存在,依然無法準確判定不存在過錯診療行為的情況下患者是否會因病情本身的發展而產生誤工費。因此,原則上,還是應當將其列入比例賠償的范圍以內。只有當原告能夠舉證說明誤工費屬于“增加的必要費用”之時,才可予以全部賠償。*比如及時確診既定病情的情況下,患者本無需耽誤其工作進度,但因過失診療行為導致既定病情的惡化而不得不放棄工作。
至于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的問題,由于我國采取了“定型化賠償”的模式,只需以此數額為基礎予以計算即可。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與死亡賠償金不同的是,殘疾賠償金中的勞動能力喪失部分可能存在程度上的認定必要,這種認定需要與其收入能力相掛鉤,以對收入能力的實際影響為基準來判斷,而非僅僅以殘疾等級為認定標準,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的含義所在。
對此,有學者從數據化的角度提出損害賠償的意見,以圖4和圖5闡述生存機會減少的賠償原理。

圖4原告能舉證其實際收入減損的生存機會減少的賠償原理圖5原告不能舉證其實際收入減損的生存機會減少的賠償原理
圖4和圖5中a%代表患者就診前的生存率,b%代表患者就診后的生存率。該學者認為,患者的總收入損失為:a%×健康時收入;如果原告能夠舉證其實際收入之減損值,則以該數值直接與a%相乘,若不能舉證,則以(a%-b%)乘a%為基礎。*同前注,吳志正文。
筆者認為,這種計算方法值得商榷。該學者的計算思路并不難理解,即以生存率來衡量患者的收入能力,但問題在于即使生存率降低,也不一定實際影響患者的收入能力,這也是為何司法解釋中以對勞動能力的實際影響為標準,而非僅僅基于殘疾能力之等級鑒定。同時,生存率的減少部分并非意味著收入能力的降低,而是反映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對結果的原因力大小。因此,筆者認為,原則上,殘疾賠償金應當列入比例賠償范圍內,此為原因力判斷的結果。當然,如果有其他證據能夠證明收入能力的降低是單純由于醫療過失行為造成,而無既定病情的影響時,則應當認定全額賠償。
2.生存機會喪失的非物質損害賠償
事實上,從筆者所收集的案例來看,法院的普遍認識是對上述費用列入比例賠償范圍并無分歧,筆者逐一分析不過是為其判決結果加強論證而已。然而,對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而言就不是這樣,個案之中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不僅存在是否納入比例賠償范圍的分歧,連比例的依據方面都存在一定分歧。為此,需要討論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實質以及是否應當列入生存機會喪失賠償的比例范圍。
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實質是對精神痛苦的救濟,從賠償目的來看,其與其他賠償項目相比明顯更具備合理性和優勢。
其一,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主體并不限于受害人,也包括已死亡的受害人的近親屬,因為在此類機會喪失案件中,受害人并非都因侵害致死,有可能只是殘疾或出現未來的患病風險,那么,精神損害撫慰金就很好地解決了請求主體的救濟問題(如果患者死亡,對近親屬造成的精神痛苦當然可予以救濟;如果患者生存,那么其自身遭遇的精神痛苦可以得到救濟)。
其二,精神損害撫慰金更符合“生存機會”的救濟目的。因為患者在生存機會喪失之際,所遭受的并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痛苦和額外增加的治療費用,更重要的是難以面對生存希望被急劇扣減、生命期限所剩無多的精神痛苦。精神痛苦的賠償實質上有一定的準入門檻,通常情況下需要有病理上的效果,如官能癥或精神病的癥狀。然而,在特殊情況下,喪失所愛親人的悲痛在適用一般條款的法律制度中也能獲得補償,且不以悲痛達到病理上的要求為前提。*參見前注,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書,第88-91頁。在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毫無疑問,患者本人對生存機會的降低乃至削減至零是絕望而沉重的打擊,因此在本人存活的情況下,給予精神損害撫慰金作為對生存機會的賠償合情合理;而在本人死亡的情況下,其對近親屬造成的沉重打擊也不亞于此,因為畢竟患者本人的死亡并非單純由于既定病情而產生,其中夾雜了醫方(第三人)的過失行為,使其生命期限提前縮短,由此引發之憤怒、失望與痛苦并不難想象。依學者之言,“近親屬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是客觀存在的,因為近親屬和死者之間存在血緣或感情上的密切聯系,其在死者身上寄托著感情、希望……沒有任何痛苦比自己的親人遭受死亡或重大傷害使人刻骨銘心”。*同前注,王利明書,第326頁。
因此,宜將精神損害撫慰金作為對生存機會的賠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精神痛苦是由于過失診療行為所引起的,并不夾雜既定病情的影響,醫方之致害原因力應當視為全部,故不應將此費用列入比例損害賠償范圍。同時,由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數額定量中有較多參考因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確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數額的參考因素,法官應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這樣有利于在個案中實現衡平和實質正義。
此外,在計算方式上,有學者提出了如下標準的公式來計算精神損害撫慰金,可供參考:“撫慰金=當地最高限額×s%×(1-v%)×(1-y%)×其他因素(s、y、v≤100)”。其中S%代表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指數,以20%為層級劃分為五個等級;(1-v%)代表受害人過錯因素,v代表受害人過錯程度;(1-y%)是年齡指數,y表示年齡。*張潛偉:《生命的價值學說的價值與死亡賠償——兼論精神損害賠償的計算公式》,《河北法學》2013年第3期。
(二)賠償的計算方法
所謂計算方法,實質上是對計算基礎如何進行利用的問題,即如何在上述考量因素的基礎上加以整合,選擇適合個案衡平的賠償金額計算方式,主要分為對已發生損害的計算和對未來損害的計算。
從美國侵權法的理論上來看,對已發生損害的計算方法有重要指導意義的主要還是前述King教授的文章,此處試舉一例,加以明晰。案例前提假設如下:有一名癌癥患者由于醫生過失性用藥過量致死,其原有40%的痊愈機會(chance of recovery)且痊愈的情況下擁有35年的生存預計年限。同時,即使其既有病情未得到治療的情況下也有至少6個月的生存預計期限。當原告聲稱患者由于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同時遭受了“確定性損失”(definitive losses)和“部分確定性損失”(partial definitive losses)并要求同時進行賠償的情況下,為避免其得到重復賠償,其計算基礎中的年限因素應當被限定為:“0.5+40%×(35-0.5)=14.3年”,用于計算的金額基礎則為其喪失的生存機會中可能包含的可預測的未來收益項目(實際上就是可得利益或所失利益),*“可得利益”的規定主要借鑒自《德國民法典》第二百五十二條。在此條文中,“所失利益”被界定為按照事物的慣常運行或根據特別情事,特別是根據所作準備和所采取的預防措施,能夠以極大的可能性期待得到的利益。如果機會損失符合此定義,則應該在損害賠償的涵攝范圍以內。從條文的設置上來看,我國《合同法》第一百十三條中所指的“可得利益”大致與這里的“所失利益”相對。在個案中可能有所不同。
從美國侵權法的實務上來看,目前對于已發生損害的計算方法主要是“比例式計算法”,其原理主要是根據生存機會的大小來對傳統的“全有或全無”規則下的賠償數額進行縮減。具體而言,此計算方法需要兩項數據:一是傳統的“錯誤死亡法”規定下此案件的患者所能獲得的總賠償數額(若患者未死亡,則數額相應變更為身體受損時可獲賠償額);二是醫生診療前后的生存機會的差值(以概率形式體現,通常適用“but-for”法則),然后將兩者相乘即可。*See 840 at Judgment of 890 N.E.2d 819 (Mass. 2008).
對于未來損害的計算,計算方法也有“單獨結果計算法”(single outcome approach)和“分段結果計算法”(weighted average computation,此為意譯)兩種。
此處試舉例說明不同計算方法可能的差異。假設有一名18歲的患者因為醫生的過失診療行為在未來可能會有失明的風險,對于這種風險的賠償數額的計算就會呈現兩種模式。在單獨結果計算法下,陪審團會以失明發生概率最大的時點(假設為40歲,發生概率為50%)為計算依據,而患者40歲時失明所產生的損害總額為100,000美元,則其應得賠償額為:“100,000美元×50%=50,000美元”。在分段結果計算法中,陪審團就需要計算其在各關鍵時點的概率。如本案中,患者失明的風險在40歲時發生的概率為30%,在30歲時為15%,在20歲時為5%,不發生的概率是50%,進一步假設其在40歲時發生失明的損害總額為100,000美元,在30歲時為200,000美元,在20歲時為300,000美元,那么患者可以得到的賠償總額為:“100,000×30%+200,000×15%+300,000×5%+0×50%=75000美元”。*Joseph. H. King, “Reduction of Likelihood” Reformulation and Other Retrofitting of the Loss-of-a-Chance Doctrine,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Law Review, 1988, p1383-1384.
相比較而言,第二種方法明顯更為合理且符合機會喪失的救濟宗旨。不過,數據的增多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結果的不確定性(因為數據本身并非客觀),但無論如何,就現有技術看來,這種方法已經是最為合理的客觀計算方法了。
從筆者研究的判例來看,在我國司法實務中,法官們的計算方法之間并不存在較大差異,基本上是將鑒定報告中給出的數據(參與度、過錯程度等)與侵害生命權和健康權的數據總額相乘,可謂單獨結果計算法的簡化版。
深究其中原因,主要是司法鑒定或醫療鑒定中僅提供了一項比例數據,法官并無選擇空間。從效果上來看,一方面,法官作為非專業人士,既無法對數據準確性予以客觀評價,則予以采納反而更為便利;另一方面,這也限制了法官欲通過多樣化的數據來追求判決結果精確性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大數據”的不斷深化,未來的生存機會喪失案件中法官所能參考的數據必將更加全面化及精確化,此時就對法官的計算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從另一層面上來看,我國的現有案件尚未涉及未來風險的處理,但未雨綢繆并非杞人憂天,通過對以上計算方法的參考,法官對將來案件的處理模式必將更加多元化,從而在個案中實現“公平正義”的目標。
LocalizationofLossofChanceofSurvivalTheoryinTortLawinChina
Ji Ruowang
There are few cases involving Loss of Chance of Survival Theory of Tort Law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Through case analysis, we may discover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legal basis for claims, disunity of compensation scope and shortage of quantitation of objective data. The protection of loss of chance of survival should be included into the system of right to life and right to health. In remedying the loss of chance of survival, “Proportional Liability” shall be adopted rather than “All-or-Nothing” Approach adopted in the case of injuring traditional personality right. In terms of the compensation scope, the compensation for material damage and the compensation for non-material damage shall 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proportional liability is applied to the former in principle.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it is supposed to pursue the diversity and accuracy of the objective data, and distinguish the existed harm and future risk in calculating method and respectively adopt the Proportional Calculation Method and Multi-results Calculation Method.
Loss of Chance of Survival, Legal Basis for Claims, Compensation, Medical Negligence, Proportional Liability
DF529
A
1005-9512-(2018)01-0116-18
季若望,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民商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美國愛荷華大學訪問學者。
陳歷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