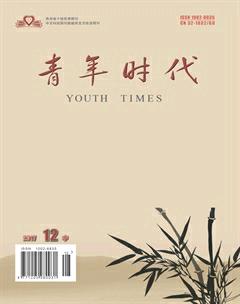賈樟柯
陳文君
摘 要:現實主義電影隨著當代電影行業的變革和現代意識的發展,不斷豐富著自己的藝術語言和表達方式,不斷適應新的審美需求,以寫實的手法承載著當代人多樣的命運與情感。賈樟柯的現實主義電影創作已經走過了十多個年頭,他的努力和對社會轉型下底層人民生活的執著守望,不僅為我們呈現了現實主義電影在今天廣闊的可能性,豐富了當代中國影壇的面貌,擴展了當代電影文化的維度,也在觀念不斷轉換,科幻暴力低級趣味泛濫的今天彰顯了他獨立的電影創作意識和風格。
關鍵詞:賈樟柯;現實主義美學
電影在中國的發展已進入繁榮時期。影視行業隊伍已很龐大,也涌現出一批思想活躍、有才華的年輕導演,但在創作水平普遍提高的形勢下還需要在藝術的深度上進行錘煉。當今世界已經是一個網絡化的“國際村”,各種類型的電影節和影展活動十分頻繁,各種資訊的傳播非常便捷,這與以前電影行業的環境迥然不同。對于現在的年輕導演如何在“泛屏”時代進行電影創作,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從研究西方電影的基礎和表現力,再到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越深入就越整體。我認為,好的電影作品不在于內容,而在于表現的高度,這個高度,古典和現代一脈相承。就賈樟柯個人創作而言,目標一直很明確,就是持續探索如何在以西方造電影體系的審美要求表現中國工人階級人物生活時,創作出具有中國文化內涵和西方技法相融合的現實主義美學。賈樟柯將人物命運與中國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相結合,并用西方現實主義美學的鏡頭結構表現出來,使中西方兩種文化在這個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彼此交流融合,創作出有飽滿現實情感的作品。
眾所周知,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電影藝術表現的手法由來已久,這種風格在新紀實運動的影響下逐漸展露頭角,“粗糙”的現實影像不同于政治現實主義和第五代導演的寓言式電影,從而表現出國際藝術片普遍具有的世界性美學特征,并在各類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成功與認可。綜合來看,現實主義的創作以觀照對象為坐標軸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是日常詩意;在這類作品中,導演把鏡頭對準自己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通過對周遭生活的審美化處理表達內心的詩性情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處理而生發的詩性表達具有后現代主義的美學特征。二是底層觀照;這類作品主要描繪處于社會底層的蕓蕓大眾,抓拍當代社會底層那些典型人物的生存狀態和性格命運。三是社會變革;這類作品以社會轉型下的中國生態環境靜物為主,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呈現了多樣的社會面貌。
所謂的“真實美學”是安德烈·巴贊對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美學的系統化概括,具有關注直接現實性主題、強調鏡頭段落、提倡非表演性的特點,賈樟柯的電影美學價值正在于現實主義的美感。賈樟柯這種強烈的紀實性風格首先表現為對于長鏡頭的充分利用,他很少使用蒙太奇,而是大量地使用長鏡頭和景深鏡頭,從而獲得一種不為外界所干擾的、最真實的客觀記錄。景深鏡頭要求觀眾更積極地思考,甚能讓他們更好的參與電影的場面調度。景深鏡頭把意義含糊的特點重新引入畫面結構之中,在景深鏡頭的客觀注視下,現實生活得以再現,著重于記錄真實的景深鏡頭,和觀眾處于平等的位置之上,它把一切影像交給觀眾,畫面的含糊多義性留待觀眾自己去理解。在色彩方面,賈樟柯采用原生態的色彩符號作為紀實電影的主色調,并使用非職業演員、自然光效、真實環境音,以及固定拍攝、長鏡頭等技術,來平淡地表現現實發生的故事,這與以張藝謀為代表的中國第五代導演,通過注重色彩和文化符號來表達主題和傳遞中華文明的方式是有差別的。但正是這種平淡,才如此的真實和深刻,在這種平淡之中,我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人與環境、與時代、與歷史進程之間關系的敏感程度。現實主義美學不是一種討好的電影風格,但它是對現實的一種自視,是一種負責任的心態。“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這種具有現實棱角的東西,他們感到不舒服,也許是因為這樣的影像在觀看的時候要求觀眾有一定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大家好像就是不愿意通過電影這種方式來承擔這些東西,寧可去消費那些打磨的光滑鮮亮的東西。”賈樟柯的現實主義美學顛覆了許多傳統的電影觀念,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將真實的生活展現在觀眾面前。例如在《站臺》中,人們的沖動,與環境的封閉,理想與現實因空間的約束而產生的沖突和緊張關系,凡此種種,都讓我們感受到一種“真”,一種青春的躁動與現實的壓抑。除此之外,賈樟柯的紀實電影風格也帶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例如《三峽好人》中那個騰空而起的建筑正是時代的隱喻,一種深刻的歷史悲涼,千年古鎮和他的人民將永遠在此地消失。還有,影片中出現的UFO,可以說唐突地增加了電影的荒誕感,但是在三峽,在這個時代,荒誕本來就是一種真實。電影結尾硬著頭皮走鋼絲的人,也正是底層人民真實生活狀態的寫照。這種超現實主義色彩的元素看似破壞了影片的紀實風格,但又真實的概括了客觀事實的真面目。賈樟柯的電影對現實的批判是微觀的、超現實的,同時也是非理性、非概念式的,通過這種方式,他能夠準確的“表達自我的感情,表達中國社會的變遷”。
賈樟柯嗜好用長鏡頭和固定鏡頭來表達紀實美學,這一點受到侯孝賢和小津安二郎的啟發,他認為這種鏡頭的表現方式更適合展現底層人物的生活和命運。電影的拍攝手法和電影制作人對觀察生活的方式和價值觀密不可分。“我不想把導演放在過于獨裁的位置,我希望我的電影有自由民主的意識”,賈樟柯認為過多的鏡頭切換會帶入導演太多的主觀意識,長鏡頭和固定鏡頭的表現形式更尊重觀眾的觀影機制,觀眾有更充足的時間與銀幕進行互動,能夠更自由的選擇關注焦點,甚至給電影本身傳達出民主的意識與符號。沒有特寫、分切、閃回的長鏡頭,攝像機既冷靜又充滿感情的全程攝入,這種極度冷靜、克制、客觀的電影語言,為電影呈現出零度敘事的風格,在靜止的凝視中強烈地顯示出真實的力量。固定鏡頭的使用能更好的保留時間的完整性,給銀幕上的時間留一點空隙,使影片具有一種獨到的節奏感,這種反電影常規反戲劇性的時間處理方式成為賈樟柯電影的一個明顯的敘事特征和最具辨識力的美學特征。例如在電影《平臺》里,即使在畫面中人物已經出畫,鏡頭也不會立即隨之轉動,或者立馬剪輯。這往往是用鏡頭平視邊緣人物,即使真實中包含人性深處的弱點、齷齪。賈樟柯把劇中人物的命運以及他們切身的失敗感放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強調時代的變化給中國底層普通人民帶來的巨大影響,影片的歷史感和真實感在每一個普通人生存的每一刻里呈現著,這種在時代變遷下小人物命運的無奈和悲哀,歸根到底源于導演對民間人生的深切體驗與關懷。
從1998年的《小武》一路走來,賈樟柯在對待電影執著的態度上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他認為電影能讓我們突破自己的生活圈去關注更多的普通人,在世俗生活的緩慢流程中,感受每個平淡生命在社會轉型下的喜悅與沉重。賈樟柯在多次訪談中表示了自己的創作態度,“電影創作不可以‘去理想,如果為了娛樂而放棄思想,終有一天無論是整個國家還是個人,都將承受泛娛樂化的后果,在這些重要的觀念上,我不能遷就觀眾”。現實主義電影的“缺席”,在中國電影發展的道路中,是一個不和諧、不健康的因素。而賈樟柯的出現和堅守,正是彌補了這一空缺。
參考文獻:
[1]潘先偉,論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的苦難意識與文化意識[J]。藝術評論,2007(06)。
[2]黃佼,賈樟柯電影的美學風格研究,2006。
[3]李徑宇、賈樟柯:我們觀察中國的角度對觀眾是陌生的[J]。新聞周刊,20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