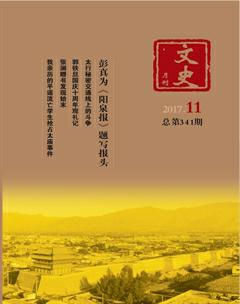我親歷的平遙流亡學生搶占太廟事件
張文宗+張永富
1948年平遙解放前夕,我從平遙中學初中畢業。在平遙縣城閑逛時,看到不少墻上貼了閻錫山政權平遙政府貼的宣傳畫。畫上有名有姓,說的是某村財主等如何被殘害,有幾顆骷髏自說自話。其中一個骷髏說:我多念了幾天書,被殺了;另一個說:我多種了幾畝地,被殺了……一共有六十種宣傳畫,總稱共產黨的“三十六刑,二十四殺”。人們看了后恐怖萬分。有幅畫上是一群學生被強迫背上炸藥沖鋒在前炸碉堡送死。我看了心驚肉跳。
一天,各街道通知,要“堅壁清野”演習,所有人都到城外“三畛兒”集合聽報告。不走的人,一經查出,以偽裝分子論處,誰也不敢留在家里不去。平遙城內形勢惡劣。
我家所在的南湖村來人說,山上的干部都回了村,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對為非作歹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團結各階層人士,革命不分前后,逃亡戶一律寬大,不究既往,一視同仁,歡迎回村。我家是從村里逃到縣城的逃亡戶,由于家里快斷炊了,我媽萬般無奈,只得冒險回村,尋點糊口糧面。只三天,我媽便從村里回來,并帶了些吃食,對我說村里一切正常,逃到南山上的干部群眾都回來了。主事的干部對她說:“快讓敏之也回來吧,共產黨歡迎青年學生參加工作,在城里沒飯吃,有啥好待的?”我對宣傳畫上的內容心有余悸,仍怕讓學生背炸藥上前線送死,對媽說:“別聽他們口上說得好,把你拴在轅里用鞭子抽,那時后悔也趕不上了。”我媽將信將疑,也不敢相信。
我的堂弟張維玄小學畢業了,來縣城和我住在一起。張維玄是我三伯的孩子,在南湖村張氏家族里排行第六,我排行第五。因為三伯母去了太原,堂弟吃飯時會到三伯在縣城的鋪里吃。因為我媽從村里帶來的糧面僅能將就幾天。
盛夏六月初的一天深夜,“咚咚咚……”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接著,有人連聲大喊:“張維玄,快開門……”這在深夜中突然響起的敲門聲,驚醒了熟睡的我們。堂弟聽到有人叫他,急忙出去開街門,隨后回來說:“五哥快起,俺學校通知,全體師生到西寺廟廣場集中,好像接到命令要全城撤退。”我急忙起來和堂弟分析情況,這是演習,得走,否則被查到,將按偽裝分子論處,亂棍打死。如果真撤退,也得走。不走,留下給共產黨去背炸藥上前線送死。不論哪種情況,都得走。
那時,我媽回了東泉村娘家。我把一條純毛毯讓堂弟打了包背上,和堂弟速速關門走了。我們急忙往西大街跑去。朦朧月色中,街上沒有行人。
西門外有推著自行車往回走的一對男女,他們說趕不上大隊了。我們只好回來,這時仍有人急急往外走,我們也急步出了西門,往西北直奔火車站。這時,路邊的一個小鋪里有人說話,我們進門見一個當兵的持槍坐在椅子上,我問:“你不走?”當兵的一瞪眼,惡狠狠地說:“往哪走?”我沒敢多問。我倆出了小鋪后急忙橫穿鐵道,卻幾乎被鐵絲絆倒。天已大亮,達蒲村沿路扔了無數行李衣物,逃跑的倉促狀態可見一斑,路上幾乎沒有人。我倆到了汾河鐵橋后,有斷后的士兵說:“快點走,追上大隊。”我倆走了一程,追上了散亂的隊伍。
我倆不辨方向,隨著大流走,慢慢融入了學生行列。夕陽西下時,大隊人馬到了文水城下。學生集合后魚貫入城。平遙中學的男生都發了槍,我由于已經畢業,所以沒槍。所有學生在一條街分住南北兩院,我住在南院,太乏睡著了。誰知北院出了大事。后半夜,北院兩個學生執勤,靠墻躺著,迷迷糊糊中,一個學生的槍被人奪走。奪了槍的人,端著在月光下明晃晃閃亮的刺刀,向他兩個刺殺過來。他倆急忙跑進里院大喊:“共軍沖進院了,快快迎戰!”大伙兒端著上了刺刀的槍,沖出外院。那個人仍然在原地端槍喊:“殺呀,殺呀……”他還沒回過神兒,便死在眾人刺刀下。眾人細看,原來是一個瘋子。我在南院,聽說了情況后,驚愕不定。
農歷六月初六,平遙、介休、汾陽、文水等幾個縣的勾子軍在一夜之間跑光了,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便解放了大片地區,這幾個縣城沒遭戰火冼劫,平平安安進入了新時代。閻蔣政權平遙縣長尹遵黨脅迫平遙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隨他一起逃往太原。那時留在縣城的人傳言,逃走的人有很多在路上病死、餓死。特別是在交城山口堂村激戰中,學生、教師死得更多,消息越傳越玄,很多學生家長心急如焚,驚恐不已。
一位從半路偷跑回來的平遙中學勤雜人說,平遙中學學生在堂村黑夜激戰中死了不少,他沒槍,趁亂跑了回來。平遙中學的學生被編為教導總隊,袖上有“4368”的軍人番號,而且有槍,被閻錫山勾子軍強迫上了前線。這消息更嚇壞了我媽。原來的謠言“解放軍要強迫年輕學生當兵上前線送死”是根本沒有的事,造謠言的勾子軍卻強迫學生當了炮灰。
我出來的時候啥也沒有拿,這次逃走是奉命行事,學校給了我半袋子白面,作為路上的口糧。堂弟張維玄已歸入自己所在班級的編隊。大道上,人群分成幾路縱隊前進。縣長尹遵黨騎著高頭大馬,不時拿著手槍來回跑前跑后,他高聲對行人說:“大家盡管放心走,左右山上有大批部隊保護隨行,十分安全。”說罷揚鞭而去。人們不聽這番安慰的謊言,只顧隨人流走,把性命交給了老天。
隊伍人多,人和人之間緊挨。我走路步步操心,走快怕踩了前面人的鞋,走慢又怕被后面的人踩了鞋。即使被踩了鞋,也不敢蹲下。鞋子丟了是小事,蹲下就會被踩死,沒了命還要鞋干嘛?
一陣狂風過后,瓢潑大雨緊隨而至,好在是三伏天,大雨澆在行人身上,大家沒覺得冷,反覺得涼爽、舒服。隊形被沖亂了,人們在泥濘水洼里艱難挪步。雨從頭頂順流而下。每個人就像一座小山頭,雨水在人身上流淌,就像小瀑布奔流,行走的隊伍成了移動的瀑布長河,彎曲的泥水大道出現了壯觀的一幕。
傍晚時分,雨停了,但天空還是陰云密布。天黑了,人流進了狹窄的街道,人們都意識到進了村莊了。人流太密,太擠,人挨著人,不管是男是女,都緊緊相挨,擠滿了前后左右。每個人都迷迷糊糊,拖著疲倦的軀體,一步挪二寸。我太困了,感覺自己在睡夢狀態里磨蹭,好像陷進大塊頭人肉堆里,暖和,安全,此外便毫無知覺。
突然,手榴彈爆炸聲響起,喊殺聲連天。我爬起來,發現肩上的面袋子丟了。逃命要緊,人們四散逃跑。臨街有一個高大的麥秸垛,四周鉆了不少男男女女,他們像蚤子,鉆進頭去,卻不管屁股,以為看不見什么,就平安沒事了。我也鉆了,但把頭鉆進去后竟然睡著了。endprint
我醒了后,口渴得要命,進了一個小院,找到一個水缸,卻發現水缸空空如也。房頂上有人喊話,說前面戰事停了,讓大家重新集合歸隊。不管哪個學校的人,男男女女混合,組成臨時縱隊,疾步往前走。瞎子跟上月亮走,你在前,我跟后,擁擁擠擠,人流又流開了。大家在黑咕隆咚的夜晚走了一陣后,被叫停,集中在一個開闊地方。所有人原地蹲下后,縣長尹遵黨喊話說:“剛才有幾個八路民兵搗亂,虛晃一槍跑了,被我們擊潰逃走。大家虛驚一場,稍歇會兒后,我們繼續上山前進,兩山上都有咱們的大部隊保護,咱們放心上山,前邊有向導帶路,大家跟著走,相互照顧,別掉了隊。”
大隊伍繼續出發了,我深一腳淺一腳,緊挨著前面的人,艱難地走著,才走出泥水濕路,又爬進黑乎乎的深山險路。我饑腸轆轆,不知道到底到了什么地方,一天沒吃東西了。所有的人就這樣走著路打著盹,突然不遠處炮彈爆炸了,火光閃亮。大家已經極度疲勞,對這種事情見怪不怪了,只要沒被炸死,仍舊打著盹排著隊往前走。不知走了多少崎嶇的山路,東方亮了,石山斜坡上彎彎曲曲的石子小路依稀可見,遠處一個山口,重機槍“啪啪”有節奏地射擊。前面傳下話來,這個關口要快速沖過,闖過這個險要就好些了。據說這山嶺叫老爺嶺。
關口過了。從山路緩緩下去后,地面開闊了些,大家發現了核桃樹,便爭搶著不顧生熟摘了,狼多肉少,我只摘了一顆,就沒了。一座野廟的墻上,用白灰刷寫著“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不遠處一個塌倒小院的外墻上寫著“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幾個小院空無一人,大家沒找到什么吃的東西,再往前,一條小河邊有幾個菜園,地里有豆角。這群學生,就像餓蝗蟲,撲上前摘了吃生豆角。但這豆角卻少得可憐。
翻過一座高峰,眼前有了點染的綠樹。綠樹雖然不多,卻也激起了大家的饑渴感覺。中午的紅太陽,不顧人們的死活,一個勁地吐火猛曬,毫無人性地烤著已快到死亡線上的人。學生橫七豎八倒臥,遍布山坡。有個人手中拿著一只茶缸,他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吃濕泥。周圍的人太羨慕了,有人取了一塊銀元要買他的這半缸濕泥。他嚇得把茶缸往懷里塞,連忙說:“不賣,不賣……”那買的人又取出幾塊銀元說:“都給你,行行好,只讓俺舔兩口濕泥就行。”這有濕泥的人拔腿就跑,好像有人要他的命,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連濕泥都昂貴無比,要是有杯水,就如擁有了金山似的。
天無絕人之路,高山深溝兩旁竟然有綠樹環繞,溝下竟然有泉水冒出大股流水。大家紛紛在水邊喝水。解了渴后,人人餓得前胸貼后背,大家尋了處緩坡歇了。這些左臂上有“4368”番號的學生,過路人不清楚他們是什么部隊的,好奇他們扛著槍,卻穿著一色的草綠學生服。
山坡上有三個軍人下來了。一個衛兵牽著馬在前,后面一個青年軍官攙護著身穿旗袍的美貌太太,一拐一拐往下走來。他們看見清澈的流水,大喜過望。軍官吩咐警衛把馬拴在路邊樹上,取出隨身帶的鋼金小鍋,讓警衛打了水。接著他們便用三塊石頭支起小鍋,找來殘樹枝打火做飯。我們這些學生眼巴巴瞅著三人吃了頓美餐,肚里的餓蟲造起反來,卻沒有安撫的辦法。這三個吃飽肚子的人一起到水邊洗鍋刷碗了,留下了半袋子白面。我們竟然做賊,把這袋面裝在自己空袋里,仍舊坐回原處,個個精神振作,把槍上了子彈,并插上刺刀,準備和這三個人來一場廝殺。
三個人上來后,這個軍官不見了自己的面袋后大怒,環視現場這些人,但不一會兒,軍官把拿手槍的手緩緩放下,讓衛兵收拾東西趕路。一場禍事就此息滅了。
見那三個人走遠,我們也想做飯,但沒鍋沒盆,咋辦?不知誰喊了一聲:“東北崖頭有個破院,上去找一下。”兩三個同學爬上崖頭,在破院中尋了個底朝天,可什么也沒有。我們撿了個破缸底下來,在缸底上和了面,接著把缸底架在石頭上,在下面生了火,把面做成大餅放在上面,缸底下用大火烘烤,烘烤了半天,餅面稍微干了點,又把餅翻過來再烘烤,我們估計餅子熟得差不多了,便掰開分著吃。
每個人吃了些生面塊,雖然僅一點兒,但總算吃了些。隨后大家啟程趕路,拐了個彎后,又往山坡上爬。我渾身沒勁,拖著千斤重的腿,一顛一顛往前挪。行人中有超過自己往前趕的,也有比自己還慢的,有的干脆坐在路旁山石上歇了。
夜幕里,繁星滿天,那些綴在黑色石板上的大小星星們,忽閃忽閃笑個不停,像是嘲笑這支疲憊不堪的雜亂隊伍。明月如鉤,爬上東邊山頭,已過夜半了,涼意襲來,給人們添了一點精神。
拂曉時分,隊伍到了一座叫白家莊的煤礦。在這里,平遙中學的學生集中起來,每人發了兩個燒餅充饑,也有開水可喝。早飯后,平遙中學的學生坐了兩節運煤的車,去了萬柏嶺車站。那里集中的人多,不僅有中小學生,還有民衛軍。縣長尹遵黨又講話說:“我們到太原了。我們將會看到一場大決戰,中央派來了一個軍,連同山西的守軍,將和共軍進行一場決戰,這場大戰我們將必勝。大家要看看這場戰爭,今天休息,明天共同進城。”
我和幾個同學領到白面后,就近找了個小鋪子,借用鍋灶做飯,大家七手八腳和面,揪揪片兒,面還沒有熟,忽然一聲哨子響,大家緊急集合,沒吃一口飯,便又繼續行進。隊伍在一個村里的廟中停下來,度過黑夜,人人水米沒進。第二天,大家又集中到車站候車,午后來了一列運煤車,眾人紛紛爬上列車。這些被強迫來的男男女女,像牲畜一般,被販運到太原站。
夕陽西下時,隊伍進城,平遙中學學生住在新道街小學,堂弟所在的那個班級另住了一個學校。同學們的每日三餐都是紅高粱面窩頭,沒有任何疏菜副食,同學們在茶缸里盛了醋,蘸著吃。我沒有隨大伙住在一起,在太原的三堂兄將我接到他家。三堂兄是在閻蔣政權糧聯社管糧庫的,我在三哥家每日吃白面大米飯。這種生活水平在當時的太原,是比較高的。和同學們相比,這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別啊。四堂兄家在太原小北門永定路,我三伯母那時也住在這里。所以,堂弟張維玄便住在了四堂兄家。
一天,我去新道街小學,同學轉給了我一封從北平來的航空信。我拆開一看,上面寫著:
敏之兄好,聽說你已抵并,祝平安。去信告兄件大喜事,北平當局為流落北平的中學生成立了“臨中”。咱省為山西臨中,管住管吃。地址為北平市天壇公園內,吾兄見信速來報名。endprint
致禮
學弟李培元
真乃“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狂喜,這不就是公費上學嗎?李培元不僅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學。原來在一起上學時,他善于辭令,常被推為演講大賽的選手。
我積極準備去北平上學,但是有兩大難題擺在面前:一是只能坐飛機,正太線全斷,坐火車已無可能,買機票要出省證;二是飛機票昂貴,每一張飛機票就得法幣6900萬元。
我是初中畢業生,以到北平深造上學的理由來辦出省證很容易。我去了父親結拜兄弟午子天那兒告知去北平的事,此時午子天正在春風厚銀號工作,當即給了我10塊銀元,按市場價,一塊銀元折合740萬法幣,10塊共計7400萬法幣,我買了票,還剩500萬法幣。臨走時,三堂兄也給了我10塊銀元,這樣,我除了買機票的錢,還剩現金7900萬元。
萬事俱備后,我去拜訪了閻錫山政府民營事業督勵委員會的牛先生,牛先生是父親的朋友,臨別時他給了我一床薄被。為防在飛機上發暈嘔吐,我買了點水果。得知南湖村章履卿和兒子金海在北平時,我又記了他們的地址。
飛機緩緩在跑道上滑行了。這時是1948年農歷6月26日中午12點25分。
到了北平后,我扛著行李走著,這時,有一個洋車夫問:“上哪兒?”我說:“紅橋兒前街甲字十三號。”我上了車,洋車夫問:“從哪兒來的?”我答:“東北。”我謊稱東北人,是因為我在太原時已知“東北臨中”在七月五號舉行了大游行,大鬧市參議會,發生了槍擊案后,學生罷課,交通阻斷,洋車夫不敢惹流亡的學生,特別是東北人。車到了前街甲字十三號。我看準門牌是十三號才付了車費。章金海熱情接待了我。飯后,我直奔天壇公園。
從前門大街往南便到了天壇公園門口,東面是一條寬大的油路,兩旁擺滿了各色小吃攤,迎面是一座醬紅色的高大門樓,進進出出的人非常多。男女老少,各式各樣,更多的是胸前戴著“山西省臨中”胸徽的學生。進了大門,有一條通往東面的寬甬道,南北兩邊都是高大粗壯的參天松柏。越往里走,各色奇花異卉越多。經指引,我來到了“山西臨中”報名處,那地方設在圓形臺上宏偉高大的祈年殿里。
我在圓形臺下巧遇了好友李培元。兩個至友相逢,喜不自勝。我們到報名處報了名,領了胸徽。不用辦什么手續,就算入學了。學校領導有“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學生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還有若干委員。其實他們都是學生,是逃亡北平市的中學生,東西兩邊有廳房,都架了前檐,院里到處都掛了被子、床單,給這個圣潔的地方添了些異樣的味道。
“山西臨中”徒有虛名,沒有教師,也不上課。每日為學生供應兩餐玉茭窩頭,燒著鍋爐,所以有開水供應。開始每餐除一個大窩頭外,還有一小碗炒茄子菜,沒過半個月,炒茄子菜沒了,原來是報名入學的人越來越多,供應不上了。
一天,所有流亡北平的平遙學生在地壇圓臺上集中,要成立“流亡北平市平遙學生委員會”,選舉產生了十名委員,我被李培元提名選進了委員會。委員會決定向社會“募捐”,一名委員帶領幾名同學上街到各商店請求救助捐款。我領了五六個同學上街募捐。我們這幾個“叫化子”每到一處商鋪就雙手捧上募捐冊,一進商店門就點頭哈腰討好商家,開口便說:“掌柜您好,生意興隆,多多發財。”那些商店伙計對這些敲竹杠的“叫化子”見多了,應付了一撥,隨后又來一撥,都打著“流亡學生”的旗號募捐。不管多少,他們總得像打發叫化子給一點。想不到讀“圣賢書”的學子竟落魄成“討吃”的叫化子。
“東北臨中”學生率先游行過后,北平市領教了學生的厲害,流亡學生坐電車、公共汽車概不買票,形成一條潛規則。所有流亡北平的學生以及并非流亡的北平學生,只要胸前戴個流亡生的牌子,即可坐車暢通無阻,不花分文。自然,“山西臨中”的學生坐車也不掏錢。
有一天,“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學生委員會”通知開會,我代表平遙分會領導出席。“山西省流亡北平市中學生委員會”的領導人據說是山西省進山中學高三的學生,他說:“山西省閻錫山政府對咱們的困難一點都不關心,沒派人來北平領導,荒廢咱們的學業,咱們生活艱苦他也不關心。現已查明:閻錫山在北平有公館,白面、大米堆積如山,山西駐北平辦事處仍積存有大量白面、大米,我們準備在兩三天內組織同學到這兩地搶白面、大米,大家等待通知。通知下達,大家立即行動去搶。”我會后向平遙的同學做了傳達,準備到時行動。
奇怪的是,通知還沒下達,山西省閻錫山政府已派來一個叫李濟生的官員,他召集“山西臨中”全體學生開會,并會上代表閻錫山說:“閻主席非常同情關心流亡到北平的同學,這是教育廳領導的失職,現在廳長已被撤職,政府派鄙人來任山西臨時中學校長,以便盡快復課。”他當場讓人給每個同學發了一個月餅和半串葡萄,因為已臨中秋,這是表示慰問。
這一變化說明有人暗中給閻錫山政府通了消息,搶白面的事于是泡湯了。
秋涼了,一場秋雨下個不停,寒意襲來,流亡異鄉的人卻沒有御寒衣物,多虧學生都年輕,能耐寒。我只帶了一床牛先生送的薄被,這下頂了大事,我十分感激這位好心先生。
一天,“流亡北平市平遙學生委員會”召集大家,宣布要“采取突擊行動,搶占太廟”,我們一伙學生雇了五輛大卡車,直奔天安門左側的皇家祠堂太廟。五輛車分兩頭,我和一些學生開著兩輛車沖向南門,另外三輛車繞到東門。南門有看門的警察,發現學生開車沖來,便急速關門。但學生人多勢眾,把大門推開沖了進去。警察便急忙要打電話,結果被預先進去埋伏的同學搶了電話。我們到了二進大門前,東門上那一路也勝利沖了進來,兩路學生智取了太廟兩個大門,勝利會師。
這時大家發現只進了太廟外園。外園作為公園,人們可以隨意來游。學生們見二道大門被關閉,門上有“中華民國行政院”貼的封條,并有很粗的鐵鎖。眾學生這時根本不把政府封條放在眼里,用石頭亂砸。一位姓王的同學,找了塊很大的石頭,他個頭大,用猛力把大鐵鎖砸開,眾學生齊力推開大門沖了進去,只見所有大殿及東西配殿都有鐵鎖,也都加了封條。大家正準備把各大殿鐵鎖再砸時,一伙警官手持槍械沖了進來,大喊住手。endprint
這幾個警官模樣的人,恭恭敬敬向同學們立正敬禮,和顏悅色地說:“同學們的困難處境,我們非常同情,我們有個請求,這各大殿里是國家珍藏的國寶級圖書,諸位是知識青年,一定非常愛國,請別砸門窗,一旦門破,不說丟沒丟國寶,光是重新查檢就需要四年之久,諸位不過是為了找避冷住的地方,這里殿前前檐很深,請大家將就在檐里避一下,如諸位不聽我勸,我們也沒辦法,只請派出四五個同學把姓名留下,作為將來檢查登記時的陪查人。”大家應了警官的勸,住在前檐下,沒有再砸大殿。
“山西臨中”流亡北平的同學搶占太廟的消息,第二天上了北平各大報紙,除了華北官辦的報紙外,清一色是一片同情聲援的聲音,贊揚山西流亡同學的這種行為是“反內戰,反饑餓,要吃飯,要讀書”的正當要求、正當行為。華北官辦報紙不敢公開罵學生犯法,只是不支持越規行動。同學們說它是御用文人的“官腔報紙”。至于“反內戰,反饑餓,要讀書,要吃飯”這一口號,則說出了同學們的心里話,符合目前的事實。
十月金秋,是中國人喜慶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獨裁專制的帝制,建立了民國,這一天被定為“國慶日”。)節日的前幾天,北平市便發出通告:鑒于市交通秩序的混亂,決定從10月10日起,全市公共車、電車等一律憑票坐車,任何軍民學生都必須遵守規定購票乘車,違者重處。對此通告,平遙學生們不屑一顧,有大無畏的造反精神,依舊我行我素不買票。
10月10日這天,全市各電車站都有憲兵荷槍實彈站崗,維持秩序。我不敢不買票上街,伙同幾個同學在太廟南大門前觀望,我們看到電車站有憲兵守衛,上下乘客有序,沒發生平常擁擠混亂的現象。誰知沒多久,電車站便發生了驚險一幕。平遙流亡學生中的兩個“勇士”沒買票被車上檢票員查獲,發生斗毆,學生膽大,奮勇跳下車來,向住地奔跑,后面憲兵持槍緊追。我們幾個學生慌忙往里院跑,學生們全進了里院,包括從車上下來的“勇士”。大家只聽得外院響起“啪啪”的槍聲。大伙兒鎮定了,不再跑,也無處跑,都擁在門里不動,太廟二門外來了兩個手中持槍的憲兵,只站在門外往里看,不敢進。眾學生虎視眈眈,如臨大敵,這兵沒一會兒便悄聲退走了。 之后,學生們在外院找到一粒子彈殼,這下有了證據,有了理了,跑到華北剿總告狀,說憲兵開槍鎮壓學生,有彈殼為據,要求懲辦兇手。
華北剿匪總司令是山西人傅作義,有一天派來了一位高級參謀,召集全體平遙流亡學生開會。參謀站在戲臺上,旁邊有衛兵,他首先向學生們敬了個軍禮,說:“傅長官是咱山西老鄉,我也是山西陽高縣人,咱們是同鄉,傅長官很同情同學們,接到報告后哭了,下令立即把開槍的那個憲兵捕了,以軍法處置。傅長官讓鄙人轉告諸位:第一,賠禮道歉,治軍不嚴;第二,請同學們聰明點,千萬不要在別人偷拔了蘿卜的坑上取土,不要沾惹腥味。”
天氣越來越冷了,學生們的生活更苦了,太廟沒開水,這時連涼水也沒有了。兩頓窩頭有車按時送來,可水卻沒有人管,學生們沒轍了,只在院中一個井亭里用繩子吊了茶缸取水,不管水能否飲用。學生裴登成,上吐下瀉,毫無辦法。也有學生就此死了。這些流亡學生就這樣在死亡線上奔跑。
不久,平遙流亡學生被接回天壇公園,安排在地壇下的樹林草地上,搭建了草綠色軍用帳篷,下面鋪了干草墊子,暖和了許多。
深秋季節,天氣越來越冷,形勢越來越緊,東北錦州解放了,山東濟南解放了,華北只剩北平、天津兩地沒有解放,而山西則只剩太原一座孤城,其余各地都解放了。
北平一天天地蕭條,市面上貨物奇缺,法幣和手紙差不多。政府發行了關金券沒幾天,就又貶值了,如今人們拿上關金券也買不到米面,連餅子也買不到,飯店基本關了門。我和同學郭生旺去太廟公園玩,坐在樹林間石頭凳上聊時局形勢,兩人長吁短嘆,非常憂愁。旁邊有個警察獨坐,聽到我倆的談話,也湊過來閑聊。三個人對時局看法相同,認為前途渺茫。忽然,這警察放低聲音悄悄說:“二位,你們學生比我強,有的是好去處。”我好奇地問道:“請問,去哪兒啊?”這警察伸手比畫了個“八”,意思是八路軍。我和郭生旺大驚,說:“八路軍強迫青年背上炸藥炸碉堡,去找不是自送死?”這警察正色道:“俺老家是保定,最近來人說解放區真好,根本沒你們所說的事,解放區歡迎有文化的人參加工作當官。可惜俺沒文化,如果俺是你們二位,立馬投奔共產黨。”我們聽了將信將疑。平遙解放了,買賣人膽子大,依然在平遙和北平之間跑生意。郭生旺接觸了來北平做生意的平遙人,得知平遙解放了,來了解放軍。封閉了近十年的六個城門都放開了,人們可隨意進出城門。閻錫山政府宣傳的“共產黨殺人如割草”全是胡說,共產黨并沒強迫年輕人上前線填炮眼。他們倒是特別歡迎青年學生參加工作當干部。這些消息很快在同學中傳開。
我決定棄暗投明,我和郭生旺決定和做生意的平遙人回鄉。之后,我們經過艱難曲折終于回到了平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