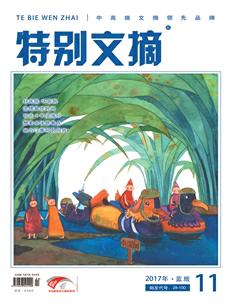火熱的快遞
秦文君
幾個月前,家在紐約的9歲小女孩凱瑟琳隨她母親又一次來到上海。紐約是全球名列前茅的繁華之都,摩登的都市生活凱瑟琳見識過,之前她對上海的建筑、風俗、飯店、生活方式很習慣,沒有驚訝之處。
這次不一樣,凱瑟琳逢人就講,上海厲害,好牛。
讓這個美國小女孩感到驚艷,大開眼界的,竟是快遞行業。
一天,她在上海某大學的校園里兜風,感到有點口渴,隨口說了一句,這時候能吃到西瓜和草莓該多好。陪同她的上海姐姐聽見了,立刻說,這個可以有。只見她在蘋果手機上按了若干下,十分鐘后,一快遞小哥騎著摩托,將洗好的草莓和切好的西瓜送來,手機瀟灑一掃,便可走人。
凱瑟琳覺得好像在夢幻中,目瞪口呆了一會。她一邊吃水果,一邊發出感慨,中國的快遞服務可以神速成這樣,門到門,桌到桌,難以想象地發達。回紐約后,凱瑟琳在選擇課外興趣班時,主動報名學中文,起源是對快遞的折服。
去年夏初,南方的好友給我快遞了兩箱黑葉荔枝,送荔枝的快遞小哥一并扛來,滿頭大汗,汗衫全是濕的。我從沒見過熱成那樣的人,于心不忍,一邊道謝,一邊遞他一瓶礦泉水。
他說:“上海人真會吃,荔枝也快遞,和楊貴妃一樣講究。”
他這么一說,讓我怪不好意思。我在考慮,要不要解釋是好友的一份心意。不料,他手一揮,豪邁地說:“上海人錢多,愛花,是好事。我來上海是享福嗎?求的就是快遞多,多送快跑,死扛到底,錢都落在我的口袋里。”
快遞絕對是兇猛的、高強度的活兒,一個快遞小哥說,他日均送近百件包裹,一大清早從地下室起床,直奔著去取件,一直送到晚上六七點。高溫天氣,中午最熱的時候,他也不會找地方歇口氣,因為這是最佳的投遞時段,大部分人會貓在辦公室躲避暑氣。為了快遞能迅速送達,他一個汗珠摔八瓣,身上曬脫一層皮。
寒冬也不好過,記得一個留著糟糕發型的快遞小哥年關之前來送貨,20來歲的人,凍得縮手縮腳,像上了年紀的人,拼命咳喘。也是這一天,另一個快遞小哥來給鄰居家送貨,鄰居家沒人,電話也不接。他用腳狠踢紙箱,怒發沖冠,安靜的走廊充滿了暴躁和戾氣。我想幫幫他,他說憋屈,這一行太苦,有的人做一陣,受不得苦、輕慢、奚落,就放棄不干了。在最冷或最熱的日子,辭職率更高,留下的人得超額送貨,送遲會被投訴,丟了貨物會被扣錢。我叮囑他把紙箱放在鄰居家門口,擔保不被人順走。他呼啦一聲敬個禮,一下就氣順了。
火熱的“快遞生活”,環保的壓力大,雙十一前后,大垃圾桶爆滿,到處都是直接丟棄的包裝盒子、緩沖泡沫、塑料膠帶,污染與資源浪費讓人驚心。不管怎么樣,快遞是一個窗口,讓我們看到發展與弊病并存,獲得和失去同在。(摘自《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