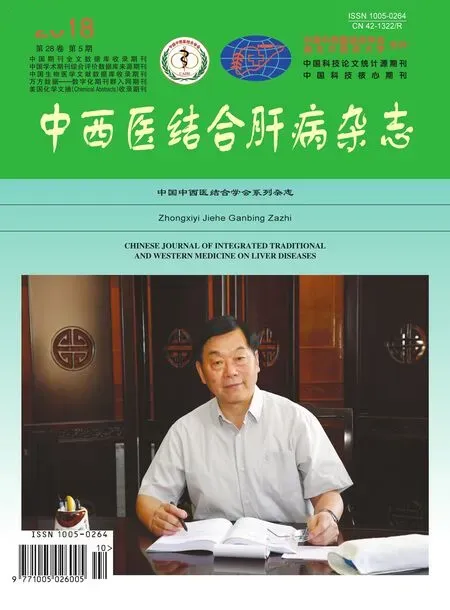中西藥物致肝損傷的臨床特點與診斷方法研究進展*
景 婧 朱 云 宋雪艾 孫永強 王伽伯 肖小河1, 何婷婷 余思邈 許文濤 王麗蘋 王睿林△
1.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院 (北京, 100853);2.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02醫院中西醫結合診療與研究中心;3.全軍中醫藥研究所
近年來,隨著全球藥物性肝損傷(DILI)相關報道逐年增多,其社會關注度不斷提高,藥物安全合理使用倍受重視,DILI臨床研究成為了非感染性肝病研究的熱點之一[1,2]。
中草藥相關肝損傷(HILI)作為DILI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樣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中藥“肝毒性”問題成為了阻礙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發展的桎梏。
本文就HILI與DILI的臨床研究現狀作比較,從流行病學、發病機理、臨床特點及診斷方法等方面綜述如下。
1 流行病學
由于缺乏健康人群大樣本數據的流行病學研究,HILI的發病率在中草藥治療前通常無法獲取。盡管如此,在德國一項小樣本的臨床研究中,只有3人(3/944,0.3%)通過RUCAM評分的因果評估方法被判定為“HILI,可能”,且這3人的谷氨酰氨基轉移酶(GGT)均低于5ULN[3]。一項來自韓國的單中心研究顯示,1196例住院患者中5人(0.43%)被判定為HILI。HILI流行病學數據特別是發病率難以獲取,主要受到基礎人群數據難以統計、醫院HILI病例數量較少及相關部門管理組織存在難度等因素影響。
相較于HILI,DILI的發病率已被多個國家調查獲取。2002年法國Nevers地區統計得出DILI的發病率是(13.9±2.4)/100,000人年[4];2004年英國在臨床全科研究數據庫中統計得出DILI發病率為(2.4±0.4)/100,000人年[5];2005年西班牙的Andrade等學者粗略估計發病率是(34.2±10.7)/1,000,000人年[6];2013年冰島的一組數據顯示當地DILI發病率為(19.1±4.3)/100,000人年[7]。各國DILI發病率不同,考慮主要與各個國家用藥背景、DILI受關注程度、納入病例標準及因果關系評估方法等多方面缺乏統一性有關。盡管各國用藥背景客觀存在、無法改變,但是DILI的關注度可以再提高,其診斷方法還需要更加標準化。
2 DILI發病機制的復雜性
根據發病機制的不同,DILI可分為固有型和特異質型[8,9]。前者發病與藥物劑量相關,用藥劑量甚至超出安全范圍;相反后者發病多不可預測,與藥物服用劑量無關,用藥劑量通常在安全范圍。這種非依賴型肝損傷在DILI中所占比例不可小窺,包括大部分HILI病例[10]。目前,特異質型DILI的發病機理假說很多,如:藥物誘導細胞毒性產生無菌性炎癥,通過抗原遞呈細胞(APCs)和/或輔助性T細胞實現免疫應答等[11]。值得注意的是,藥物致病物質和宿主因素在DILI的作用途徑、易感人群、臨床表型和預后等發病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11]。盡管如此,由于特異質型DILI具備發病率極低、研究對象不可復制等特點,其發病機制難以依靠動物實驗去探索和驗證,這是基礎研究難以深入的瓶頸,也是DILI臨床研究深入發展的優勢。
3 臨床特點
3.1 兩類DILI的構成比情況 不同國家的DILI臨床研究中,中草藥或西藥誘導肝損傷的構成比分布存在差異,這與各個地域的文化特點和用藥習慣差異密切關聯。美國學者歷時10年,對一組899例已在DILIN注冊登記的DILI隊列進行前瞻性研究,發現中藥及相關保健品(HDS)誘發肝損傷的患者比例占16.1%(145/899)[12]。日本學者通過對1676例DILI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得出HILI病例占7.1%[13]。新加坡學者對一組來自當地三級醫院的33例DILI患者進行前瞻性研究,發現了較高的HILI構成比例(55%)[14]。在一項單中心回顧性分析中,韓國學者得出了中草藥(43.2%)、西藥(21.6%)及傳統藥/保健品(35%)三大類藥物相關肝損傷的構成比[15]。中國學者對1985例診斷DILI的住院患者進行單中心、回顧性分析,發現HILI占28.4%(n=563)[1]。
不同國家的HILI構成比差異較大,可能與以下原因有關:第一,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差異影響了當地人的用藥習慣;第二,這些研究設計類型包含了單中心研究和回顧性分析等,臨床證據等級的差異影響了結果的一致性;第三,導致肝損傷的藥物統計方法差異也影響了HILI構成比的不同[1,16]。
3.2 兩類DILI的人口學資料比較 中藥肝損傷病例的年齡分布較化學藥引起的肝損傷差異不大。Navarro等報道的一項839例DILI前瞻性研究顯示,中藥和化學藥導致肝損傷患者的中位年齡是50歲[17]。吳曉寧等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檢索127篇記錄患者年齡的DILI文獻,分析出8528例患者的平均年齡為46.1歲[18]。朱云等回顧性分析了解放軍第302醫院住院治療的1985例DILI病例,比較中藥和化學藥引起的2類肝損傷患者的平均年齡發現無顯著性差異[1]。
中藥或化學藥相關肝損傷患者的性別差異性分布在各項研究中存在不同的結果。吳曉寧等[18]和陳一凡等[19]通過回顧性分析,顯示男性DILI或HILI的發生率高于女性。Chalasani等發現DILI(尤其是肝細胞型DILI)好發于女性[12,20]。個別研究推測這與部分藥物的藥動學、性激素效應差異和免疫反應有關[21]。
3.3 兩類DILI的不同致病藥源分布 致病藥物的不同導致了DILI發病機理存在差異,從而影響了DILI的分型特點、臨床特征,甚至預后。HILI作為DILI的一部分,具備相同的特質:固有型HILI發病比例低,但實驗研究易于深入、操作性強;特異質型HILI占據了較高的比例,但動物實驗可重復性難度大。不飽和吡咯里西啶生物堿(PAs)肝毒性物質與藥物劑量相關,含有PAs的土三七、千里光、石蠶等中藥及保健品被貼上了肝毒性的標簽,其病理表現為肝竇阻塞綜合征(HSOS)[22]。何首烏相關HILI為特異質型肝損傷,其易感物質經過科學假說和實驗研究推測與順式二苯乙烯苷有關,已通過實驗研究在不斷地重復和驗證[23]。
3.4 兩類DILI分型特點比較 根據發病機制、病程、損傷的靶細胞,DILI可分為不同類型。由于不同的發病機制,DILI和HILI分為固有型和特異質型,其中固有型由于存在劑量依賴、潛伏期短、個體差異不顯著等特點,其涉及藥物較為突出但數量少,中、西藥代表藥物的關注度高,相關研究已在開展并深入。一項單中心、大樣本、回顧性分析顯示,對乙酰氨基酚致肝損傷的例數(n=13,0.65%)較土三七(n=4,0.2%)更為多見[1],這可能與臨床適用范圍不同、購置渠道差異等因素有關。根據病程長短,DILI或HILI分為急性和慢性肝損傷,中、西藥致肝損傷病例之間差別不大[1]。根據靶細胞和臨床生化指標的情況,通過計算R值大小,DILI或HILI可分為肝細胞型(R≥5)、膽汁淤積型(R≤2)和混合型(2 3.5 兩類DILI臨床特征比較 無論是中藥還是西藥相關DILI,其潛伏期、臨床表現、生化指標等臨床特征差別不大[18,25]。相比較西藥引起的肝損傷,HILI好發于女性,很少有飲酒史,其罹患率略低,發生肝細胞損傷型肝損傷的比例更高[1]。一項關于中藥與西藥導致急性肝衰竭比較的回顧性分析提示,中藥相關急性肝衰竭患者更易發生腎功能惡化,這可能與中藥多成分、多靶點的特點有關,中藥存在多種物質成分,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更容易發生多臟器功能衰竭[26]。 3.6 兩類DILI危險因素比較 鑒于不同種類的致病藥物存在成分、質量及代謝等差別,中藥和西藥致DILI的影響因素存在不同的特點。除了小部分中藥有明確的肝毒性成分外,大部分被認為是傳統無毒中藥,發生肝損傷的機率極低。由于中藥在生產加工過程中受產地、種植壞境、炮制等多環節因素的影響,除了關注藥物本身成分是否存在肝毒性,還需要高度警惕中藥是否存在同名異物、偽品誤用、不合理炮制、污染變質等情況發生,這些因素均可導致肝損傷事件的發生[16]。除外中草藥因素的影響,HILI還可能與中藥臨床運用的不合理、患者機體免疫狀態差異及中西藥物相互作用導致肝毒性等影響因素有關[16]。 與HILI相反,西藥化學成分明確,藥品質檢標準統一,西藥致肝損傷的危險因素更容易被監測和研究。微觀方面,特異質型DILI的影響因素包括了基因相關因素和非基因相關因素[25]。人白細胞抗原(HLA)基因位點和藥物代謝酶基因多態性等基因相關因素可作為發生DILI的危險因素[27]。除此以外,DILI的危險因素還與藥物的理化物質、毒理物質、宿主因素和壞境因素等非基因相關因素有關,包括了很多分子層面的危險因子,如:親脂性、廣泛代謝和日間大劑量等[11]。宏觀方面,飲酒(飲酒量被定義為男性30g/d、女性20g/d)可作為DILI的危險因素之一。一項來自英國的病例對照研究顯示,飲酒(平均10標準杯紅酒/周)可作為128例DILI患者潛在的危險因素(OR,2.0)。飲酒可增加部分藥物發生肝毒性的機率,如對乙酰氨基酚、氟烷及多種抗結核藥物等[28~30]。基于一些病例的有效性數據分析,年齡≥ 55歲可作為判斷DILI因果關系的評估項目之一[31]。另外,由于高雌激素濃度可降低膽汁淤積門檻,妊娠可作為膽汁淤積型或混合型DILI的危險因素,與肝細胞損傷型DILI無關[31]。 3.7 兩類DILI預后因素比較 無論中藥還是西藥導致的DILI患者均有著良好的結局和預后。盡管急性肝衰竭(ALF)、肝移植、死亡是病情惡化的嚴重結局,但發生機率較低。中藥或西藥導致肝損傷患者的總體結局優于慢性肝臟病[32]。HILI與西藥致DILI相比,兩者在ALF、慢性化、肝移植和死亡等結局因素方面比較差異無顯著性意義[1]。但是,相較于西藥,中藥致ALF更容易誘發肝腎綜合征,考慮與致病中藥成分復雜多樣有關,容易發生多臟器功能障礙[26]。 一項來自韓國的DILI回顧性分析顯示,13.1%的患者預后較差,終末期肝病模型(MELD)評分和血紅蛋白可作為獨立預后因素[33]。基于風險比(HR)評價,一項泰國DILI患者的回顧性研究發現,肝硬化、HIV感染和慢性腎臟病/老年人群(年齡≥60歲)可作為病死率的主要影響因素[34]。一項來自中國DILI患者的單中心、回顧性研究通過單因素分析發現,生化指標(ALT、TBil)、凝血功能(INR)和肝損傷類型可作為DILI的獨立預后因素[1]。一項來自美國32家醫院住院的藥物導致ALF或急性肝損傷臨床研究顯示,HDs膳補充劑比常規藥物引起ALF患者登記肝移植的比例更高[35]。 大約15%~20%的急性DILI患者可能發生慢性化,其進展時間從3個月到3年不等,一般超過6個月進展為慢性DILI[25]。部分慢性DILI患者預后差,可能與膽管消失和膽汁淤積性肝硬化有關。一項來自國內單中心中藥與西藥致肝損傷的比較性分析提示,單一藥物致肝損傷的病例中,中藥以何首烏及其制劑致HILI的例數最多(n=66),約16.7%的患者進展至慢性肝損傷,而西藥以抗生素最為多見,其中阿奇霉素例數最多(n=15),約20%的患者發生慢性化[1]。 4.1 RUCAM評分法 迄今為止,RUCAM評分法因其簡單、方便的特點被廣泛運用于DILI及HILI的診斷,國內外很多臨床研究通過RUCAM評分法對入組病例進行診斷和排除[32]。RUCAM評分法可以較為清楚地判定藥物與肝損傷的因果關系,其中“非常可能”和“很可能”兩種判定結果預示著DILI診斷較為明確和肯定[31]。通過RUCAM評分法判定中、西藥致肝損傷的因果關系,HILI的判定結果以“非常可能”較為常見,而西藥致DILI則以“很可能”較為常見[1]。但是,RUCAM評分由于個別項目評分規定模糊,容易使運用者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差[36]。 4.2 結構化專家觀點程序 自美國DILIN前瞻性研究開展以來,為了尋找一個更為客觀、可靠、重復性強的DILI診斷方法,Don C.Rockey等學者提出了結構化專家觀點程序(SEOP):3位肝病科專家通過因果關系判定的方式對DILI病例進行診斷,最終將各專家的診斷意見匯總并達成“共識”,得出結論性診斷[25,37]。雖然SEOP較RUCAM評分法更易達到較高的診斷一致性和相似度,但由于其操作復雜、步驟繁瑣,在全球中未得到大力推廣。 4.3 整合證據鏈判定法 由于中草藥成分多樣、炮制加工流程復雜及特異性診斷指標不足,HILI診斷更易受臨床經驗主觀因素影響,甚至發生誤診。因此,尋找一種適合HILI的客觀辨識方法,對診斷HILI至關重要,同時將中草藥溯源這一環節加入診斷流程中,對中醫藥產業健康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2016年中華中醫藥學會肝膽病分會發布的HILI指南首次提出“整合證據鏈”的診斷方法,即通過9條判據、3級診斷,精準診斷HILI,為HILI客觀辨識提供了對策,為中藥肝損傷的逐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相比較RUCAM評分法,整合證據鏈判定方法能夠降低HILI/DILI構成比的假陽性病例,達到客觀辨識HILI的效果,更適用于HILI診斷[38]。 綜上所述,無論中藥還是西藥導致肝損傷在流行病學、發病機理、發病特征、預后結局及診斷方法等方面存在共同的特點。雖然DILI包括了HILI,但是由于中藥成分復雜多樣,臨床運用情況特殊,HILI在臨床中也具備自身的特點。因此,HILI的臨床研究不能照搬西藥DILI的研究模式,應該構建符合自身特色的個體化研究策略。 雖然DILI倍受全球關注,HILI患者的發病特征、預后等內在因素被廣泛調查研究,但是仍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難題:尋找診斷DILI或HILI的特異性標志物,探索DILI或HILI的臨床病理特征,篩查特異質DILI或HILI罹患人群的易感因素,確立DILI或HILI特效治療方案。這些難題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科學問題,有待逐一解決,最終服務于臨床工作,服務于廣大患者。4 兩類DILI診斷方法的比較
5 小結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