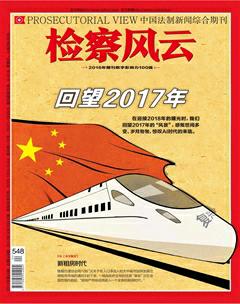滋味
吳秉衡
生活在大都市的好處之一便是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到世界各地美食的不同滋味兒,以至于這充裕的選項偶爾還會造成飲食男女們的選擇困難,引申出一串甜蜜的小糾結、小苦惱,直至一點點的小脾氣,恰如就著春光,篤悠悠地品完一杯意式咖啡后,又含上一粒薄荷糖的感覺。
猶記得,《石頭記》里,“水月庵”中,智能兒向著秦鐘,含嬌帶嗔地輕啟薄唇:“一碗茶也爭,我難道手里有蜜!”這些年,我在別的小說里,橫豎是找不出比那一句更傳神的話來,曹公的筆頭真是絕了!
對此,也許有的讀者會說:“哎呀!文字固然是讓想象安上了翅膀,但怎如影視作品來得形象呢?”這一問,倒真不會教人噎住無語。“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便是回答。各有各的好,何必硬湊著去比較。在這事兒上,一旦較起真兒來,就沒勁了。
不過,既然說到影視作品,我還是想到了黑白片《新舊上海》中所塑造的袁瑞三夫婦。影片中,袁先生因為工廠不景氣而暫時失業,并因此失掉了每天早晨的豆漿,但仍然以“面子”為借口偶爾吃一次最愛的紅燒蹄髈解饞;袁太太雖然常與丈夫斗嘴斗氣,卻還是精心為丈夫準備紅燒蹄髈。當然,袁太太對袁先生的情意,和智能兒對秦鐘的比起來,因是有了歲月的沉淀、時光的熏染,故而全然不同。細細說來,袁太太對袁先生的感情,雖已褪去少女懷春的悸動,卻多了不少對自己、對愛人生命的尊重。
在北地,袁先生嗜好的紅燒蹄髈又叫紅燒肘子,是道名副其實的國民菜品。若誰有質疑,只消勞駕度娘輕挪蓮步,網頁里立馬連篇累牘地跳出許多關于這道菜的制作方法來。有時候自個兒想想,這道普普通通的菜品的普及程度簡直叫人咂舌! 倘若,有哪位有識之士去刨根問底其中原委,想必他是可以印出一本博士論文來。
以前翻看耿寶昌老先生撰寫的《明清瓷器鑒定》一書時,曾經讀到過一種叫做“肘子碗”的瓷器。由于僅僅是在插圖里匆匆一瞥,我對之印象也只是浮光掠影。后來,陰差陽錯地,個人倒也在外埠收入件兒清中期民窯哥釉肘子碗。這方才得了機緣,能近距離好好地欣賞這類瓷器。
個人收到的那只肘子碗,因其釉色系在炒米色的地子上布滿了細碎的文武片,故而古董行里專門有個詞兒稱呼它——“米哥窯”。哥窯,自明代始,便是歸入奇珍異寶之屬,常人難得一見,更遑論日日捧用。但是,到了清代,一個“米”字悄然冠諸其上。于是乎,高冷名物也漸漸得到市井煙火氣的滋潤,有了新的演繹。
有一回,我和一位閱歷豐富的同行前輩聊起了那只肘子碗。在聽完我的介紹后,這位前輩抿了抿杯中的咖啡,幽幽地言道:“你說的這只碗倒有幾分禪意。”
“禪意?”我兩眼一亮:“怎么會上升到禪意的層次了?”“你是因為它的名稱,所以有了先入為主的印象,因此看不見它身上的禪意,”前輩繼續不急不慢地說,“你想想,你剛才都和我介紹了:這只碗的釉水放在前明那會兒,是尊貴的代名詞;可是一到前清,就開始平易近人了。這種角色替換,不就蘊含了某種禪意嘛。”
前輩繼續平緩地說,“禪意這事不好說破,說破就沒意思了。還是跟你打個比方吧,你肯定能頓悟,就一句,聽好嘍:女學霸終究嫁男學渣。咱且不說網絡小說,你先咂摸、咂摸那句話,是不是這個兒道理:無論曾經多么輝煌燦爛,到頭來,百川入海,還是得歲月靜好,歸于生活。生活本身吶,就是件神奇的事情。”
聽完前輩這番話,我心一笑。果然,最走心的滋味還是那普通卻又不平凡的家常菜。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