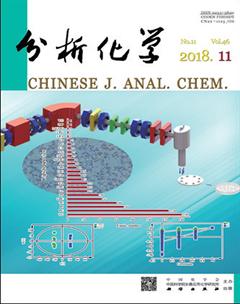利用非天然氨基酸代謝摻入法檢測新生成蛋白
崔秀雲 孫寧寧 謝小娜 孫萬春 趙晴 劉寧
摘 要 以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Raw264.7細胞產生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為模型體系,建立了非天然氨基酸代謝摻入法檢測特定新生成蛋白的方法。通過代謝摻入的方法,使細胞中的蛋白質,特別是新生成的蛋白質一級結構中摻入非天然氨基酸,即帶有疊氮基團的甲硫氨酸類似物(Azidohomoalanine,AHA)。考察了在不同濃度的LPS和FBS,以及不同的刺激時間等條件下,LPS刺激Raw264.7細胞產生TNF-α的實驗參數,確定了最優的實驗條件為: 在含有1%胎牛血清的無甲硫氨酸(Met)的DMEM培養基中,分別在不加LPS和加10 ng/mL的LPS條件下刺激Raw264.7細胞4 h,在刺激細胞的同時摻入AHA。利用Cu+催化的疊氮基團與帶有生物素(Biotin)標簽的炔烴基團的環加成反應,使蛋白質標記上Biotin標簽。利用吸附在固相載體上的抗體特異性捕獲TNF-α分子,再用耦聯辣根過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的鏈霉親和素(Streptavidin)對TNF-α分子上的Biotin進行識別,實現對特定的新生成蛋白質(TNF-α)進行檢測。本方法為檢測特定微量新生成蛋白、表征特定蛋白質的周轉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法。
關鍵詞 新生成蛋白;非天然氨基酸;腫瘤壞死因子α;點擊化學
1 引 言
蛋白質是細胞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幾乎參與所有的生命過程。正常以及病理狀態的細胞,都會通過蛋白質的合成與降解、翻譯后修飾等維持正常細胞生理狀態及快速適應環境變化[1]。因此,對蛋白質進行活體標記,進而研究新生成蛋白質、表征蛋白質的代謝狀況具有重要意義[2,3]。
通過代謝摻入方式,可以利用非天然氨基酸對新生成的蛋白質進行標記。非天然氨基酸是指自然界不存在的、由人工合成的氨基酸,例如帶有疊氮基團的甲硫氨酸類似物(Azidohomoalanine,AHA),它可以在細胞的正常蛋白質合成過程之中摻入到蛋白質的一級結構中,在細胞中無偏愛性,無毒性,也不會引起蛋白的降解[4,5]。當非天然氨基酸成功摻入細胞后,利用Cu+催化的疊氮與炔基的環加成反應(Copper catalyzed azide-alkyne cycloaddition, CuAAC)[6],使細胞中新生成的蛋白質標記上生物素(Biotin)等標簽,進而富集,并利用質譜技術對新生成蛋白進行鑒定[7,8];或者將新生成的蛋白質標記上熒光分子,從而可以利用影像學技術對新生成蛋白在細胞內的分布狀態進行直接觀察[9,10]。
目前,該領域大多數的工作集中在對特定條件下的新生成蛋白進行整體的組學研究,即所研究的對象和目標分子為一組蛋白質混合物(蛋白質組)[7~10]。而對特定目標蛋白分子的新生成情況尚沒有較為成熟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將抗體-抗原反應的特異性與代謝標記方法有機地結合,首先,將非天然氨基酸AHA通過細胞自身的蛋白質合成機制摻入到蛋白質中,使新生成蛋白質上攜帶上Biotin標簽;再利用抗體將特定目標蛋白分子特異性捕獲,采用耦聯辣根過氧化物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的鏈霉親和素對目標蛋白分子上的Biotin進行識別,達到對特定的新生成蛋白質進行檢測的目的。
2 實驗部分
2.1 儀器與試劑
ELx50洗板機(美國BioTek公司);Tecan SUNRISE酶標儀(瑞士Tecan公司);CO2培養箱(美國 Thermo 公司);96孔培養板和24孔培養板(美國Costar公司);AllegraTMX-22R Centrifuge離心機(美國Beckman Coulter公司);Tanon6200 化學發光成像儀(Tanon公司)。
不含甲硫氨酸(Met)的DMEM培養基(DMEM(-),Gibco公司);胎牛血清(FBS, Hyclone公司);青霉素和鏈霉素混合物(PS)、磷酸鹽緩沖液(PBS)(康寧公司);Azidohomoalanine(AHA, 美國AnaSpec公司);BIOTIN alkyne(美國Lumiprobe公司);Tris(3-hydroxypropyltriazolylmethyl)amine(THPTA, 美國Clickchemistrytools公司);Lipopolysaccharide(LPS)、Met(≥99.5%,)、碳酸鹽-碳酸氫鹽緩沖液(Carbonated-bicarbonate),CuSO4(≥99.99%)(美國Sigma-Aldrich公司);蛋白酶抑制劑(Roche 公司);核酸酶(美國GE Healthcare 公司);抗壞血酸鈉(美國ACROS Organics 公司);生物素標記的辣根過氧化物酶(Biotin-HRP, 美國Thermo Scientific公司);鏈霉親和素標記的辣根過氧化物酶(SA-HRP, 美國Invitrogen 公司);抗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抗體、生物素-抗TNF-α抗體、TNF-α標準品、TMB 底物(美國Bioscience公司);ECL化學發光試劑(美國Thermo Scientific公司);Raw264.7細胞購自美國標準生物品收藏中心(ATCC)。
2.2 Raw264.7細胞的培養、非天然氨基酸摻入及LPS刺激實驗
將Raw264.7細胞在含有10% FBS和1% PS的DMEM培養基中培養。當細胞密度達到80%左右時,將細胞鋪到24孔板中,于37℃、5% CO2培養箱中培養過夜,以恢復細胞形態。次日,棄掉24孔板中的培養基,用提前預熱的PBS清洗細胞,然后用DMEM(-)培養基在37℃,5% CO2培養箱中繼續培養細胞1 h。棄掉24孔板中的培養基,用含有不同濃度LPS的DMEM(-)培養基對細胞進行培養,同時摻入4 mmol/L AHA或Met,37℃、5% CO2培養箱中培養4 h或6 h。
2.3 蛋白質提取及點擊化學反應
棄去培養基后,用PBS清洗細胞3次,再用細胞刮子收集細胞至新的離心管中,以500 g離心10 min。 棄上清液,用PBS(含1% SDS)裂解細胞,并加入適量蛋白酶抑制劑和核酸酶。然后將細胞裂解液煮沸10 min,離心,收集上清液。用PBS稀釋10倍后,向樣品中加入適量THPTA、抗壞血酸鈉、CuSO4、Biotin alkyne。高速渦旋混勻后,4℃避光反應過夜[6]。
2.4 ELISA法測定TNF-α
用0.05 mol/L碳酸鹽-碳酸氫鹽緩沖液(pH 9.6)將抗TNF-α抗體稀釋1000倍,加入 96孔板中,每孔100 μL,4℃孵育過夜。棄去孔中的液體后,用含有0.5% Tween-20的PBS(PBST)清洗3次。用含有0.5% BSA和0.1% Tween-20的PBS封閉,室溫孵育1 h。經清洗后,每孔加入100 μL樣品,37℃孵育2 h。棄去上清液,經清洗后,加入適量稀釋的生物素-抗TNF-α抗體,37℃孵育1.5 h。用PBST清洗96孔板3次,每孔加入100 μL經適當稀釋的SA-HRP,37℃孵育1 h。充分清洗96孔板后,每孔加入100 μL TMB底物反應液,37℃避光孵育20 min。每孔加入50 μL 2 mol/L H2SO4終止反應后,在酶標儀上測定450 nm處各孔吸光度。以系列梯度稀釋的TNF-α為標準品,在上述同樣條件下測定,以TNF-α各孔吸光度對其濃度作圖,繪制標準曲線。
2.5 Western blot檢測
將樣品與SDS上樣緩沖液混勻,煮沸10 min,冷卻至室溫,進行SDS-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采用濕轉方法,冰浴條件下將凝膠上的樣品轉移至PVDF膜上。轉膜后,先用含有5% BSA的TBST(50 mmol/L Tris-HCl (pH7.5),150 mmol/L NaCl,0.1% Tween-20)將膜在室溫孵育2 h。清洗后,用適量稀釋的一抗或HRP與膜在4℃孵育過夜。與經適量稀釋的二抗在室溫條件下孵育2 h后,用TBST清洗,經化學發光(CL)成像后分析結果。經SA-HRP孵育過夜的膜,用TBST清洗后,直接采用CL成像,分析結果。
2.6 標記Biotin的TNF-α的檢測
抗體在96孔板上的包被、封閉、清洗及上樣等步驟與2.4 節中的步驟一致,待加完樣品于37℃孵育2 h后,棄去上清液,經清洗,加入適量稀釋的SA-HRP,37℃孵育1 h。充分清洗96孔板后,每孔加入100 μL TMB底物反應液,37℃孵育20 min。每孔加入50 μL 2 mol/L H2SO4終止反應。使用酶標儀測定450 nm處各孔吸收值。同時,以系列梯度稀釋(8×105、1.6×106、3.2×106、6.4×106和1.28×107倍稀釋)的Biotin-HRP(1 mg/mL)為標準品,直接包被,經封閉、清洗后,利用SA-HRP測定各孔450 nm處吸光度,以Biotin的濃度對吸光度作圖,繪制標準曲線。
3 結果與討論
3.1 實驗參數優化及方法建立
Raw264.7細胞是小鼠單核巨噬細胞,在藥物開發、免疫機理、信號通路等研究中應用廣泛。Raw264.7細胞易于培養,且當細胞在外界刺激(病原體入侵或者藥物刺激)下,能夠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如白介素-1β、白介素-6、TNF-α等[11~13]。本研究以LPS刺激Raw264.7細胞產生TNF-α[14~16]為體系,對實驗條件進行了優化,首先考察了LPS濃度、LPS的處理時間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由于AHA與Met相互競爭摻入蛋白分子,為了最大程度提高AHA代謝摻入的效率,必須盡量減少培養基中所含有的Met。因此,本研究共使用了3種不同的培養基,分別為不含Met的DMEM培養基(DMEM(-))、含Met 的DMEM培養基(DMEM(+))、含AHA的DMEM培養基(DMEM(*))。初步研究結果表明,LPS刺激Raw264.7的最佳時間是6 h, 能夠產生最大濃度的TNF-α。而通常利用AHA代謝摻入的時間在2~4 h時,已經足以檢測到標記蛋白產物,而摻入時間過長有可能會對細胞的正常生理過程產生影響,因此在不添加FBS的情況下,分別用DMEM(-)、DMEM(+)和DMEM(*)培養Raw264.7細胞,同時加入不同濃度的LPS,分別培養4 h和6 h后,收集上清液,ELISA法檢測上清液中的TNF-α濃度。
如圖1所示,當用DMEM(-)培養基時,LPS刺激細胞后所產生的TNF-α濃度都比較低,且刺激6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比刺激4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低,說明培養基中不含有Met或者Met類似物時,對細胞的生理活性影響很大,且時間越長,影響越大。當摻入Met時,LPS刺激細胞4 h和6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很高,且趨勢相似,說明摻入Met的DMEM培養基對細胞的生理活性影響很小,且不隨時間長短發生變化。當摻入AHA時,LPS刺激細胞所產生的TNF-α濃度也比較低,且刺激6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低于刺激4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說明AHA對細胞的生理活性有一定的影響,且時間越長,影響越大。因此,本研究選擇LPS刺激的時間為4 h。
考察了LPS在1% FBS時刺激Raw264.7細胞4 h所產生的TNF-α濃度。當DMEM(-)培養基中含有1%血清時,用不同濃度的LPS刺激Raw-264.7細胞4 h,同時摻入Met或AHA。收集上清液,ELISA法檢測上清液中的TNF-α濃度,結果如表1所示。當不加LPS時,細胞所產生的TNF-α本底濃度很低,隨LPS濃度升高,TNF-α濃度顯著升高;當LPS濃度高于10 ng/mL時,摻入AHA的細胞經LPS刺激后所產生的TNF-α濃度有所下降。綜合以上結果,確定最優的實驗條件為: 在含有1%胎牛血清DMEM(-)培養基中,分別在不加LPS和加10 ng/mL的LPS條件下刺激Raw264.7細胞4 h,在刺激細胞的同時摻入AHA。
3.2 在LPS刺激下Raw264.7細胞新生成蛋白質的檢測
在24孔板里對所選取的4組樣品進行細胞裂解,將所得的細胞裂解液轉移至新的1.5 mL離心管中,離心后收集上清液,吸取600 μL進行點擊化學反應,使新生成的蛋白質被標記上生物素。
將樣品用0.05 mol/L碳酸鹽-碳酸氫鹽緩沖液(pH 9.6)稀釋到合適濃度后,4℃孵育過夜。利用生物素與親和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使SA-HRP對新生成蛋白質上連接的Biotin進行識別,從而間接地指示新生成蛋白質的濃度(以Biotin濃度表示,圖2A)。同時,用Western blot法對所得結果進行驗證(圖2B)。摻入AHA的兩組樣品,測得的Biotin濃度明顯高于摻入Met的兩組樣品測得的Biotin濃度。Western blot結果表明,摻入AHA的兩組樣品通過HRP檢測的結果為陽性,而摻入Met的兩組樣品的結果為陰性, 說明細胞中成功地摻入了AHA,且新生成蛋白質上成功地標記上了Biotin。然而,天然氨基酸Met分子由于沒有疊氮基團,無法與Biotin-alkyne發生點擊化學反應,因此新生成蛋白質無法標記上生物素。由圖2可見,在摻入AHA的兩組樣品中,4號樣品中的Biotin標記蛋白信號高于3號樣品,說明細胞在LPS刺激下有更多的AHA分子被摻入到蛋白質中,產生了更多的新生成蛋白。
3.3 Raw264.7細胞在LPS刺激下新生成TNF-α蛋白的檢測
利用抗體-抗原反應的特異性,用抗TNF-α抗體特異性捕獲細胞裂解液中的TNF-α,再用SA-HRP對TNF-α上連接的Biotin進行識別,從而間接地反映新生成TNF-α的濃度(以Biotin濃度表示,圖3B);同時,以系列梯度稀釋的Biotin-HRP為標準品,利用SA-HRP測定各孔在450 nm的吸光度,以Biotin的濃度對吸光度作圖,繪制標準曲線(圖3A)。根據標準曲線計算,分別得出4組樣品中TNF-α的相對含量,發現LPS濃度為10 ng/mL時刺激細胞4 h后新生成的TNF-α的相對量為28.37 pmol/L。當LPS摻入濃度為0時,測得的新生成TNF-α濃度為12.11 pmol/L,高于摻入Met的兩組,可能是因為AHA摻入時間較長,刺激細胞產生了額外的TNF-α。
4 結 論
以LPS刺激Raw264.7細胞產生TNF-α為體系,通過代謝摻入AHA ,并利用點擊化學反應,使細胞中新生成的蛋白質標記上生物素標簽。再利用吸附在固相載體上的抗體將TNF-α分子特異性捕獲,達到對特定的新生成蛋白質(TNF-α)進行檢測的目的。本研究為檢測特定微量新生成蛋白、表征特定蛋白質的周轉等方面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
References
1 Zhang T, Shen S, Qu J, Ghaemmaghami S. Cell Rep., 2016, 14(10): 2426-2439
2 Welle K A, Zhang T, Hryhorenko J R, Shen S, Qu J, Ghaemmaghami S. Mol. Cell. Proteomics, 2016, 15(12): 3551-3563
3 Stastna M, Gottlieb R A, Van Eyk J E. Expert Rev. Proteomics, 2017: 1-15
4 Hinz F I, Dieterich DC, Tirrell D A, Schuman E M. ACS Chem. Neurosci., 2012, 3(1): 40-49
5 Dieterich D C, Link A J, Graumann J, Tirrell D A, Schuman E M.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6, 103(25): 9482-9487
6 Kolb H C, Finn M G, Sharpless K B. Angew. Chem. Int. Edit., 2001, 40(11): 2004-2021
7 Glenn W S, Stone S E, Ho S H, Sweredoski M J, Moradian A, Hess S, Bailey-Serres J, Tirrell D A. Plant Physiol., 2017, 173(3): 1543-1553
8 Zhang J, Wang J, Lee Y M, Lim TK, Lin Q, Shen H M. Methods Enzymol., 2017, 588: 41-59
9 Beatty K E, Tirrell D A. Bioorg. Med. Chem. Lett., 2008, 18(22): 5995-5999
10 Hatzenpichler R, Scheller S, Tavormina P L, Babin B M, Tirrell D A, Orphan V J. Environ. Microbiol., 2014, 16(8): 2568-2590
11 Li X,Shen J, Jiang Y, Shen T, You L, Sun X, Xu X, Hu W, Wu H, Wang G. Int. J. Mol. Sci., 2016, 17(11): E1938
12 Hossen M J, Yang W S, Kim D, Aravinthan A, Kim J H, Cho J Y. Sci. Rep., 2017, 7: 42995
13 Lakshmikanth C L, Jacob S P, Kudva A K, Latchoumycandane C, Yashaswini P S, Sumanth M S, Goncalves-de-Albuquerque C F, Silva A R, Singh S A, Castro-Faria-Neto H C, Prabhu S K, McIntyre T M, Marathe G K. Sci. Rep., 2016, 6: 34666
14 Corriveau C C, Danner R L. Infect. Agents Dis., 1993, 2(1): 35-43
15 Kubes P, McCafferty D M. Am. J. Med., 2000, 109(2): 150-158
16 Watson W H, Zhao Y, Chawla R K. Biochem. J., 1999, 342: 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