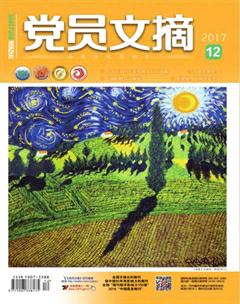哈佛八博士后“集體歸國”:看得見未來,也看得見自己定位
邱晨輝
祖國就是一個強磁場,對這個國家沒信心的人,是不會選擇主動回國的。
即便是在經歷最大“海歸潮”的當下中國,這也是一個罕見的歸國故事。
故事主角是八名青年科學家。
八人都曾在美國打拼十幾年,因為在哈佛大學“同一個樓道”里共事,而有了命運軌跡的第一次交集。爾后,一人率先離職回國,觸發連鎖效應,另外七人接連離職回到中國,命運軌跡再次交織。這一次,他們找到“共同事業”。
在講究團隊合作的大科學時代背景下,這種“集體式的回歸”顯得彌足可貴。
那么多年過去終于不用再“漂”了
王俊峰是觸發連鎖效應的第一人。但他不想“拔高”這次選擇:“所謂放棄國外的優厚生活——那不是真實的情況。”
20多年前,王俊峰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后,開始到美國闖蕩,2004年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生化與分子藥理學系從事核磁結構生物學的博士后研究,科研事業可謂風生水起。
搞科研的人經常稱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探索未知”,這需要他們練就一個很強的本領,就是“看得見未來”,至少“看得見未來的方向”。王俊峰覺得看見了自己在美國的“未來”——上面有一層觸手可及的“天花板”。
一來,沒有屬于自己的大科學裝置平臺;二來,沒有如今這么兵強馬壯的作戰大團隊,他很難想象在美國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樣。
14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王俊峰來到合肥科學島,見到了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匡光力,這是被他們八人稱作“不像領導的領導”——沒有官腔,惜才,實干。
王俊峰至今還記得,當時匡光力非常興奮和激動,向他介紹了強磁場科學中心的規劃,那時強磁場中心剛起步,相當于一張白紙,渴望優秀的人才加盟。而對王俊峰來說,面前似乎展開了一張巨大的科研藍圖,這是他在美國從未見到過的樣子——“一個屬于‘未來的樣子”。
王俊峰再清楚不過強磁場裝置的意義:強磁場與極低溫、超高壓一樣,可為科學研究提供極端實驗環境,是科學探索的“國之重器”。自1913年以來,19項與磁場有關的成果獲得諾貝爾獎。一旦屬于中國的40特斯拉的穩態強磁場建成,將躋身世界一流。
探索未知的敏銳嗅覺很快上線,王俊峰心動了。
這一年是2009年,距離穩態強磁場實驗裝置落戶科學島還不足一年。
王俊峰老家在山西,讀大學是在北京,后來去美國深造,也換了幾個城市,待的時間長則六七年,少則三四年。他說:“這么多年過去,我很難對自己的身份有一個準確定位。”這種感覺就是“漂泊”,他說自己以前一直在“漂”。
如今回國已八載,他既看得見強磁場建成世界最高水平的未來,也看得見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中國強磁場人——這種身份,讓他感到踏實。
后來,在和另一歸國青年交流中,王俊峰說了這樣的話:“祖國就是一個強磁場,對這個國家沒信心的人,是不會選擇主動回國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的發展勢不可擋。”
夫妻還家一起干事業
“王俊峰回去了!”還在哈佛的劉青松聽到這個消息后,有些按捺不住了,對他這個一直在尋找回國機會的人來說,“身邊的人回國”就像一塊巨石投入湖中,比任何名人效應的沖擊都要大。
在王俊峰回國的第二年,32歲的劉青松就飛到合肥科學島“考察”。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島上的美:郁郁蔥蔥,四面環水,環境怡人,在那之前,劉青松從未到過合肥,也從未考慮把這個地方當作“歸處”。
但看到眼前的一切,他開始有了一絲好感:這里美得“好安靜”。
那是2010年,匡光力接待了他。匡光力的一句話打動了他:“青松,你今年也是32歲,我32歲的時候,剛從德國學成回來,就是來到這里,抱著創業的決心,為科學島打開了新的天地。”
劉青松出了門,就給妻子劉靜去了電話,電話里劉靜沒有任何反對。她相信他的選擇。
多年過去,八個人在一起聊當年的情形,他們中很多人對劉青松的回來并不意外,但對劉靜毫不猶豫的同意卻吃了一驚。
劉青松在美國的華人朋友多是如此:男性喜歡“在自己地盤”做事業,往往希望回到國內,而女性則會考慮更多生活層面的問題,舒適度、孩子上學等等。
在看到丈夫劉青松描繪的藍圖之后,劉靜卻放下這一切,決定支持他,也給她自己的科研事業一個新的開始。
王文超、張欣是八人中另外一對夫婦,不過相比劉青松、劉靜夫婦的選擇,他們的回國之路就顯得慎重許多。
在美國,他們的女兒和兒子相繼出生,生活穩定,科研順利。張欣說,當時女兒7歲了,已經完全融入了周邊的環境,回國面臨很多考驗。
張欣至今記得,一天中午,劉青松在午飯時向她和丈夫發出了邀請:“我回國后希望組建一個團隊,需要做細胞生物學的,你和文超可否考慮下?”
張欣并沒有立即答應。最終讓這對夫婦下定決心的,是一次偶然的聚會。
張欣帶女兒參加孩子小學舉辦的“國際日”活動,每個孩子都要拿自己國家的國旗,但在當時,她的女兒連五星紅旗是哪一面都不知道,這深深地刺痛了張欣的心:“孩子已經完全西化,我們跟她說中文,她回答的卻是英文。”
2012年,他們結束了哈佛醫學院的課題,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了科學島。
一條完整的研究鏈蓄勢待發
八人中,還有三位是張鈉、林文楚和任濤,相比之下,他們作出選擇的過程則要干脆一些。
張鈉是北京人,從1996年到2012年,16年的時間里他也有了屬于自己的生活習慣,去酒吧找朋友聊天、每周打三次網球等。
有一次,幾個美國人在酒吧討論競選,張鈉側耳聽后發現,一些政客為了競選,會刻意貶低中國,“我很不高興,身為中國人不能容忍有人不分青紅皂白抹黑中國,我會跟他們辯論。”但那是別人的地盤,這次辯完了還有下一次。在外時間越久,張鈉越想回國。
林文楚是為了一個“獨立實驗室”的夢想回來的:“這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基本是給別人打工。”
任濤則一直從事藥物的高通量篩選,在劉青松的邀請下,基于“對老朋友的信任”,以及“想回國為中國人的新藥創制做點事情”,也回來了。
至此,八位哈佛博士后悉數回來,一條依托強磁場大科學裝置與技術,開展以重大疾病為導向的多學科交叉研究網絡的“學術鏈”完成組合——
王俊峰、張鈉研究結構生物學;張欣研究磁生物效應;林文楚研究動物模型;劉青松、劉靜、王文超、任濤則研究腫瘤藥物。
“這正好是從最基礎的理論研究到可以直接制藥的應用研究,是一條完整的研究鏈條。”王俊峰說,這是他們在美國夢寐以求想要達到的一種團隊組合。如今,實現了。
“萬人計劃”領軍人才、“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青年千人計劃”、中科院“百人計劃”、安徽省“百人計劃”……這些國家、地方的人才政策,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必為資金、項目或者人員操心。
今年2月,中科院強磁場科學中心混合磁體工藝通過國家驗收,40特斯拉穩態強磁場,磁場強度居世界第二。匡光力說,八年間,中心從“一無所有”成長為“世界第二”,實現了從“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這背后,人才的力量不可小覷。
(邱寶珊薦自2017年9月21日《青年參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