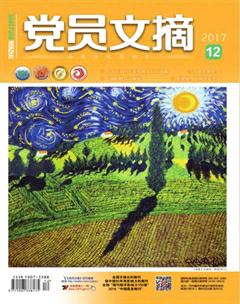院落春秋
雪小禪
院落兩個字很中國。仿佛五千年的歷史中,落腳點就是應該有個院落的。
唯美的中國元素,一定要有院落:凄清的早春,推開厚重的門,有雞有鵝有花有鳥;房前種花,房后種菜。
院落承擔著一種心思。是踏實,是肯定,也是溫暖。
電影《愛有來生》中,女主人一進那個院落,看到老房子和銀杏樹時,她安靜地發了呆。她說:“我再也不想走了。”
南方院落更精致。門口永遠是狹窄的。小到以為是小門小戶。進去之后卻是別有洞天。以蘇州留園、同里退思園、胡雪巖故居為例,都是如此。
徽州院落有陰氣,卻懷了別樣的情調。也是粉墻黛瓦,卻和江南的院落有不同。馬頭墻和四水歸堂的天井里,總把思緒壓到最底。
北方院落有天方地闊的開朗。不明媚,但鄭重其事。從正門就開始壯闊起來。里面好壞先不說,門一定要氣派。門樓建得越高,仿佛底氣越足。這是南北差別。
北京四合院,其實也是北方人的夢想——團團圍緊了,密不透風。四面都有院落,心里可真踏實。透過窗,可以觀察春夏秋冬,也可以看人間冷暖。
我更傾向于南方的院落,一進一進的。很遞進,很深入,很私密。北方的院落之開闊,豪無隱私可言。
如果住到三進之后的南方院落里,會是什么樣的幽然思緒?
忽然想起林黛玉。姑蘇女子,怎么能忍這早春的寒?梅才開了,一夜風雨又落了。北方的花必然是開盛了才落。可姑蘇的花,來不及盛開,一場早春冷雨,紛紛落了個繽紛。在院落里,她如何葬花?如何悲泣?如何與蝴蝶低語?
院落里的時間是流動的。從你的身上流到他的身上。留園幾易其主,仍然保持著院落的美——詩意,典雅,黯然銷魂。玉蘭依然優雅地開著。揖峰軒依然清幽寧靜,西窗下琴弦低轉暗流。五峰仙館似有舊人知已在品茗觀戲。只有院落有這樣的雅意,看似封閉,實則開闊——很符合中國人做人的方式,外圓內方,外化而內不化。
在“還我讀書齋”讀一會宋詞,時光就這樣淡然流走。時光是慢的,甚至是多余的。那些梅花開得也正好,映在粉墻上,有一種說不出的頹艷。遠處有人在唱戲,緩慢的聲音像是在澆花似的。流到院落里四處都是,又被水吸走了。
中國人還習慣了在心里建一個院落。自己住著,房門鎖得很緊,不會輕易打開,也不會讓人四處打探這個院落。也許有人會走進第一進門。可是,走進第二進門的人就少了,第三進門就更少了。到最后一進,根本就沒人了。自己也不行。自己最不了解自己。
院落是個多么深幽的意象。鑲嵌在光陰里,什么都老了。光陰也老了,院落也老了,把自己最后一道門的鑰匙捏得緊緊的。前廳是這樣的:繁花似錦,或者,芳草萋萋。最深的那個院落,緊緊地閉著,生怕被打開。怕嚇到誰,首先怕嚇到自己。
“彼美淑姬,可與唔歌。”詩經中《東門之池》曾經這樣贊美著。誰能懂得誰?誰都有一個自己的院落,或者獨住,或者呼朋喚友。
我喜歡獨住。在蘇州,早春二月,來寫作。住在明涵堂的院落里,幾百年的老房子,院子中只有我一個人。院內有芭蕉、木椅、竹、鐵線蕨……
下雨的黃昏,我總是坐在二進門的老椅子上發呆,手邊一本翻舊的書,桌上一杯快涼的茶。
我住的屋子鋪滿了青磚。青磚散發出的氣息,很舊,很涼,味道久遠。像一個故人,很體己的樣子。
還有不停路過的旅游團隊。出門左轉是一條青石板小巷,十多米右轉就是七里山塘老街。那些游人是來看這條老街的,完全被商業化的老街。我總是到老街的對面去。對面是蘇州的日常人家,仿佛還是明清時代,居然還有以貨易貨的。
旅社的老板幾次說給我調房間。我說,不了。我喜歡這一個人的院落。
守著幾百年的光陰,在黑的夜里,聽著雨打芭蕉,獨自沉溺于這種孤寂的幽靜……就這樣平靜了,就這樣收斂了光芒,和院落一起沉溺于平淡。
(摘自《記者觀察》2017年第9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