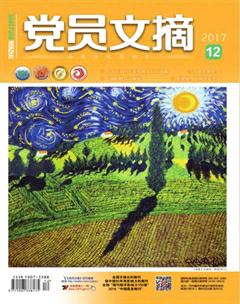解讀中國義利觀
徐秀軍
“海岳尚可傾,口諾終不移。”自古以來,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信義一直都備受推崇,小至安身立命,大到邦交之禮。幾十年來,從對外援助到堅守《巴黎協定》承諾,再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正在以實際行動踐行“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大國義利觀。
以義為先
以義為先是中國倡導的正確義利觀的特色,也是中國外交長期恪守的基本信念。在處理自身發展與世界共同發展的關系上,中國不只顧自身發展,還將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對貧窮國家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自1950年中國實施第一個對外援助項目以來,中國不斷加大對外發展援助。中國致力于消除本國貧困的同時,積極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
根據2016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各類人員1200多萬人次,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先后7次宣布無條件免除重債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到期政府無息貸款債務,向69個國家提供醫療援助,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提供幫助。
從20世紀70年代的坦贊鐵路,到2016年建成通車的亞吉鐵路,都是中國踐行以義為先的國際主義精神的重要見證。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克服困難,堅持維護貨幣和經濟穩定,為有關國家和地區應對危機提供了寶貴支持,在推動世界經濟的復蘇與增長上發揮了積極作用。2008年以來,中國連續多年成為最不發達國家第一大出口市場,吸收最不發達國家約23%的產品出口,推動了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與發展。
同時,在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經驗的基礎上,中國明確提出并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解決全球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借鑒。
根據2016年1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發展權:中國的理念、實踐與貢獻》白皮書,未來5年中國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6個100”項目支持,包括100個減貧項目,100個農業合作項目,100個促貿援助項目,100個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100所醫院和診所,100所學校和職業培訓中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2萬個來華培訓和15萬個獎學金名額,為發展中國家培養50萬名職業技術人員;設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200萬美元的現匯援助。中國的這些行動和承諾,既是為正確義利觀提供了有力詮釋,更是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理念和風范。
義利并舉
在國際交往中,義利相兼是實現合作共贏的基本要求。所謂義利并舉,放在國際關系上,反映的是利益與責任兼顧,權利與義務相一致。
當前,一些國家的政策調整以鄰為壑,保護主義和內顧傾向不斷加重,一味追求權利和利益,盡力逃避國際責任和義務。從短期來看,這些政策以損害他國利益增進了自身利益;但從長期來看,這些政策必將引發其他國家針鋒相對的政策調整,并由此形成不公平競爭甚至是相互敵對的國際關系氛圍,最后大家都是輸家。
在處理對外關系中,中國政府一貫主張通過合作、協調與對話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積極參與和推動雙邊、區域和全球多邊合作進程。從根本上講,合作的目的在于實現互利共贏,這是中國參與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在合作的過程中,要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讓所有參與方都能夠公平合理地分享到付出努力帶來的收益。
在國家發展和全球治理領域,各國目標和重點不盡相同,但只有將全體人民和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發展和合作才能擁有可持續性,并由此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
破解全球困局
2017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這些挑戰之所以形成并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全球主要國家扭曲的義利觀,重利輕義,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拋棄信義、情義、正義和道義。
在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中,中國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堅定支持者和重要貢獻者。自1990年4月中國軍隊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中國已累計派出維和軍事人員3.5萬余人次,先后參加了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中國是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中國的維和攤款出資額居世界第二位。
同時,中國積極支持和落實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發展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是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使貧困人口比例減半的國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的發展成就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并為全球發展提供了可復制的中國方案。
在全球治理上,中國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并已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在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上,為了應對全球挑戰和促進國際合作,中國貢獻了新的方案,并推動世界主要國家達成共識。中國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不僅是對當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的有力回應,更重要的是為應對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摘自《環球》2017年第19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