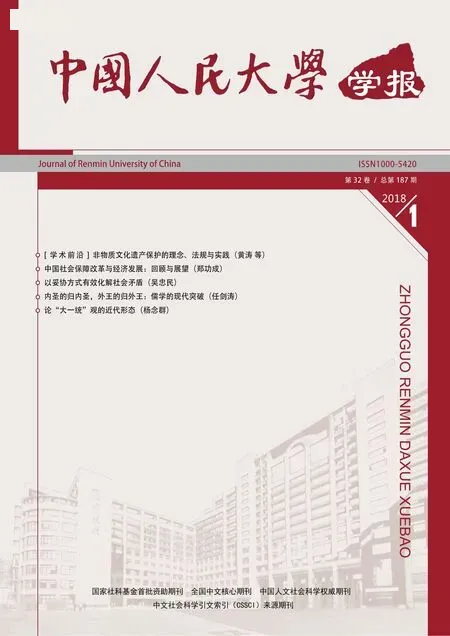技術發展的歷史分期與“后現代技術”
——從技術與科學的關系看
王耀德 譚長國 王忠誠
對技術發展進行歷史分期,其角度、依據和方式多樣。但一般而言,有一個共同的劃分點,即古代與現代的分野。“現代技術”的形成,標志著技術品性的根本性變化。盡管并非所有學者都直接使用“現代技術”一詞,但他們一般都會劃分出一個與之相近或對應的發展階段,例如,馬克思所指的“蒸汽磨”或“機器磨”時期、奧特加·伊·加西特所指的“工程科學”的技術時期。“現代技術”一般也就是與科學相結合的技術。在海德格爾的技術分期中,不僅現代技術與科學相結合,而且現代科學本身也就是“技術的”、“來源于技術之本質”*Heidegger.“Gesamtausgabe 77: Feldweg Gespr?che”.1982.In B.W.Davis(Trans.). Country Path Conversation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116.。
“現代”之前的技術,一般被稱為古代技術或“前現代技術”。古代技術史還可以細分出若干階段,“現代”之后的技術發展亦然。但是,現代技術既然已經是“形而上學之完滿實現”*Heidegger.“Overcoming Metaphysics”.In Richard Wollin (ed.).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p.75.,“現代”之后的技術發展,何以還能再進行歷史階段劃分,例如再細分出現代、當代甚或“后現代”?
本文以技術與科學的關系為線索,來考察技術發展在現代之前和現代之后的細分。之所以從科技關系來考察這個論題,是因為技術的“前現代”、現代、當代等特征都能在它與科學的關系中找到依據或得到表述,并且技術是否存在“后現代轉向”,也有必要把科技關系與“后現代科學”相關觀點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一、古代或前現代的技術史的分期
現代以前,技術以較為“純粹”的方式存在和發展,既非“工業化的”,也非“科學化的”:技術的存在和發展并不依托“機器大工業”,且沒有普遍地與科學相結合,技術活動也沒有與科學活動進行制度化的互動。
本文并不詳細探討對古代技術發展的各類具體分期原則以及方法,而是力圖說明:第一,古代技術的不同發展階段之間,其差異或變化也是巨大的;第二,在造成所謂人與技術、技術與自然的“對立關系”方面,古代技術并非例外,至少,古代技術緩慢地、不斷地朝著這種對立關系發展。
對古代技術發展的分期,可以有很多方法,既可以從技術的自然屬性,也可以從它的社會屬性,例如以它所對應的社會經濟形態來進行分期,而且這些分期都顯示了技術的顯著變化。例如前者(從技術的自然屬性來看),人類社會的古代,可以根據技術制品所使用的材料類型細分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馬克思則以“磨”的發展形式細分出“風磨”時代與“水磨”時代、“蒸汽磨”或“機器磨”時期。從技術或其活動的社會屬性來看,奧特加·伊·加西特將古代細分出“機會技術時代”與“工匠技術時代”*拉普:《技術哲學導論》,73頁,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6。;蘇聯學者庫津(А.А.Кузии)等人則把古代技術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1)社會生產形成及其發展第一階段的技術(遠古—公元前 4000年); (2)手工業生產產生及形成期的技術(公元前4000—公元500年); (3)發達手工業生產期的技術(5—15世紀); (4)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技術(15—18世紀)。*姜振寰:《技術的歷史分期:原則與方案》,載《自然科學史研究》, 2008(1)。而這四個時期不僅技術本身,而且和技術相關的生產方式也有著巨大的變化。
既然古代技術的共同特征就是基本不包含對科學的運用,那么古代技術的分期與科學的發展沒有直接關聯。與科學的結合給技術帶來深刻的變化,與科學尚未結合時的古代技術自身的變化也很深刻,以至于從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從青銅時代到石器時代可以被看成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這似乎表明,技術相對于科學而言,具有更久遠的歷史。如同現象學哲學所揭示的那樣,技術是人的“在世方式”, 具有更深刻的本質,而且這本質上是人的生存論意義上的,是人作為“此在”與世內的存在者打交道,即“煩忙”。打交道首先就是要“操作”,而“認識”是次要的。
在海德格爾看來,古代技術與現代技術的區別在于,它保持了“物之為物的完整性”,技術物向人展示的是物性的“帶出”(進一步說,是“順應性”地帶出);而現代技術是對自然的“逼索”,即挑釁、強求、促逼,等等。由于這種逼索是現代技術所獨有的,因此只能認為它們是在技術與科學的結合中達到的。但是,在近代科學誕生以前,從“物性”的“順應性帶出”到“逼索”之間似乎具有一條連續的譜線,因為我們很難說青銅、鐵器等金屬物的制造絲毫不帶有“逼索”的性質。實際上,不僅金屬制品產生于“古代”,“逼索”自然的蒸汽機在其早期與近代科學幾乎沒有什么關聯,只是在瓦特時代才可能用到熱力學中的“潛熱”理論,而且瓦特是否有意識地利用這種理論,科技史界還存在爭議。這很可能說明,對自然物的“逼索”并不是在技術與科學相結合以后才開始發生的。
而且,不管技術對自然物是否“逼索”,古代技術及其關聯的生產活動照樣可以形成人對自然的破壞:農牧社會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耕地擴張、濫采濫伐、過度放牧、植被破壞、水土流失,也對自然資源造成過嚴重破壞。
二、近代以后技術史的分期:現代與當代
在(近代)科學尚未正式誕生的情況下,古代技術能緩慢地進化并累積成巨大的發展,似乎切合喬治·巴薩拉的觀點,即“技術和技術發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學知識”*喬治·巴薩拉:《技術發展簡史》,3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巴薩拉的這種觀點不僅僅針對古代,而是針對整個技術史。德紹爾也把技術的本質放在“第四域”以圖澄清和確定技術的獨立地位。但是,技術落入科學的視野,以及科學從自然哲學變成特定的經驗知識體系甚至“理論技術”,就是“近現代時代”的特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技術與科學的結合使技術失去了其鮮明的獨立性。
工業社會以來,技術一般被稱為“現代技術”。人們普遍認為,18 世紀產業革命和蒸汽機的改進和廣泛使用是現代技術的起點。這個“現代”至今已歷兩百多年,技術發展日新月異,肯定會呈現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完全可以進行階段劃分。但是,劃分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所劃分的若干階段總體上仍屬于“現代技術”。例如,以有代表性的技術(群)來指稱不同的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電子與信息技術時代,只是主體技術群的更替,并未對“現代性”的變化發展進行描述,給出脈絡;另一種是依據“現代性”的變化發展來進行歷史分期,甚至提出不同(近)現代的“當代”乃至“后現代”(在有些人看來后現代也約等于當代)。例如,芒福德把近代以后的技術發展分為“古技術時代”與“新技術時代”。實際上,這個“古技術”是指近代工業革命和早期資本主義時期的技術,其特征是煤炭和蒸汽機的使用,也就是近代技術,而他說的新技術時代大致開始于20世紀初,相當于“當代”。
本文著重分析第二類歷史分期,探討(近)現代以后,是否有一個在品性上不同于現代技術的“當代技術”,以及當代技術何以與現代技術有所不同。但在考察技術的“現代性”“當代性”以及兩者的區別和聯系之前,我們僅僅以技術與科學關系變化為視角,從三個方面來考察技術從近代到當代的變化。
(一)技術與科學的關系的變化——從科學時代到技術和創新時代
從總體上看,“現代技術”是工匠傳統逐步與學術傳統相結合的技術,它大致表現為對科學的“亦步亦趨”。這是因為有代表性的現代技術是緊隨科學革命的技術。科學革命的歷史也就是各門科學形成的歷史,是科學為人類社會(當然也包括技術)打開視域、開疆拓土的歷史。因此這個時期的技術進步對科學而言,顯得如影隨形,急速去填補科學開辟的領域,以“科學革命—技術創新”的方式發展。在這個時期,科學幾乎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為它主要面對比較純粹的自然客體,用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概念,如運動、慣性、質量、時間、空間、原子、分子、反應等去為自然“立法”,去照亮伽利略所說的那個“上帝用數學書寫的自然”,而不是特定的“人工自然”。“人工自然”或者說技術物、技術裝置,只是一種認識工具,是使“自然哲學”轉變為自然科學的一種必要手段,或者說,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用以“揭蔽”的“座架”。人工自然或者技術物尚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目標。在這些意義上,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科學時代”。
然而,從現代到“當代”,科學與技術的關系至少發生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方面,科學所面對的客體與牛頓時代的客體有著很大變化,“客體”越來越受到技術手段的限定。舉個極端的例子來說,伽利略可以通過自己脈搏來研究單擺的周期,而當代科學家卻日益受到技術物的限制;不僅如此,技術也成為科學的研究對象。總的來說,“人類已從‘客觀性’的時代進入‘規置性’的時代”*馬琳:《海德格爾論現代性紀元中科學與技術逆轉的關系》,載《學術月刊》,2015(6)。。另一方面,科學落入“研究與發展”(R&D)這種體制之中,其研究客體或對象受到技術發展的影響甚至指定。科學的“自主性”逐漸讓位于技術的“自主性”。在當代,技術發展由緊隨科學革命及其發展,變得在更多情況下“左右”科學的發展。科學由開疆拓土式的革命式發展,變成在各個高度分化的領域以積累性的方式進化發展。技術由單純地去開發科學新開辟的疆土,變成主要在自己固有的領域綜合利用多項研發(R&D)成果(包括科學發現)而得以發展。因此,技術顯得具有“選擇”的自由,即根據自己發展的需求,來選擇科學研究的成果,有時甚至為科學研究提供課題和方向。正如美國科技政策專家斯托克斯在《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在很多領域,科學是技術的先導,很多技術原型出自科學,是科學實驗的放大;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技術發展也已經成為科學的源泉。基礎科學探索中的許多結構和過程只能利用技術成就來揭示。實際上,在某些情況下,科學只能“存在于技術當中”。因此,越來越多的科學已成為“派生技術”*D.E.斯托克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7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該書特別提到,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一書中“可能”隱含技術的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而這種模式在當代顯得過于簡單和“線性”,提出以應用研究所引發的基礎研究(也就是巴斯德象限)在國家科技政策中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認為當代科技創新已經從“R&D”變成“D&R”。*費多益:《大科學的模式轉換——從“研究與開發”到“開發與研究”》,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1)。
如此看來,現代技術可以說是“科學時代”的技術,而科學時代以科學理性為文化內核,以追求真理為基本價值取向。而在當代,技術則似乎不僅“自主”甚至極大地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方向,因此當代可以說是“技術和創新時代”,而當代文化“則可以說是‘技術文化’,以創新為基本價值取向”。*周昌忠:《試論科學和技術的歷史形態》,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 (6)。
(二)技術進步和創新方式的變化
與科技關系的以上變化不無聯系,技術發展由利用一項顯著的科學成就取得巨大進展,變成綜合利用多領域、多項科學成就(包括技術科學)來取得發展,例如一個手機就要集成利用材料科學、電子科學、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多樣科學成就,不斷創新和不斷發展,集成創新變成當代技術進步的重要形式。技術進步和發展由“科學革命—技術創新”轉變為“研發—創新—集成創新—研發—創新”。在一個技術物上,例如手機,可以集中和涉及幾千件專利。而一個公司,例如華為,作為通信技術專利的持有大戶,截至2015年底,在全世界范圍內累計獲得授權專利50 377件*袁勇:《近五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明專利申請、授權量總體呈增長態勢》,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12/doc-ifxvueif6547898.shtml。,這些專利包括對智能手機具有很高價值的LTE通信、智能手機操作系統、用戶界面等。
但是,當代技術創新的這種主要模式并不是對“科學革命—技術創新”模式的否定,而是把它包含在創新的各個過程之中。粗略地說,現代技術更多的是從“無”到“有”地產生,而當代技術則更多的是從“有”向更好、更優的進化,盡管這種進化也可能是飛躍的、突變的。這意味著現代技術仍然依賴科學的發展,只不過它面臨的是已經高度分化的科學知識體系。“知識”一詞很好地表述了當代技術的特征:知識管理已經成為技術活動的重要內容——不僅要管理技術知識本身,而且還要管理技術的“人力資源”,因為不僅要知道怎樣做,而且還要“知道誰知道”,等等。知識和信息的“爆炸”是當代技術發展面臨的、與“近(現)代技術”時期完全不同的背景。
(三)技術對象和發展領域的變化
技術對象和發展領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代表這個時代的主導技術從某個領域變成多個領域,以至我們必須用主導“技術群”來描畫這個時代。信息時代、大數據時代、生物技術時代、新能源時代等等都只是對“當代”的某個側面的描述。第二,從“物理技術”發展為生命技術和智能技術,這里的“物理技術”不是指僅僅基于物理學的技術,而是指利用和改造“物理世界”的技術。當代人工智能、虛擬技術與大數據技術方興未艾,這不是技術(和科學)對象在又一個新領域的簡單延伸,而是技術和科學對自然乃至人類更徹底的“袪魅”:把腦力勞動中可以步驟化和可計算的工作交給計算機來處理,把生命秘密還原為生物學的DNA,其本質是對“腦力勞動”和生命“在一定意義”上的“解魅”。信息技術不是簡單地造就“信息社會”,不是使人的腦力簡單地從機械重復中解放出來,而是形成新的“座架”和解蔽方式,以及新的生存論意義上境域及其矛盾:“算法”和“步驟”與人的感性存在以及創造性思維的“對立和統一”。于是,新的問題或危機出現了:信息爆炸使人成為海量信息的奴隸,思維被計算和步驟左右,生命的“制造”打亂了生命的自然生成和發展秩序,等等。人工智能、數據的挖掘和利用,雖然要依托物理技術,但其本質性的東西不是一種物理方法而是數學方法,技術越過物理世界的問題而直接與數學、邏輯學等思維科學發生聯系,圖靈問題、哥德爾問題和邏輯悖論問題都可以在計算機科學技術和人工智能科技中找到對應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應對、化解或深化就是這類技術的豐富和發展。
三、現代性、當代性與“后現代技術”
然而,我們以上討論的實際上只是技術從“近代時期”到“當今時代”(一般認為開始于20世紀)的變化,而不是技術發展的“現代性”與“當代性”之區別和聯系。而且我們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當代性僅僅是現代性的展開和發展,還是對現代性有著某種超越,甚或是某種反叛乃至否定性的超越?
“現代 ”(英文與“近代”同義,即modern)、“現代性”其實是非常復雜的指稱和概念。就“現代”的開始時間而言,在人文社會歷史學者那里,一般從文藝復興或啟蒙時代算起,但在多數科技史學者看來,“現代技術”卻晚至工業革命才開始。而“現代性”一詞,也有著豐富的內涵和“與時俱進”的闡釋空間。由于技術哲學存在兩種傳統——人文主義傳統與工程學傳統的對立,而且這兩種傳統的對立“根源于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的對立”*劉大椿 :《關于技術哲學的兩個傳統》,載《教學與研究》,2007(1)。,因此對技術的“現代性”的闡釋就應該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對“現代性”的肯定、順應、追隨或批判、反思、拒斥,都能在技術哲學中得到反映。
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反思、拒斥”的思潮莫過于“后現代主義”了。因此,我們把“后現代”作為一個參照,來考察現代性與當代性的關系。就技術的發展而言,如果確實有一種實體存在的技術能承載這種“后現代性”,即存在某種不僅僅是思潮而且是實體的“后現代技術”,那么,“當代性”的確是對“現代性”的“揚棄”或者“否定性”的超越。但這是令人懷疑的,缺乏實際的根據。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說明這一點:
第一,由于當代技術與科學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如果有實體存在的“后現代技術”,那么也應該有得到廣泛公認的“后現代科學”。然而,到目前為止,只存在對科學的后現代審視、反思、引導或批判,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后現代科學”。
近代以來,科學還有過若干次革命,這些革命所帶來的只是自然觀的變化,遠沒有改變或消解近代以來所確立的科學內在規范和社會規范。科學的內在規范主要包括:內在一致性、可重復檢驗性、解釋性和預見性,等等。社會規范即默頓所說的普遍性、公有性、競爭性和合理的懷疑精神,等等。這些規范不僅沒有被消解反而不斷強化和發展。而且,技術規范日益受到科學規范的影響,在很多方面,科學規范日益成為技術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技術步驟的明晰性、后果的可預測性、操作的可能性等要求,正是科學理性和規范在技術規范上的體現。
科學革命的確帶來自然觀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卻沒有朝著“后現代科學”所假想的“返魅”或“附魅”的方向發展,而是朝著更深、更廣的“袪魅”方向發展。例如,沒有發展出脫離還原論的整體論,沒有發展出能脫離結構分析的有機論,沒有發展出可以否定科學理性的生態倫理,等等。
計算機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擴展了“袪魅”的范圍——進入人的思維領域。人工智能機器人AlphaGo戰勝世界一流棋手,使圍棋這種智力游戲基本失去了智性上的神秘感。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已經把握人類思維的所有規律,把精神世界也完全納入“萬物皆數”的形而上學假設之中了,而只是說明,人類自身也是可以認識的。生命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更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如果沒有與“后現代科學”相關的后現代技術(例如不存在“附魅”的后現代技術),是不是還可以存在符合現代科學理性和規范,但能夠克服“現代性危機”(例如技術異化、人與自然對立)的“后現代技術”?我們認為這也是不可能的。
一些論者所說的后現代技術,是指某種在人類活動中已經存在或將要出現的,而且比現代技術更為先進和優越的技術,能克服現代技術的諸多缺陷,例如克服了“技術異化”,使人與物的關系更加和諧、更少對立。這種后現代技術作為一種“實際存在”的技術,是否真的言之有物?哪怕它只是若隱若現、暫時未成氣候,但只要代表了某種發展趨勢,只要它對“現代技術”確實存在特定意義上的改造和優化,這種存在性的判斷就是成立的。
大數據、網絡技術、人工智能等等往往被一些論者視為“后現代技術”的實體性代表。甚至“工業4.0”被視為后現代技術時代的一個重要啟動者,“在某種程度上工業 4.0 本身即是一場后現代運動”*。工業4.0即德國所謂的工業四代(Industry 4.0),它將利用物聯信息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簡稱CPS)將生產中的供應、制造、銷售信息數據化、智慧化,最后達到快速、有效、個人化的產品供應。據說,工業4.0將改變集中生產模式,即改變工業社會的“大機器生產”模式,因為它能運用智能去創建更靈活的生產程序,實現“海量定制”,支持制造業的革新以及更好地服務消費者,所以可以代表集中生產模式的轉變。
一般認為,網絡通信等技術能減少某些交通或運輸的必要性,從而減少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工業制造的信息化、智能化能更好、更低成本地滿足各種“個性需求”,甚至實現設計者的工匠精神,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流水線的機械重復,能恢復生產者的“智慧特征”,使技術人員或制造者能像古代工匠那樣,運用技術活動中最本質的東西——“技巧”或“技藝”。有人甚至認為,作為高科技條件下精細化和個性化融合的產物,工業4.0能達到以下效果:(1)去中心化: 互聯時代的平等制造;(2)差異化: 海量定制與自由選擇;(3)回歸制造: 作坊和工匠精神的再現;(4)道法自然的量子化生產。*徐玉祺、史玉民、任雪萍:《工業4.0的后現代隱喻與生活制造》,載《貴州社會科學》,2017(7)。
照此看來,當代技術似乎呈現出某種“后現代技術”的特征,即克服了技術的“異化”性質,技術(和科學)作為雙刃劍的性質似乎有所減少或減弱。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大數據、信息技術、新能源的使用,固然可以減少甚至取代交通及物流運輸,減少能源消耗,然而由于技術更新和升級速度的加快,產品廢棄速度也加快,電子垃圾(無論是手機還是電子計算機)越來越多;網絡技術的發展,也可能帶來(實際已經帶來)人際交往減少、人性人格的封閉、個人隱私權難以保護等問題。對虛擬世界的沉迷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而大數據輕而易舉地追蹤、“計算”和分析個人隱私,早已經是人們熱烈談論的話題。此外,大數據、智能技術離不開新能源、新材料等技術,而這些技術可能會創造更多的在廢棄以后難以被自然界消化的穩固材料。
由此可見,科學技術的“雙刃劍”性質并沒有改變,技術異化并不是暫時性的(或者說是工業社會特有的)、將來不再出現的特征。黑格爾指出,“異化”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實現了的目的因此即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確立了的統一。但這種統一的主要的特性是:主觀性和客觀性只是按照它們的片面性而被中和、被揚棄……達到了的目的只是一個客體,這客體又成為達到別的目的的手段或材料,如此遞進,以至無窮”*黑格爾:《小邏輯》,39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 。。埃呂爾認為,技術的負面作用不會因技術的進步而不再出現。“每一項技術的運用,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某種不可預見的附加效應,這種附加效應較之該項技術的缺乏更具災難性。這些附加效應伴隨著那些所預計、所期待的有價值而積極的結果而生。”*Donald L.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Inc.1977.p.107.轉引自王佩瓊:《論異化的技術史觀》,載《自然辯證法通訊》,2011(3)。“后現代技術”也不例外。因而,從這種意義上看,能否存在克服了“現代性”缺陷的“后現代技術”,也是值得懷疑的,至少在當今,這類“后現代技術觀”盡管早已有之,但相應的“后現代技術”尚難見端倪。
第三,科學與技術關系的變化,也沒有實現后現代主義的思想主張,如反對普遍化,去除本質論、基礎論,等等。
從現代到當代可以粗略地描述為從科學時代到技術時代。技術與科學關系的這種變化,似乎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反本質主義”或“反基礎主義”的一些“后現代”思想,例如“知識的元敘事機制的衰落”。表現在科學與技術的關系上,就是利奧塔爾的觀點:“科學知識的語用學代替傳統知識或啟示知識的地位,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性能代替原理成為合法化標準。那種知識的獲取與精神,甚至與個人本身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則已經過時,而且更將過時,知識的供應者和使用者與知識的這種關系,越來越具有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與商品關系所具有的形式,即價值形式。”*讓-弗郎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93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但是,我們所提出的科技關系的變化——從“科學時代”到“創新時代”,是科學與技術的社會關系的變化,即科學與技術的社會角色和戰略地位的變化,甚至只是它們在“研發統一體”中的戰略優先地位的變化,而不是知識論或認識論意義上關系的變化:科學(和技術)已經由小科學時代向大科學時代轉化。過去人們關注的是小科學的自由研究,而現在科學技術研究對社會資源的依賴度越來越強,科學研究的組織化程度越來越強。科學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而科學的社會化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它與技術的互動——這種互動正如“舞伴關系”*Rip A.“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In Kroes,P.,and Bakker,M.(eds.).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231.,在某個時期、某種意義上由科學領舞,在另一個時期、另一種意義上由技術領舞,而且這種角色更替是兩者作為“社會活動”意義上的更替,而不是什么知識的“元敘事機制”的衰落,以及性能代替原理成為“合法化標準”。此外,我們說當代“以創新為價值取向”并不是對“以追求真理為價值取向”的否定,而是前者把后者包含于其中。
四、小結
從技術發展的歷史分期來看,無論古代、近代還是當代,人與技術、自然的關系都既有和諧也有對立。從所謂“物性的順應性帶出”到人對自然的所謂“逼索”之間,在古代和現代之間有一條連續的譜線,“逼索”并不是隨著技術與科學的結合而突如其來,技術的“異化”或負面效應也并非現代技術所獨有,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古代技術并非沒有負面效應, 而可以“返魅”或消除異化的“后現代技術”也未見端倪。
盡管我們可以把技術發展區分為古代、現代(實際上是近代)、當代,甚至還可以有更細的劃分,但“現代性”只是一個開端,一個需要不斷展開、深化和發展的面向未來的品性集合,而不是一個已經結束或完成的、可以馬上超越或否定的過渡性的時期。韋伯將“現代”特征概括為自主性、理性化和專業化的時代。這些在技術上也得以體現,從當代技術的發展來看,我們只能說這三個特征表現得越來越充分、內容越來越豐富。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現代”與其說是一個“時代”,不如說是一個指向未來的時間之箭 ,是哈貝馬斯所說的“一個方案”和“一項未竟的事業”*Habermas.“Modernity: An Uncompleted Project”.In Hal Foster(ed.).Postmodern Culture.London and Sydney: London: Pluto Press Limited, 1985.pp.3-15.。那么,“當代”只是與“近代”(中文意義上的)相區別,它仍是“現代性”的展開,其現代性的品性較之近代而言,有所發展、提升和優化。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是“形而上學的完滿實現”。那么,這個“現代”作為技術的一種品性(而不僅僅是一種時代的限定和指稱),就應該具有不可逆轉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人類要想“詩意地棲居”,不是靠改變技術的“現代性”(這也不可能做到),而只能通過社會和經濟的改革、改良、改進,形成更好的社會機制,建構更合理的社會規范,來化解科學和技術帶來的負面效應,引導科學技術更好地為人類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