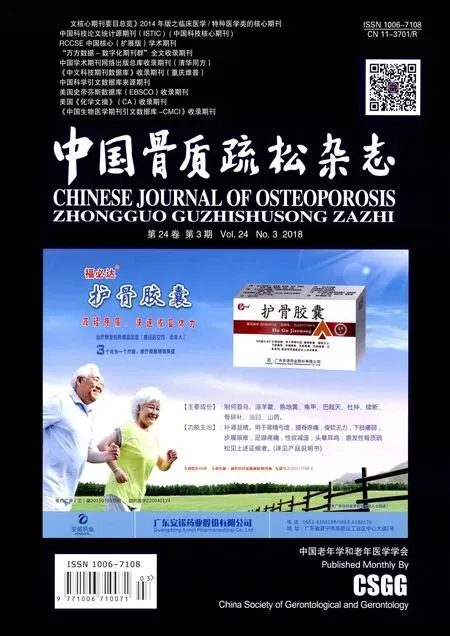腸道微生態失衡為骨質疏松癥發病的易感因素
董萬濤 黃凱 宋敏* 侯紅燕 宋志靖 周靈通 劉小鈺 蔣林博
1.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2. 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甘肅 蘭州 730020
腸道微生態(gut microflora)是腸道菌群與其宿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統一體,是人體最為龐大的微生態系統。腸道微生態失衡與多種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包括骨質疏松癥在內的代謝性疾病。近年來,腸道菌群結構和骨代謝之間的關系備受關注,通過調控腸道菌群來促進骨骼健康、抑制骨鈣流失,從而為骨質疏松提供新的靶點治療是目前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文就腸道微生態失衡與骨質疏松癥的聯系作一探討。
1 腸道微生態平衡具有重要的生理意義
腸道菌群是一個強大的人體“功能器官”,成人腸道中定植著數目龐大(1014)、結構復雜(超過1 000種細菌)的微生物群落,重達1~1.5 kg,是人體體細胞的10倍,編碼330萬個基因,是人類基因數的150倍左右[1]。宿主體內的腸道菌群形成了復雜而又龐大的微生態系統,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生理情況下,腸道菌群與宿主共棲互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響。腸道微生態的平衡直接影響著宿主健康,其在促進營養食物消化吸收、產生有益營養物質、抵御外來致病菌的侵襲以及調節免疫機制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
腸道微生態平衡指的是人體腸道菌群與菌群之間、菌群與宿主之間構成的平衡關系,是人類在長期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正常微生物菌群與其宿主在不同發育階段互動的生理性組合,維持著機體的生理功能和健康[2]。O’Hara等[3]提出腸道菌群是個“代謝器官”;Cani等[4]進一步認為腸道微生態系統具有作為潛在藥物治療靶點的可能性。隨著人類對腸道微生態系統認識的不斷深入,其與多種疾病的關聯日益受到重視,腸道微生態的臨床應用價值亦備受關注。研究[5-7]認為,當宿主內、外環境改變時,腸道菌群的種類和結構隨之改變,破壞了菌群內部以及宿主與腸道菌群間的平衡狀態,可引發消化道疾病(如腸炎)、免疫性疾病(如風濕性關節炎和脊柱關節病)以及代謝性疾病(如骨質疏松、肥胖癥和糖尿病等)。
2 腸道菌群結構是宿主重要的“微環境”
腸道菌群包含了益生菌、有害菌和機會致病菌等3類菌群,主要由專性厭氧菌構成的優勢菌群和需氧菌或兼性厭氧菌構成的次要菌群組成。人體腸道菌群結構隨著年齡的變化不斷發生變化。嬰兒攜帶的菌群基本都是一致的,但分娩方式、哺乳等因素都會影響嬰兒菌群結構,剖腹產嬰兒優勢菌群是Staphylococci(葡萄球菌),接近于產婦皮膚的微生物群,陰道分娩嬰兒的優勢菌群則是Lactobacillus(乳酸菌)、Prevotella(普雷沃氏菌)和Atopobium(阿托波氏菌);離乳期則以Bacteroidaceae(類桿菌)、Peptococcaceae(消化球菌)和Clostridium(梭菌)等為主,兼性厭氧菌開始出現,且數量持續增加;成年期腸道菌群是非常穩定,以Bifidobacteria(雙歧桿菌)、B.Adolescentis為優勢;老年期腸道菌群的組成和功能也隨之轉變,兼性厭氧菌升高,Bifidobacteria數量顯著降低,免疫系統功能開始下降。
飲食、益生菌及抗生素的使用均可改變或修飾腸道菌群的組成和結構。腸道菌群通過消化道結構與功能影響物質代謝,產生大量的生物活性代謝分子,從而發揮“激素樣”效應,參與宿主的物質代謝、促進營養物質消化吸收,在維持腸道正常生理、拮抗病原微生物定植以及調節機體免疫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8]。
3 骨質疏松的危險因素與腸道菌群失調相關
3.1 衰老與胃腸道功能不足是老年性骨質疏松的危險因素
隨著人體年齡增長,機能逐漸老化,胃黏膜的萎縮程度和范圍隨之擴大,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上皮細胞和壁細胞數量逐漸減少并萎縮,從而引起胃腸功能的紊亂并影響消化功能,使得骨質疏松的易感性明顯增加,這與人體腸道菌群的功能和結構紊亂有著密切的關系。
胃腸道是人體最主要的消化吸收部位,腸道菌群好比土壤中存在的大量微生物,在分解物質的同時形成新的有益代謝產物,重新進入循環利用。隨著衰老的進程,老年人腸道內條件致病菌、有害菌、腐敗菌逐漸增多,有益菌特別是乳酸菌、雙歧桿菌等益生菌逐漸減少,必然導致胃腸功能下降,消化吸收功能受影響,食物通過腸道的時間縮短,或者胃腸病變導致腸壁上轉運通路減少,相應受體數量不足,即使有足夠的鈣、磷及1,25(OH)2D3也不能發揮其生物學作用。
衰老與胃腸道功能不足,直接或間接影響腸道鈣、磷的吸收及1,25(OH)2D3的生物學功能。換言之,胃腸功能下降,宿主所必須的營養物質不能進入機體,食物中的鈣、磷無法入血,血鈣水平下降,無法進行正常的新陳代謝,從而影響與骨代謝相關的激素的調節。當血鈣下降到一定水平時,骨吸收加速,促使骨骼中的骨鈣釋放入血,維持血中的鈣的濃度,導致骨吸收增加,骨形成減少,骨量流失,最終導致骨質疏松。
3.2 炎癥性腸病是并發骨質疏松的危險因素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病因尚未明確的慢性復發性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克羅恩病(Crohn disease,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腸道菌群在腸道免疫及 IBD的發病機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IBD患者腸道菌群結構發生顯著改變,有益菌減少,有害菌增多,抑制Treg細胞,激活Th1和Th17介導的免疫反應,失去免疫耐受功能[9]。
近年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IBD誘發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的發病率分別達22%~77%、17%~41%,顯著髙于正常健康人群[10]。研究認為,IBD患者比正常健康人群骨折的風險增加了40%[11],Card等[12]對16550例IBD患者和82917例正常對照者進行隊列研究,結果顯示UC發生髖部骨折的相對風險是正常對照的1.49倍,而CD的風險是正常對照的2.08倍。此外,Vestergaard等[13]對丹麥16,416患者調查研究發現,IBD患者脊柱骨折的風險較正常人增加了6.5倍。
腸道對鈣、維生素D、維生素K的吸收不良是IBD誘發骨質疏松的主要病因。IBD患者由于腸道菌群結構紊亂,腸道微生態失衡,機體攝入的鈣和維生素D等營養物質不足,加之患者腸道黏膜功能受損,維生素D腸肝循環障礙及長期、大量使用糖皮質激素,腸道對鈣、維生素D等吸收不良。維生素D缺乏可激活T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導致小腸黏膜屏障的破壞,從而加重鈣的吸收不良[14]。維生素D缺乏(低于30ng/mL)及鈣吸收不良引發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從而增加骨量丟失[15]。Ulitsky等[16]研究提示維生素D缺乏在IBD患者中發生率較高,缺乏率達到了49.5%(n=504,P=0.04),Shirazi等[17]研究認為維生素D亞臨床缺乏可能促使IBD患者骨量丟失。維生素K缺乏與骨質疏松關系密切:維生素K可促進谷氨酸γ羧基化骨鈣素的合成和分泌,從而抑制骨吸收、促進骨形成以提高骨量;其水平減低可引起未羧化的骨鈣素增高和骨密度下降,骨量流失。此外,維生素K還可調節鈣平衡,間接影響骨代謝,其機制與影響骨鈣素及IL-1、IL-6水平有關[18]。
IBD高水平的炎癥因子通過多種途徑誘發骨質疏松。目前,眾多的研究報道證實IBD患者腸道炎癥在骨質疏松的發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IBD患者腸道菌群結構和功能異常,與腸上皮細胞及免疫細胞之間的“應答對話”受到抑制,體內出現異常的免疫應答反應,導致免疫細胞分泌如腫瘤壞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2、IL-6、核轉錄因子(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各種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且NF-κB能夠調節TNF-α、粘附因子、IL-1、IL-6等的轉錄,進一步促進炎癥因子的產生[19]。而最新研究證明,IL-6是骨質疏松的一個重要致病因子,IL-6、TNF-α、IL-1α、IL-1β等炎癥因子能夠促進破骨細胞的活性,在骨質疏松的進程中具有重要作用,IL-1受體拮抗劑和IL-6基因的遺傳變異與IBD臨床病程和骨質丟失的嚴重程度相關[20]。此外,IBD高水平的炎癥因子通過RANKL/RANK/OPG信號通路誘發骨質疏松:NF-κB受體活化因子配體(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 ligand,RANKL)- NF-κB受體活化因子(RANK)-骨保護蛋白(osteoprotegerin,OPG)途徑是破骨細胞生物學和骨代謝的關鍵調節因子,IBD患者釋放高水平的炎癥因子抑制OPG的表達,使RANK與RANKL發生交互作用,破骨細胞分化和活性明顯增強,發生骨量丟失,最終導致骨質疏松。Bernstein等[21]研究證明外源性的OPG可逆轉IBD動物模型的骨量減少,由此認為,OPG可能是IBD繼發骨質疏松患者的治療靶點之一。
3.3 糖皮質激素是IBD誘發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的重要因素
皮質類固醇激素是治療中重度IBD的重要藥物,但同時其被認為是IBD誘發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的主要因素之一。皮質類固醇激素可抑制骨基質蛋白質的合成,促進骨基質蛋白的分解,抑制成骨細胞及前體分化,減少骨膠原合成,減少骨鈣素的合成和分泌,從而導致骨形成降低,此外皮質類固醇激素還可直接作用于破骨細胞促進其活性,影響鈣磷代謝從而促進骨吸收。
研究[22]發現,臨床使用強的松或其等效劑量大于5 mg/d的IBD患者,骨丟失量在治療最初的3~6月中最大,停止應用糖皮質激素之后骨折風險顯著降低,說明IBD患者服用糖皮質激素藥物后骨折風險增加。此外,有學者研究認為,當累積量激素大于5 g時,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的發生率會顯著上升[23]。但也有學者調查發現IBD患者在使用激素之前或已出現骨質疏松。Walther等[24]通過對90名IBD患者和52名健康志愿者進行骨密度檢測,發現IBD患者骨密度較健康志愿者明顯下降,IBD患者中20%的男性及8%的女性可同時診斷為骨質疏松癥,IBD患者罹患骨質疏松與是否應用激素并無影響。因此,目前對IBD患者應用皮質類固醇激素與誘發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仍有爭議。
3.4 腸道菌群失調是絕經后骨質疏松發生的關鍵因素
婦女絕經后,體內雌激素水平會急劇下降,釋放大量炎癥因子,刺激破骨細胞使其活性增加,干預了骨轉化過程,誘導骨量減少及骨質疏松的發生。
體內較高水平的雌激素與腸道菌群的多樣性均有助于維持機體免疫系統的穩態。研究[25]發現,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可以減少腸道菌群的多樣性,同時降低了包括梭菌屬在內的厚壁菌門細菌豐度。而絕經后女性尿雌激素代謝產物與糞便中微生物的多樣性、梭菌屬和桿菌屬的相對豐度呈正相關,且腸道菌群的多樣性隨著尿中羥基化雌激素代謝產物比例的增高而增加[25]。絕經后由于雌激素急劇減少,不能有效與腸道上皮的雌激素受體結合,無法激活胞質激酶(如Raf、MEK1/2、Erk1/2等)和三磷酸鳥苷結合蛋白Ras,胞核內轉錄因子的磷酸化減弱,胞質蛋白減少,TJ跨膜蛋白Occludin的表達減少,腸道上皮屏障功能減弱,腸道微生物的有害代謝產物作為抗原進入上皮下組織引發免疫反應[26]。炎癥因子(如IL-1、TNF-α等)的高表達可導致絕經后女性發生骨質疏松的風險增加。TNF-α是參與骨吸收的關鍵因子,TNF-α可直接作用于破骨細胞前體細胞并促進其分化成熟,并可通過CD40 L和DLK1/FA-1誘導RANKL和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的生成,并下調OPG[27]。
雌激素抑制骨吸收主要通過下調機體炎癥免疫應答,影響破骨細胞和成骨細胞兩條途徑來實現。絕經后女性體內雌激素的缺失及腸道微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均可導致雌激素的骨保護效應減弱。有害抗原經腸道上皮進入宿主體內并引發T細胞介導的免疫反應。雌激素缺失誘導骨髓細胞內活性氧簇(ROS)堆積,激活CD4+T細胞,隨即增加的IFN-γ通過上調MHCⅡ的生成增強骨髓巨噬細胞(bone marrow macrophage,BMM)功能,直接上調了包括TH17在內的CD4+T細胞的數量和活性[28]。因此,包括TH17細胞在內的TNF-α和CD4+T細胞等促破骨細胞生成因子是腸道菌群介導的絕經后骨質疏松骨吸收的關鍵因素[28]。
4 腸道微生態失衡可能為骨質疏松發生的易感因素
腸道微生態可以調節機體的代謝和免疫狀態,特定的腸道菌群可通過免疫系統影響宿主的健康狀態,具有免疫調節、促進正常的細胞代謝、抑制骨鈣流失、延緩衰老等作用。近年來研究[29]表明,腸道菌群可以通過釋放雌激素類似物、血清素等小分子物質、免疫調節、影響鈣磷的吸收代謝等方面對骨代謝進行影響。王飆等[30]通過腸道菌群多樣性分析發現骨質疏松組人群特異性腸道菌群明顯多于對照組。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微生態可能為骨質疏松發生的易感因素。
腸道微生態失衡引起的炎癥狀態、自身免疫改變可導致骨質流失,骨形成減少。研究[31]發現,腸道菌群缺乏的無菌小鼠股骨遠端骨體積分數比正常小鼠增加39%,骨小梁數目增多,間距減小,皮質骨骨量也有顯著增高。通過骨髓培養發現,無菌小鼠的骨形成速率并沒有顯著變化,但破骨細胞數目減少,破骨細胞前體細胞(CD11b+/Gr1-)和CD4+T細胞形成量顯著減少[32]。此外,飼養在無菌條件下的無菌小鼠,與非無菌小鼠相比,炎癥因子的表達減少,而血鈣及血磷水平并無顯著性差異,但破骨前體細胞與T細胞形成顯著減少,破骨細胞也相對較少,然而促進骨形成的速度并未降低[33]。因此,無菌小鼠骨量的增加是由于缺乏作為抗原的腸道菌群,腸道內免疫調節因子IL-6、TNF-α等下降,骨骼中炎癥因子形成減少,破骨細胞作用減弱造成的。從實驗角度證明了腸道菌群是調節骨量的一個重要因子,而且是通過免疫系統來影響破骨細胞的生成,從而達到調節骨代謝的目的,進一步證實了腸道微生態與炎癥因子、免疫系統、破骨細胞減少及骨密度具有密切相關性[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