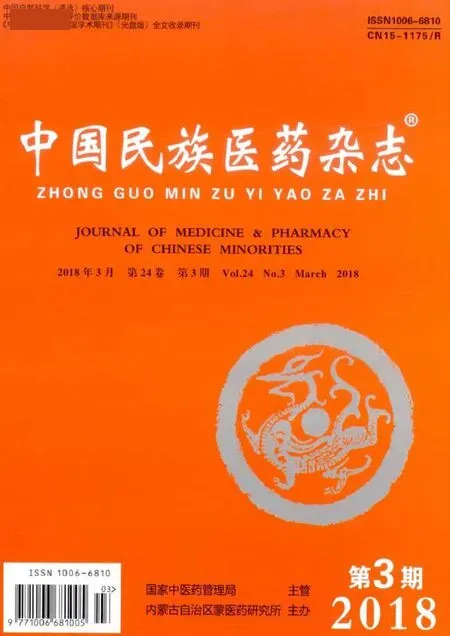論朝醫學與中醫學的整體觀念
屈重陽 徐玉錦
(延邊大學中醫學院,吉林 延吉 133000)
朝醫學是在朝鮮族固有文化和傳統醫藥的基礎上,吸收中醫藥學的理論,并結合本民族的防病治病經驗,以“天、人、性、命” 整體觀為理論指導,以“四維之四象”結構為主要形式,以“辨象論治”為主要內容的一門獨特的醫學科學體系[1]。其中四象醫學是朝醫學理論的精華和核心,也是朝鮮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四象醫學的形成和發展又與中國古代哲學密不可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四象醫學的理論基礎與中國古代哲學的某些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中醫學是以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經驗為主體,研究人類生命活動中健康與疾病轉化的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綜合性科學,是中華民族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代傳承并不斷發展的科學的醫學理論體系。朝醫學和中醫學的理論體系中都涉及到了整體觀念,整體觀是朝醫學關于人體自身完整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統一性的認識,即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的關系及人體本身如何適應生活環境。而“天、人、性、命”的整體觀正是闡述這種人與自然社會之間關系的學說。同樣的,整體觀念也是中醫學理論體系重要的指導思想,體現了中國古代醫家在關于人體自身完整性及人與環境的聯系性和統一性的認識。
1 人體自身的統一性
人體自身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在朝醫學的理論中認為,人體是由四臟、四腑、黨與三者組成的,三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李濟馬在《東醫壽世保元》中就指出了這種關系,“五臟之心,中央之太極也,五臟之肺脾肝腎四維之四象也”,“肺脾肝腎立于人也,頷臆臍腹行其知也,頭肩腰臀行其行也”,用來說明人體的各個臟腑是互相依存相互為用的。這就是朝醫學獨特的臟腑論。朝醫學臟腑論的特點是它立足于“四維之四象”的觀點,把體內臟腑所在部位劃分為四焦,臟分為四臟,腑分為四腑,全身組織器官歸類為四黨與[2]。四個黨與即肺之黨,脾之黨,肝之黨,腎之黨,各自由性質和功能相同的部分和器官組成, 維護人體正常的生理活動,并且相互協調。正是這種臟腑、黨與之間的統一性,維持了人體內部環境的平衡穩定,從而人體才能進行正常的生理活動。從某種程度上,這種觀點與中醫學整體觀念中生理功能的統一性理論是相一致的。在中醫學的理論中認為,人體的肝心脾肺腎在功能上是相互統一和制約的,分布在人體全身各處的精氣血津液也是相互配合和協調的,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使得人體生命活動正常進行。同樣,人體臟腑或基本物質發生病變,也會導致人體生理或精神活動失常。此外,中醫學理論還提到了關于診斷防治和養生康復的整體性。如通過望聞問切的診法及病理表現,可推測出機體內在的病變。中醫學認為,人體是形神統一的,即人的形體和精神意志是相互統一互不分離的,要想治療疾病康復,必須形神共調,通過合理飲食,適度勞逸,做到形神統一,形健而神旺。
2 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統一性
《東醫壽世保元》中提出:“天機有四:一曰地方,二曰人倫,三曰世會,四曰天時。”這里的“天機”即是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天時”和“地方”即自然環境,“世會”和“人倫”即是社會環境及倫理道德。這是李濟馬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闡述了人與自然社會息息相關,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是一個整體的觀念。此外,李濟馬還提到了人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統一性。人類的日常生活是在社會的這個大環境下進行的,人與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社會環境的發展變化會影響人類的身心健康,而人類本身的活動也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東醫壽世保元》中指出:“人事有四:一曰居處,二曰黨與,三曰交遇,四曰事務。”“人事”是指人類的各種社會活動,“居處”即是居住環境,“黨與”是社會團體,“交遇”及人類之間的相互往來,“事物”即是所從事的社會工作,說明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會對人體的身心健康產生相應的生理病理變化。
這種關于人與自然社會環境的認識,正是和中醫學中“天人一體”的整體觀相一致的。《素問·寶命全形論》中提出,“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意思就是說自然環境會對人體的生理病理產生不同的影響,如人體的脈象可以隨著四時節氣的變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出現相應脈象的規律性變化(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人體的陽氣也會隨著天氣冷暖和晝夜時辰而發生盛衰的變化。此外,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的變化也會對人體產生影響。如社會動蕩、政治腐敗、饑荒戰亂、經濟蕭條以及一些不良的社會習俗都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身疾病。
由此,根據這些疾病發病原因,中醫學提出了相應的防病原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如在面對惡劣的天氣變化時,要“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防治疾病侵犯人體;要因時制宜,根據四時節氣的變化考慮治療用藥,也可“夏病冬治”“冬病夏治”,要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地方的體質特點,給予相應的治療原則。要注意精神調攝,提高自身對社會的適應能力,維持身心健康,防治疾病發生。
朝醫學“天、人、性、命”整體學說對指導醫療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病因學方面,肯定了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均可致病;在治療和疾病防治方面,強調了調攝情志對診斷治療的重要性;在預防保健方面,提出了“簡約得壽、勤干得壽、警戒得壽、聞見得壽”“懶怠減壽、偏急減壽、嬌奢減壽、貪欲減壽”“好欲樂善,天下之大藥也”等養生保健措施。
3 辨象(證)論治的整體性
朝醫學在診病過程將辨象和辨證結合起來,先辨象后辨證,辨象同樣用的是望聞問切的方法,觀察和了解體形、表情、容貌、性情、排泄物、人際交往、多發病、步態、肌肉體格、四官(耳目鼻口)、舌象、聲音、呼吸、哭笑樣、氣息、嗜好飲食、喜歡季節、健康和病態特點、藥物反應、脈象、臟器、皮膚肌肉骨骼的情況等方面的信息綜合推理判斷,確定其屬象。朝醫的體質診斷重點闡述四象人辨象綱要,朝醫辨象方法,四象人與辨證、辨病的關系,全面收集病人的資料,進行分析、綜合和推理,辨認太少陰陽四象人中的哪個體質,確定疾病,病情程度及其發展趨勢(辨證)。辨象是朝醫診斷的核心,是施治的前提,只有辨象準確,才能取得好的療效。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又一大特點,是以中醫學理論對四診(望聞問切)所得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明確病變本質確定證型而確定相應的治療原則及治法和方藥。通過望聞問切收集到患者的癥狀、體征和病史,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局部的病變可以產生全身的病理變化,全身的病理變化也可以反映到局部,通過四診合參,確定出相應的病癥,從而確定正確的治療方法。
辨證滲透在辨象的過程中,而辨象的確定完成了中醫學中的幾道辨證程序,這是李濟馬對中醫學的貢獻,發展仲景理論之處,也是朝醫學能夠生存、發展至今之所在[3]。
由此可見,整體觀念不論對中醫學還是朝醫學的理論基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既有相通之處又各自發展,對人體疾病的防治具有借鑒作用。不論是在人體自身的統一性、自然社會環境的統一性,還是在辨象(證)論治的整體性上,都相互聯系但又各具特色。中醫學和朝醫學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當在整體觀念的指導下,繼續深入發展,為疾病預防和治療做出更大的貢獻。
[1]徐玉錦. 朝醫基礎理論[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13:1.
[2]全基浩.論朝醫學與中醫學的不同[J].中國民族醫藥雜志,2012,4(4):5.
[3]崔海英,崔正植.淺談朝醫學“辨象”與中醫學“辨證”之比較[J].中國民族醫藥雜志,1997,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