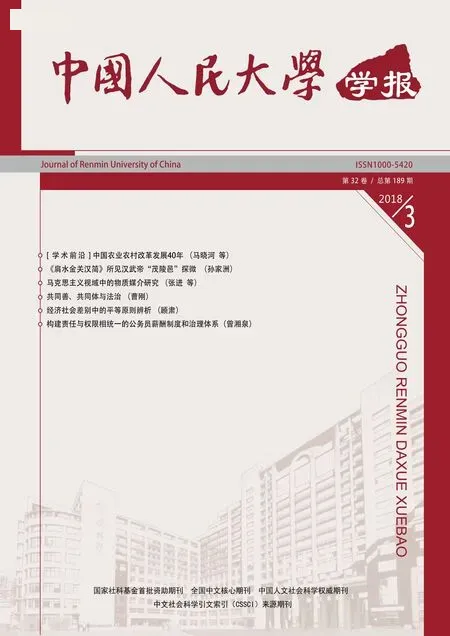論生活與倫理的關系
肖群忠
日常生活倫理學的創新建構,首先要澄清一些前提性的基礎問題,比如,“生活”與“日常生活”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生活與倫理的關系,日常生活倫理的特點,日常生活倫理研究的對象、方法與意義等。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生活與日常生活
何謂生活?生活就是生命的存在以及為了謀求生命存在并尋求人生價值而展開的活動。謀生就是謀取生命的存在,即生存,生命的存在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因此,人要保證生命的存在、追求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必須進行謀生和有價值意義的活動。作為一個文化承載者和有意識的主體,人必定要追求活著的意義與價值,因此,“生活”一詞就必然包含人們對生活意義和合理生活方式的探尋和追求。生活不僅是一種謀生、生存的客觀生命活動,也是對生活的價值和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追求,這才是人的生活。如果僅有活命和謀生,那么就難以區分人的生活和動物的生存,反過來說,正是生活的意義、價值、觀念、方式這些精神性、文化性的要素使人的生活區別于動物的生存。
因此,在研究生活時,我們一定要研究客觀的社會生活和人的觀念之間的互動關系,唯有有意識自覺、價值引導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生活這個詞的核心意涵是生存與意義。生存就是活著或存在,它是前提,但意義才體現著生活的價值與本質。
什么是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如下問題或含義:我們活著是為了什么?什么樣的生活是值得過的?生活指向一個什么目的?生活的意義是眾多哲學家和普通民眾普遍關心和思考的問題。人作為萬物之靈,其存在與活動的根本特點就在于人是有意識的動物,人可以探索、創造價值與意義,對生活意義的追尋與探索恰是人與萬物的不同之處。對生活價值與意義的探索,必然使人們形成一定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生活觀,也必然會以一定的觀念、規范、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規范、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就是生活倫理。因此,倫理源于生活,是生活觀念與規范的凝結。
要理解把握生活這個范疇,應該把握生活的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人是生活的主體。理性自覺與意義追求是人的生活的特質。生活是人的生活,生活只能由人來完成、來主導,人通過生活才能成為“人”,人在生活中存在,在生活中發展。一切生物都在一定意義上要謀求生活,即個體生存與種族的繁衍,區別在于動物的生活是完全依靠本能以適應自然而活著,而人的生活則是一種理智與理性的生活。所謂理智與理性的生活,就是指人對外在生存條件不僅是被動地適應,而且要主動地改造,創造物質與精神財富以服務并改善自己的生活。這種在為了生活、服務生活的過程中所創造出的物質與精神成果就是社會的文化或文明,其中不僅包括社會的物質成果,而且包括精神成果,這種精神成果不僅包括智力性的科學技術成果,而且包括對善的生活、合理生活方式的理解與追求。因此,所謂人的理性生活就是一種合乎科學規律與善的價值觀念的生活。
第二,對意義與價值的追尋與建構是生活的本質。追尋合理的生活方式,不僅是人類群居的需要,也是人追求善良、健康合理生活的內在需要。用中國哲學話語來講就是“成物”與“成己”。所謂“成物”,就是創造外在于己的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成果,對人類社會文化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所謂“成己”,就是在“成物”的創造過程中,使人自身內在的心智能力和道德人格得到發展和提升。人在創造藝術作品的過程中使自己成為一個藝術家,人在行善利他的行為過程中使自己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即慈善家、道德家,或君子、圣賢。這種成物成己的創造生活、文化、文明的生活追求,按中國古代經典《左傳》提出的“三不朽”觀念來講,“成物”表現為“立功”、“立言”,而“成己”則表現為“立德”。
第三,對理想、幸福和德性的追求就是對好生活的追求。人作為有意識的存在,這個存在既包含著對過去的記錄和反思,也包含著以未來為指向的規劃和憧憬。一個喪失對過去的全部或部分記憶的人,與一個不能規劃或想象未來的人一樣,充其量只能過一種非常不完整的生活。充實的人生往往是與高度自覺的人生規劃相聯系的,它是人的連貫的、系統的目標和意向,包含著一個人的持久的價值追求。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必須要有過一種好生活的理想,要有幸福的期待與追求,要有自我完善的憧憬和目標,要不斷實現從現實的我到理想的我的超越。
意義與價值是未來、應該和理想賦予我們的。如果一個人的生活和人生沒有了目標,那在某種意義上就失去了意義和價值,至少這種意義和價值就會減少。有理想目標,才會有目標實現的愉悅感受,而這種愉悅體驗就是幸福。身體健康,豐衣足食,美麗的家園,良好的人際關系、安全公正的社會,健康的心智,快樂的心態,自我價值與尊嚴的實現,這些幸福的要素都是我們每個人所期盼和向往的,也使我們的人生和生活有了目標和價值。人們追求德性、完善、和諧、公正,就是追求一種理想、幸福的好生活。
人的生命存在是生活的基點,人生價值的追求是生活的展開過程,而人的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則是生活的歸宿。生活或者說人的生存、生活與交往的社會性決定了生活需要倫理的指導和調節。
生活這一概念雖包含著上述豐富的含義和本質,但在狹義上往往是指與“政治生活”相區別的“日常生活”。“不同的社會對于何為‘日常生活’有著不同觀點。然而,他們都大致將‘日常’定義為日復一日所發生的事情,它們是那些源于尋常‘卻沒有明顯標志的事情’”*。“我們可以將日常生活狀況有效地稱之為‘生活世界’(Life world),這個術語是在即將進入20世紀時由現象學派哲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創造的。”*戴維·英格利斯:《文化與日常生活》,11、1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日常生活是維系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續發展不可缺少的庸常的、反復的生命活動,即日常實踐或日用常行。按赫勒的理解,所謂日常生活,是“指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3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這一看法注意到了日常生活與個體的生存、延續的聯系,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要為吃穿住行等基本物質生活去奔波、奮斗、交往。這種日常生活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它顯然不同于人的制度生活,但它是人的其他歷史活動的起點。
制度生活是指人在特定的制度體系中展開的生活。在制度體系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觀念受到制度、社會給定的規范的約束,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往往通過與社會制度和規范相符的程度來加以判斷,這些制度不僅僅具有規范的意義,而且具有法律的意義。制度生活往往不具有自在性,不是人的自在生活,而是一種社會制約性的生活,要求人們在某些具體場合遵循制度和規范。日常生活是人的一種自在性、自主性的生活,是在非制度約束情景中的生活。日常生活具有明顯的自生性、習慣性和情感性等特征,人在這種生活中“缺少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性實踐的空間, 人的行為以重復性的實踐為特征, 他直接被那些世代自發地繼承下來的傳統、習慣、風俗、常識、經驗、規則以及血緣和天然情感等所左右”*衣俊卿:《現代化與日常生活批判》,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盡管日常生活也受到社會制度和規范的影響,但在日常情景之中,日常生活總是試圖擺脫社會規范給定的約束。制度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具有思維和理性的色彩,往往具有模式化、穩定性的特點;而日常生活則更多具有情感性和情景性,更具有活力,因而往往是生機盎然、豐富多彩的。當然,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隨心所欲的,它同樣具有生活的規則,只是不像制度生活那樣認可制度或規則的理所當然性,而是更具有批判性。
在1978年前,中國人的生活是被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所裹挾的生活,連談對象這種極其個人的事件都要得到組織的審查批準,因此,那時社會的主流道德必然只能是一種建立在革命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教化道德。在改革開放后,隨著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中的弱化,社會更加開放、多元,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也日益突顯,再用過去那種教條化的革命道德來指導日常生活中的民眾,顯然是力不從心了。為什么近年來國學特別是儒學在民間社會再次熱起來了呢?這是因為,儒家倫理是一種建立在人性與人倫日用基礎上的日常倫理和生活規則,儒學本質上是生活秩序的維護者,是高尚人格的倡導者。到了漢以后,儒學和儒家道德雖被高度政治化,但它從來沒有失去其生活基礎和民眾根源。
日常生活確實具有某種客觀的既成性、自在性。日常生活中的個體,在他出生來到這個世界時,就面臨著客觀已經存在的國家、民族、家庭等既成的客觀環境,這是他只能認同、接受而無法選擇的,而且他還無形中受到這些既成條件與傳統的影響,它們塑造著他的生活習慣、日常趣味,制約著他的行為方式。這樣,日常生活的自在性就強于社會的制度生活。所謂自在性,既是指獨立于人的目的性活動,也是指與自覺相對的非反思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日常生活完全沒有反思性,而只是說相比較在一定意識形態或者制度指導約束下的高度自覺性,其反思性與自覺性要稍微弱一些。這是對日常生活的主體來說的,但作為一名日常生活的研究者,揭示人們日常生活行為背后習而不察的文化原因,則是非常自覺的研究活動。
西方文化比較強調生活世界與理念世界或者終極關懷的疏離,比如宗教,大多都是以否定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超越現實世界,進入極樂世界為旨歸的。可是,中國哲學卻非常強調日用即道的觀念,強調人生、人倫之理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人生之道、人倫之理并不遠人,即所謂“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生活的極高明的道理就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與人倫交往中。“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的道必須貫徹、完成于人倫日用中。
日常生活雖然也離不開人與人的交往,但日常生活卻體現了對個體生命存在的維護,對生命價值的肯定與確證,或者說日常生活主要是以個體為承擔者的。維護生命存在的日常生活,相較于人的政治、科學、藝術生活,具有先在性。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78-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將上述論述看作是馬克思的偉大發現:“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7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雖然各民族和地區的日常生活似乎大體上是差不多的,但正如格奧樂格·齊美爾所指出的:“即使是最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態,也是對更為普遍的社會和文化秩序的表達。”*“換言之,每一個群體的生活世界是由這個群體的文化所塑造的。個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他們所屬的不同群體中所有相互交織的文化力量組成,并且由他們生活其中的社會語境所構建。”*戴維·英格利斯:《文化與日常生活》,4、15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人類是文化的存在,他們的行為取決于人們不同的觀念和態度——即文化,也就是人們長期以來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性和(或)養育他們成長的特定社會群體所形成的文化。一個特定的群體如何思考和做某一件事,是由該群體的文化而非本能決定的。反過來說,日常生活在自身延續的同時,也以習俗、常識、慣例、規范、傳統等形式使一定民族與人群的價值—倫理文化成果得到了傳承。因此,生活倫理學應該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文化的詮釋分析和價值評估。
二、生活與倫理的關系
生活與倫理的關系如何?生活是為了倫理?還是倫理是為了生活?
顯然,生活對于倫理來說具有存在的優先性,因此,從根本和終極的意義上來說,只能是倫理為了生活,使生活更美好,而不能本末倒置,使生活一味地曲從于倫理。當然,為了使生活更有價值與意義,我們需要自覺服膺那些符合生活真理與善價值的倫理,因為倫理是賦予生活以價值與意義的重要價值向度之一。生活是事實存在,倫理是價值意義。生活是倫理的來源,倫理提升生活的意義。道德作為人的價值自覺與意義追求,其目的是為了人們更好地生活。對意義與價值的追求是以人的存在為前提的,但是對意義與價值的追求卻是生活的本質所在。
在生活與倫理的關系上,倫理要以生活為前提,倫理源于生活,因為倫理是一定民族文化核心價值觀、生活方式的集中體現。如果一定的倫理脫離了其生活本源,就會成為人們生活的一種異己力量,必然是沒有生命力的。“活”先于“善”,生活先于道德,道德“參與”生活而不僅僅是“規范”生活。人為了“活”,有時可能會被迫放棄或違背“善”, 這可能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倡導生活要有倫理,還是意在讓倫理影響并規范引導生活。
強調生活之于倫理的這種先在性,就在于強調倫理從根源上是源于生活的,倫理產生之后其作用的發揮,一定要強調生活化。一定的倫理規范原則只有貼近生活、貼近實踐、貼近民眾,才能內在于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才會實際發生作用,而不是外在地強行規約生活,否則,就有可能出現倫理的異化,即源于生活最終卻由于脫離生活而反對生活。存在先于本質,生活必然先于道德。
道德需要融于生活,或者說生活中應該滲透著道德,換句話說,生活雖然是道德之源,卻需要接受道德的指導。但這種指導最好不是道德強加于生活的,而是生活內在地需要道德的指導。一方面,過一種美好的、善的生活是道德的目的,道德必須落實于生活實踐中。弗蘭克納認為:“社會必須記住:道德是用來幫助人們的善生活的,而不是要對他們進行不必要的干涉。道德為人而設,不是人為了道德。”*威廉·弗蘭克納:《倫理學》,24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另一方面,生活確實也離不開道德的指導,道德使人的生活更加合理,更能體現出人性的光輝,更能實現人的幸福。道德使得生活更加美好。一個沒有道德的人,他的生活不可能是美好的。沒有道德的指導與約束,生活就沒有和諧;沒有道德的升華,生活就沒有光明。“在社會中,沒有人認為流氓、無賴可以出人頭地,流氓、無賴們自己也不會這么認為。不公正的生活很容易成為缺乏保障和讓人憂慮的生活。如果有人靠偷盜、詐騙發跡,那么他的財富最終極易化為烏有。”*西蒙·布萊克本:《我們時代的倫理學》,97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倫理道德使我們的純粹自然生活提升為德性或倫理生活。人們基于純粹生理需求滿足的生活是一種自然生活,而有人類文化與道德指導的生活則是一種屬于人的有意義、有價值的德性生活。自然人經過“人化”后,在某種意義上說,人的純粹自然性已經相當程度上被“人化”了,這就像不能把人的吃等同于豬的吃,也不能把人的性活動完全等同于動物的交配一樣。但也不可否認,處于不同人生境界的人,其人化、文化、道德化的程度是不同的。馮友蘭先生曾經在其《新原人》一書中把人生境界分成“自然”“功利”“道德”與“天地”四個層次。他認為,處于自然境界的人對生活的自覺性不高,“少知寡欲”,“不著不察”,過著一種原始自然的生活。處于功利境界的人,其行為都有他們所確切了解的目的,但這種目的都是為了利,而且都是為了私利。而處于道德境界的人,他們都知道人的生活是離不開他人與社會的,人的生活資料的取得,必須盡倫盡職。功利境界的人,其行為是求利,而道德境界的人,其行為是行義,即遵照“應該”以行。行義之人,其行為不能以求他自己的利為目的,而是要利人助人的。而天地境界的人,其覺悟就更高,自認為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他的生活與道體完全合一,人得到徹底覺解,知天樂命。生活是生命的存在與延續,倫理是生活的意義與價值的規范體現。直面生活又要反思生活,面向生活又要提升生活。倫理離不開生活,生活又需要倫理提升。生活只有經過文化、倫理的塑造與引領,才是真正人的生活,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文化與倫理的價值就在于塑造、引領生活。
對生活倫理的探討與建設是為了倫理生活,但它卻不等于倫理生活。追求理想是為了理想的生活,追求道德是為了道德的生活。倫理或道德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動中已經具有倫理價值并符合倫理規范的善生活。它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道德思考與道德習慣。*M·奧克肖特·巴比塔:《論人類道德生活的形式》,載《世界哲學》,2003(4)。道德思考反思批判現實并建構理想道德生活,而道德習慣則反映體現現實生活。在人的道德生活中,這兩種意識與行為的要素實際上是統一的,但在人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后者的因素即道德習慣的因素要更多一些。無論是學理化的道德、制度化的道德,還是意識形態的教化道德,由于其具有更高的自覺性,因此,道德思考與反思的因素要多一些。這兩種道德生活類型構成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常態。不斷追求理想的道德生活,過著日常的現實道德生活,為了追求理想的道德生活,人們不斷反思并改造現實道德生活,構成了人類道德生活的動態過程。
日常生活在空間維度上是由社會行動聯結而成的,它不僅是生存、謀生的行動,也包含人際間性的交往活動,即可分為個人之“日用常行”和人際間“人倫關系”兩個方面。在時間維度上,日常生活是歷史性的“意義結構”, 也就是歷史積淀下來的文化傳統、以習俗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富有價值內涵的民族生活方式。兩者的重合則構成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圖景。正如德國學者許茨所說:“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主體間際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體間際的,是因為我們作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過共同影響和工作與他們聯結在一起,理解他們并被他們所理解。它之所以是一個文化世界,是因為對于我們來說,這個日常生活世界從一開始就是意義的宇宙,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意義結構。”*阿爾弗雷德·許茨:《社會實在問題》,36-37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這就是說,日常生活本身是實踐的、行動的、交往的現實生命活動,這種實踐、行動與交往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傳統、習俗以及其中所蘊涵的價值意義所決定的,這兩者的交集使日常生活世界結構得以形成和維持。
日常生活中的人,首先是以“我”的個體性存在的。生命、生活總是你的生命與生活,別人是取代不了你的活動、選擇與決定的,你的生老病死,必須由你來承擔。當然,作為人的存在和生活,肯定也是社會性的、交往性的,或者說是人際間性的。我之生命存在,是由于父母的生產活動而產生的,因此,我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要面對我和父母的關系。如果我父母不是生了我一個,那么,我就還要面對兄弟姐妹的長幼關系;我長大了,要結婚了,就會面對夫妻關系;我在社會上去討生活,求發展,又要面對師生、朋友、同事、上下級等關系。這些日常活動與交往,離開了倫理的規約與指導,將無法順利進行。
日常生活與倫理有著非常直接與密切的聯系,而且通過風俗直接交集在一起。倫理在最初產生時,就是一種習俗,現在英語中的“ 道德” (morality )一詞就起源于拉丁語中的“mores”, 為“風尚”“習俗”之意。風俗就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積累起來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習慣。社會在不發達的階段,人們的生活主要是求生存的日常生活,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的道德還不像后世發達社會那樣具有高度的自覺性,風俗與道德有更多的重合性,因此,日常生活與習俗、道德有著密切的聯系。即使社會文明發達了,產生了制度、政治、藝術等更加自覺的非日常生活及意識形態(教化)道德,傳統、習俗、常識、戒律等道德形式還是常常與日常生活存在更為密切的聯系。
日常生活道德與習俗緊密聯系,這使它與歷史傳統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系,繼承的因素多,變化的因素較少。在傳統中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 奉行“道在日用常行間”, 這意味著日常生活的言行舉動無不與道德要求聯系在一起,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無不要求符合禮儀禮節,從尋常百姓的待人接物到皇朝貴戚的祭祀朝拜,無不為龐大的禮儀制度所覆蓋。當然,這種體現在習俗禮儀中的日常生活倫理也是在不變與變的辯證統一中延續發展的,人類文化的進步一方面要保留傳統與習俗,但同時也會與時俱進,移風易俗,在新習俗中,也一定體現了當時人的價值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日常生活與倫理總是動態發展地密切聯系在一起。
三、日常生活倫理及其研究
日常生活倫理就是指直接產生于日常生活中的與習俗、禮儀、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倫理觀念與行為規范。它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日常生活倫理具有基礎性與先在性。日常生活倫理在人們的生活中具有基礎性與先在性的地位,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可須臾離的。在人們的生活中,這種日常生活倫理對于生活于一定歷史文化中的個體來說,具有某種前在性與既定性,按羅爾斯的說法是一種“社會整體的契約”*約翰·羅爾斯:《正義論》,51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對人們的觀念與行為選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型塑作用。正是這種前在性與既定性,使日常生活道德更具客觀性與環境的壓力,具有普遍的約束力,而基于反思自覺的信仰與教化倫理則具有更多的應然倡導性特征。適應、遵循基于社會文化傳統的日常生活倫理,是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具備的基本文明素質。
第二,日常生活倫理是實然性與應然性的高度統一。道德規范、習俗或習慣是日常生活世界得以保持延續性和同質性的基本內容之一, 它們原本就與日常生活世界相生相長,這說明日常生活倫理較之意識形態的教化倫理,具有實然與應然的高度統一性及知行合一性。意識形態立足于教化,因此,可能具有更多的應然指向性,從而有可能疏離于生活。我們的生活固然離不開一定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與主流倫理來引領、規約,但確實需要一種更加親民的日常生活倫理來指導民眾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世界并非自然就是規范化、秩序化的,相反,由于日常生活是異質成分駁雜混存的,因而穩定的生活秩序需要不斷進行修補調整才能得以維持。因此, 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建構需要進行還原性的、合理性的理論論證,這恰恰就是日常生活行為倫理學所要做的工作。
第三,日常生活倫理具有習而不察的自發性、世俗性。日常生活倫理規范多是日常生活中普遍流行的、習以為常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是日常生活中的集體無意識。對于道德主體來說,這些生活倫理雖然已經成為普遍的行為模式,但在意識上卻不是非常自覺的,而是無意識地認為踐行這些規范是理所當然的。正因為如此,日常生活倫理世俗性強,超越性差,實用性與靈活性強,普遍性與原則性弱,常因不同主體、關系、情境而改變倫理態度與規范原則。但這并不是說它就沒有任何基本的、普遍的德性與規范,按照赫勒的看法,下述四種德性或規范是日常生活倫理的基本原則:“遵守諾言,講真話,感恩和基本的忠誠。盡管這四種德性在無數場合被拋棄,但它們依舊代表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方面,舍此我們幾乎沒有機遇成功地駕馭日常生活的激流。”*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91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赫勒提出的這四種具體的日常生活倫理的原則是實質主義的基本品德要求,類似于中國傳統道德中的誠信、報恩、忠誠,雖然其具體內容還可以討論,但起碼在他看來人類是有某種普遍的日常生活倫理要求的。由于生活情境的多變性,除了概括實質性的對人的基本品德要求外,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文化還概括出“中庸”這一普遍適用的、形式化的“至德”,與亞里士多德把德性的特征概括為“中道”有某種契合。可見,無論是從內容還是從形式上,都可以對日常生活倫理的普遍要求進行探索。
第四,日常生活倫理具有經驗性與具體性。相較于具有較強自覺性和抽象性的學理化、制度化及意識形態化的道德,日常生活倫理規范具有質樸、具體的特點。常識、習慣等日常生活規范既然是規約具體的日常生活的,那它肯定會表現出一時一事何者當為、慣為的具體性,這種經驗的、庸常的具體規范更能指導具體的實踐,更能在主體間產生“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共感與共識,得到主體的普遍認同,因此,也就能更為有效地塑造、建構、指導、規約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倫理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而經驗性與具體性可能是其更為突出的特點。
社會生活日益世俗化,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益突顯,這要求我們必須重視民眾日常生活倫理的研究。現代道德中的主體間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現代倫理意識的形成是一種平等主體在對話協商基礎上達成的價值共識,一種倫理體系如果嚴重脫離民眾的實際生活那將成為偽善。生活是倫理和道德產生與發展的源泉,若離開生活本身而從某一既定的倫理體系與道德原則出發來解讀現實生活,就會本末倒置。對民眾日常生活倫理的研究將成為中國倫理學新的突破點和生長點。
生活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在我們看來,大致包括如下三個方面:(1)日常生活行為倫理;(2)日常生活交往倫理;(3)民眾價值心理。如果要簡單地給上述三個方面一個關鍵詞的話,那就是行為、交往與價值心理。生活倫理首先要面向生活行為本身,對生活行為現象進行倫理分析詮釋,以指導民眾確立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是社會生活,因此,人有其生活和交往的不同場域和交往對象,生活倫理應該從群體的視角和實存的現狀分析的角度來研究這些交往倫理,做出描述、分析、評估和引導。人的生活和交往都是在一定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的,分析當代中國人的價值心理,幫助人們厘清價值沖突,以正確的價值觀去指導民眾的生活,這將是生活倫理學的歸宿和目的。
日常生活倫理的研究與以往教化倫理的致思方向和學術旨趣是全然不同的,是面向民眾的、生活的、實踐的,是科學的、詮釋的、反思的。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倫理研究是既“說事”又“說理”的,是把應然的“道理”從傳統或者現代的“事實”中概括、提煉出來,“事實”是“道理”的基礎,“道理”是“事實”的“應然”,而不像以往的教化倫理那樣只是一味地給人們講“應然”之理。這是因為生活本身就是生存的事實和意義的探索的統一。這也是我們所堅持的“經史”合一方法最重要的特點。因此,進行生活倫理研究不僅需要視角的轉換,而且應進行方法論上的變革,需要把敘事描述與詮釋分析相結合、歷史透視和現實觀照相結合、社會觀察與文化分析相結合、價值批判和規范建構相結合。只有進行視角和方法的變革,才能實現下述研究目標:第一,探尋生活的意義;第二,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形成生活倫理的價值觀念和規范;第四,指導民眾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