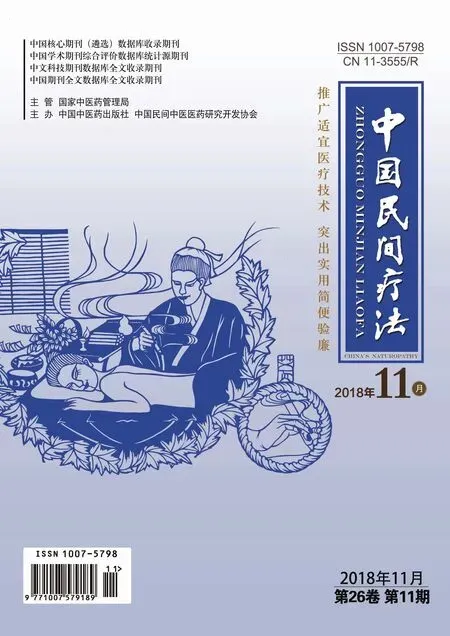李佩文治療胃癌經驗總結
倪育淳,趙紅艷
(山西省中醫院,山西 太原030012)
胃癌是我國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每年造成很重的醫療衛生負擔[1]。西醫對胃癌的治療,早期主要以手術治療為主,中晚期以放化療和靶向治療為主。由于胃癌術后容易復發轉移,且胃癌發現時多為晚期,導致中晚期患者的生活質量較差,中醫藥在治療胃癌方面有獨特的療效。
李佩文教授為中日友好醫院中西醫結合腫瘤內科專業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李佩文教授認為,脾胃損傷為百病之源,治療腫瘤當從脾胃論治,主張以扶正培本為主治療。胃癌的治療更以顧護脾胃為主,益氣健脾,調暢氣機,化痰逐瘀,正本清源,祛邪外出,并運用升降理論治療胃癌,臨床效果較好。筆者有幸跟隨李佩文教授工作和學習,現將其治療胃癌經驗總結如下。
1 李佩文教授對胃癌病因病機的認識
1.1 脾胃虛弱學說 金元時期李杲編著的《脾胃論》核心學術思想包括:脾胃為元氣之本,是人體一切生命活動的動力來源;脾胃為人體氣機升降的樞紐;脾胃為百病之源;脾胃為論治之本[2]。李佩文教授認為脾胃損傷為百病之源,治療當從脾胃論治。胃癌病位在中焦脾胃,脾胃虧虛,正虛邪積是胃癌發生發展的主要病機,如《醫宗必讀·反胃噎膈》曰:“大抵氣血虧損,復因悲思憂恚,則脾胃受傷。”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運化失常,納食不佳,脾氣受損;衛外功能失調,邪毒內侵,蓄結不除,導致癌瘤生成。
1.2 氣機不暢學說 李佩文教授強調脾胃為人體氣機升降的樞紐,常提及李杲在《脾胃論·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中提出:“蓋胃為水谷之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為天者也;升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為地者也……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升以而降,降以而升,如環無端,運化萬物,其實一氣也。”李杲闡述了人體飲食消化吸收的全過程,強調了脾升胃降在飲食運化中的樞紐作用[3]。
1.3 痰瘀互結學說 六腑以通為用,胃氣宜降宜和,升降則胃氣和順,如胃氣不和,氣機逆亂,中焦輸布津液不利,久則聚而成痰,痰濁阻滯氣機,瘀血內阻,痰瘀互結,凝聚成瘤。李佩文教授認為本虛為脾胃虛弱,外邪(情志、飲食不節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胃氣失和,痰氣交阻,凝聚成癌,其本虛為脾胃虛弱,標實為痰瘀互結。
2 李佩文教授對胃癌治則治法的認識
李佩文教授認為胃癌為脾胃虛弱,氣機升降失常,痰氣交阻,瘀血內阻所致,導致胃癌的基本病理過程是脾胃虛弱。胃喜濕而易傷陰,脾升清功能失職,未能為胃行其津液,則濕濁內蘊脾胃,變生為痰瘀。胃的主要功能集中在“降”,以“通”為用,以“降”為順,降則和,不降則滯,化生濕、痰、瘀等腫瘤病理產物,漸而形成癌毒而致胃癌,脾胃失于和降,易產生很多升降失調癥狀,如惡心、嘔吐、呃逆、大便失調等癥狀。
李佩文教授認為胃癌形成的病機為脾胃升清降濁功能失職,故在治療上根據臟腑生理特性及基本病機,恢復脾胃升清降濁功能,為治療胃癌的根本原則。脾為臟,“藏精氣而不瀉”,以虛為主,治療上以補氣升清為主;胃為腑,“傳化物而不藏”,以實為主,治療上以降氣、行氣、理氣降濁為主,益氣升清與降濁相輔相成,使機體達到和諧相處。
李佩文教授在治療上一直強調“帶瘤生存”“人瘤共存”的思想。李佩文教授認為,“帶瘤生存”是中醫治療癌癥后常客觀存在的事實,注重“人瘤共存”的和平共處的平衡狀態,強調“和”的思想,即調和氣血、陰陽、臟腑、經絡,使之平和協調,改變人體內環境,從而達到治癌或人癌共存的目標。
李佩文教授在藥物應用上,強調益氣健脾、疏肝理氣之法,以恢復機體氣機升降平衡,常用代表方劑為四君子湯合逍遙散。臨床辨證為胃陽不足者,常以養陰降胃之法,方用麥門冬湯。李佩文教授在扶正補虛基礎上,注重祛除濕痰瘀毒及阻礙氣機平衡的病理產物,如痰濕較重者,則常用平胃散、小半夏湯、三仁湯以達祛痰、祛瘀、解毒之目的。
3 驗案舉隅
患者,男,46歲。胃癌術后化療后1年,復查提示腹腔淋巴結轉移,肝轉移,于2014年3月14日就診于中日友好醫院。癥見:面色晦暗,四肢乏力,形瘦,納差,腹脹,進食后尤甚,眠差,大便溏薄,小便利,舌淡暗,有瘀斑,舌苔白膩,邊有齒印,脈弦滑。
處方:黃芪30 g,黨參片20 g,炒白術15 g,茯苓30 g,半夏10 g,陳皮10 g,薏苡仁30 g,炒山藥18 g,柴胡10 g,枳實15 g,厚樸15 g,三棱10 g,莪術15 g,焦三仙各15 g,雞內金30 g,浙貝母30 g,萊菔子30 g,首烏藤30 g,甘草片3 g。15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分服。半個月后復診,患者精神好轉,納食增加,腹脹減輕,大便成形,舌質轉紅,舌苔轉薄,但失眠未見明顯緩解,上方去黃芪、厚樸,加藤梨根30 g,炒酸棗仁30 g,遠志30 g,15劑。服藥后進食基本正常,腹脹消失,睡眠好轉,繼續以益氣健脾法治療半年,后改為補中益氣丸服用。
按語:該患者為胃癌術后復發,經歷手術及化療,脾胃更傷,運化失職,濕濁內阻,氣機不暢,加之病久瘀血內停,故辨證為脾胃虛弱,氣機不暢,濕瘀內阻。治以益氣健脾,疏肝理氣,祛濕活血。方中黃芪、黨參益氣健脾,炒白術、茯苓、半夏、陳皮、薏苡仁、炒山藥、浙貝母健脾祛濕,軟堅散結,柴胡、枳實、厚樸、萊菔子燥濕行氣,三棱、莪術活血散結,焦三仙、雞內金消食散結,首烏藤活血安神,甘草調和諸藥。復診時,患者舌質轉紅,恐補氣過甚,故去黃芪;舌苔轉薄,故減少行氣燥濕之藥,防止耗氣過度;睡眠未見明顯改善,故加用炒酸棗仁、遠志加強安神之效。治療過程中,以益氣健脾固本為主,行氣燥濕、活血散結為輔,根據隨癥變化之不同,及時調整藥物。該患者為胃癌晚期,西醫治療手段有限,積極使用中醫藥辨證施治,可改善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達到較好的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