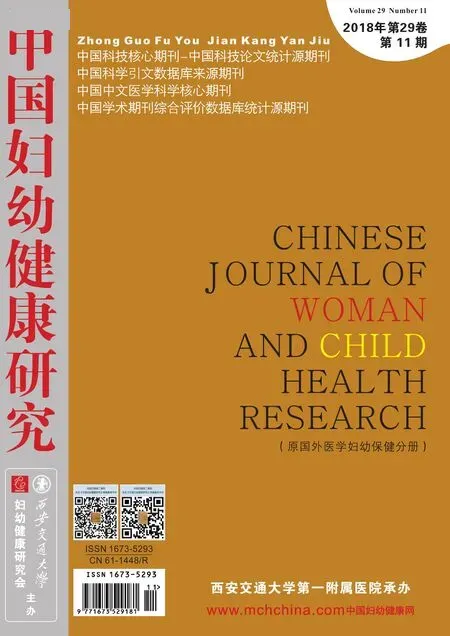自閉癥譜系障礙與維生素D的流行病學研究進展
中國預防醫學會兒童保健分會
自閉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其他中文文獻又稱孤獨癥譜系障礙,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以社會交流和交往缺陷、興趣狹窄、行為重復刻板為主要特征。最近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Ⅴ)將兒童自閉癥(AD)、未分類的廣泛性發育障礙、Asperger綜合征統稱為ASD[1]。李洪華等于2014年報道稱ASD患兒社會適應能力低下,目前沒有特效的治療藥物,給社會、家庭帶來極大的精神、經濟負擔,兒童ASD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
ASD病因復雜,目前認為ASD源于遺傳學,由環境危險因素誘發產生。近年來對ASD與環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母親孕期風險因素、感染、免疫、營養問題等。董涵宇等于2017年報道稱維生素D(VitD)缺乏是世界范圍內的公共健康問題,生命早期VitD缺乏可導致腦部發育異常,損傷兒童學習、記憶及認知等功能。在2008年,Cannell[2]提出假設,認為胎兒期或兒童早期的VitD水平降低是ASD一個重要的環境危險因素,從那以后VitD與ASD的相關性成為流行病學關注的熱點。
1 ASD患病率
早期報道ASD為罕見病,近20多年來,各國報告的ASD患病率均出現上升趨勢[3]。美國、英國、韓國等國家及時開展ASD患病率調查,美國甚至有專門的ASD監測網絡,能及時更新數據。
1.1各國ASD患病率
美國孤獨癥和發育障礙監測網絡數據顯示,美國8歲兒童ASD患病率從2000年的6.7‰上升到了2012年的14.6‰[4],大約每68個兒童中就有1個ASD兒童。Russell等[5]于2008/2009年對英國14 043例6.3~8.2歲的兒童資料的調查研究顯示,ASD患病率為17‰。2014年,Kim等[6]對韓國55 266例7~12歲小學生開展流行病學調查,數據表明,ASD的患病率高達22‰。
1.2我國ASD患病率
李洪華等于2014年報道稱迄今為止,我國尚沒有全國性的ASD流行病學調查數據。2017年,戴瓊等對2000—2016年中國兒童ASD患病率進行了Meta分析,兒童ASD患病率合并為2.4‰[95%可信區間(CI):1.8~2.9],且呈逐年上升趨勢。2017年,石慧峰等Meta分析了中國0~6歲兒童ASD患病率,患病率在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分別為3.52‰(95%CI:1.48~8.34)和3.48‰(95%CI:1.77~6.84),兩個時期差異未見統計學意義,結論是2006—2015年ASD患病率保持穩定。英國Sun等[7]對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地區1987—2011年的18個關于ASD患病率調查的Meta分析研究發現,3個地區的總患病率為2.66‰(95%CI:1.85~3.46),其中中國大陸為1.18‰(95%CI:0.82~1.53),患病率呈上升趨勢,從2000—2004年的0.85‰(95%CI:0.30~1.39)上升到2010—2011年的1.64‰(95%CI:0.70~2.57)。
雖然對于ASD患病率是否上升,各研究得出了不同結論,但對于ASD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李洪華等于2014年的研究結果歸結于診斷技術的提升,以及人群意識的提高。另一方面,國內的ASD患病率低于國外報道,武麗杰于2013年分析認為其原因可能為篩查和診斷的方法不同,包括:①調查納入的年齡段不同;②調查時間點不同,疾病診斷和分類的依據發生變化;③國內主要為各地區橫斷面調查,缺乏動態監測數據。因此,我國需要建立統一、規范的ASD患病率調查方法和篩查、診斷標準,以獲得可靠的ASD患病率。
1.3性別與ASD患病率
雖然國內外及各地報道的ASD患病率比例不一,但性別差異趨于一致,均為男多于女。美國的監測報告顯示,2012年,男孩的ASD患病率顯著高于女孩(23.6‰ vs. 5.3‰)[4],男女比例約為4.5∶1。戴瓊等于2017年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男性ASD患病率為3.5‰(95%CI:2.6~4.4),女性為0.7‰(95%CI:0.5~1.0),有統計學差異。石慧峰等于2017年Meta分析得到2006—2015年0~6歲兒童ASD患病率男女比例為2.59∶1。
2兒童ASD與VitD水平相關性
兒童VitD水平與ASD相關性的研究開展較多。近期,已經有很多證據表明,ASD兒童的血清25-(OH)D水平較正常兒童低;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兒童VitD水平與ASD診斷量表評分之間存在相關關系。
2.1 ASD兒童的血清25-(OH)D水平
2016年,Wang等[8]對ASD患兒血清25-(OH)D水平進行了Meta分析,共納入了11個研究,包含了870例ASD患兒和782名健康對照兒童,結果表明ASD組25-(OH)D水平顯著低于對照組,提示ASD患兒存在VitD不足。為了排除家庭社會經濟狀況的混雜影響,有研究納入同胞作對照。2014年,Kocovska等[9]的研究顯示,調整了季節差異后,ASD患兒的25-(OH)D水平顯著低于其健康同胞的。2015年,Fernell等[10]對58個ASD患兒及其健康同胞用出生時代謝篩查的紙血片進行了VitD含量的檢測,結果表明ASD患兒組外周血中25-(OH)D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對照兒童(24.0±19.6nmol/L vs.31.9±27.7nmol/L,P=0.01)。
2.2 VitD水平與ASD診斷量表評分
也有研究試圖揭示VitD水平與兒童ASD癥狀的相關性。2014年,Gong等[11]的研究發現ASD患兒血清25-(OH)D水平與兒童孤獨癥評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總分呈現明顯負相關。2017年,徐寧安等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ELISA)檢測60例ASD患兒和60例健康對照兒童血清25-(OH)D水平,發現ASD組VitD水平明顯降低,但未發現其與CARS分數的相關關系。2017年,董涵宇等的研究結果顯示,ASD患兒血清VitD水平較健康兒童明顯降低,ASD患兒VitD水平與孤獨癥行為量表(ABC)總分、軀體行為、生活自理、語言、交往能區均呈負相關(r=-0.53,P<0.01;r=-0.40,P<0.01;r=-0.28,P=0.007;r=-0.25,P=-0.02;r=0.26,P=0.01);與CARS總分、模仿、非語言交流、整體印象能區均呈負相關(r=-0.35,P=0.001;r=-0.22,P=0.05;r=-0.248,P=0.02;r=-0.22,P=0.05);與社會反應量表(SRS)行為能區、孤獨癥治療評估量表(ATEC)社交能區亦均呈負相關(r=-0.54,P=0.005;r=-0.40,P=0.01)。
3 母親孕期VitD與兒童ASD相關性
對于母親孕期VitD水平與兒童ASD相關的人群研究很多都是陰性結果,但也有控制混雜的陽性研究結果[2]。2012年,Whitehouse等[12]對743名母親開展追蹤性研究,采集母親孕18周時的血樣,對其孩子在2、5、8、10、14和17歲時做行為量表檢測,結果發現,母親孕期VitD水平<46nmol/L者,與VitD水平>70nmol/L者相比,出生后的兒童在5歲和10歲更易發生ASD的典型臨床癥狀——言語發育遲緩。2013年,Whitehouse等[13]檢測929名孕婦孕18周時的血清VitD水平,發現生育過ASD孩子的3個母親,其VitD水平高于人群平均水平(58.02nmol/L);同樣,在Whitehouse等的研究中,406名母親的孩子完成了ASD量表測試,其母親的血清VitD水平與量表中大部分內容的分數無關。然而,血清VitD水平<49nmol/L的母親,其后代分量表的分數較高[比值比(OR):5.46,95%CI:1.29~23.05]。我國的Chen等[14]于2016年報道,病例對照研究68例ASD患兒,其母親孕11~13周時的血清VitD水平較正常兒童的母親同時期的VitD水平顯著降低(19.2ng/mL vs.24.3ng/mL),VitD水平缺乏率更高(55.9% vs.29.4%);此外,母親孕期VitD水平與兒童CARDS評分呈負相關。我國缺乏這方面的人群隊列研究,邵紫賢等于2014年的綜述中認為,盡管VitD在神經發育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很多學者所認同,但我國的大量研究只停留在動物實驗,需要開展更多的人群流行病學研究來揭示母親孕期VitD水平與ASD兒童及其認知的關系。
4 補充VitD與兒童ASD
2016年,Stubbs等[15]開展孕期補充VitD是否預防AD發生的研究。研究者招募生育過ASD患兒的母親,在之后胎次的孕期中補充每日5 000IU的VitD,分娩后,在哺乳期每日補充VitD 7 000IU,給非母乳喂養的新生兒每日補充1 000IU的VitD,直到兒童1歲。觀察這些兒童的AD患病情況,與文獻報道相比較,減少到1/4(5% vs. 20%)。
很多研究也顯示,兒童補充VitD,對改善兒童ASD癥狀有幫助。2015年,Azzam等[16]的隨機對照試驗報告,ASD患兒補充VitD 3個月后,其CARS分數、社會IQ比對照組有所提升。2015年,Jia等[17]報告稱,給32月齡的AD患兒補充2個月的高劑量VitD3(每月150 000 IU肌注,加每天400IU口服),血清25(OH)D水平從31nmol/L升高至203nmol/L,AD的核心癥狀有所改善。2017年,Feng等[18]報道,給37名ASD患兒[25(OH)D<75nmol/L]補充3個月的VitD,CARS和AD行為量表分數顯著提升。
5 ASD與VitD缺乏環境
綜上所述,很多流行病學研究已經證明ASD與VitD存在相關性,但是否也可以認為導致VitD缺乏的環境因素與ASD相關呢?皮膚利用光照中的紫外線合成VitD是人體VitD的重要來源。很多研究者研究了居住地光照的多少與ASD的關系。Cannell[19]于2017年的綜述文章中專門討論了陽光紫外線的獲得與兒童ASD患病的關系:有研究證明,陽光紫外線弱的地區,如城市、多云和多雨的地區,以及空氣污染物多的地區與ASD有關,因此可以用VitD理論來解釋其中的關系;此外,季節因素、人口遷移至高緯度地區,甚至胎次等與ASD相關,都可以用VitD理論來解釋。作者肯定了地理緯度與ASD患病的關系,高緯度紫外線弱的地區,其ASD患病是低緯度紫外線強地區的3倍。Hajar等[2]在2016年的綜述文章中提到:用緯度來解釋人體VitD的狀態是合理的,如果VitD水平低是ASD的危險因素,那么在VitD水平低的地區,其ASD患病率也應該高,反之亦然。不少研究也證明了這點。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果:VitD水平低的地區,其AD患病率不高,作者認為,這應該歸于診斷方法的問題。
6結論
隨著篩查和診斷技術的改進,ASD在我國兒童患病率呈上升趨勢,但我國仍需要篩查和診斷方法統一的大范圍流行病學調查,以獲得可靠的患病率數據。已經有很多證據表明,ASD兒童的血清VitD水平較正常兒童低;兒童VitD水平與ASD診斷量表評分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母親孕期VitD水平與兒童ASD相關;孕期補充VitD,能減少兒童ASD患病率;兒童補充VitD,對改善兒童ASD癥狀有幫助;兒童ASD與導致VitD缺乏的光照環境因素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