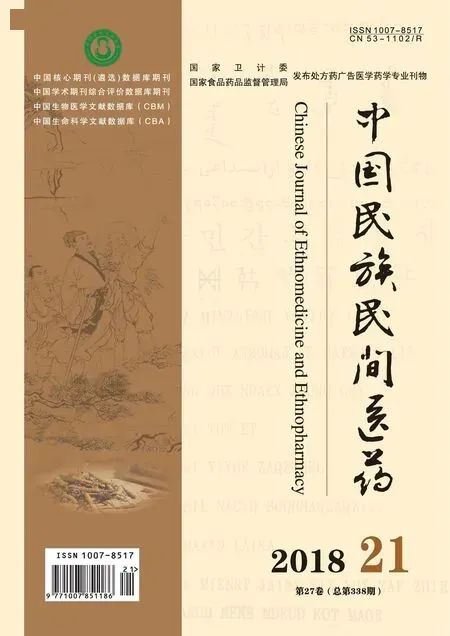傣醫“心”與中醫“心”之比較
西雙版納職業技術學院,云南 景洪 666100
中醫、傣醫是我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有相似之處,也各具特色。在傣醫理論學習過程中,部分概念易與中醫混淆,往往難以分清,筆者以“心”為例,把傣醫“心”與中醫“心”進行比較,總結如下。
1 “心”的哲學基礎
傣醫最早起源于古印度醫學,后經泰國經由南傳上座部佛教傳入我國西南地區,并在我國傣族聚居地與當地人民的實踐經驗相融合而形成的一門醫學。因此,傣醫學的傳承與發展與南傳上座部佛教息息相關。古印度醫學在發展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阿輸吠陀》中有關于健康與疾病的“三體液學說”及“五大元素”(地、水、火、風、空,其中疾病由風、火、水三要素的平衡遭到破壞而引起)是“四塔五蘊”學說的雛形。后經泰國由南傳上座部佛教帶入中國傣族聚居地與“本民族二元論”原理與思想融合后形成頗具自身特色的“四塔連心”與“識蘊”[1]。這使得傣醫學對于心臟的認識豐富而深刻,使傣醫之心有了外延和內涵、狹義和廣義之分。
中醫哲學的發展融合了道學、陰陽五行學說、精氣學說等各家學說,這些學說的出現與融入形成了中醫特有的思維形式。如中和思維、類比思維等。中醫學對事物的認識主運用這種特有的哲學思維,從宏觀的角度觀察事物,強調各事物間功能的聯系,注重整體上的研究。如天有六氣,地有五行,五臟配五行,人之五臟六腑應運而生,相生相克,且有陰陽之分。其中對心的詮釋就是對中醫哲學觀的最好體現。《說文解字》中對心有著這樣描述,“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凡心之屬皆從心,息林切”。“陽中之陽,心也”[2]。明代醫家張介賓在《類經》中也指出:“心為臟腑之主,而總統魂魄,兼該意志”,可見中醫之心分為有形之心與無形之心。
2 “心”的解剖
傣族有土葬、火葬、水葬和天葬四種形式[2],其中以火葬為主且最為獨特,火葬過程中需要用刀剖開尸體,這是傣族最早尸體解剖的過程,也是傣醫解剖學在同一時期領先于部分民族的原因。
傣醫在很早的時期就擁有自己的解剖學專著《嘎牙山哈雅》,在該專著中對人的骨骼、肌肉、內臟、胚胎等內容都有詳細的記錄。比如,對于心的描述為“心,偏于左側,色如蓮瓣的背面,形似含苞待放的荷花倒垂在兩乳之間”[3]。從記錄中可以看出,該專著對心的解剖位置、形態特征上描述都是十分詳細的。
中醫對“心”的描述,謂之于“在肺之下,膈膜之上,著脊第五椎。形如蓮蕊,上有四系,以通四臟。心外有赤黃裹脂,謂之心包絡”,“有血肉之心,形如未開蓮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氣血所化,生之本也,萬物由之盛長,不著色象,謂有何有,謂無復存,主宰萬事萬物,虛靈不昧者是也”。此“血肉之心”即指解剖之心,“神明之心”則相當于腦。可見,中醫的“心”,不僅僅是解剖結構的體現,它還是意識的體現。
3 “心”的生理功能
傣醫的四塔五蘊中,以土塔為中心,類似于宇宙中太陽的位置與作用。心屬土塔,在傣語中心稱之為“zai”,具有因緣集合之義,傣醫心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心是全身的中心,統領人的身體與意識;其二,心的功能源于因緣集合,形成于胚胎,變為神、識,是自然賦予的功能;其三,心在濡養全身的同時,受到人的神、志、意、思的影響,同時四者均依心而動。
中醫從整體觀念出發,認為“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有心主血脈和主神志[4]“心主血脈”,血在脈中運行,有賴于心氣的推動,心氣推動血液運行于機體各部分,以營養全身,保證全身各器官功能正常運行。“心主神志”,神志即人的意識與思維活動,是大腦功能的體現。《靈樞·本神篇》說:“所以任物者謂之心”,《靈樞·邪客篇》又有“心者,精神之舍”之說,心所運行的血液是神志活動的基礎,“心藏脈,脈舍神”[4],只有血脈充盈,人的精神才能旺盛,思維才能敏捷。
4 小結
傣醫與中醫對于“心”的認識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也有著較為顯著的差別。從臨床過程上來看,傣醫與中醫對于“心”功能的理解具有相似性,他們都認為“心”具有精神意識層面上的意義,類似于中醫學“神”的含義,但傣醫學的“心”不等同于中醫學的“心”。因受各自傳統文化的影響,二者在具體的內含上有著不同的闡釋。傣醫對“心”的認識更側重于實體解剖和功能對應的關系[5],臨床上對心的運用則多注重功能心的應用[6],其對心的認識主要從“四塔連心”和五蘊(特別是識蘊)理論加以闡述,臨床上較為側重“四塔連心”理論即心代表自然界一切物質運動變化規律的應用。而中醫常以“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來強調神的重要和指導臨床。
綜上,筆者認為對于“心”應該從兩者的來源、形成、歷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剖析清楚,才能夠更好理解兩者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避免相互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