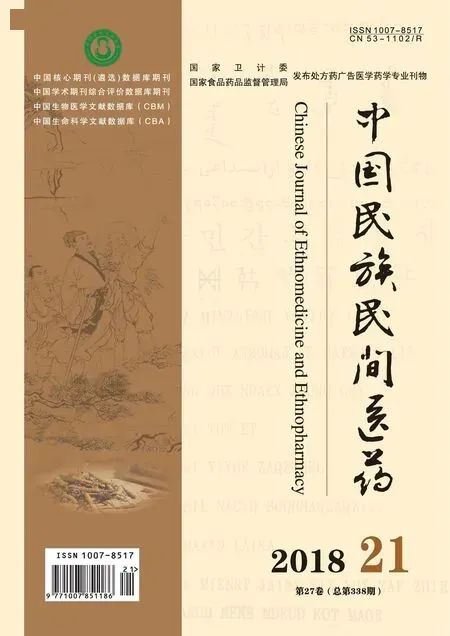基于大數據技術的名老中醫醫案價值挖掘困境及對策分析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云南 昆明 650021
傳統中醫藥學是古代哲學與古代科學的完美結合,從中醫藥學發展歷史看,中醫學的傳承與發展依賴于各個時期中醫醫師尤其是中醫名家對于臨證經驗與相關理論的不斷探索與創新。對于醫案的整理及研究是中醫學傳承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說:“中醫之成績,醫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經驗心得,醫案最有線索可尋”[1]。鑒于中醫藥療效確切、學術內容豐當、流散失傳迅速等特點以及國家對中醫藥發展的日益重視,近年來,隨著大數據的興起,國內學者對中醫醫案數據挖掘方法、電子病歷數據共享、中醫醫案數據庫建設等進行了研究,提出構建基于本體的中醫醫案知識服務與共享系統能夠實現中醫醫案管理和知識挖掘,利用文本挖掘能夠開掘出醫案中隱藏的大量知識[2];以及中醫電子病歷的標準化、結構化是實現醫案數據共享的基本方法等觀點[3]。但未對利用大數據技術挖掘名老中醫醫案價值的困境進行系統分析,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未涉足。鑒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對大數據技術在名老中醫醫案價值挖掘中的應用、面臨的困境進行分析,并結合學習、工作經驗提出解決策略,以期對進一步推進中醫藥文化傳承與創新有所裨益[4]。
1 名老中醫醫案與大數據技術
1.1 名老中醫醫案 名老中醫醫案,又稱為診籍、脈案、病案等,是名老中醫診療過程中對患者疾病的把握、臨床經驗、學術思想以及實施辨證論治的原始記錄和具體體現,是祖國醫藥文獻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文化發展的具體承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價值和研究價值[2]。
中醫醫案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經歷了十分漫長的發展過程。最早可追溯自殷商甲骨文疾病卜辭,至周代,各家據《周禮·醫師》中的記載均認為當時已有病歷記錄,但未流傳下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所載西漢醫學家淳于意創立的“診籍”可視為我國醫案源流,書中記載了25個病案,詳細記錄了患者信息和診療信息,雖然形式尚不統一,所記項目也不完善,但已具備了醫案的雛形[5]。
1.2 大數據技術 大數據通常定義為超出了常用硬件環境和軟件工作在可接受的時間內為其用戶收集、管理和處理能力的數據。很多大數據源是半結構化的,半結構化的數據源有一定的邏輯,但是可能并不漂亮。大數據也可以是非結構化的。而大數據技術主要指數據挖掘(data mining),也叫數據開采、數據采集等,就是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音的、模糊的、隨機的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之前無法察覺的,但又具有潛在價值的信息和知識的過程。數據挖掘的實質是綜合運用各種信息技術,對相關數據進行一系列科學分析和計算的處理,其核心是利用算法生成模型,然后再對模型進行驗證。這個過程需要用到數據庫、統計學、應用數學、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相關知識和技術。由此可見,大數據挖掘對數據分析師、數據挖掘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6]。
1.3 大數據技術在名老中醫醫案價值挖掘中的應用 經過長期沉淀,各類不同形式的中醫醫案紛紛涌現,面對海量而又不標準、不規范的中醫醫案信息,如何對其進行整理,分析挖掘出隱藏的價值,更好推動中醫文化傳承與創新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不斷興起的大數據挖掘技術為人們打開了中醫醫案研究的另外一扇窗,越來越多的學者將視角轉移到利用大數據挖掘技術進行名老中醫醫案價值挖掘上,取得了良好成效,證明了大數據挖掘確實適用于名老中醫醫案研究。大數據應用于中醫醫案研究主要集中于證候分析、用藥規律分析等方面,中醫醫案研究中常用的數據挖掘方法是聚類分析、關聯規則分析、回歸分析、因子分析等,還有粗糙集、貝葉斯網絡、信息熵理論等方法[7]。
總體說來,大數據挖掘已成為中醫醫案價值挖掘的重要工具,將來的應用前景也會更加廣闊。但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中醫醫案的數據挖掘多采用單一方法,即使同時運用多種數據挖掘方法,也只是進行相互比對,嚴重制約了所取得結果的效用度。由于中醫醫案的非結構化、非標準化,加上中醫文化價值認同度和知名度不夠高、對其研究的投入不夠等因素,使得中醫醫案數據挖掘研究面臨重重障礙。要充分運用好數據挖掘這一工具,并將相關結果用于臨床,指導中醫實踐,探索新的中醫發展路徑仍任重而道遠。
2 利用大數據技術挖掘名老中醫醫案價值的困境
2.1 中醫醫案的個性化與非標準化 中醫強調個體化特征和三因制宜思想,強調辨證論治,體現因人而異、同病異治的個性化治療的追求[8];目前隨著各種書寫規范、診療標準及教材的推廣,疾病病名、癥狀、證型等方面逐漸統一,但仍有爭議;醫案書寫規范雖然推行,但實際中因醫務人員的水平差異存在很多問題[1]。就象脈診和舌診,全憑醫生的主觀感覺和經驗,在病歷中無法得到準確記錄,中醫醫案的個性化、非標準化加大了大數據挖掘的難度。
2.2 中醫醫案的文本屬性 中醫醫案屬純文本、非結構化形式,具有異質性、隱私性、多樣性等特點,需要將其轉化為可挖掘、可分析的數據形式,也即進行數據預處理,才能為之后的分析、利用提供前提,但對其預處理,需要掌握中醫理、法、方、藥的基礎理論與運用規律,能夠正確理解中醫醫師辨證論治思想,才能確保清洗數據的準確性,這就要求在名老中醫醫案數據挖掘過程中需要中醫藥專業技術人員、信息技術人員、檔案管理人員等多方配合,才能找出隱藏在數據深處的中醫臨床知識,分析名老中醫的辨證論治規律,從而推動中醫文化傳承與創新,實現中醫現代化與智能化[3]。
2.3 傳統文化觀念的阻礙 檔案是文明的產物、文化的源泉,勢必具備所屬文化的特有屬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庸和諧、重視歷史、強調傳承等特性是中國文化可以流傳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毋庸置疑,但缺點也不容小覷,比較突出的是由小農經濟生發的功利、保守及內斂,使得檔案工作者的思想和行為呈現出一種保守狀態[9]。中醫藥學根植于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沃土,植入了中華傳統文化基因,既具備中華傳統文化的優點,同樣也夾帶了其缺點,加上中醫醫案自身的特殊性,包含了患者信息和診療信息,出于保護患者隱私、避免“秘方”外流及我國的專利制度對于中藥領域的保護不夠完善等顧慮[10],多數中醫醫家不愿將經典處方、驗方進行共享,這與大數據共享理念有悖。
2.4 中醫藥文化自信不足 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土壤的破壞,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盛行,中醫藥多次遭遇被取消、被廢止的命運,長期處于被質疑、被改造的尷尬境地,中醫藥文化自信一次次遭遇打擊。臨床西化、教學現代化、科研實驗化等,讓許多傳統中醫人的自信心不足,認為中醫沒有什么價值可以挖掘,轉而把更多資源投入對西醫的研究,使中醫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
3 解決策略
3.1 加強中醫病歷規范化建設 數據挖掘中耗時最長的環節是數據的準備,數據是數據挖掘的基礎,只有足夠、豐富、高質量的數據才能確保高質量的數據挖掘結果[6]。因此,要加強中醫病歷尤其是電子病歷的質量控制,一方面,中醫醫師在診療過程中應嚴格遵守《中醫臨床診療術語》《中醫電子病歷基本規范(試行)》及《中醫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試行)》等有關標準,規范書寫“四診”信息,豐富中醫病歷內涵;另一方面,醫院要嚴格按照標準抓好病歷抽檢,嚴把質量關,促使中醫醫案不斷規范化、科學化[5]。
3.2 健全保護機制,消除中醫醫師顧慮 在現代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專利保護制度是最為重要和有效的。為了進一步提升中醫藥的開放度,應當完善專利制度對于中藥領域的保護辦法,或者引入知識產權管理理念,加強對中醫藥資源的保護,確保公開的中醫知識能夠得到很好保護,消除中醫醫師顧慮。
3.3 多措并舉提升中醫藥文化自信 其實中醫文化基因存在于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脈之中,千百年來早已融入國人日常生活和思維方式,只是有時被文化自信的缺失抑制了“表達”。要激活更多民眾的中醫文化基因,一方面,要從精神領域層面去解決對中醫藥概念的認識問題,應進一步加強中醫藥健康文化科普。另一方面,要從制度層面去解決中醫藥傳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要建立健全中醫藥管理體系和適合中醫藥發展的評價體系、標準體系,讓老百姓放心吃藥、放心看病;還要加強中醫重點專科專病研究,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放大醫改惠民效果,保基本、強基層、控費用,通過不斷增加的中醫藥服務獲得感來強化國人中醫文 化基因,堅定中醫文化自信[11]。
4 結語
中醫醫案是名老中醫學術思想和臨證經驗的重要承載,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醫案的研究是促進中醫藥發展的重要智庫資源。大數據技術開辟了中醫醫案研究的新路徑,但由于受歷史、人為等因素的影響,基于大數據技術挖掘中醫醫案價值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們要搶抓機遇,既要在完善管理制度、實現中醫醫案數據的結構化和標準化等方面花功夫,更要在提升中醫藥文化自信、推動中醫藥文化創新性發展上深花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