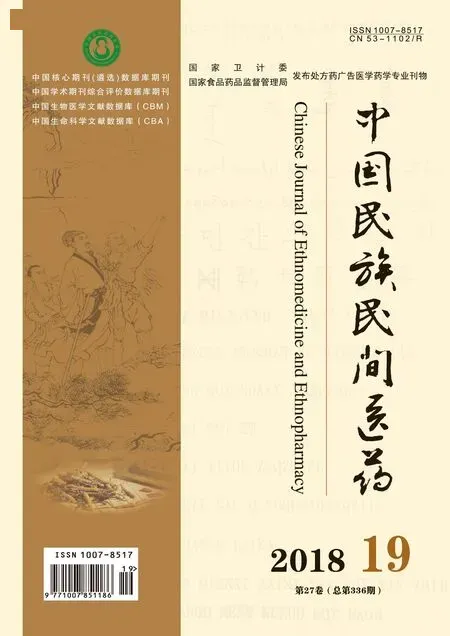從痰論治哮病
江西中醫藥大學,江西 南昌 330006
在漫長的醫療和臨床實踐中,中國傳統醫藥對哮病的治療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方法頗多,效如桴鼓,不僅能夠改善哮病發作時的癥狀,而且通過扶正祛邪的基本治則,能夠達到祛除夙根,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質量。
1 哮病的病因病機
《內經》中雖無哮病病名,但“夠貽”與本病的發作特征尤為相似。漢代張仲景《金匱要略》中則之稱為“上氣”,詳細闡述了本病發作時的典型特點,提出了相關診療方案,在病機上將其歸納于痰飲中的“伏飲”,至今都堪稱哮病宿痰伏肺的理論基石。除用“上氣”病名外,還有稱作“呷嗽”、“哮吼”[1]。直到元代朱丹溪才首提“哮喘”病名,闡明病機主要在于痰,提出“未發以扶正氣為主,既發以攻邪氣為急”的治療原則[2]。經過醫學不斷的進步與發展,眾醫家認為引起哮病的病理因素以“伏痰”為根本,又遇誘因而引觸。發作時,則痰隨氣升,氣因痰阻,痰氣相互搏結,壅阻氣道,肺管因而狹窄,肺氣升降失調,致呼吸不暢,氣息喘促[3]。同時,氣體的升降出入又引觸積蓄之痰,痰氣相擊,則發哮鳴之音。因此,哮病發作時的病因病理關鍵要點在于痰阻氣閉,既發的以邪實為主[4]。更因長年復發,肺氣日益消耗,脾虛不能化精微,日久及腎,必然導致腎虛精虧,陽虛水泛,或陰虛火升灼津而成痰。若寒痰為病則損傷脾腎之陽,若痰熱內郁則損害肺腎之陰,則病變可從實轉虛,在平素表現肺、脾、腎等臟器衰弱之象。總之,哮病的實質為本虛標實之病,痰濁為邪實,臟腑陰陽虧虛為本。本虛與標實互為因果,因邪實而導致臟腑陰陽虛衰;臟腑陰陽虛衰又可引觸痰濁產生,使伏痰益固,交替發生,故本病難以速愈和根治。在急性發作期,以治標為主,袪痰利氣,但應明清痰之寒熱。平時以扶正為主,但應審清臟腑之歸屬,予以培補。人體內部臟腑生理機能運轉失序,臟腑氣機出現紊亂,久久蓄積不化而成。對待哮病,醫者不能僅僅停留在歷代的認知上,還應有更廣泛、更深入的思考與研究。
2 哮病之痰論思想內涵
2.1 中醫理論依據 祖國傳統醫學認為哮病的發病機理以痰氣交阻為要。由此可知,痰在哮病的發病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痰”有“有形之痰”和“無形之痰”之分[5]。有形之痰是指能夠視之可見,聞之有聲的痰液,即呼吸道的分泌物;無形之痰是指只見表象,不見其形質,主要根據臨證所見進行綜合判斷的[6]。“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痰的產生與肺脾兩臟密切相關。肺主氣司呼吸,調節全身氣機的升降出入。當肺臟被外感之邪侵襲時,肺失宣降,水精不布,出現水液代謝異常,導致肺內津液凝聚成痰。脾主運化,即消化和運送水谷精微供臟腑營養。若寒濕浸漬,暴飲暴食,勞欲過度都能傷及脾臟,影響其運化功能,以致水濕內停,凝聚成痰。喜燥惡濕是脾臟生理特性之一,脾臟最怕受困,一是氣困(氣機不布),二是濕困。脾臟健旺,脾氣升動如常的前提就是脾體干燥而不被痰飲水濕所困,正所謂“脾燥則升”。由于津液在體內正常輸布需要脾氣發揮交通樞紐作用,使之上行到肌表,下達到臟腑,調暢全身氣機,從而維持了機體內環境的穩定。
2.2 現代醫學理論認識 西醫學中的支氣管哮喘所致的以哮喘為主癥者,可參考哮病辨證論治。當代醫學認為支氣管哮喘是由多種炎癥細胞和細胞組分參與的一種以氣道高反應、氣道炎癥和氣道重塑為特征的反復的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7]。目前認為這種慢性炎癥與氣道高反應關系緊聯,可使呼吸道對刺激物的敏感性增強,當氣道接觸到危險因素時,會可導致氣道上皮損傷,從而引發支氣管平滑肌收縮、血管壁通透性改變以及呼吸道粘膜充血、水腫、炎性滲出物增多(痰液),促成氣道狹窄、攣急、阻塞,最終引起缺血缺氧,嚴重的話會導致氣道通氣功能障礙[8]。這些客觀現象與中醫痰阻氣閉的發病機理相契合,表明了哮喘發作離不開痰的病理現象,具備一定可循性。
2.3 中醫治則治法 哮病之根本在于痰飲,痰飲為陰邪,寒主收引,遇寒則凝;痰飲濕性重濁粘膩,容易阻礙氣機運行不暢,陽主溫煦,遇陽則行,得溫則化。痰飲之本源在于體內陽氣虛衰,氣化不利,從而產生水液輸布障礙。《金匱要略》針對痰飲提出:“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甘溫以補陽,振奮人體陽氣,一方面溫化飲邪,另一方面杜絕痰飲滋生之源。辛溫、苦溫用以祛邪利水,使痰飲之邪能通過肌表和二便分消而去。對于本虛標實之病證,單純運用扶正的方法易戀邪,單純運用祛邪的方法易傷正,故應以和為原則,兼顧痰飲之標與本,虛與實。猶如陰陽辨證關系,祛邪和扶正是一對互根互用又相互對立的治療原則。臨證觀察,發作時,患者一般以邪實為主,另有以正虛為主;但緩解期常常以正虛為主,究其病因主要是宿痰伏于體內所引起[9]。故對哮證的治療,不要拘束于“發時治標”,要審證求因,標本兼治,靈活將理論與臨床相融合。平時當重視治本,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時,分清肺、脾、腎三臟的主次,其中尤以補腎為要,腎乃先天之本,五臟陰陽之本。在用藥上適當加入一些宣肺化痰之品,以宣發肺氣,開肺化痰,進而清除體內膠固之痰。
2.4 注意事項
2.4.1 用藥 肺氣郁閉,不利于痰的排出,而痰伏于肺,必致肺閉痰阻,故治療選藥時,必須宣發肺氣,開肺化痰,臨床常用炙麻黃,取麻黃開肺定喘作用,而不在發汗,但使用麻黃需注意不可長久,中病即止[10]。由于痰是本病關鍵,因此,忌用一切助濕生痰之品。熟地黃滋膩,可助濕生痰,不利痰的排出;甘草有益中作用,對于苔膩者,當列為禁用。治病與治氣相輔相成,氣順則痰消,故臨證時,常可加理氣之藥物,益化痰之功效。
2.4.2 過敏問題 由于哮喘因接觸某些過敏原而發作,所以哮喘發病常責之于過敏體質,其實過敏僅是一個現象,實質是外邪引觸宿痰。目前應用抗過敏的藥物可能使哮喘暫緩解,但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更無法根治,祖國醫學重視機體的抗病能力,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因此治療各哮喘必須重視培本治療,提高局部支氣管的抵抗力,兼顧解決過敏問題,才能達到根治的目的。
2.4.3 抗生素使用 中西醫結合治療哮喘,可以提高臨床療效,但在西藥使用中切忌濫用抗生素,要嚴格掌握適應癥,否則適得其反。因為濫用抗生素常可致白細胞減少,機體抗病能力下降,衛外不固;哮喘患者早期濫用抗生素則不利于痰液的排出。體虛痰伏是哮喘發作的隱患,因此對于哮病使用抗生素要謹慎。
3 典型案例
黃某,男,70歲,2016年12月9日就診。患者訴4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胸悶、氣喘,一年四季均可發作,冬春季節變化時癥狀明顯加重,每遇到冷空氣、異味或感冒后誘發,發作時喘息憋悶,痰鳴,無咳嗽。于當地診所就診服藥,癥狀緩解則停藥(具體用藥量名不詳)。因天氣變寒復出現諸癥,特來求治。現癥見:患者喘憋明顯,動則尤甚,喉中痰鳴,咳痰黏膩難出,納寐可,二便平。舌淡紅,苔厚膩,脈滑。聽診雙肺可聞及少許干啰音。西醫診斷:支氣管哮喘急性發作期;中醫診斷:哮病,辨證:風痰證。處方:沙美特羅替卡松50/250 μg早晚各1次吸入;三子養親湯加減:白芥子15 g,蘇子15 g,萊菔子15 g,陳皮10 g,法半夏10 g,厚樸10 g,蜜炙麻黃6 g,杏仁6 g,茯苓10 g,防風10 g,地龍10 g。以上藥物取400 mL水煎煮,分早晚兩次溫服,共7劑。2016年12月16日二診,患者喘氣癥狀好轉,痰量減少、色白,舌淡紅,苔薄偏膩,脈細滑。擬守前法,上方加蟬衣10 g、僵蠶5 g,共7劑;繼續予沙美特羅替卡松規范化吸入。2016年12月23日復診時患者諸癥皆消,至今哮喘未發。
按語:患者喘憋,喉中痰鳴,發病隨天氣、季節變化明顯,舌淡紅,苔厚膩,脈滑,辨病為哮病,辨證為風痰證。予三子養親湯加減,方中白芥子溫肺利氣滌痰,蘇子化痰止咳平喘,萊菔子行氣祛痰,陳皮、法半夏、厚樸降氣化痰,蜜炙麻黃、杏仁宣肺平喘,茯苓健脾,防風祛風,地龍通絡。又因患者雙肺可聞及少許干啰音,再吸入沙美特羅替卡松解痙平喘。7日后患者癥狀改善,痰量減少,舌淡紅,苔薄偏膩,脈細滑。考慮患者痰濁伏肺,風邪未完全宿除,故在原方基礎上加蟬衣、僵蠶加強祛風化痰之力,繼續堅持沙美特羅替卡松治療,2個療程后有效改善患者癥狀,達到臨床治愈。
4 小結
支氣管哮喘歸屬祖國醫學“哮病”范圍,治療時應運用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思維,重點突出“證”的證型特征,根據哮病患者痰的性質(痰的色澤、粘稠度、氣味等),結合中醫四診及舌脈象,以“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原則進行診治。哮病屬慢性、長期、反復發作的疾病,表現多為虛證,最基本的病理特點是正虛邪實。據此,扶正培本法在哮病防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可以說它貫穿了哮病診療的整個過程。用扶正培本法,達到“養正積自除”的效果。隨著現代醫學的不斷發展,哮病的發病機制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證候分類和辨證內容亦可進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哮病的防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