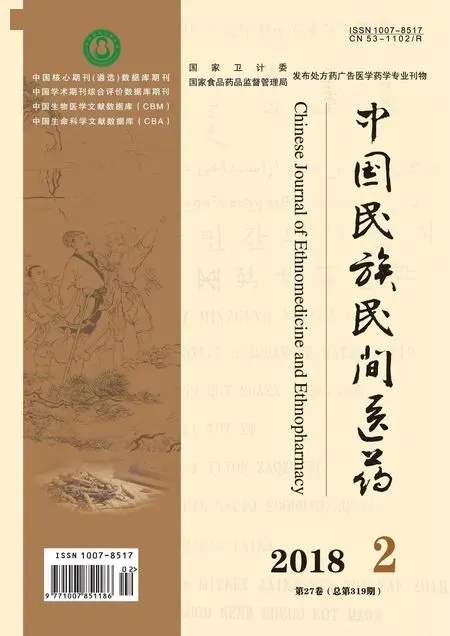中醫醫案學發展歷程簡述
屈 杰 趙天才
陜西中醫藥大學,陜西 咸陽 712046
醫案是醫家記錄臨床診療過程的文獻資料,是中醫幾千年發展的基本載體之一,也是中醫理論繼承、發展的寶貴資源[1]。中醫學的基本理論、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診療經驗、中醫的學術創新和學術爭鳴都在醫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醫醫案以其“宣明往范,昭示來學”的重要價值,受到了歷代醫家的高度重視[2]。如名醫余聽鴻認為:“醫書雖眾,不出二義,經文、本草、經方為學術規矩之宗,經驗、方案、筆記為靈悟變通之用,二者皆并傳不朽。”中醫醫案學是以中醫醫案為研究對象,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以分析、提煉和總結中醫臨床實踐記錄為目的,研究中醫診治規律、臨床思維特征、學術思想及相應研究方法的一門學科[3]。 研究中醫醫案學的首要問題是厘清中醫醫案學的發展歷程,明確學科特點和定位[4]。但傳統的醫案學歷史研究未能重視現代醫案學的成就,有鑒于此,文章在結合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將中醫醫案學發展概括為萌芽時期(先秦、兩漢)、發展時期(宋、金、元)、成熟時期(明、清、民國)和繁榮時期(建國后),茲分述如下。
1 萌芽時期(先秦、兩漢)
先秦、兩漢時期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確立時代,其標志為《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傷寒雜病論》四部經典問世[5]。這一時期,從歷史文獻角度來看,中醫醫療水平已經居于較高層次,但是醫案學發展尚處于萌芽時期。醫案數量較少,多散見于文史著作中,醫案記載比較簡單,重在敘事為主,醫學價值有限,醫案、醫話、醫論等混為一體。成書于東周時期的《周禮》載有:“民死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又次之,十失三又次之,十失四為下” 表明早在周代,醫案記錄已經成為醫療活動的一部分。有文字記載的醫案多見于先秦諸子、史學著作中,如《左傳》中秦醫緩醫和論治晉候之疾,《漢書·外戚傳》載女醫淳于衍用附子澤蘭丸給新產許皇后服用,以致身死等。這一時期醫案記載較為完整的要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扁鵲與太倉公的二十余則醫案[6]。倉公所載醫案記載了患者的姓名、住址、職業、病情、治療、預后以及所用劑型,突出了倉公脈診的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倉公記載醫案的目的與之前史學記事不同,重在“觀其所失所得”,不斷總結經驗,以期提高自己醫療水平。
漢至唐代,中醫學不斷繁榮發展,本草學、臨床各科取得了較大成就,仍然沒有醫案專著問世,醫案資料多散見于經、史、藝文志中[7]。
2 發展時期(宋、金、元)
宋、金、元時期,雖然民族政權并存,但科學、文化、技術高度繁榮,統治階層重視醫藥事業,有完善的醫療行政機構和醫事制度,醫學教育事業得到了極大發展,政府創建了校正醫書局,校正《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古代醫書,為中醫文獻保存、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中醫藥事業步入繁榮昌盛、學術爭鳴時期[8]。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醫個案專著紛紛問世,其代表作為錢乙《小兒藥證直訣》和許叔微的《傷寒九十論》、《普濟本事方》。《小兒藥證直訣》由錢乙門人閆孝忠于公元1119年著成,載有錢乙親手治愈的19則兒科醫案,此書不僅是現存首部兒科專著,還開創了以論附案的編寫體例,影響深遠。許叔微于公元1133年著成《傷寒九十論》,分為九十證,每證一案,先舉醫案,后列評論,類似今日醫案分析與討論,此書被譽為我國第一部醫案專著,后人有“醫案之作,蓋始于宋許叔微”。許氏晚年所著之《普濟本事方》,雖為方書,但在個別方后附有驗案,以印證方劑療效,開創了以方附案的編寫體例。
受錢乙、許叔微影響,金、元不少醫家采取了上述編寫體例,著書立說,如張子和的《儒門事親》、李東垣的《脾胃論》《蘭室秘藏》、朱丹溪的《格致余論》等。
這一時期醫案不僅受到醫學家所重視,而且已經成為官方醫學考試內容之一,如宋代規定,醫學生理論考試每年三場,前兩場考三經大義題,第三場考假令病法三道,類似今日的病案分析題。此外,高年級的醫學生還要輪流為其他三學(太學、律學、武學)學生及各營將士治病,并記錄在案[9]。
概括起來,這一時期中醫醫案發展特點為:有醫案專著開始問世;醫案考試成為官方規定;個案總結逐漸為醫家所重視;以方附案、以論附案的編寫體例意在印證醫學理論的正確或方藥的效驗[10];醫案、醫話、醫論三者不分。
3 成熟時期(明、清)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國家長期統一穩定,文化、科學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中醫學在承襲宋、金、元的基礎上,名醫輩出,醫著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群,據統計現存明代個案專著30余種,清代醫案近300種[11]。這一時期由于溫補學派、溫病學派先后興起以及臨床各科日趨分化成熟,醫案著作具有鮮明的學派特點、流派特點、專科特點,如反映溫補學術思想的薛立齋的《內科摘要》,反映溫病學思想的《臨證指南醫案》《吳鞠通醫案》《王孟英醫案》等,反映經方特色的陳念祖的《南雅堂醫案》等,楊繼洲的《針灸大成》中有針灸醫案30則,傅仁宇《審視瑤函》中有眼科前賢醫案22例,則是專科醫案的體現。
明清個案中,以清代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影響最為深遠,此書不僅對溫病學建樹頗多,且對臨床各科貢獻卓越,其用藥輕靈,自成一家的風格,令后人嘆為觀止。此外,晚清時期以費伯雄、馬培之為代表的孟河醫派興起,他們醫案以善于化裁古方,平穩淳正,醫理文采并茂著稱,對民國時期醫家影響甚大。江蘇中醫世家陳蓮舫、何長治家族代有名醫,醫案用藥穩健,平正輕靈,論理淵博,也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明清時期大型類案相繼問世。嘉靖年間,江瓘父子等搜集了自《史記》至明嘉靖1600年間經、史、子、集、醫著中的醫案,加以整理、分類,著成《名醫類案》12卷,是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大型類案專著。
受其原創性的整理思路的影響,清代魏之琇的《續名醫類案》摘取了從《史記》至清代嘉慶朝1800年間的各家醫案36卷,集案5000則,是現存篇幅最為浩繁的醫案類書,足以羽翼《名醫類案》。
這一時期,中醫醫案書寫理論研究引起了不少醫家的重視。韓愗在《韓氏醫通》中規定醫者書寫醫案應該有規范化的格式,認為“凡治一病用此式一紙為案”,并且提出了六法兼備之案,即“望、聞、問、切、論、治,六法必書”。明代吳崑著《脈語》一書,制定了“七書一引”醫案書寫格式。清代俞昌在《寓意草》一書中有《與門人定議病式》一文,系統講述了醫案格式與要求。
清代以后,醫案與醫話、醫事分家,醫案逐漸規范化,大多理、法、方、藥具備,語言簡練,論理透徹。明清以后,醫案教學在醫學教育中的地位受到了重視,學習醫案成為醫學生的必由之路。
民國時期,西醫大量傳入我國,醫學院校與現代醫院紛紛建立,不少中醫人士從現代醫學研究中醫,中西醫處于匯通時期。這一時期的醫案,除用現代漢語敘述病情之外,在書寫格式上受到了西醫病歷格式影響,風格比較嚴謹、規范,且增加了現代醫學病名和相關化驗檢查,反映了中醫轉型的時代特點[12]。這一時期以何廉臣所編著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張山雷所著的《古今醫案平議》影響較大。
4 繁榮時期(建國后至今)
建國以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中醫藥事業,創辦了一批中醫藥高等院校,組織出版了大量中醫醫案著作,代表性個案著作有《蒲輔周醫案》《岳美中醫案集》《趙炳南臨床經驗集》等;類案有余瀛鰲的《現代名中醫類案選》、魯兆麟教授領銜主編《近現代中醫名家臨證類案》等。此外,大量的專科醫案、流派醫案也紛紛問世。中醫醫案教育逐漸受到了重視[13],不少學校嘗試開設中醫醫案課程,進行醫案相關學術研究[14-15],中醫醫案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正快速發展起來。
5 小結
中醫醫案從先秦兩漢肇始,迄今兩千余年,傳承不絕。宋代以后隨著個案專著問世,以及明代醫案巨著出現,研究、整理醫案逐漸為眾多醫家重視,清代醫案著作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進而今日發展為中醫醫案學學科。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約有古今中醫醫案著作1500余種[16],從醫案的發展歷史來看,主要有古籍附案、醫籍附案、醫案專著三種主要體例[17]。隨著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特別是國家不斷加大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政策扶持,中醫醫案學的發展迎來了大好機遇,主要表現在國家高度重視名醫學術思想傳承工作,各地紛紛建立名中醫工作室,出版名老中醫醫案專著,臨床專科醫案大量問世,不少醫家注重醫案研究方法[18-19],應用數理統計、數據庫等技術創新研究方法[20],提高了研究水平,但同時本學科發展也面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對醫案學的學科定位不夠清晰,醫案學應該是交叉學科,既有文獻學、各家學說特點又兼具中醫臨床思維的特色,目前出版的不少教材編寫思路仍然停留在古代中醫醫案或者說各家學說編寫體例中,不能體現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所選醫案內容相對陳舊,學生學習興趣不高;二是缺乏一支專業致力于醫案學研究的人才隊伍,目前從事醫案學教學、研究的教師大部分是醫古文、各家學說的學術背景,不能完全勝任中醫臨床思維培養的要求,理想的人才隊伍應該是既要有較為深厚的古漢語水平,又要有豐富的臨床水平;三是目前個別院校對醫案學的重視程度不高,全國缺乏統編的醫案學教材,開設醫案學課程院校相對較少。因此,中醫醫案學這門古老的學科既面臨著機遇也面臨著挑戰。
[1]謝心,陸金根,林鐘香,等.從中醫醫案探求古代醫家的診治規律[J].遼寧中醫雜志,2007,34(7):886-887.
[2]孟慶云. 宣明往范,昭示來學-論中醫醫案的價值、特點和研究方法[J].中醫雜志,2006,47(8):568-570.
[3]卞蕓,邱家學.對中醫醫案現代化的思考[J].中國中醫藥信息志,2011,18 (2):1-2.
[4]李園白,崔蒙.關于中醫醫案的綜合性分析研究近況[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6(2):91-93.
[5] 邢玉瑞,王平.中醫基礎理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6-7.
[6] 蘇禮.中醫醫案學概論[M].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6.
[7] 田代華,董少萍.中醫文獻導讀[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572.
[8]王雅麗.從中醫醫案文獻的發展史看醫案的鐫載體例[J].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2012,21(2):13-14.
[9] 陶廣正,高春媛.古今名醫醫案評析[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4.
[10]魯兆麟.中醫醫案學[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6.
[11]鮑健欣,葉進.略論明代中醫醫案的成就及影響[J].中醫雜志,2014,55(22): 1897-1899.
[12]賀慧娥.中醫醫案核心價值研究[D].長沙:湖南中醫藥大學,2014.
[13] 崔應珉,時軍,王麗鴿.關于開設中醫醫案學教學的思考[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2(17):75-76.
[14] 陳玲玲,劉詩發,張晨.中醫醫案類數據庫的構建與數據處理研究[J].中醫文獻雜志,2014(6):24-27.
[15]劉愛玲,周光.中醫醫案課程對研究生培養的作用[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12,10(20):58-59.
[16] 裘沛然.中國醫籍大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1310-1453.
[17] 王雅麗.從中醫醫案文獻的發展史看醫案的鐫載體例[J].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2012,21(2):13-14.
[18] 王佑華,陸金根,柳濤,等.中醫醫案中的知識發現研究[J].中西醫結合學報,2017,5(4):368-372.
[19] 于智敏,宇文亞.中醫醫案評價路徑與方法[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2,18(5):503-504.
[20] 劉賢亮,黎創,毛煒. 近十年中醫醫案研究進展[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2,(8):2132-2134.
——中醫藥科研創新成果豐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