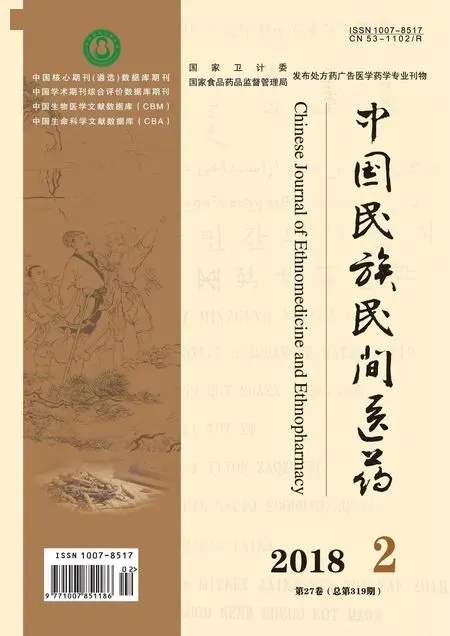陳筱云主任醫師從肝脾論治糖尿病臨證經驗
王 浩 陳筱云
1.山西中醫藥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2.山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山西 太原 030024
糖尿病,歸屬于中醫“消渴”范疇,古有丹溪從上中下“三消”論治,近代有從臟腑(肝、脾、腎)論治,也有從氣血津液(氣虛、陰虛、血瘀)論治和從痰濁毒論治等。這些治法不僅針對糖尿病的癥狀,更關注的是對血糖的控制。通過總結前人經驗,再結合多年臨床心得,陳筱云主任醫師認為肝脾功能失調影響津液代謝、精微輸布異常可導致高血糖的產生,從而形成糖尿病。
1 理論基礎
1.1 肝與氣血津液代謝的關系 肝主疏泄,調節氣機升降出入。周學海《讀醫隨筆》言:“肝者,貫其陰陽統血氣……據升降之樞者也……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說明肝處中焦,為氣機升降的樞紐,對臟腑的氣化活動及水液的吸收、轉輸、敷布、排泄等有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唐榮川有言: “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則水谷乃化。”氣血津液由水谷通過脾胃化生而成,在氣的推動下,灌溉全身臟腑經絡,“凡臟腑十二經之氣化,皆必得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能幫助脾胃運化、心肺宣散,行氣運血,并將津液之清者,運送、敷布至肌肉關節、皮膚毛發等組織器官,在完成滋養作用后,其氣化的產物,通過汗、淚、涕、唾、涎等產物代謝出體外[1]。肝為剛臟,喜條達、惡抑郁,但又不能升泄太過,須保持柔和。若肝疏泄太過,“肝木侮土,則土衰而水濁”(《金匱要略論注》),可產生痰濕等病理產物。肝又主藏血,對全身的血液代謝起調節作用。《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人臥,血歸于肝。”肝為血海,有調節十二經氣血的作用。肝郁日久,血行不暢,瘀血內停,津液不能上輸,而下趨州都引發消渴。《血證論》言: “瘀血發渴者,以津液之生,其根出于腎水……有瘀血,則氣為血阻,不得上升,水津不能隨氣上布。”肝血虧虛,肝陽亢盛,下擾腎水,引起津液代謝紊亂。《素問》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說明肝還可貯藏部分精微物質[2]。
1.2 脾與精微輸化之間的關系 脾主運化,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素問》云:“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脾的運化功能即脾氣促進胃受納腐熟水谷,并將其氣化為精微物質,而后通過脾的“散精”功能輸送到全身,潤養五臟六腑、五官九竅、四肢百骸。正如《素問·奇病論》中所言:“五味入口藏于胃, 脾為之行其精氣”。脾既為機體提供充足營養,又負責將體內的代謝廢物及時清除,從而保證正常的生理功能[3]。若清除不及,可出現水液代謝異常,即“諸濕腫滿,皆屬于脾”。正常情況下,脾旺氣健,納運有序,清陽得升,濁陰得降,氣暢血和,則痰濕無以聚,全身臟腑器官正常運轉,將食物中的淀粉、脂肪、蛋白質水解為葡萄糖、乳糜微粒、氨基酸等營養物質后被機體吸收,并進一步產生能量,或合成各種組織蛋白、酶類和激素等供機體需要。除了脾氣在精微輸布中的作用外,還應重視脾陰在其中的作用。脾為陰中之至陰,朱丹溪《局方發揮》云:“脾土之陰受傷,轉輸之官失職,胃雖受谷不能運化,故陽自升陰自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指出脾陰受到損傷會影響脾的轉輸運化功能,繼而降低胃的降濁能力,說明脾陰對脾的運轉功能和胃的受納功能均有重要影響[4]。
1.3 肝脾與糖尿病的關聯性 肝與脾同居中焦,生理上互相聯系,功能上相互影響。不論何種原因引起的肝失疏泄或脾失健運,均會導致氣血津液及水谷精微的運化、輸布、代謝異常,產生痰濕、瘀血等病理產物。
劉河間《三消論》云:“五志過極,皆從火化,熱盛傷陰,致令消渴。”明確了七情等因素經由肝郁化火環節致令消渴。消渴的基本病機為陰津虧損,燥熱偏勝,情志過極化火,損耗五臟津液,陰津愈損則燥熱愈勝。肝為五臟之賊,欺強 凌弱。怒氣傷肝,肝郁氣結,疏泄失司,脾臟虛弱,飲食不節,肝郁乘脾,脾胃失健則痰濕自生。
李東垣提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長期飲食不節,多食肥甘厚味,加之情志不節、勞欲過度等,直接或間接地損傷脾胃功能,脾失健運,精微不得輸布至肺、胃、腎等臟腑,使其滋養不足,則更傷其陰,發為消渴。《靈樞·五邪篇》指出:“陽氣有余,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這句話很好地解釋了消渴癥出現消谷善饑癥狀的原因,即胃陽過盛,而脾陰不足[5]。血液中的“糖”是水谷精微中的一部分,是人類生存必不可缺的物質,脾的“散精”功能受損,“糖”在血液中累積,就會產生高血糖,形成糖尿病。因此,《景岳全書》云:“消渴病,其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變,皆富貴人病之而貧賤者少有也”。脾失健運,痰濕易生,“肥人多痰多濕多氣虛”,肥胖被認為與胰島素抵抗密切相關,而高胰島素血癥亦會導致肥胖,二者互相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2 治則治法
綜上所述,糖尿病從肝脾論治是行之有據、有效的治療方法。陳筱云主任醫師根據多年臨床實踐,總結出“燮理中焦,輸化精微”的8字治療大法;在具體治療過程中,重視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治標與治本相結合。
2.1 調理肝脾,舒暢氣機 臨床上,陳筱云主任醫師常用柴胡、白芍、陳皮、姜半夏、黨參、白術、茯苓、香附、郁金、荔枝核、八月札、甘草等為基礎方加減運用。肝喜條達,故以瀉為補,柴胡升陽散熱,合芍藥以平肝,使木得條達;香附辛苦而微溫,長于疏肝理氣;木盛則土衰,黨參、白術、甘草和中而補土生金,半夏姜制,助其燥濕化痰之力,合茯苓淡滲利濕,助參、術以益土;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郁金行氣解郁,清心涼血,以防郁久化熱;荔枝核、八月札理氣調中。現代藥理研究證實,人參、白術、茯苓等具有降低血糖,改善糖尿病癥狀的作用[6]。諸藥配伍,調和肝脾,使氣機舒暢、痰濕得化,氣血津液等精微得以正常輸布,從而降低血糖,改善糖尿病癥狀。2.2 重視肝脾之陰 肝體陰而用陽,脾為陰土。就補肝陰、肝血的藥物而言,陳筱云主任醫師多選用當歸、白芍、川芎、炒棗仁、何首烏等補血養肝之品。歸、芍養血斂陰柔肝,潤養肝體;川芎辛散溫通,上行頭目,下行學海,中開郁結,旁通血脈,補血而不留瘀,使血虛得補,血滯得行;棗仁、首烏肝腎同補,乙癸同源,滋水涵木。
在補脾陰時,應選擇甘潤入脾之養陰生血固精之品,陳筱云主任醫師常用太子參、懷山藥、白扁豆、麥冬等。山藥味甘性平,入脾腎經,以益氣養陰為主,其補而不膩,合脾喜潤而惡燥的特性;白扁豆健脾止瀉,太子參健脾益氣生津,麥冬甘寒質潤,益氣生津,皆為氣陰并補之藥,且其性較緩和,使補脾而不礙胃。
3 驗案舉隅
患者劉某,女,43歲,2016年11月8日初診,患者3年前體檢時發現血糖升高,后間斷口服二甲雙胍、阿卡波糖等藥降糖治療,平素未規律監測血糖,近日口干口苦加重明顯,遂來就診。患者口干口苦,乏力納呆,食后腹脹,偶有胸脅脹痛,大便不調,時干時稀,小便色黃,舌淡苔薄黃,脈弦滑;查即刻血糖:8.7 mmol/L。西醫診斷:2型糖尿病;中醫診斷:消渴(肝郁脾虛)。治法:行氣疏肝,養血健脾。用藥如下:醋柴胡12 g,白芍12 g,當歸12 g,黨參24 g,茯苓12 g,白術12 g,山藥30 g,川芎10 g,姜半夏9 g,陳皮9 g,甘草6 g,7劑,水煎服。囑其規律監測血糖,控制飲食并適當運動,調節情志。2016年11月15日二診,患者諸癥緩解,自測空腹血糖:6.8 mmol/L,餐后2 h血糖:7.9 mmol/L。繼服7劑,諸癥消失,血糖波動在理想范圍。
按:陳筱云主任醫師辨病與辨證相結合,認為患者為中年女性,易于肝氣郁滯,久郁化火,煎熬津液,火熱上炎故見口干口苦,下趨可見小便色黃;肝氣橫克脾土,損耗脾氣,故見納呆腹脹;肝郁與脾虛并見,可有大便不調,時干時稀,脾虛則舌淡,肝郁化火則見苔薄黃,脈弦滑。方中醋制柴胡,可增強其行氣疏肝之力;歸、芍養血斂陰柔肝,潤養肝體,既防疏泄太過,又可補充肝火煎熬之肝陰;參、術、苓、草四君益氣健脾,半夏姜制,增強其化痰功效,助四君健脾化痰;山藥益氣養陰,為補脾陰之要藥;陳皮行氣化痰,既助柴胡行氣, 又助半夏化痰。諸藥合用,共奏行氣疏肝,養血健脾之功,使肝氣得疏,脾運得健。
4 小結
陳筱云主任醫師認為消渴病形成的原因是未化為精微的“濁氣”隨清氣(水谷精微)注于血脈,因肝失疏泄、脾失健運,運化不及所致。各種原因引起肝脾功能失調均可引起“糖”等精微物質的聚集,導致糖尿病的發生。其立足肝脾,闡述了肝脾與糖尿病發生發展的關系,體現了中醫治未病的思想。隨著心身醫學模式的興起,情志與疾病關系越來越受到臨床醫生的重視,筆者闡述了肝脾與糖尿病發生發展的關系,可為臨床防治糖尿病提供有益的借鑒,豐富臨床治療糖尿病的思路。
[1]王智明,魏子孝.從肝論治消渴(糖尿病)的理論探討[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9(4):35-36.
[2]史曉燕.淺論肝為氣血調節之樞[J].陜西中醫,2003(1):44-45.
[3]楊麗,王彩霞. 脾主運化的源流及發展[J]. 中華中醫藥雜志,2016,31(5):1773-1777.
[4]于漫,王彩霞,崔家鵬,等.“脾陰”之探源[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3):1203-1205.
[5]程憲文,朱雅莉.消渴病從脾陰論治[J].中醫藥學報,1992(3):8-9.
[6]金汀龍,陳霞波.臨床常用中藥降糖作用研究進展[J].浙江中西醫結合雜志,2015,25(5):526-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