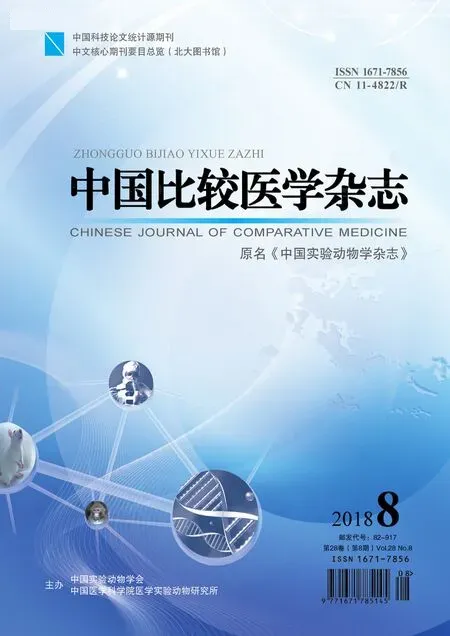NLRP3炎癥小體在肝疾病中的作用
孔德龍,崔 潔
(1.徐州醫科大學病原生物學與免疫學教研室,江蘇省免疫與代謝重點實驗室,江蘇 徐州 221004; 2.徐州醫科大學生理學教研室,江蘇 徐州 221004)
機體內免疫細胞通過表面和細胞質內的受體識別病原體或其產物而活化,活化的受體介導下游信號通路,啟動炎癥應答反應的發生。隨著“危險信號假說”的逐漸發展,人們發現免疫細胞也可以在沒有致病體存在的情況下,通過識別損傷細胞釋放的內源性信號活化[1]。這兩種情況相互補充,逐漸形成了炎癥反應可由病原體入侵或來源于宿主的危險信號所誘發形成的觀點,并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其參與了許多疾病的致病機理過程,包括肝疾病。
1 NLRs模式識別受體
不同的病原體如肝炎病毒及腸道菌群的成分等都能夠激活肝先天免疫反應,促進肝病變的發展[2]。這些微生物組分和病毒衍生分子通常稱為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3];除微生物和病毒等外源性分子外,肝暴露于實質或非實質細胞受損傷時所釋放的非病原體刺激物后也會誘發免疫反應,這些來自宿主的有害物質統稱為損傷相關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DAMPs代表內源性信號,在組織細胞損傷時釋放并活化細胞的各種受體進而活化靶細胞,發揮各種生物學功能[4]。這些PAMPs或DAMPs通過與肝內表達于細胞膜或細胞質內的各種模式識別受體(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相結合,誘導炎癥反應的發生;PRRs作為機體抵抗各種危險因素的第一道防線,迄今為止已有四種不同家族被發現和證實,分別是跨膜蛋白類的Toll-樣受體(toll like receptor, TLRs)、C 型凝集素受體(C-type lectin receptors, CLRs)以及屬于胞漿內蛋白類的維甲酸可誘導基因I樣受體(retinoic acid-inducible gene I-like receptor, RLR) 和NOD樣受體 (nucleotide binding and oligomerization domain like receptors,NLRs)[5]。NOD 樣受體是一類主要表達于胞漿內的重要PRRs,目前已發現的NOD樣受體家族成員在人體內有22種,小鼠則有34種[6]。NLRs在感知不同的危險信號后能夠誘發細胞質中稱為“炎癥小體”的蛋白復合物組裝,其信號通路被激活后,NLR形成一個包含效應分子絲氨酸蛋白酶Caspase-1前體蛋白和ASC(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的復合物,活化的Caspase-1剪切加工并促進IL-1β等促炎細胞因子的成熟和分泌,進而構成組織局部炎癥微環境的形成[7]。
2 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及功能
在眾多能形成炎癥小體的分子中,已發現在肝疾病中發揮功能作用的主要為NLRP3,AIM2和NLRP6,其中NLRP3在肝疾病中的研究最為廣泛[8]。NLPR3炎癥小體的活化主要包含兩個過程:(1)病原體信號。如:脂多糖(LPS)能夠通過NF-κB依賴的信號通路上調NLRP3表達[9];(2)損傷相關信號。其中在肝疾病中典型的信號分別是ATP,尿酸,棕櫚酸,膽固醇結晶和活性氧(ROS)[10-14]。目前,對于誘導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機制仍然是一個沒有明確且存在眾多爭論的論題。不同的疾病或模型中其活化各不相同。較為普遍認可的理論主要有三個:(1)細胞外ATP通過P2X7受體導致細胞鉀離子外流誘導NLRP3的活化[15];(2)細胞吞噬膽固醇結晶,尿酸和淀粉酶等導致細胞內溶酶體破裂釋放溶酶體組織蛋白酶B活化炎癥小體[16];(3)ROS依賴的方式活化[17]。然而目前并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能夠更為全面詳細的闡明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確切機制。
研究表明,炎癥小體在肝疾病中的主要作用是其在肝不同細胞內活化后釋放IL-1β進而誘發炎癥反應[18]。此外,炎癥小體活化誘導的趨化因子表達,進而招募各種免疫細胞到達受損的肝部位,在肝疾病的發生發展中也發揮重要作用[19]。有研究報道,IL-1β的促炎作用可能是由于其與TLR信號的協同效應顯著擴大了LPS誘導的炎癥因子釋放[20];而且,IL-1β信號可以進一步通過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而增強,例如:炎癥小體介導的IL-1β釋放促進其自身前體(pro-IL-1β)的轉錄水平升高、其他炎癥小體組分的生成以及炎癥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產生[21],這樣形成一種正反饋式的方式促進局部病變的不斷加重。在肝疾病中,IL-1β能夠促進肝臟中炎癥細胞募集和肝星狀細胞(HSCs)活化,參與肝纖維化發生[22],也能促進甘油三酯在肝細胞中累積,進而聯合腫瘤壞死因子(TNF)誘導肝細胞凋亡[23]。
除產生IL-1β影響肝局部微環境外,NLRP3炎癥小體活化所引起的炎癥因子IL-18和IL-33的釋放也可能參與了肝疾病的發展。研究發現在使用缺乏蛋氨酸膽堿(MCD)飲食誘導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模型中,小鼠IL-1β信號的缺失并不影響NASH模型肝炎的加重,而IL-18的缺失改變了腸道菌群結構而更有利于誘導結腸炎菌群的產生,導致細菌代謝產物從腸道轉移至肝,誘導炎癥的發生,促進肝炎病情的惡化[24]。IL-33在肝疾病中的作用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認為它是肝壞死細胞釋放的一種警告信號[25];在小鼠酒精性肝病、肝纖維化和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中,IL-33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26]。有報道發現,IL-33在華支睪吸蟲感染所致的肝致病免疫調控中發揮重要作用[27]。然而,在刀豆蛋白-A誘導的急性肝損傷模型中,阻斷IL-33信號并沒有顯著改善肝損傷作用[28]。IL-33在酒精、非酒精性肝病以及其他病因所誘發的肝損傷中的作用,仍有待進一步闡明。
炎癥反應需要迅速高效地發揮作用后立即被機體有效地控制并及時消除已經出現的刺激因素,避免過度炎癥應答。炎癥小體活化所釋放的IL-1β和IL-18等促炎細胞因子,其持續存在勢必導致組織器官的損傷[29],因此,誘發以及活化炎癥小體的因素都需要被精細調控。基于此,對于抑制炎癥小體的相關機制研究也逐漸受到廣泛關注。自噬是由溶酶體介導的細胞自我保護過程,有研究發現,細胞內的自噬作用能夠通過間接的抑制內源性刺激因素或者直接降解炎癥小體組分從而抑制炎癥小體活化[30-31]。另有研究報道,干擾素(IFN)通過調控轉錄因子STAT1的表達進而抑制NLRP1和NLRP3炎癥小體活化[32]。在肝纖維化的藥物治療中也發現,抑制NLRP3炎癥小體能夠很好的改善纖維化的發生發展[33-35]。目前,有關抑制炎癥小體活化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具體調控NLRP3活化的精確靶點仍不是十分清楚,需要更多的臨床及動物模型研究進行深入探討。
3 NLRP3炎癥小體在不同肝疾病中的作用機制
3.1 酒精性肝病
急性飲酒會誘導脂肪肝的發生,長期酗酒導致脂肪性肝炎、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晚期酒精性肝病伴隨的肝硬化或嚴重酒精性肝炎通常是不可逆轉的,最終引起肝功能衰竭。在急性酒精性肝病的患者中發現,病人肝中的Caspase-1、NLRP3表達水平明顯升高[36],并且,嚴重酒精性肝病患者與正常人相比,血清中IL-1β水平顯著升高[37]。有研究發現,NLRP3炎癥小體參與酒精誘導的肝細胞死亡[38]。而一些能夠活化NLRP3炎癥小體的小分子物質如尿酸、ATP等介導了肝內肝細胞和免疫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加快了病程的惡化[39]。這些研究都表明,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促進了酒精性肝病的發展。
然而,在酒精性肝病中,能夠激活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信號尚沒有完全闡明。有研究發現,腸道來源的LPS通過TLR4信號通路是誘導IL-1β釋放的第一信號[40]。另有研究報道,酒精誘導的線粒體功能障礙導致尿酸和ATP等小分子代謝紊亂是參與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第二信號[41]。在小鼠誘導酒精性肝病的模型中發現,酒精處理組的小鼠血清中尿酸水平顯著升高,在使用尿酸合成抑制劑后肝炎癥和肝損傷程度都得到顯著改善[42]。盡管無菌性炎癥信號在酒精誘導肝臟炎癥中的作用還不十分清楚,但現有的研究提示,來自腸道的PAMPs和來源于肝細胞的DAMPs在酒精性肝病發病過程中的發揮著重要作用。或許以NLRP3炎癥小體和IL-1β為作用靶點將為酒精性肝病的治療提供新的治療手段。
3.2 非酒精性肝病
NLRP3炎癥小體活化在非酒精性肝病中的作用已經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在代謝綜合征和胰島素抗藥性研究中表明,炎癥小體的活化參與了疾病的發展[43-44],而這些疾病過程都能夠誘發非酒精性肝病。研究發現,在2型糖尿病患者血液單核細胞內NLRP3炎癥小體信號通路顯著活化[45]。另有報道,在非酒精性肝病動物模型研究的早期階段,肝被認為發生脂肪變性但是缺少炎癥反應,炎癥小體信號通路相關分子NLRP3、ASC和Caspase-1的mRNA水平升高,但是卻沒有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發生(Caspase-1的剪切活化)[46]。提示我們,組織或細胞特異性炎癥小體的啟動可能促進了疾病的進展,并最終擴展到其他器官內。基于復雜的肝細胞環境,研究細胞特異性炎癥小體活化在非酒精性肝病發展中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在酒精性肝病的研究表明肝中巨噬細胞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起重要作用[47],但NLRP3炎癥小體在非酒精性肝病中的作用比預想的更加復雜。在非酒精性肝炎中,除了肝免疫細胞外,肝實質細胞也介導了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在MCD飲食誘導的非酒精性肝炎小鼠模型上表明,無論骨髓來源的單核巨噬細胞還是肝實質細胞均參與了NLRP3炎癥小體的活化[21]。而在非酒精性肝炎中,NLRP3炎癥小體在肝特異性作用是由不飽和脂肪酸誘導的,它能夠上調并且活化肝細胞中NLRP3炎癥小體,誘導IL-1β產生[48]。為了闡明肝細胞中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作用,有研究者利用過表達NLRP3的小鼠模型,盡管該實驗沒有特異性的研究非酒精性肝炎的肝病理過程,但是小鼠全身NLRP3炎癥小體活化介導了肝細胞發生細胞焦亡(一種炎癥小體介導的細胞死亡形式)[49]。而NLRP3炎癥小體在骨髓來源的細胞中活化并沒有明顯導致肝病理損傷[50]。另有研究報道,膽堿缺失飲食能夠誘導肝細胞死亡以及炎癥小體活化和肝纖維化發生,而敲除NLRP3后這些癥狀得到顯著減輕[51],提示NLRP3炎癥小體活化在非酒精性肝炎中是必不可少的。
3.3 HCV感染所致肝病
全球范圍內約有1.8億人感染HCV[52]。HCV病毒能夠識別TLR2、3、4、7、8、9等多種細胞內模式識別受體并且能夠誘導IFN的生成[53-54]。有研究發現,HCV感染引起巨噬細胞IL-1β的釋放促進肝病變[55]。而利用小干擾RNA(siRNA)阻斷TLR3、TLR7、TLR8和TLR9后,HCV誘導的炎癥小體活化被顯著抑制[56]。在感染HCV患者單核細胞中炎癥小體活化能夠導致IL-18產生,進一步活化自然殺傷T細胞;HCV病毒能夠通過誘導細胞內NLRP3炎癥小體活化,促進膽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SREBP)表達,進而誘發脂質代謝紊亂,介導肝臟病變[57]。綜合以上數據表明,HCV感染能夠誘發炎癥小體活化并參與其引起的肝病變過程,雖然HCV感染所誘發肝病變中涉及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相關研究,目前仍處于早期階段,但我們相信,聚焦特定靶細胞及肝內不同細胞間的相互作用,深入探索HCV感染致病過程中NLRP3炎癥小體活化在機體免疫調控中的作用,無疑將為HCV感染致病機制的研究及病毒性肝炎的臨床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3.4 肝纖維化
炎癥小體可以通過直接或間接作用調節肝纖維化過程。其直接調節主要通過肝星狀細胞(HSCs)內炎癥小體的表達進而促進肝纖維化發生[58]。研究發現,經典的誘導炎癥小體活化物質如尿酸結晶,可以活化小鼠原代HSCs和人肝星狀細胞系LX-2,尿酸結晶可以上調轉化生長因子(TGF-β)表達誘導HSCs活化并且誘導膠原等細胞外基質的產生和積累,而當敲低HSCs內ASC基因后,細胞外基質的過量產生得到顯著改善[59]。炎癥小體間接調節肝纖維化過程是通過誘導肝巨噬細胞分泌IL-1β和IL-18進而促進HSCs活化發揮作用。腸道來源的PAMPs和肝細胞損傷釋放的DAMPs都能夠活化肝巨噬細胞炎癥小體,誘導HSCs活化促進肝纖維化發生[60]。在肝纖維化小鼠模型中,IL-1β水平顯著升高,并且減少IL-1受體的表達能夠顯著抑制纖維化發生[61]。此外,在大鼠模型中,阻斷IL-1β信號能夠抑制四氯化碳誘導和硫代乙酰胺誘導的肝纖維化發生,敲低NLRP3或ASC的表達能夠顯著減少TGF-β和1型膠原蛋白的表達[62]。另有研究表明,Caspase-1作為關鍵的調控因子,在高脂誘導的肝纖維化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63]。而且研究發現,NLRP3通過IL-1R/MyD88參與了肝纖維化關鍵分子MMP與TIMP平衡的調控,促進了細胞外基質的沉積[64]。這些報道都表明,NLRP3炎癥小體參與了肝纖維化的發生發展。
纖維化形成的一般機制可能適用于大多數慢性肝病,但是,目前有關炎癥小體在除了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肝病外,其他肝纖維化疾病中作用的研究報道還是比較少。NLRP3炎癥小體在肝纖維化中的作用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闡明,其是通過DAMPs對HSCs的直接活化作用還是通過DAMPs間接誘導肝內免疫細胞分泌IL-1β和IL-18進而激活HSCs促進纖維化發生,仍需更多的相關理論及疾病模型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
4 總結
綜上所述,肝病變中,來自損傷肝細胞的無菌炎癥信號和來自腸道細菌或病毒感染細胞的病原體相關分子模式參與了肝致病過程。這些信號分子通過不同的信號轉導途徑誘導NLRP3炎癥小體蛋白復合物的組裝和活化,最終導致生物活性分子IL-1β、IL-18和IL-33的產生以及誘發細胞焦亡,而炎癥小體活化促使IL-1β等促炎因子在肝沉積,誘導肝細胞死亡以及更為關鍵的誘導炎癥小體瀑布式級聯反應在肝損傷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生物學效應。然而,在不同病因所誘發肝病理損傷中,NLRP3炎癥小體的具體激活途徑、調控NLRP3活化的不同靶點及其相互聯系以及肝微環境對炎癥小體活化的影響等仍需更多疾病模型進行探討。我們希望通過對NLRP3炎癥小體在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肝病、慢性HCV感染和肝纖維化中的作用及主要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整合及分析,進而能更加深入的了解NLRP3炎癥小體功能及在肝致病中的重要性,這既有助于為將來確切闡明其在肝疾病發病中的作用機制,也有利于尋找有效的調控NLRP3炎癥小體活化的相關信號分子或藥物,從而為臨床肝疾病的治療提供更加直接有效的藥物作用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