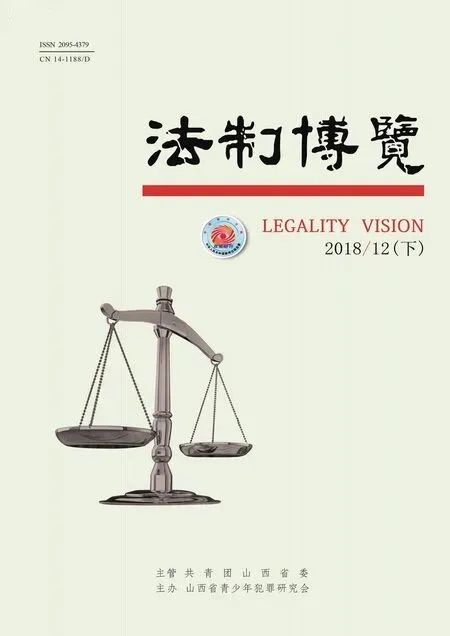漢武帝、唐太宗法律思想及其現代法治價值
黃建濤
西華師范大學,四川 南充 637002
漢武帝、唐太宗的法律思想均體現了“法律儒家化”的特征。
所謂“法律儒家化”,即在立法、司法過程中以儒家“德禮”思想為核心,將儒家思想融入法律制度,實現儒家化法律治理。漢武帝和唐太宗作為“法律儒家化”的典型代表,對“法律儒家化”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漢、唐分屬法律儒家化進程的不同階段,各自側重又有所不同,本文擬通過對漢武帝、唐太宗法律思想的對比研究,發掘“儒家化”法律思想對現代法治的啟示意義。
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法律儒家化”思想集中表現為“德禮入律,刑罰并施”、“輕刑慎罪”、“三綱”、“等級特權”四個方面,現就各自異同及對現代法治的啟示做出如下分析:
一、德禮入律,刑罰并施
即漢武帝和唐太宗治理國家時都兼采德禮和刑罰。但二者對“德禮”、“刑罰”的適用關系立場不同。漢武帝時期出現了“禮刑相悖”的司法,如漢代法律明令禁止復仇,但儒家強調“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在漢武帝推行孝道的宣傳下,全國上下孝風日盛,為親復仇者屢見不鮮,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對復仇者多加以寬免。而唐太宗則指出應“禮法相助”,如《唐律疏議》中提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即德禮是為政教化的根本,刑罰是為政教化的手段,確立二者之間的主輔關系,進而將法律的功效和禮義道德的教化作用有機結合起來,主張針對禮刑沖突案件的不同情況,做出既合禮又合法的情況。
筆者認為,對現代法治而言,應借鑒漢武帝和唐太宗“德禮入律,刑罰并施”的法律思想,一來規避刑罰僅對犯罪行為加以懲處而不能將之從源頭預防的弊端,二來可以發揮德禮對人心自覺和社會輿論自發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
而對德禮與刑之間的關系,應借鑒唐太宗“禮法結合”的法律思想,漢武帝時期禮與刑的矛盾,導致司法中有些合乎禮義的言行并不合法,而有些合法的言行并不合禮,進而司法混亂。而唐太宗“禮法相助”的思想較好的糾正了漢武帝“禮法相悖”的偏頗做法,使法律不因禮德失了威嚴,同時克服了單純刑罰的弊端,實現源頭教化。
二、“輕刑慎罪”
即貫徹“德治”傳統,在立法方面強調寬減,在司法方面體恤罪犯。對此漢律規定某些老弱婦孺病者犯罪,可減免刑罰或區別對待。唐太宗也較好的做到了“輕刑慎罪”,如貞觀時期以斷趾法代替死刑,對于重大疑難案件和死刑案件專門規定“三司會審和“三覆五奏”制度。
筆者認為,對現代法治而言,“輕刑慎罪”體現了人文主義關懷和對權力的審慎使用。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一旦定罪,公民往往處于弱勢一方。因而對以法律為實施媒介的國家權力必須秉持高度謹慎,在立法和司法環節堅持:犯罪懲處“必要性”和犯罪量刑“合理性”原則,以實現恰當懲處和優質教化的目的。
三、“三綱”和“等級特權”
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法律思想都體現了對“三綱”思想的堅守。漢武帝時“三綱入律”主要體現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強調父權和夫權,如父母的子女婚姻決定權和丈夫解除婚姻主動權,而唐太宗時亦是將違反“三綱”作為刑罰打擊的重點。
再者,“等級特權”。即將人分為不同等級,按照等級規定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權利義務。對此,漢武帝和唐太宗也是殊途同歸。漢武帝規定“貴族官僚有罪上請原則”,即遇有官僚貴族犯罪時,一般司法機關沒有私自審理的權力,須奏請皇帝,同時在具體審判時應根據其與皇帝的遐邇親疏關系、官職高低、功績大小,決定刑罰的適用或減免。唐太宗則突出的表現為“貴族、官吏可以減免刑罰”、“良賤異法”。
筆者認為,現代法治無不體現“自由、平等、公正”等核心理念,而“三綱”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爪牙,其本質與現代法治相悖,我們應對法律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的“異化”、“變質”、“腐敗”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權力的濫用。
綜上所述,筆者看來,漢、唐兩帝的法律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產物而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的時代烙印,對現代法治而言,如何對歷史理性分析并從中汲取營養是滋潤現代法治的必修功課。現代國家從不缺法律,相反,缺的是如何通過法律實現良治、善治。因此,漢武帝和唐太宗的法律思想或許給現代法治建設提供了另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