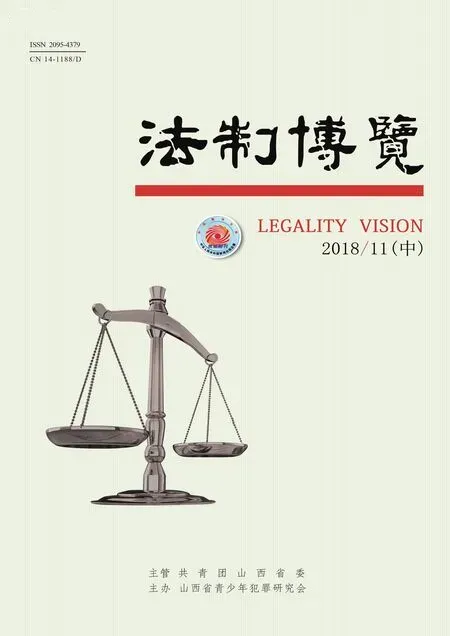淺議社會法的責任體系構成
梁秋芳 肖 珊
石獅市人民法院,福建 石獅 362700
一、社會法責任的特點及價值目的
社會法責任,是由于違法社會法而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公法責任與私法責任相互融合而產生的一種新型的法律責任。社會法責任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不同。無論是公法責任還是私法責任大多以主觀過錯為必要條件;而社會法責任則不一定將主觀條件作為歸責的要件。
第二,法律責任的形成過程不同。民事責任一般只有通過民事訴訟的提請行為才能促使國家權力的介入;行政責任是由于具有行政職權的政府部門來行使的,一般不需要通過訴權。違反社會法的法律責任,有時需與訴權聯系在一起,通過訴權將社會權利轉化為國家公權力(違反合同約定);有時則不需要通過訴權便可轉化為公權力(違反社會基準法的法定義務)。
第三,法律責任的強制程度不同。公法責任的強制程度較強,具有制裁的現實性;私法責任的強制性程度較弱,具有制裁的可能性;社會法責任的強制程度則兼具兩者的特點。
第四,承擔責任的財產去向不同。公法責任有些也是以財產來承擔;私法責任的責任主體交付財產一般交由受害人所有;而社會法責任的款項一般交給弱勢主體或特定群體。
第五,社會法責任的單向性。社會法責任是一種單向性、非對稱的、不均衡的法律責任。此外,社會法責任的過程性。社會法責任不僅僅是對違法行為或特定事件造成損失的事后彌補或懲罰,也應包括過程的控制,使責任的實現過程化。
社會法責任的價值目的:社會法對弱勢群體、特殊群體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及對社會不公平、非正義現象的糾正,對社會良性運行狀態的推動和維護。
二、社會法責任體系的構成
(一)社會法責任的主體及其特點
社會法責任主體,即社會法責任的具體承受者。其特點有:群體性;責任性;嚴格性;擴散性;復雜性;聯合性與關聯性。此外,在責任主體的認定中,社會法責任主體不一定具有法定性。在我國有些是通過法定,有些則是通過行政確認;在國外,第三方確認,如通過評估機構確認等。
社會法責任主體的上述特征,使得其在立法或實踐中,往往相當籠統,不利于社會法責任的追究和落實,使得社會法的規制作用和價值目的的實現大打折扣。這有待于日后的再研究,尋求有效的對策,以期加以圓滿解決。
(二)社會法責任主體的多元結構
其一,政府的社會法責任。作為不同于公法和私法的第三法域,社會法領域中有相當一部分體現為國家責任,因此,政府作為國家的代表,是社會法的當然責任主體。確保政府職能到位,推動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肩負起對國民、對社會的責任,以確保相關群體利益的實現和各種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進而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維護和社會良性運行,是社會法對國家責任的必然要求。因此,在社會法領域,政府必須保證立法、執法、司法投入,并完善相關程序;應推動公益性投入,構建惠及全體國民的公共財政體制,建立公共服務和產品的問責機制;應積極正當行使職權,促進資源的合理分配,落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以期實現社會法的本質追求——公平與正義的實現等等。
其二,社會中間層(組織)的社會法責任。社會中間層主要包括社會福利機構、社會保障機構、中介服務機構、工會、消費者協會、自愿者等等。社會中間層是社會法責任主體體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極,在落實社會法責任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當前,應制定和修改社團法,行業協會法、社會中介機構、福利機構法等法律,促進民間社團、非政府組織、商業、行業協會等具有各類公益、互助性質的社會組織的發育成長,規定其權利和義務及責任,進而提升整個社會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使其承擔其一定的社會法責任,改變政府對社會管理無所不包、一統到底的陳規,使得各類社會管理資源有效利用,在政府的發動和主導下,構建其多元化、民主性、合作性的社會管理模式,使社會法責任得到真正落實。
其三,弱勢群體、特定群體本身的社會法責任。在社會法領域,弱勢群體,特定群體通常扮演著權利主體的角色;但這并意味著其作為社會法責任主體就失去了可能。弱勢群體、特定群體也應被納入到社會法責任主體的多元結構中。如,國家將一部分保障弱勢全體生存的社會利益體現在社會法義務規范中,如:勞動義務等,弱勢群體自身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履行該義務,否則也須對自身的處境或弱勢狀況承擔一定的責任。
此外,個人和國際組織也是重要的社會法責任主體。個人是社會的組成單位,享有從社會獲得福利的權利,也負有積極地促進他人及社會福利的義務和責任。如必須履行納稅義務,否則,就會違反相關的社會法,承擔相應的社會法義務。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眾多環保組織、經濟聯盟、教育交流與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作用日益凸顯,其在解決國際性、全球性的社會問題時,所發揮的作用,往往是其他主體無法比擬的。在這種情況下,賦予這些國際組織社會法責任主體,使其承擔起各自的社會法責任,以推進社會的良性運行等社會法目標的實現,已成為一種共識。
總之,要構建一個多元的責任主體結構,既注重責任到人,又注重各主體在責任承擔方面的分工與協同,進而解決社會責任主體間“協同缺失的問題”,解決阻礙社會良性運行的相關問題,如結構性、突發性、弱勢性、侵擾性等問題,共同促進社會法責任得以落實和兌現。
(三)社會法責任的責任形式
社會法責任的責任形式有以下特點:其一,懲罰性賠償。在傳統私法領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而這種擴大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趨勢恰恰是社會法中法律責任形式的一個表現。(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關于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時增加賠償的規定)
其二,傳統責任形式的融合。社會法是公法和私法相互融合的產物,因而其責任形式也呈現出傳統責任形式的融合的特點,其責任設置上更側重于多種責任形式的綜合運用。傳統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或說公法責任、私法責任都可以也應當被納入到社會法的責任體系當中,以期發揮真正的作用。
其三,行為(責任過程化)。傳統的民商事領域和刑法領域,責任的承擔更注重行為和結果,及二者間的關系。社會法責任則不一定如此,其有許多特殊的東西,且行為與結果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系。其責任形式存在一個過程化的問題,以求社會法價值目的的更好實現。因此行為的發動、行為的過程、行為的關鍵階段、行為的結果等都可能產生相應的責任,承擔相應的責任形式。因而注重對相關群體行為的監測和評估,使其及時糾正,將危險或不利隱患消除在過程中,而非發展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使責任過程化,設置行為的事前預測、事中監測和事后救濟相適應的責任形式,具有重要意義。
三、社會法責任實現的保障機制
(一)完善法律體系
首先我國現有社會法領域很多法律是缺失的。如,沒有社會救助法、農民權益保障法、兒童社會福利法、社區服務條例、志愿者條例等。其次,立法層次不完善,立法層級比較低,有些法律制定出來后也沒有配套性的法律,銜接不夠。再次,是立法規劃混亂,沒有系統科學的設計和規劃,像醫療、教育等關乎生命健康與人口素質的,現有法律很有限。因此,需要制定、修改、完善社會法法律文件中的責任部分的規定,使其具有操作性和現實意義。如,現有《工會法》中對不履行法定職責所以承擔的法律責任只字不提,這種工會法律責任的闕如,使工會法演變為工會自身的權利法案,而工會法的內在價值——保障勞動這通過自由結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則有可能被架空。
(二)完善相關支持系統和保障機制
以《勞動合同法》為例,這部法律的執行和實施就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政府部門的監管積極性和監管能力、工會制度的完善和NGO組織的發展、雇主和用人單位的意識水平、勞動者自身的權利意識和維權能力以及技術水平等很多因素相關。非獨勞動領域如此,社會法的諸多領域里,社會法責任的實現也都有賴于眾多因素的綜合影響,有賴于相關支持系統和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完善社會法責任的監督體制
目前,社會法責任的兌現大打折扣,很大一個動因是群眾、外界或說社會的監督不力。因此為促使社會法責任的真正兌現,就有賴于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體制的構建和完善。既要繼續強調內部的自身監督,又要強調外部監督:如社會組織的監督、國家的監督、社會成員的監督、輿論監督等等,促就各監督主體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共同督促責任主體在承擔責任方面的態度和舉止,進而使社會責任得以兌現,相關社會問題得以圓滿解決,相關群體利益和社會公益得以維護,社會得以良性運行、社會實質公平和正義的目標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