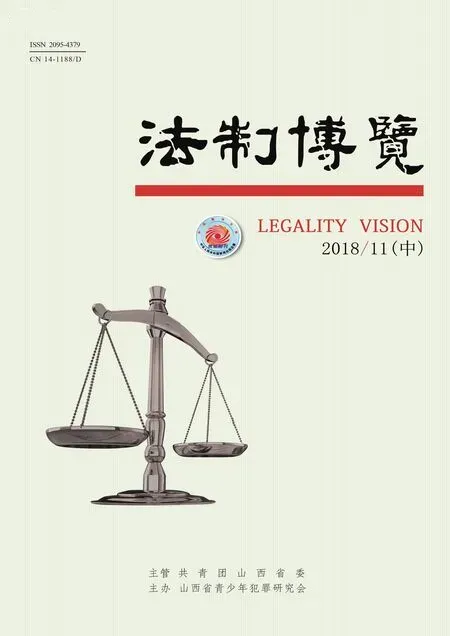暴力奪回被扣車輛應如何定性
許青青 張愛玉
福州市倉山區人民檢察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基本案情
2013年4月18日凌晨3時許,犯罪嫌疑人王某糾集犯罪嫌疑人程某和白某、齊某及其他幾名男子(另案處理),攜帶液壓鉗等作案工具,分乘由犯罪嫌疑人王某和齊某駕駛的兩部車前往某市某區某停車場,在犯罪嫌疑人王某的指揮下,由齊某及另一男子望風,由犯罪嫌疑人程某翻墻進入停車場拉掉電閘,用犯罪嫌疑人王某提供的液壓鉗剪斷停車場大門門鎖,由另三名男子進入停車場保安室對保安余某進行人身控制,防止其報警,由白某將被某市水政監察支隊依法扣押的涉嫌非法運砂的閩ABXXXX自卸貨車開走,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等人也即逃離現場。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根據刑法第九十一條之規定,在國家機關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因此被暫扣物品應以公共財產論,犯罪嫌疑人暴力搶回上述被扣物品屬不法占有公共財產,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應以搶劫罪定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搶劫罪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絕不是指行為人僅僅以侵犯占有權為滿足,其犯罪意圖是對所有權各項權能的整體侵犯。其犯罪目的是為了使財產所有權發生非法轉移。也就是說非法占有侵犯的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而不是占有權。“非法占有”的內涵是對所有權的侵犯。行政扣押行為并沒有發生所有權的轉移,而是產生了一種合法的“他主占有”,行為人奪回被扣財物,主觀上并不存在使財產所有權發生轉移的意圖,主觀上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
三、案件評析
筆者認為本案應定妨害公務罪,理由如下:
(一)本案水利局的扣押行為是否合乎法律規定?
如果水利局的行政執法行為不符合法律規定,則存在行政執法無效的可能性,那么犯罪嫌疑人取回自己所有的車子,并不構成犯罪,其暴力手段若達到刑法規制范疇則只能相應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因此,執法合法性問題是探討本案定性的基礎。
原有證實執法合法性的證據主要有執法人員黃某證言,停車場開具的“扣留道路交通違法車輛進(出)場通知單”和某派出所出具的“暫扣違法運砂車輛移交單”。因黃某執法證已過期,水利執法部門和某派出所均未出具車輛暫扣證明或相關行政處罰文書,上述證據無法證實有合法的行政強制措施或行政處罰行為存在。經退回補充偵查,現已補充某市水利局案發當日出具的《違法采(運)砂船舶(車輛)調查告知單》、《扣押物品決定書》及某市水政監察支隊出具的《某市水行政執法現場調查記錄》、現場車輛照片,某市水利局同時出具情況說明,證實市水政監察支隊系該局下屬單位,受該局委托對全市水事活動進行監督、檢查、協調,負責打擊處理管轄范圍內的非法采(運)砂活動。
由上述證據可知,2013年4月17日,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發現行駛過程中的閩ABXXXX重型自卸貨車涉嫌非法運砂,即將其移交某市水政監察支隊處理。市水政監察支隊工作人員在對運砂車輛情況進行現場調查取證后,初步認定其無證運砂,對其出具扣押文書。因當事人不在現場,由見證人簽字確認。根據《行政強制法》的第二條、第九條之規定,扣押財物是行政執法單位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為制止違法行為對公民或法人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政強制措施。根據《行政強制法》第十八條之規定,當事人不到場的,邀請見證人到場,由見證人和行政執法人員在現場筆錄上簽名或者蓋章。也就是說水政監察支隊依法履職,執法程序上是可行的。
筆者認為還需強調的是,水利部門執法瑕疵是否會影響到執法有效性的問題,關鍵要看執法人員有沒有根本性違法行為的存在。本案中,由于車輛確實因無證運砂被交巡警部門發現并移交水利部門,而水利執法人員依法執行權限,當事人也明知車輛因無證運砂被水利部門扣押,雖文書上有一定瑕疵,但并不存在根本性違法的問題,因此不影響執法的有效性。
(二)作為車輛的實際所有人,王某結伙暴力奪回被依法扣押的車輛的行為,應該如何定性?
筆者認為,將主觀故意與客觀行為割裂開來,圍繞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就會陷入財產犯法益的爭論中無法厘清思路。財產犯法益中,所有權與占有權原本就是無法分離的,占有權是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基礎,他主的合法占有,并不以單純占有為目的,同樣也有為了使用、處分等權能的實現。侵犯所有權之一的占有,同樣是對所有權能的侵犯,純從法益角度來分析主觀故意是不科學的。
回到案件本身,行為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犯罪嫌疑人王某供述體現,其主觀上是“因為車子被扣沒辦法運砂賺錢,又要交幾萬的罰款,這樣損失很大,影響做生意。”也就是說,其主觀上是希望車子既不被扣也不用交罰款,希望通過暴力奪車的行為逃避行政機關的處罰。也就是說,其主觀上是為了對抗執法,目標是阻礙行政強制措施(扣車)和行政處罰行為(罰款)的執行。客觀上實施的暴力奪車行為也反映了其主觀上的供述。這樣的主客觀是否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之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搶劫公私財物的構成搶劫罪。我們知道,搶劫罪不僅侵犯他人財產,也侵犯他人人身權利,因其嚴重影響人民生產、生活安全,社會危害性巨大,成為了財產罪中最嚴重的犯罪。而本案車輛并不屬于“他人財產”,奪回自有車輛和強取他人財物在本質上和社會危害性上都是有明顯不同的,行為人的錯誤在于沒有通過合法手段取回財物,而不是暴力占有他人財產。奪車行為只是其對抗執法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其目的。
再看法律規定,刑法上對于行為人隱藏、轉移、變賣、故意毀損被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的非法處置行為專門規定了第三百一十四條“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被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本質上也屬于一種合法的“他主占有”,按刑法擬制規定也屬于“公共財產”,行為人不管作何處分,均要以轉移財產占有權為前提,如果將這類處分行為理解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那么上述罪名就應修改為“盜竊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等。從法條中我們亦能體會到立法的本意,并不認為上述行為侵犯的是他人的財產權。
那么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妨害公務罪?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從主客觀上分析,行為人主觀上是希望通過暴力奪車的行為逃避行政機關的處罰,目標是阻礙行政強制措施(扣車)和行政處罰行為(罰款)的執行,符合妨害公務的故意和目的。客觀上,行為人實施了暴力奪取被扣押車輛的行為,符合妨害公務罪的主客觀構成要件。從行為對象上看,根據高檢院2000年4月24日《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執法職務是否可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對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有事業單位人員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中受委托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事業編制人員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以妨害公務罪論處。水政監察支隊受該局委托對全市水事活動進行監督、檢查、協調,負責打擊處理管轄范圍內的非法采(運)砂活動。水政執法人員符合上述行為對象要求。再次,妨害公務罪要求行為發生應是發生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執行公務的過程中,包括從開始執行職務時至職務執行完畢的全過程。執行職務行為通常表現為一個連續性的過程,而要完成行政處罰行為,除本案中體現的已完成的調查、扣押手續之外,還需履行告知、聽取當事人申辯、做出決定、送達文書等程序,因此,就本案而言,行政處罰行為當日尚未完成,公務尚在履行當中。
不同觀點會認為,案發時水政執法人員并不在現場,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對象是停車場保安,因此不構成本罪。經辦人認為,本案中,水利監察支隊將暫扣車輛委托停車場代為專門看管,則停車場保安的看管行為應視為國家機關依法執行公務的延續,與水利執法人員的暫扣行為是一個有機整體,作為扣押車輛的公務行為的執行過程,不能將二者簡單割裂開來。暴力阻礙保安看管暫扣車輛,同樣是阻礙了公務的正常履行,因此本案仍然符合上述構成要件。若對本案行為對象還有疑慮,可從相關司法解釋分析,兩院2003.5.15施行的《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治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而采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第三款的規定,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兩院2007.3.1施行的《關于辦理危害礦山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礦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顯然不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后者直接未規定行為對象,而是只描述“阻礙礦山安全生產監督管理”,也就是說,如果本罪要求一定要針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的話,那么刑法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已有明確界定,就不應再規定上述司法解釋,對其作如此擴大化解釋。我們可以據此得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應是側重于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作為一個賓語整體來看待,只要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這個整體,那么就構成妨害公務,而不是一定要阻礙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的職務。而本案中執法人員不可能全天候自己看管扣押車輛,保安受托看管被扣在停車場的非法運砂車輛,顯然屬于執法過程的一個重要環節,符合上述內涵。
在案例搜尋過程中,發現三個類似判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江世田聚眾以暴力手段搶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一案[1]判處妨害公務罪;江蘇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判決的一起朱某某等妨害公務一案中,朱某某等人持械結伙進入停車場搶回被交通稽查大隊查扣的車輛,依法判處妨害公務罪。該案在泰州晚報中有報道“靖江法院請示最高院,把本案定性為妨害公務罪”;甘肅省天水市中級法院也對一起楊某某等暴力奪取因無《道路運輸證》被道路運輸管理局稽查大隊扣在停車場的案件裁定維持原審判決,定妨害公務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