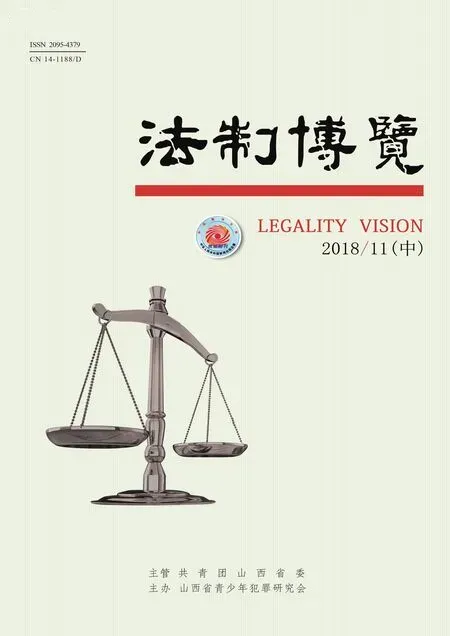秘密退回網購支付價款行為的定性
宋香達
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科,天津 300450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王某曾因犯盜竊罪被判處緩刑。犯罪嫌疑人王某2017年3月28日通過網上閑魚軟件在與被害人李某達成協議,以人民幣5000元的價款購買李某的一部蘋果7PLUS手機。2017年3月31日下午兩點多,王某與李某在李某所在單位的門衛崗亭進行交易,王某在確認被害人的手機沒有問題后,在閑魚軟件上向李某支付了5000元的價款,并向李某承諾,其已經將錢支付到咸魚軟件的支付平臺,待其回到住處檢測過手機沒有其他問題后會在自己的閑魚軟件上點擊確認收貨,價款自然就轉到李某的賬戶,李某見其已將價款支付,便將手機內卡取出后將手機交付王某,后王某離開。當天下午四點左右,王某向李某索要蘋果手機的手機解鎖密碼打開蘋果手機后,發現被害人李某使用的閑魚軟件尚未關閉,遂產生能否將之前支付的5000元錢退回來的想法,于是王某先在自己閑魚軟件上點擊申請退款,然后在李某手機上的閑魚軟件點擊同意退款申請,在輸入密碼時,嘗試著輸入李某告訴其的手機解鎖密碼,因李某設置的手機鎖屏密碼與其在閑魚軟件的密碼相同,王某輸入密碼后,其支付的5000元人民幣轉回到自己的支付寶賬戶。待被害人發現自己手機內的申請退款短信,登錄自己的閑魚賬號時,發現退款已經成功,遂向公安機關報警。
公安機關將犯罪嫌疑人王某以涉嫌詐騙罪刑事拘留后,向天津市濱海新區塘沽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逮捕。
二、爭議焦點
本院受理案件后,經過審查,對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形成了三種意見:
(一)王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此案是典型的三角詐騙,被騙人是支付寶公司,實際的受害人是賣家。
(二)王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在買家未確認收貨之前,支付寶賬戶內的資金由買賣雙方共同占有,犯罪嫌疑人將雙方共同占有的財產占為己有,構成侵占罪。
(三)王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支付寶中的財產歸被害人所有,王某某以秘密的手段將被害人的財產據為己有,構成盜竊罪。
三、評析意見
(一)王某行為的不構成詐騙罪
公安機關認定被害人手機被騙,缺乏事實依據。本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基于真實的購買意圖在閑魚軟件上購買被害人的手機,且已經向支付寶平臺支付價款,根據交易規則,被害人只有在王某“確認收貨”后才能取得價款,因此,被害人交付手機是正常履行買賣合同的行為,王某按照交易流程合法取得手機,不存在騙取手機的行為,其犯罪行為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取得交易價款,由此可見,被害人并未因陷入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產。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王某是冒用被害人的身份,欺騙了支付寶平臺,對其代管的被害人財產進行處分,該行為構成三角詐騙。對此,學界的主流觀點(如張明楷、陳興良等的觀點)是,“機器不能夠被騙”①,因為機器本身沒有意識,更無錯誤認識。本案中支付寶平臺同樣是按照符合程序的交易指令進行轉款,其在本案中只能被視為王某取得退款的作案工具,故不能構成三角詐騙。
(二)王某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
有觀點認為,在買家未確認收貨之前,支付寶平臺內的資金是由買賣雙方共同占有,王某將雙方共同占有的財產占據為己有,構成侵占罪。網購活動的特點就在于,存在一個第三方支付平臺,買方是將自己賬戶內的交易價款支付給支付寶平臺,由支付寶平臺來代為保管,一旦支付成功,買方隨即喪失對價款的支配地位,其不能單方面收回,賣方也無法直接取得,只有在買方收到賣方交付的貨物之后,進行確認操作后,該筆價款才會轉入賣方賬戶。所以,支付寶平臺在買方支付價款后,成為了這筆資金(也即背后的存款債權)的占有者,買賣雙方享有的只是債權請求權。退一步來說,即便不承認該筆價款是歸支付寶平臺占有,至少從王某的角度來說,由于其將價款支付出去的事實,其已經不具有對價款單方面的支配地位,既不占有價款的現金,也不占有價款的債權,應當認為其喪失了對價款的占有,不能構成侵占罪。
(三)王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盜竊罪在客觀上是竊取他人財物,其與詐騙罪的差別是被害人是否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物,與侵占罪的差別是行為人是否合法占有財物。結合上述論述,王某沒有騙取被害人的手機,也沒有侵占被害人的價款,但王某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登錄了被害人的閑魚軟件賬戶,并進行了退款操作,這就等于非法獲取他人賬戶權限,盜取他人的資金。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與被害人李某通過閑魚軟件進行交易,基于意思自治,雙方應當遵照平臺的交易規則,只要王某收到手機并檢驗無誤,就理應配合賣方,進行確認操作,使這筆價款轉入賣方賬戶。本案被害人當場交付了手機,但王某沒有當場“確認收貨”,而是承諾事后檢驗手機沒問題再操作,但是王某在知曉手機原有解鎖密碼,且發現所購手機上被害人的閑魚賬戶尚未關閉后,產生了非法占有目的,利用解鎖密碼恰巧成功進入被害人的賬戶,完成了退款操作,支付寶平臺按程序將價款轉回王某賬戶,進而盜取了5000元的價款,構成盜竊罪。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聯合出具的《關于搶劫、盜竊、詐騙、搶奪借據、欠條等借款憑證是否構成犯罪的意見》中:債務人以消滅債務為目的,搶劫、盜竊、詐騙、搶奪合法、有效的借據、欠條等借款憑證,并且該借款憑證時確認債權債務關系存在的唯一證明的,可以以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論處。這一規定也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上述觀點,結合本案事實,買賣雙方以5000元價格購買手機的買賣合同已經訂立,并通過支付寶平臺進行交易支付。被害人交付合同標的物,已經履行了合同義務,依法享有合同權利,即要求王某支付價款。王某基于合同,在收到手機且確認無瑕疵或缺陷后,負有進行確認操作的義務,而支付寶上價款支付情況就相當于被害人所持有的一種債權憑證。王某對處于已支付價款情況進行了更改,導致價款按程序退回,消滅了債權債務,侵害了被害人財產權,使自身形成財產性獲利,屬于盜竊。
推而廣之,王某的這種行為,與實務中存在的利用木馬程序盜取資金的行為其實沒有差別。對于這類行為的定性,筆者認為可以作這樣的區分,如果是在交易平臺或交易過程中,利用虛假鏈接或釣魚網站,將被害人支付的錢款轉入犯罪嫌疑人賬戶,應當認定為詐騙罪;如果是在被害人登錄賬戶或進行其他操作過程中,利用植入的木馬程序,盜取被害人賬戶并進行轉賬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這其中的本質差別就是被害人是否基于認識錯誤而處分財產,前者存在處分財產的行為,只是由于受到虛假程序的欺騙,將錢款支付給了錯誤的對象,而后者則不存在處分財產的意思,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盜取了財產。本案同理,王某雖然合法取得了手機,但手機和手機上的軟件賬戶是相互獨立的,閑魚軟件雖然存在于該部手機上,但被害人的閑魚賬戶當然歸屬于被害人,王某對手機上的被害人賬戶沒有處分權,被害人也沒有將自己的閑魚賬戶交給王某使用的意思,其只是利用手機解鎖密碼恰巧成功登錄了被害人的賬戶,從而獲得了操作權限,因此被害人對價款沒有處分行為,王某是在被害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取回價款,符合盜竊罪的行為模式。犯罪嫌疑人王某故意竊取應當由被害人取得的價款5000元,損害了被害人的財產權,構成盜竊罪。
四、處理結果
承辦人經過審查,最終改變了公安機關以詐騙罪移送審查逮捕的定性,對犯罪嫌疑人王某以盜竊罪批準逮捕,后提起公訴。
天津市濱海新區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被告人王某犯盜竊罪,判處拘役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其被撤銷緩刑,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
[ 注 釋 ]
①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