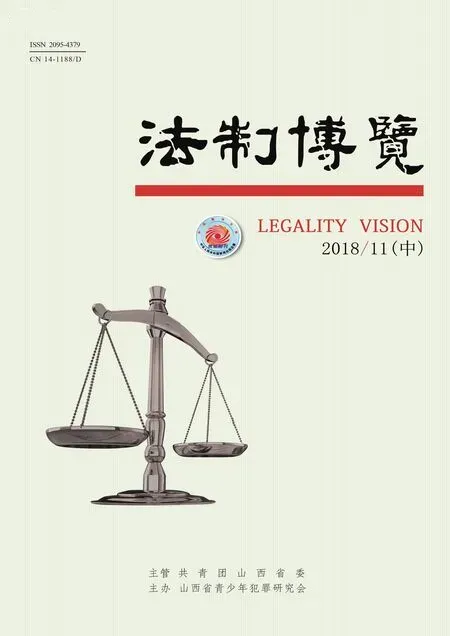高度蓋然性證據規則適用
張遠雄
天柱縣人民法院,貴州 天柱 556699
一、基本案情
2016年3月2日21時37分,公安民警出警現場,發現楊某已經死亡,死者仰面平躺于路面,頭朝邦洞方向,腳朝大河邊方向,閩ANC031號普通二輪摩托車(系死者楊某生前駕駛)。經檢驗,結合死者左胸部損傷及外衣左胸部破口特征、大小分析,將致傷工具推斷為一類圓形或橢圓形且帶有不規則粗細不均長短不一凸起的鈍性物體。結合死者皮衣及左腰部皮膚搓擦痕分析,符合死者生前被撞擊后仰面摔跌軀體背側與粗糙地面縱向滑行形成的損傷特征。事發地位剛好處于盲區,死者倒地不遠處有另一叉路通往事故發生路段,且該交叉路段無任何監控。通過調取該路段的兩個視頻監控發現,一輛裝載木柴的三輪車有重大作案嫌疑。在公安機關偵查過程中,對被告駕駛三輪車及死者楊某駕駛普通二輪摩托車進行了痕跡檢驗,經檢驗,三輪車未與任何車輛及物品相接觸,二輪摩托車除現場路邊的刮擦泥土痕跡,未與其他車輛及物品相接觸。
二、案件爭議焦點
死者楊某的死亡與被告李某的駕駛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三、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認為,事故發生時間為晚上,該路段沒有路燈,結合事故現場記錄及死者尸檢報告單,死者不符合被一般車輛(如當晚經過的大貨車等)直接撞擊死亡的情形,死者駕駛的車輛未被撞擊的痕跡,證明車輛沒有與任何物體接觸,人體受傷部分距地面高1.2米左右,形成是由一類圓形或橢圓形且帶有不規則粗細不均長短不一凸起的鈍性物體造成。因無法查找當時經過的全部貨車,公安機關就卡口照片中經過貨車照片比對車形,選擇相同車型的車輛進行比對,該車型在1.1米至1.3米處無突出部位,更沒有類似圓形或橢圓形的突起鈍性物體,由此排除了當晚經過的大貨車為肇事車輛的可能性。被告在公安機關的筆錄中陳述其當時因喝酒后有些頭暈,駕駛速度在40-50碼的范圍,也認可在事故發生地附近與一輛車會車時感覺到左邊車廂伸出的木柴與對方發生了刮擦,但因當時他正在試圖超一輛大貨車,所以不清楚后果。結合公安偵查機關做的偵查實驗,在符合死者駕駛車輛情況和被告駕駛車輛木柴擺放特征,雙方駕駛達到一定速度發生碰撞的情形下,摩托車駕駛人在與對向行駛三輪車會車時,被伸出車輛的木柴直接撞擊左胸是完全可能的。根據事發路段前后兩個監控的記錄,被告李某在該條道路的駕駛期間為當晚21時25分至21時33分,結合證人吳培友、李家彪等人的證言也能相互印證發現死者及報案的情況,從以上的時間點來分析,事故發生的時間應當是被告李某在該路段行駛的期間內,與吳培友、李家彪相遇的裝載木柴的三輪車應為被告李某駕當晚駕駛的車輛。至于交叉道路的疑點,該路段的確有一條交叉道路通往事故發生地,剛好那條交叉道路無視頻監控,根據實地現場查看,該條分支道路較窄,平時車流量也較小,從事故現場圖死者倒地的位置來看,死者倒地位于該交叉路口的前方,死者損傷部位是在其前左胸位置,從死者行駛的方向和路線來看,從該交叉路口直接駛出車輛撞擊死者,應當是撞擊到死者的右側或者后方,形成不了死者損傷及事故現場的情形。在短短幾分鐘內,從該條道路駛出符合能夠造成死者死亡特征的車輛,從岔路口開出后又調頭返回行駛并撞擊死者的可能性很小。綜合本案的現有證據,與被告駕駛的三輪車發生刮擦的車輛系死者楊某駕駛的二輪摩托車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據民訴證據高度蓋然性的規則,可認定死者楊某的死亡與被告李某的駕駛行為存在因果關系,被告李某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二審法院認為,一審判決認定李某酒后駕駛行為與與死者楊某的死亡存在因果關系,系采用了民事訴訟中“高度蓋然性”證明規則。《最高人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為達到法律的角度認為最接近于客觀事實的法律事實狀態,只能依據現有的證據來進行綜合判斷,故一審判決采用高度蓋然證明原則,并無不當。
四、實務經驗總結
筆者認為適用“高度蓋然性”標準時,其法理依據為:
(一)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和認定,在雙方當事人舉證和質證的基礎上,以優勢證據原則理論為依據,以區別法官的主觀臆斷。高度蓋然性規則以證據證明力優劣,作為法官裁判的尺度。
(二)法官須恪守中立、超然地位,應依據舉證規則來調節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承擔,并可依職權對任何一方的不當行為予以干預,保障當事人間對抗式訴訟的有序進行。
(三)高度蓋然性規則要求法官對認定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的理由在判決書中詳加說明,這要求法官須具備淵博的法學理論知識、文字表達能力、邏輯分析本領、社會生活經驗以及清正廉明的優良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