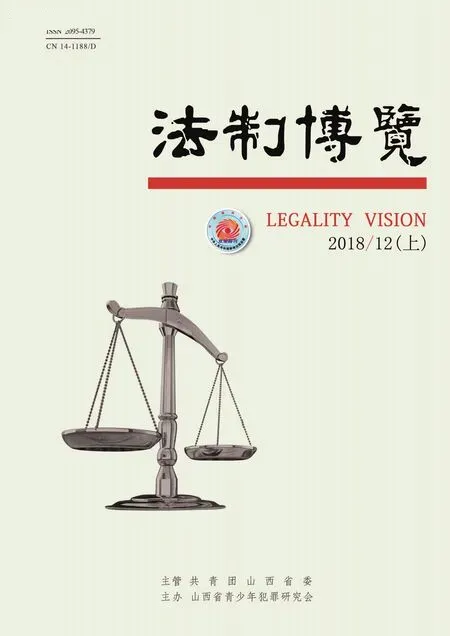移動設備內財物非法轉移定罪問題研究
——以王某某盜竊案為例
耿一斐
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檢察院,天津 300300
一、案件簡要事實
2017年10月6日下午,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母親劉某甲在其居住的樓下撿到的被害人劉某乙丟失的手機,后將此事告訴王某某。王某某經過反復嘗試,試出了被害人劉某乙的微信支付密碼,發現被害人劉某乙的微信零錢內有人民幣5000元,并且綁定的平安銀行卡。之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通過四次轉賬操作,將綁定的平安銀行卡內的人民幣10000元轉入被害人劉某乙的微信零錢內,并使用該手機,以微信支付的方式將被害人劉某乙微信零錢內人民幣15000元用于消費購物。
二、本案爭議的焦點
如何認定本案中王某某行為的性質是本案爭議的焦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王某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數額為人民幣15000元。該種觀點認為,雖然王某某實際控制了被害人的手機,但是其在將被害人銀行卡內的錢轉移至微信零錢中后,被害人并沒有完全喪失對微信零錢內的財產的控制權,即被害人可以通過補辦電話卡,使用其他手機登錄微信的方式,控制自己的微信賬戶,并將微信零錢內的錢通過轉賬、消費的方式進行處置。而在王某某使用該手機,以微信支付的方式進行消費后,被害人對王某某購買的產品完全喪失了控制能力,進而使得王某某對于以被害人財產等價交換的財物完成了非法占有。而在王某某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過程,王某某是以一種秘密的方式進行的,所以符合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的規定,應當以盜竊罪追究王某某的刑事責任,盜竊金額為人民幣15000元。
第二種觀點認為,王某某的行為應當以盜竊罪、信用卡詐騙罪數罪并罰,其中盜竊罪的數額為人民幣5000元,信用卡詐騙罪的數額為人民幣10000元,盜竊罪數額為人民幣5000元。該種觀點認為,王某某獲得手機的方式雖然不是非法方式,但是其使用該手機微信零錢內的余額的行為,是一種以秘密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應當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而對于王某某從被害人銀行卡中轉賬到被害人手機微信零錢內的10000元人民幣,該種觀點認為,該行為符合信用卡詐騙罪中“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規定。因為根據2009年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規定,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竊取、收買、騙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互聯網、通訊終端等使用的。而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以非法方式取得被害人微信支付密碼,獲取了被害人信用卡信息資料,并通過手機這種通訊終端獲取了被害人的財物,符合刑法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規定,所以王某某非法取得被害人銀行卡內的人民幣10000元的行為應當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三、對本案的認定
筆者認為,認定該案的關鍵是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何時實際完全占有了被害人的財產,即被害人何時對自己的財產失去了控制。對此問題的解答需要對移動設備支付的流程有所了解。對于微信、支付寶這類移送支付軟件,需要獲得本人真實身份信息并與一有效銀行卡綁定才能完全實現其支付功能,在支付的過程中,行為人可以選擇將銀行卡內的錢轉入支付軟件中,然后通過支付軟件支付,也可以直接通過支付軟件關聯的銀行卡支付。簡而言之,對于第一種支付方式,支付軟件具有類似于銀行卡的功能,支付是由支付軟件完成的,與綁定銀行卡沒有關系;而第二種支付方式,支付軟件只是一種支付輔助工具,類似POS機的功能,支付的主體還是銀行卡。
對于本案來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明顯采取的是第一種支付方式,即先將錢轉入到支付軟件中,在通過支付軟件進行支付。所以對于被害人來說,對其手機內的支付軟件是否失去控制是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實際占有財物的關鍵。而支付軟件由于賬戶的唯一性、特定性以及與身份證明的關聯性,使得被害人可以通過輸入賬戶、密碼或者使用關聯身份證明重新獲得該唯一、特定的支付軟件賬戶的控制權,從而對該支付軟件賬戶內的財產進行處分。而如果被害人先于犯罪嫌疑人對該支付軟件賬戶內的財產進行了處分,就很難認定犯罪嫌疑人已經對該財產非法占有了。所以,應當認定當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在使用該支付軟件賬戶進行購物消費時,財產以消費換取等價物的方式被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了。由于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并沒有將支付軟件認定信用卡或者具有信用卡功能,所以不能將支付軟件類推為信用卡,即不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同時,該行為符合具有違法性、秘密性的盜竊罪的特征,所以應當以盜竊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