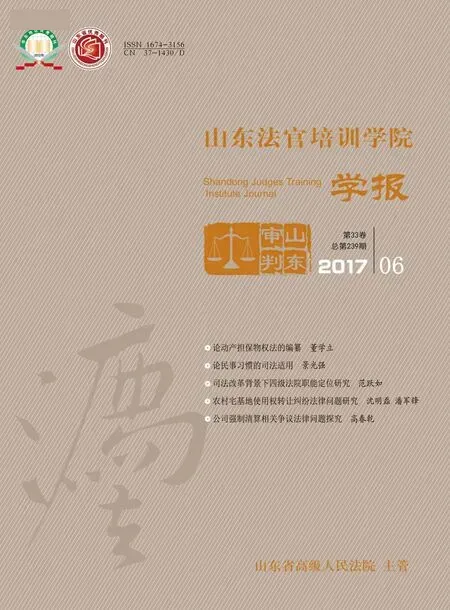挑戰與機遇:新形勢下人民法庭發展的路徑選擇
●孟祥剛 任運通
新形勢下,人民法庭發展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基層司法需求快速增長與法庭資源配置和司法能力有限性的矛盾;二是司法改革中審判權運行的統一性和單向性要求對傳統法庭工作理念和模式的沖擊。人民法庭作為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依法行使審判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著聯系群眾、服務基層、化解矛盾、推行法治等多項職責使命。面對挑戰,唯一的出路深化基層司法“供給側改革”,更新司法理念,匡正職能定位,創新工作模式,發揮便民優勢,“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①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載《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頁。
一、基礎數據:德州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概況
(一)法庭分布和隊伍建設情況。平均每個縣市區法院設有3.9個人民法庭。每個法庭平均配備7.1名干警,其中有1.34名員額法官,3.55名法官助理和書記員,1.21名法警,1名工勤人員。

全市人民法庭和隊伍情況表

轄區陪審員人數禹城市法院 5 28 11 13 7 7 0 24樂陵市法院 5 37 11 12 5 10 4 24寧津縣法院 3 9 6 3 4 0 5 15齊河縣法院 5 23 10 16 0 4 0 20臨邑縣法院 5 22 14 18 6 3 6 21平原縣法院 5 15 12 21 10 4 0 39武城縣法院 3 8 5 4 7 1 1 12夏津縣法院 5 15 13 12 2 0 0 70慶云縣法院 4 12 9 6 4 6 14 20合計 47 206 110 122 57 47 34 337法院名稱 法庭個數正式干警人數法官人數書記員人數法警人數其他輔助人員人數編外工勤人數
(二)法庭審判工作情況。全市人民法庭2012年至2016年審結案件分別為15047件、13707件、14097件、18806件、19798件,每個法庭平均值為320件、292件、300件、400件、421件。占全市基層法院結案總數的33.4%,在一些法院法庭結案占到51.5%。

全市人民法庭審判工作情況表
(三)法庭基礎建設情況。全市人民法庭占地面積共100652.5平方米,平均2141.5平方米;建筑面積44741.65平方米,平均951.95平方米。共建有高清審判法庭41個,普通審判法庭39個,平均每個法庭有審判庭1.7個。共配備辦案車輛43輛,平均每個法庭0.92輛。2016年以來,新建成和在建法庭9處,建筑面積共11450平方米,項目投資共5000余萬元。
二、客觀挑戰:基層司法需求增加與人民法庭的“不可承受之重”
隨著城鄉一體化、城鎮現代化進程加快,城鄉制度結構和社會結構加速轉型,社會矛盾糾紛復雜多變,基層社會對司法的需求、依賴和期待日益提高,對人民法庭工作提出重大挑戰。
(一)行政手段自抑導致社會矛盾司法化。近年來,“依法治理”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準則,基層黨委政府正在逐步實現治理方式轉型。這既是基層治理現化代的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一是全面依法治國成為國家戰略;二是城鄉二元結構逐漸瓦解,新的利益群體和利益訴求不斷涌現,日益呈現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點,②劉爽:《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哪些突出難題》,載《人民論壇》2017年第2期。原來長期使用的“老辦法”不管用了;③參見習近平:《依靠學習走向未來》,2013年3月1日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載《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頁。三是基層行政治理方法,很容易產生纏訪鬧訪、群體性事件、個人極端事件等“次生災害”,導致矛盾糾紛的復雜化長期化。因此,基層黨委政府逐漸改變“為了追求地方秩序穩定,違反規則處理社會矛盾或者回避矛盾的做法”,④參見常怡:《中國調解的理念變遷》,載《法治研究》2013年第2期。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把大量土地征收、拆遷安置、勞動報酬等矛盾引導到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承載了巨大的政治、信訪和輿論壓力,同時基層黨委政府對法庭的支持減少,很多矛盾難以化解。
(二)基層自治缺位導致司法防線前沿化。基層自治是消化社會矛盾的第一道防線。當前,基層自治的缺位主要表現在四個層面:一是一些基層組織不健全,或渙散無力、功能弱化,或缺少權威性和凝聚力,僅能完成最基本的治理任務;二是基層人口流動性增加,農村常住的大部分為留守婦女、兒童、老人,難以形成完整的社會自治結構;三是賴以維系傳統社會秩序的宗法體系和“禮治”文化崩壞,基層社會關系的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減弱;四是民間調解組織很多處于半癱瘓狀態,缺少解決矛盾的內生動力。由此,大量本來可以在基層組織內部消化的矛盾糾紛涌入人民法庭。
(三)基層矛盾多發導致訴訟壓力劇增。從近5年來我市法庭審理案件的數據看,基層社會的矛盾糾紛明顯呈現數量多發、類型多樣的趨勢。傳統民間糾紛如婚姻家庭、民間借貸、勞動爭議、土地承包、人身權利等持續增加,新類型案件不斷增長。
與此同時,人民法庭審理案件的調解率持續下降,服判息訴率略有下滑,二審改判發還率略有上升,反映基層社會矛盾糾紛的激烈程度、復雜程度和處理難度日益加大,人民法庭承載的辦案壓力不斷加重。
(四)基層社會變遷提高了法庭辦案成本。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農村訴訟不便的問題得以解決,但產生的大量新問題。如大量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糾紛當事人多為年輕人,很多外出務工,路途遙遠,往返費用高,請假離崗難,使當事人一再請求法庭延期開庭,要么聽之任之不到庭參加訴訟,增加了辦案難度。再如一些當事人居住點經常變動,有的還刻意回避矛盾糾紛,對法院有排斥心理。這些現象造成大量案件送達難、溝通難、調解難,傳統的舉案說法、耐心交流、法律引導等調解工作方法難以使用,難以從根本上化解矛盾。
(五)司法需求多元導致法庭公信危機。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期待和要求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聘用律師代理訴訟的越來越多,不但要求實體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二是對立案、信訪、接待、咨詢等司法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不但要求司法公平公正、便捷高效,還有一些當事人認為基層法庭不莊重、工作不規范,強烈要求自己的案子移交到法院機關審理;三是對法官的綜合素質要求更高,既希望法官具備過硬的專業能力,又希望法官能夠用他們聽得懂的方式溝通交流;四是一些群眾仍存在“信訪不信法”的現象,要求領導出面、特事特辦、馬上解決。人民法庭樹立司法公信,任重道遠。
三、自身問題:法庭司法服務供給不足與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隨著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深入推進,人民法庭的職能定位、司法理念、隊伍結構和權力運行模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人民法庭工作產生了一些新短板、新問題,需要“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為契機,進一步發揮人民法庭便民的獨特優勢,當好司法為民排頭兵”。⑤孟建柱:《在第三次全國人民法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中國法院網,2017年9月6日訪問。
(一)政治擔當弱化,職能定位單一化。司法責任制改革的影響既深且巨,人民法庭工作在全方位調整轉型過程中,司法體制和運作程序中的統一性及隨之而來的僵化性日益增強。⑥高其才、黃宇寧、趙彩鳳:《基層司法——社會轉型時期的三十二個先進人民法庭實證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頁。一是“去地方化”矯枉過正。有的法庭對自身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清晰,片面強調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由于人財物對駐地基層黨委政府的依賴度降低,有些法庭對基層黨委政府“敬而遠之”,不愿意“多管閑事”。二是過分突出“審判主業”。有的法庭把全部資源力量投入到辦案中,新型審判團隊職能單一化、集約化、程式化,對審判之外的聯系群眾、司法宣傳、法律服務等職能發揮不夠重視。三是協作配合的主動性不夠。有的法庭多元化解矛盾糾紛機制不完善,與相關部門協調聯動不夠,主動把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變成“最前線”,把“綜合治理”變成“單打獨斗”。“審判權是獨立的,但它不是孤立的……它要發揮作用離不開外部機制的承接、支持、續展甚至監督”。⑦蔣惠嶺:《同步推進司法改革的五大配套工程》,載《法制日報》2016年1月20日。以上種種,造成法庭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參與度不夠,綜合性職能作用發揮不充分。
(二)基礎建設不均衡,資源配置不合理。由于種種原因,“兩便原則”和“三個面向”在一些法庭落實不理想,亟待加強和優化。有的法庭空間設計不合理,審判區、辦公區、生活區混同,便民崗位和設施不健全,不能提供訴訟引導、立案審查、咨詢解答“一站式”服務;有的法庭信息化投入不足,不能保證全程錄音錄像,網上立案、電話預約、電子簽章等工作平臺闕如;有的法庭隊伍配置不全,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等輔助人員配備不足;有的法庭聘任制干警占比較高,人員流動性強、更替頻繁,整體業務素質不高;有的法庭工作程序不規范,司法各工作環節銜接不順暢,造成程序性內耗。總之,法庭在加大資源投入的同時,要提高審判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集約化水平,以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
(三)服務意識不強,工作方法簡單化。一些法庭工作水平不高、效果不好、得不到群眾認可,主要是司法理念和工作方法存在問題。一是自身定位不準。以國家權力行使者和基層社會的管理者自居,坐等當事人上門。二是紀律作風不嚴。有的法庭管理粗放,紀律松散,工作人員著裝不規范,用語不文明,習慣于用治理邏輯而不是法治邏輯解決問題,⑧參見趙曉力:《基層司法的反司法理論——評蘇力〈送法下鄉〉》,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對群眾動輒冷硬橫煩。三是工作方法簡單。有的法庭只求結案數量,不管辦案效果,長期不搞巡回審判、送法上門、判后回訪活動,⑨參見周磊:《職能回歸:人民法庭參與創新社會管理新模式探尋——以S省P縣法院人民法庭職能轉型為微觀樣本》,載《今日中國論壇》2015年第10期。疑難復雜案件不會爭取黨委政府領導支持、協調有關部門共同化解。四是創新意識不強。有的法庭成為“辦案作坊”,總結不出可推廣的經驗做法,提不出有價值的司法建議。人民法庭思想政治、司法能力、紀律作風建設的任務仍然很重。
(四)法庭隊伍不穩定,綜合素質不過硬。當前,人民法庭處理的案件類型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田土細故”和“家長里短”,⑩參見蘇力:《中國農村對法治的需求與司法制度的回應——從金桂蘭法官切入》,載《人民法院報》2006年3月27日。對法官綜合素質提出更高要求。司法改革在短期內不可能使隊伍素質產生質的變化,在過渡期司法能力與任務不匹配的矛盾可能會更突出。如新型審判團隊成員要經過充分磨合,才能發揮分工協作的優勢;年輕法官要經過相當時間的實踐鍛煉,才能適應基層工作環境,掌握辦案技能;法庭隊伍保持相對穩定,職能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基層司法環境和條件艱苦,真正長期扎根在基層、奉獻在基層的優秀干警不多。隊伍素質是決定法庭司法水平最根本的因素,因此必須深化系統性改革,解決這一關系全局的問題。
四、路徑探索:人民法庭發展的理念更新和機制創新
面對新形勢新挑戰,去年利用大半年時間,走遍全市47個法庭,總結經驗,查找短板,研究對策,提出“強化四個理念、打造四個品牌”的工作思路,推動人民法庭轉型升級。
(一)強化政治理念,打造基層社會治理品牌。一是高點定位,全面參與。找準法庭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定位,理順基層黨委政府的關系,圍繞中心工作出思路、劃重點。如去年以來,樂陵市全面構建社會矛盾大調解格局,法庭全面參與市鎮村三級調處平臺,與綜治、信訪、公安、司法等部門建立聯調聯動機制,得到樂陵市委市政府充分肯定。二是把握機遇,主動融入。堅持“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全方位、多層次介入全局性工作,為地方發展作出貢獻。如我市陵城區提出“全面融入城區、創建文明城市”的任務目標,陵城區5個法庭開展“弘揚司法文明、建設法治陵城”活動,通過法治宣傳、法律咨詢、凈化環境等工作,為創城加油助力。三是發揮優勢,服務全局。針對影響基層改革發展的突出問題,發揮法庭陣地靠前、熟悉民情的優勢,主動為黨委政府排憂解難。如寧津縣在農村信用社銀行化改革過程中,法庭開通“綠色通道”,一年審結3200余件金融借貸案件,為優化全縣金融環境、建設“誠信寧津”作出突出貢獻。
(二)強化專業理念,打造基層“法官工作室”品牌。一是科學配備法庭隊伍。法庭按照“1+1+N”模式組建1—3個新型團隊,按照“資深法官+年輕助理+書記員”模式配備力量,原則上法官應為具有5年以上審判經驗、業務能力強、審判經驗豐富的員額法官,實現優勢互補、業務傳幫帶,保持隊伍穩定。二是提高法庭審判規范化水平。選取典型案件,先后組織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示范觀摩庭,開展裁判文書評查活動,印發《人民法庭庭審操作規程》。三是精心打造“法官工作室”。全市建立31個法官工作室,其中22個在基層法庭,培樹基層品牌法官。如我市陵城區糜鎮法庭的“郭正芝法官工作室”、鄭家寨法庭的“張浩法官工作室”,年均結案超過300件,調撤率均在65%以上,成為遠近聞名的優秀女法官。再如我市禹城市中法庭的“韓杰法官工作室”,本人為回族,發揮熟悉民族風俗的優勢,化解大量民族內部糾紛,為維護民族地區穩定作出突出貢獻,他本人剛剛被表彰為“全省優秀法官”。
(三)強化協作理念,打造多元化解矛盾糾紛品牌。一是搭建訴調對接平臺。認真落實《山東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各法院全部建成“四室一中心”(訴調對接中心和指導分流室、人民調解室、法官工作室、司法確認室),在各基層法庭設立訴調對接工作站,引入169名調解員進駐,分流化解大量案件。二是加強專業訴調聯動。德城區、開發區、陵城區、樂陵等8個法院均建立了交通事故聯調機制,法庭法官到交警部門常駐辦公;2個法庭在醫院設立“法官工作室”,現場調處醫療糾紛。三是構建家事調處網絡。武城法院被確定為全省家事審判改革試點,納入全縣社會治理重點項目,在3個法庭建立家事審判專業團隊,組建基層家事調解、家事調查、心理疏導等輔助團隊,開設基層家事矛盾化解“三大課堂”,使化解家事矛盾、維護家庭和諧成為一項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事業,得到最高法院、省法院和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工程。
(四)強化為民理念,打造司法服務品牌。一是升級服務平臺。新建法庭嚴格按照最高法院標準設計施工,全部在一樓建成“一站式”服務大廳,開通網上立案、預約開庭、視頻接訪、網上查詢等信息化平臺,從細節入手,提升大廳和窗口服務水平。二是創新服務方式。經常性組織典型案件巡回審判,深入開展“法庭五進”活動,探索利用微信和QQ視頻開庭,提升了司法的便捷性和親民性。三是改進司法宣傳。在5個法庭建成法治教育基地,利用便民站點開展法治宣傳,寧津柴胡店法庭朱孟友法官熟悉民情,熱心細致,開通24小時“小朱熱線”,成為當地有名的司法服務和法治宣傳品牌。
五、前瞻思考:實現人民法庭新突破的建設性意見
在法庭隊伍素質、基礎建設和保障水平都已經顯著提升的基礎上,實現人民法庭工作的新突破,要充分吸收最新理論研究成果,加強頂層設計,鼓勵基層創新,推廣先進經驗。要牢牢把握“便民”這一法庭設立初衷、工作優勢和核心理念,把現代信息技術融合法庭工作,開拓基層司法新境界。
(一)建立人民法庭“互聯網+訴調對接”機制。目前,法院法庭內外網已實現了“庭庭通”,廣大農村也實現了互聯網“村村通”,村委會或社委會一般作為集體設施開通了互聯網。在原有的基層法庭訴調對接工作基礎上,可以探索引進信息化辦公手段,法庭與轄區派出所、司法所、社區、村委會建好互聯網訴調對接平臺,利用網絡開展工作,互通互聯,資源共享,即時互動,支持好、指導好農村基層群眾調解組織做好矛盾糾紛化解工作,發揮好群調組織的對于訴訟案件協助調解作用,減少和避免矛盾激化,將大量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二)建立人民法庭“互聯網+便民訴訟”機制。多年前,各地法院積極探索便民訴訟機制,一些地方建成“縣鄉村三級便民訴訟網絡”。近幾年,隨著法庭審判任務的日趨加重和農村道路交通、通訊條件的改善,以及上級法院越來越規范和嚴格的庭審模式要求,原有的“便民訴訟網絡”的功能趨于弱化。新形勢下,法庭便民訴訟工作可充分利用好這一網絡平臺,在基層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下,把工作觸角延伸到每個村莊和社區。讓“便民訴訟網絡”這一傳統經驗真正上網,通過辦公辦案設施升級、網絡建設和技術支持,網格化、立體化辦案,實現網上立案、網上送達、節點信息推送和個案流程查詢工作,方便群眾訴訟,緩解法庭辦案壓力。
(三)建立人民法庭“互聯網+法治宣傳”機制。轉變傳統法治宣傳思路,充分利用好網絡宣傳平臺,并做好審理案件與法治宣傳的結合,在法院門戶網站為每處法庭開通工作窗口,掛接典型案例、判決文書、法庭動態、普法資訊等,開通法律知識和訴訟常識咨詢平臺。在黨委政府支持下,把村委會、社委會與法庭互聯網接通,納入社會矛盾化解和農村法治建設綜合考核,整合“互聯網+便民訴訟+訴調對接+法治宣傳+遠程辦案”等多種功能,實現一網多用、一網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