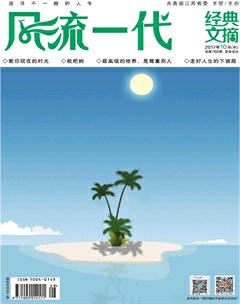切·格瓦拉肖像:信手抓拍的經典
史春樹
與許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一樣,古巴裔美國記者奧蘭多·拉佐兒時最常見到的“大人物”便是切·格瓦拉。時值上世紀70年代中期,每當家中停電,拉佐的老祖母都會點起蠟燭;搖曳的燭光中,一張特大號海報中的格瓦拉目光炯炯、意氣風發。彼時,距這位古巴革命領袖在南美叢林中喪生已有10年之久。
“祖母不喜歡無止境的革命,但她欽佩格瓦拉的精神。”回望歷史,拉佐相信,是古巴甚至各國民眾對格瓦拉長盛不衰的敬仰,讓后者的肖像被一遍遍復制、傳播,逐漸成為一種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文化現象。如美國作家帕特里克·希姆斯所言:“時光流逝,格瓦拉越發‘時尚,只因他‘代言的事物越來越多。”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紅遍全球的格瓦拉肖像出自信手抓拍。攝影師的名字阿爾貝托·迪亞茲·古鐵雷斯,更是少有人知曉。
最上鏡的古巴革命領袖
美國《史密森尼雜志》寫道,無論出身和信仰,所有人心中都有英雄崇拜的情結。從各方面看,格瓦拉短暫而富于戲劇色彩的人生,都讓他很適合扮演這樣的角色。格瓦拉原本不是古巴人,而是憑借對革命的貢獻才獲得古巴國籍;他并非經濟學家,卻做過古巴國家銀行行長,用假名批準貨幣發行。同樣,真實的格瓦拉并不英俊,長期被哮喘困擾。然而,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特質,都無法阻止他成為古巴革命領袖中最上鏡的那一位。
事實上,格瓦拉從未刻意要求國家為自己制作肖像,但1960年3月4日的一起意外改變了一切。當天,滿載軍火、停泊于哈瓦那港的貨輪“考布雷”號突然發生爆炸,造成百余名碼頭工人喪生,數以百計的普通市民卷入事故,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當時供職于古巴《革命報》(現已停刊)的阿爾貝托·迪亞茲·古鐵雷斯旋即接到任務:前往公墓報道追悼儀式。次日一早趕到現場時,古鐵雷斯注意到,著名哲學家讓·保羅·薩特及其伴侶波伏娃均獲邀到場,同樣神情肅穆的格瓦拉就站在他倆身旁。
當時,古鐵雷斯以“科達”的化名從事創作,屬于半公開的秘密。這個化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巴革命之前。古鐵雷斯與友人合作,用兩位匈牙利導演的名字建立了“科達”工作室,主要利用古巴的自然風光為時裝打廣告,或是幫娛樂明星制造話題。
1959年以后,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政權開展國有化運動,古鐵雷斯隨之告別了時尚圈,轉型為專職攝影記者。因為抓拍技術高明,他很受古巴政府高層賞識。
一切都發生在半分鐘內
1960年3月5日上午的追悼儀式上,卡斯特羅慷慨陳詞,借“考布雷”號貨輪事故譴責美國對古巴的威脅。古鐵雷斯對講話內容沒有印象,他只想著尋找更好的機位。
多年后,他以“科達”的筆名描述了拍攝格瓦拉的瞬間:“講臺下方,我一直盯著萊卡相機的取景器,焦點集中在卡斯特羅和他周圍的人。忽然,透過90毫米鏡頭,‘切出現在正上方。他的神情令我渾身一震。出于本能反應,我連續兩次按下快門,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拍了。由于格瓦拉迅速退回人群中,我無暇拍攝第三張照片,一切都發生在半分鐘內。”
回到家,古鐵雷斯在檢查底片時注意到,另一個人出現在格瓦拉右肩附近,他的左上方還有一些棕櫚枝,遂將照片四周的部分做了裁減。然而,《革命報》的編輯對這張構圖簡單的人像特寫缺乏興趣,只挑選了卡斯特羅和薩特夫婦的照片,刊發在當天的報紙上。
在當時的古巴,除非獲得官方許可,攝影師不得擅自傳播涉及國家領導人的照片。古鐵雷斯只能將無人問津的格瓦拉肖像掛在自己的公寓里。在他看來,照片中的“切”好像一名游擊戰士,“目睹死亡后,雙眼發出憤怒的光芒,表情中蘊含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
此后,古鐵雷斯為格瓦拉拍攝了數以百計的照片。在他看來,對方為人低調,原因在于他并不迷戀理政和外交,而是更關心“輸出革命”,以至于每次出席公眾活動時,都更愿意把自己藏在卡斯特羅等人身后。“他是實干家,只有工作能讓他滿足。”古鐵雷斯說。
經左翼商人之手聲名遠播
同為1928年生人,古鐵雷斯和格瓦拉似乎注定將走向不同的道路——前者繼續致力于新聞攝影,后者則將視線投向了廣袤的拉丁美洲。1965年,格瓦拉突然在古巴民眾的視野中消失,半年后,官方才公開了他的告別信。信中,格瓦拉聲明放棄所有的民間和官方頭銜,因為“世界其他地方需要我哪怕微不足道的支援”。
兩年后,孤立無援的格瓦拉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殺害。
就在格瓦拉去世前幾個月,意大利商人費爾特里內利敲響了“科達”工作室的門。此君受同情古巴政府的歐洲文化機構“美洲之家”負責人海蒂·桑塔瑪利亞之托,請求古鐵雷斯挑一張“切”的照片給他。
古鐵雷斯指了指墻上。“這就是我最好的格瓦拉照片。”
費爾特里內利對這張肖像照很滿意,當即翻印了兩張。當客人問及價錢時,攝影師擺手拒絕,因為“費爾特里內利是他敬重的人派來的”;另一方面,遭到封鎖的古巴實施貿易管制政策,私下與外國人交易,可能給古鐵雷斯帶來麻煩。
作為意大利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繼承人,費爾特里內利關心左翼運動,并設法使其服務于自身的商業運作。獲悉格瓦拉遇害的消息,他立刻意識到這兩張照片的價值,用它們翻印了紀念海報,但沒有提及原作者的姓名。此后不久,菲德爾·卡斯特羅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文稿交予他出版,費爾特里內利將那張未署名的照片印在新書的封面上。
這位商人的故事同樣以悲劇結束。1972年,他被發現死在米蘭附近。警方稱,他是在試圖破壞高壓輸電線時意外身亡的。然而,一些陰謀論者堅信,費爾特里內利之死難以擺脫“謀殺”的嫌疑,理由之一是,上世紀50年代,他曾幫助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將后者的成名作《日瓦戈醫生》偷運出蘇聯并在歐美出版,因此激怒了莫斯科。
創作者始終遠離商業營銷
如《史密森尼雜志》所言,誕生半個多世紀以來,切·格瓦拉的面部特寫成了有史以來被復制次數最多的照片之一,堪與名畫《蒙娜麗莎》媲美。早在視頻網站和社交媒體出現前,他便名揚四方,從玻利維亞到剛果,從越南到南非,從蘇聯到美國……成為各國社會活動家和叛逆年輕人的偶像。而在商業世界里,無論是音樂專輯的封面,還是太陽鏡、雪茄煙盒,乃至哈瓦那街頭小販兜售的手工紀念品,他堅毅的神情似乎能為任何載體增色。
阿爾貝托·迪亞茲·古鐵雷斯卻未能從中獲得太多利益。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在古巴長期處于法律空白,這位攝影師只能憑借個人力量與泛濫的侵權行為斗爭。上世紀90年代,他曾將一家英國酒業公司訴至倫敦高等法院,希望阻止被告在伏特加酒瓶上使用格瓦拉肖像,并在接受采訪時強調,格瓦拉生前很少和酒精打交道。雙方和解后,古鐵雷斯獲得了大約5萬美元的賠償。他將這筆錢捐贈給古巴,用來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兒童用藥。
古巴政府是另一個有權合法使用格瓦拉肖像的主體。如今,格瓦拉的形象被印刷在該國面值3比索的紙幣上。古巴內政部大樓外墻上有一幅巨型涂鴉,經常被游客嵌入自拍照。2016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哈瓦那期間,兩國領導人曾以格瓦拉肖像為背景合影。
在看著格瓦拉肖像長大的奧蘭多·拉佐眼中,“切”的魅力是永恒的。但另一方面,隨著這張肖像成為商業化的符號,真正愿意去了解格瓦拉生平和思想的人越來越少。endprint